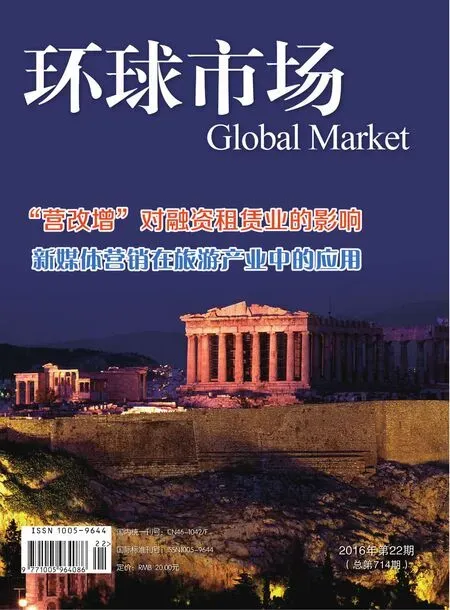对雪国中源自于《源氏物语》的虚无基调分析
袁 芳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对雪国中源自于《源氏物语》的虚无基调分析
袁 芳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川端康成是一位具有虚无思想的作家,以情爱为叙事主线的《雪国》,其作品中无处不在透露出一种虚无之感。中年以后的川端在思想情感上日渐消沉,更多了虚无的色彩,为了创作《雪国》中为世间所不存在的美感时,川端把《源氏物语》当做创作的源泉,努力在作品中挖掘日本传统的物哀,《雪国》的物哀与《源氏物语》的物哀是一脉相承的。《雪国》中表现的人生悲苦、虚无感受和日本传统中物哀思想联系密切。
雪国;虚无;源氏物语;物哀
前言
《雪国》当中处处流淌的虚无的基调和物哀的思想无不深受《源氏物语》的影响。他在谈论日本文学的渊源和发展时说道:“在《源氏物语》之后延续的几百年,日本的小说都是憧憬和悉心模仿这部名著的,不断从它那里吸取美的精神食粮。” 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特殊的审美理念,它的内涵比“感动”更丰富,有感动、感慨、可怜之意,以可怜对象的爱情为主情,它是日本民族思想感情的主线。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表现的人生悲苦、虚无感受都和物哀联系密切。而紫式部就是对物哀文学理念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她认为物哀要逐渐深入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真实出发,哀叹男女之间的爱情;第二阶段超越男女之情,开始感动于自然风物的美与咏叹季节变化所带来的无常感;第三阶段范围扩大到对世间万相的感叹,包含同情、可怜、悲伤的广泛含义,弥漫着一种均匀的、淡淡的哀愁,贯穿着缠绵悱恻的抒情基调,体现了人生的悲剧性,它所奠定的独特的感受性、抒情性、悲剧性的美学风格,而凡此种种《雪国》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充满虚无、纯洁、悲哀感情基调的《雪国》洋溢着作者对美学的另类追求,是展现日本民族精神特性的经典之作,也正是这种虚无思想使得该部小说充满了魅力与灵魂。
一、虚无的爱情
《雪国》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描述空虚的舞蹈研究家与艺妓驹子和少女叶子之间的情感纠葛,人物之间错交的情感都被川端用细腻的笔触痛苦地表现了出来。从男女间恋情出发来表现物哀的思想,这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源氏物语》以爱情为舞台,集中表现了对女性恋爱的不幸和男女不伦之恋的同情哀感,女性爱情中付出得越多,就越期望得到爱的回应,心灵就越发痛苦,就犹如坠入了爱情的沼泽,越是挣扎,陷入地就越深,源氏在男女情爱的沼泽之中感受到了深深地无常感,出家的念头也在逐渐加深。《雪国》之中错综的男女情感就如同沼泽,就如同作品中三位主要人物的虚无无果的爱情一样,纠缠其中痛苦却无力自拔,出身富贵无需为生计发愁的岛村整日感受到的就是空虚,为了排遣寂寞不惜千里迢迢到雪国去追求瞬间欢畅的感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虚无的爱情观和游戏人生的态度,是无法理解驹子对爱情和对生活的憧憬,更无法理解叶子为了爱情而奉献的精神,他迷恋驹子的专情,却无法实际回应她的爱情,同时又倾慕叶子却难以触及,在川端笔下一切是那么虚无而无意义。驹子为了自己患重病的未婚夫行男,被迫靠卖笑为生,但是她有着纯洁一尘不染的精神世界,向往并期盼两情相悦的纯洁爱情,她倾心于薄情冷漠的岛村,不计回报地投入自己的情感,却不可避免的得到难以遏制的悲哀与失落。叶子爱着没有希望的行男,她的美仿佛不是来自现实世界,而是来自遥远的虚幻世界,她的爱情也是一场虚无,而伴随她的生命终结于一场火灾中,也使得岛村对叶子的爱情的渴望与向往也随之变成了虚无的梦幻。
二、对自然风物的咏叹与感动
日本的文学观不是直观而是靠情绪、靠想象力去感受自然,欣赏自然的同时潜藏着诗意的哀愁情绪,包含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在对自然的描写中流露出淡淡的哀愁。《雪国》中那种变我为物,变物为我。物我一体的境界就是《源氏物语》景色描写里所达到的美学境界,就是从《源氏物语》中汲取营养,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悲境,日本人的自然美意识集中在月、雪、花之中,“雪月花时最怀友”,“雪月花”最能表达四季时令变化的美,日本文学以它们作为其自然美乃至整个美意识的核心。《源氏物语》中有大量的月景描写,如源氏被贬到须磨描写也很精彩,身处异地的他,“夜色越来越深,海风送凉,残月西沉,天空明净如水,人间肃静无声。”表现被贬他乡孤苦无助的心境。也善于用雪景来烘托人物或喜悦或悲伤之情,不同的花草象征不同女子的性格特点,比如紫姬是一个喜欢热闹、繁华的女子,身边的花草也多是“红梅”“樱花”等春花,川端康成在作品中描写了白雪、白花和月色,《雪国》中的景物都是通过岛村的眼睛反映出来的,并将自然之景与个人之情完美地交织融合在一起,故事的开篇“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就给读者们呈现出了一个超脱于世外的仿佛虚幻而又灵动的世界,还原了自然景物的古朴与淡然景象,给人一种脱俗飘逸的美感,关于花的描写,“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山上的白花。从陡峭的山腰到山顶一带,遍地盛开着这种花,白花花地一片银色,好像倾泻在山上的秋阳一般”,月色在《雪国》中也别有风韵,“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明亮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这些自然景物的描写当中都在流露着淡淡的哀愁,浸透着岛村的主观情绪,包含一种空虚的美感。
三、生死世相的虚无
川端虚构超脱于世外的雪国世界,事实上是因为对现实世界有一种无力感,只能把现实抽象化,把对世相的感动贯穿于人情世相中,他时刻在暗示着生活在其中的人活着是徒劳,所作的任何努力都改变不了命运的安排,行男的生命就是一场徒劳,无论是叶子的精心照顾,还是驹子的卖身都挽救不了他的生命,他也相信世间万物本是虚无,无论怎么变化不止,物质都不会消亡,生死不灭,叶子在大火中丧生,她的身体笔直地从二楼摔下来,死了,成为川端笔下一个唯美的背景,在她离去的瞬间,生与死放佛融合在了一起,并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了重生,她的爱情虽然因为行男之死未曾结果,但纯洁的爱情一直在净化、升华,她的爱情留在了读者心中,这些将川端康成对死亡虚无思想的认知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他对死亡的独特视角,也是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化中的“物哀”思想的结果,在《源氏物语》中人物死亡时哀感可以说是物哀美的极致体现,作品中许多人的死亡都笼罩着一种幽情与哀美,隐含着淡淡的哀伤与惆怅,比如光源氏最钟爱的妻子紫姬病重即将离世之前,赋诗道“青青获上露,不能长久驻。偶遇风消散,人生本无常。”紫夫人竟将自己比作随风倾侧的花枝与稍留即逝的花上露,紫氏隐去了死亡的恐怖,只给读者留下了美的哀伤。爱恋三公主的柏木备受心灵的煎熬,疾病缠身,虚弱不堪之时自语道“悲乎!我生虚度,无所念怀,惟这“两烟”之语最宝贵!”如此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在无可奈何的现实面前只能夭折,然而这份不被世人容许的爱情在死亡面前迸发出感人至深的哀美,无论紫式部还是川端康成都在描写死亡意象时,将其描绘成了美的艺术。
四、共同的佛学思想基础
佛教的无常观深刻揭示了人生普遍面临的基本矛盾,紫式部本人就精通佛典,她的思想明显就带有佛教认为人生虚无的观念,《源氏物语》中众多人物在爱情生活或政治生活遭到挫折时,往往深感人世无常,于是企图通过出家、苦修、灭寂欲望,以求消灭烦恼,企求来世之福。源氏的无常感总是在他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涌现,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强烈,但是源氏经常举棋不定,留恋现世生活,而这也恰恰反映了紫式部从日本神道及日本化了得佛教现世主义的角度,把现世生活放在首位,诞生于平安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的《源氏物语》深受佛教思想文化的影响,佛教宣扬的无常、出家、因果报应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佛教的观念与思维方式更深刻影响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佛教禅宗在12-13世纪传入日本后,受到武家政权幕府的支持和保护,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渗透进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审美情趣、文艺创作思想,佛教对川端康成的影响很大,它把“佛典”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他的作品中始终都在贯彻佛学当中“生追求美,美即是虚无,虚无即死,死就是美”的审美理念。
五、总结
川端通过自身对人生悲哀和寂寞的感受来构思了这部作品,描写了雪国里的凄美的爱情和无常的人生,流淌在其中的虚无的环境,虚无的感情,无不透露出一种虚无之美。正是这种虚无思想使得该部小说充满了魅力与灵魂,总之,川端康成是以禅的“虚无”通过塑造《雪国》这一虚幻的世界表达出其独特的虚无思想。
[1]石田一良.日本思想史概论[M].吉川弘文馆,1986.
[2]高勤慧.雪国.古都.千纸鹤[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
[3]叶渭渠.川端康成谈创作[M].北京:三联书店,1992.
[4]李贻桂,汪盛春.《雪国》人物命运与川端康成的悲观虚无思想[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袁芳(1987.12--)女,文学硕士,辽宁对外经贸学院日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