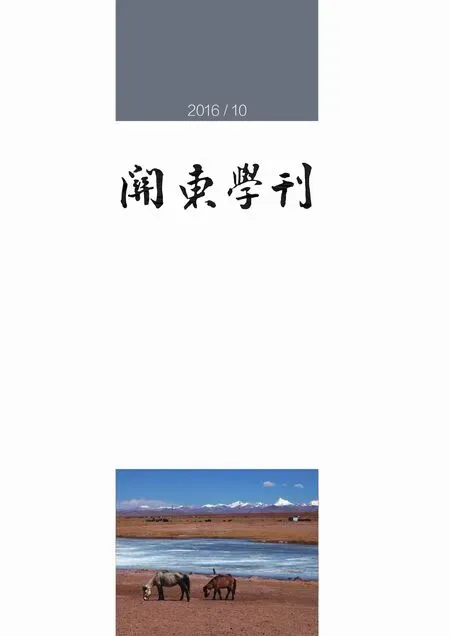席勒游戏理论的政治表达与权力追求
张秀宁
席勒游戏理论的政治表达与权力追求
张秀宁
游戏理论是席勒的一个重要贡献,他进一步探讨了游戏与自由之间的可能,同时也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划定了审美的边界,由此创造性地将游戏和审美联结起来。又通过审美与自由之间的关联,建立了游戏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从而使游戏成为通往其理想政治乃至理想社会的门户和通途。席勒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政治表达和权力追求的形式,为艺术的权力表达功能建立了合法性,虽然在席勒本人的理论表述之中,游戏理论仅仅是一种话语操作,但却为日后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石。
游戏理论;审美;诗性政治;席勒
在席勒之前,康德曾经对游戏有所发掘,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游戏视为“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开启了将艺术视为游戏的大门,进而打通了游戏与自由之间的通途。席勒对游戏冲动的描述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一切价值归根到底从属于伦理的品格,而在席勒那里出现了美的内在价值,虽然他还没有抛弃康德的道德化观点。”*[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26页。
一、席勒视野中的游戏及其特征
席勒所言之“游戏冲动”建立在历史悠久的二元思维的基础之上——“感性冲动要求变化,要求时间有一个内容;形式冲动要废弃时间,不要求变化。因此,这两个冲动在其中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那个冲动,即游戏冲动……所指向的目标就是,在时间中扬弃时间,使演变与绝对存在、变与不变合而为一。”*[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也就是说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结合,形成了游戏冲动。追求调和、均衡、和谐几乎是席勒的标志性态度,所以,对于这个由感性——理性、物质——精神、肉——灵的彼此妥协所形成的概念,最关键的问题是被想象为对立的双方是如何糅合在一起的。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席勒认为“两个冲动都必须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法则,一个通过精神法则。当两个冲动在游戏冲动中结合在一起活动时,游戏冲动就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14页。也就是说席勒首先开掘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在于两者都是基于“人”而生发的,或者说,所谓游戏理论的二元基础并非席勒关心的要点,“人”才是他极力思索、真正关心的要点。“席勒正是由此出发,并直接看到古希腊人由于更尊重艺术的游戏目的本身,并保持着游戏生活的自由特质。因此希腊文化意义上的人才可以称为完善而自由的人,而现代意义上的人由于受制于工业化生产,人性发生分裂,生存的目的和生存的重压剥夺了审美艺术活动的正常地位,艺术自身也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变成了单面人。”*李咏吟:《解释与真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席勒认为,无论感性冲动还是形式冲动,对于人而言,其共同特征在于其强制性。这也就是说无论外在于人的是理性还是感性、精神还是物质,都按照其固有的法则对人提出要求,因此,如果仅以这两者为人立法,那么人就只能在两者之间徘徊折冲,要么陷于物欲不可自拔,要么以戕灭自身的方式去追索精神世界,显然,这与席勒想象和认同的人的自由、解放极为相悖。故而,席勒将游戏和游戏冲动设计为解决两者对立的更高级的实践与概念。
“游戏”这一概念被席勒表述为“一切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非偶然的、但又既不从内在方面也不从外在方面进行强制的东西。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脱开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它对于物质冲动和形式冲动的要求都是严肃的,因为在认识时前者与事实的现实性有关,后者与事实的必然性有关,在行动时前者以维持生命为目标,后者以保持尊严为目标,二者都以真实与完善为目标。”*[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1页。也即是具有必然性和非强制性的东西,都是游戏,而游戏也必定要具有必然性和非强制性。席勒敏锐地发现了人类游戏活动对其他行为的悖反,无论其外在形式还是内在追求,似乎都与其他行为有着不小的距离。游戏毫无疑问与现实生活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游戏中所应用的所有资源、所有技艺无不来自于现实,但在现实与游戏之间却横亘着模仿、隐喻、象征……,游戏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视为现实的镜像,但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游戏的所有内涵。游戏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由于其先天的非现实性和先天的隐喻性,游戏内在地具有超越现实的动力,游戏总是疏离于现实以保障其存在的独特性,而这种疏离又促成了游戏远离现实的推动性力量。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游戏总是与现实不同的,这种“不同”内在地决定了游戏拥有疏离现实的力量,可以保持紧张的关系。这也就是席勒所说的“主观和客观上都非偶然的”,即游戏的必然性。
此外,游戏的动力是内在的、先天的同时也是唯一的,这就意味着以强制力量进行的游戏必然远离游戏的先天属性,意味着对游戏的反动和背叛,更直接地说,强制进行的游戏不是游戏,无论这种强制力量是来自于外在的压迫还是内在的本能。外在的压迫意味着主体性参与的缺失,意味着主体迫于某种强制性力量不得不进入“游戏”之中。在此,外在的强制性力量——例如暴力虽然可以迫使主体进入游戏的操作层,但却无法决定游戏主体的主动性参与,于是,在这种游戏行为中主体实际上处于取消或压抑的地位,而无主体的游戏显然是无法成立的,正如不能将一具肝脏称之为人一样。内在的强制力量则往往意味着对人类动物属性的利用,意味着人在生理和精神上遭到外在力量的控制,实际上仍然是主体非自主地进入“游戏”。正如阿片类物质对人脑的影响——“大脑垂体分泌内啡肽,而内啡肽能够使人兴奋。人脑有自我调节能力,内啡肽的分泌量是受大脑控制的,能够限制人的兴奋在正常范围内。经常吸毒抑制了自我分泌内啡肽的能力,而变成依靠外来的毒品,打乱了人体机能的自我平衡”,*冯雪:《多巴胺受体与毒品依赖》,《中国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4年第6期。从而最终导致人的行为遭到了毒品与药物的控制。遭到生理控制的人自然也可以看似主动地参与游戏,但无疑其自由意志已经遭到了损害甚至取消,其“游戏”也不能称之为游戏。同样地,精神依赖也会消磨主体的自由意志,而且所有的精神依赖都最终连接着人脑垂体。内啡肽的发现是在20世纪70年代,席勒在300年前对此作出的预见和努力不能不令人由衷赞叹。“当心情与观念相结合时,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小了;当心情与感觉相遇合时,一切必然的东西就放弃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得轻松了。”*[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1-122页。所以,主体性参与、主体性建构成为游戏的重要特征,这也是席勒所称的“非强制性”的内涵所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席勒在思考和定义“游戏”概念的时候,极为重视人的主体性参与,这种主体性参与的另外一个名称其实就是自由。同时,席勒也极力反对任何外在力量对主体自由意志的干涉,无论这种外在力量来自于暴力还是精神、其机制是强迫还是诱惑。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席勒使游戏理论为人的自由、解放奠基成为可能,使游戏理论和权利争取、权力斗争联结了起来。正如他所说:“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2页。,“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4页。他的游戏理论实际上也是他的自由宣言。
二、游戏与艺术的关系
随着席勒的步步推演,艺术与游戏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与审美之间存在着深刻联系的重要存在,艺术与游戏之间的重合与差异对席勒的审美教育理念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审美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席勒宣称“在力的可怕王国与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5页。“艺术被看作是某种终极,其教化作用颇受重视,用以刺激人的审美能力。”*Herta Pauly,“Aesthetics Decadence Today Viewed in Terms of Schiller’s Three Impulse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of and Art Criticism,1973,No.3.也即是说,席勒认为经过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凭籍模仿、隐喻和象征,艺术得以建构起一套平行而又独立于感性法则和理性法则的全新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消除现实的粗野与腐朽、规避感性欲望与理性戒律从而解放人类的可能。而席勒又曾经断言“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3页。他所宣称的审美的第三王国,也就是一个游戏的王国,同样是经由艺术创造而来,于是,艺术创造与游戏体验就建立了联系,但同时,艺术与游戏之间的种种差异也隐藏于其中造成了审美教育论的内在问题,席勒本人对此并未给予明确的阐释,因此对其进行明晰的辩正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艺术与游戏之间,既有大量的重合之处,同样也有不少的不够周延之处,重合与周延塑造了艺术王国与游戏王国之间的迷津。两者在愉悦性、想象性、隐喻性方面的共通与批判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方面的差异是这一迷津的主要面貌。
艺术与游戏同样能够带来愉悦性,而且这种愉悦性往往能够摆脱外在的理性和感性限制,进入所谓“第三王国”。艺术与游戏的同构性和同质性与这种愉悦感受密不可分,席勒以朱诺雕像为譬喻,称“这个完整的形体就静息和居住在它自身之中,是一个完全不可分割的创造,仿佛是在空间的彼岸。既不退让也不反抗;这里没有与众力相争的力,没有时间能够侵入的空隙。我们一方面不由自主地被女性的优美所感动、所吸引,另一方面又由于神的尊严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处在同时是最平静和最激动的状态,这样就产生了那种奇异的感触,对于这种感触知性没有概念,语言没有名称。”*[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5页。其感受恰如凌空虚度,正如《老子》所云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不言。此外,这种愉悦必须在一种对立的背景之下才能够存在。英国著名批评家罗杰·弗莱在讨论这种感受的时候强调:“当艺术家静观某个特殊视阈时,诸形状与色彩(审美上)混乱而偶然的组合便开始凝结成一种和谐;当这一和谐渐渐在艺术家面前明晰起来时,他内心确立的强烈节奏便会歪曲其实际视觉。这时对他来说线条诸方面的种种关系变得充满了意义,他不再是漫不经心或纯属好奇地理解它们,而是充满激情地理解它们……描绘对象本身似乎消失了,失去了它们各自的和谐统一,在整个视觉的镶嵌组合中像无数色点一样各得其所。”*[法]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5-406页。也就是说,主体与对象、活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彻底的重新构造,愉悦体验占据了这个新铸世界的全部,这是游戏体验与艺术体验的共同之处。
想象在游戏与艺术之中都承担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还是游戏参与者与游戏活动之间,想象的存在都是不可更易和质疑的。想象意味着在具有任意性的多元个体中建构联系的努力,意味着个体超越实存凭借想象重塑世界的可能。在这里,想象既是自由本体,也是自由的手段,达到了自由这一目的,前所未有的和谐统一出现在想象之中。游戏与艺术的共通之处在于,无论审美行为还是游戏行为,其内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也就是说参与者凭借想象建立起一种虚拟性的联系,模仿但又超越现实逻辑。在这一想象过程之中,声音、线条、色彩、符号……统统遭到重组,如果没有想象,这些基本要素就无力构建艺术与游戏的王国。想象是弥合游戏破绽与艺术的黏合剂,正如儿童将沙粒作为“米饭”喂给洋娃娃,达利将绘画中的一切刚性物体都塑造为柔性的,其可能性与合法性只能依赖于想象。想象巧妙地将自身与现实分割开来,仿佛它具有先天的合法性,而现实又很难在机制上对想象施加影响力,于是想象成为一块“飞地”,为游戏和艺术提供了种种可能。鲍姆加登声称:“对于想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人来说,较为重要的、而且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低级认识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能力不仅可以同以自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能力共处,而其后者还是前者的必要前提。”*[德]鲍姆加登:《美学》,简明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26页。在这里,所谓的“低级认识能力”就是想象。席勒称,“人的想象力也有自己的自由运动和物质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它与形象不发生关系,只是为有自主性和不受束缚而快乐。……等到想象力试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0-231页。
隐喻几乎是构筑物理世界与符号世界、思维世界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整个世界存在的普遍方式,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世界本身。隐喻联结同时也渗入了人、意识形态和物质存在,它是如此之庞大,人对于隐喻的依赖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人一旦离开了隐喻就失去了言说和实践的可能。在艺术与游戏中更是如此,隐喻几乎构成了两者内部所有的关系。隐喻也打开了由艺术通往政治的大门,政治话语、政治事件、政治理想以隐喻的形式在艺术中得以呈现。总而言之,隐喻无所不在,无论是在游戏中还是在艺术中,隐喻几乎都无法忽视。对游戏而言,游戏往往和现实呈现摹仿甚至镜像关系,这种直接对应式的关联往往建立在较为简单初级的游戏之上,譬如儿童模仿成年人行为所进行的游戏就是典型例证。而隐喻则更多出现于更为大型、复杂的游戏场景之中,譬如大规模的体育活动。越是复杂的游戏活动,其隐喻性越强。正如奥运会中奏起的国歌、冠军们胜利后身披国旗、拉拉队员旗帜鲜明的助威……作为喻体遥指着民族和国家,人们在体育游戏中不断复习政治激情,从而建立起对国家的普遍性认同。而在艺术之中,隐喻的呈现更加多样、普遍和深刻。普罗大众通过文学和影视形象来学习恋爱法则、交谈技巧、生活方式甚至幸福人生;画家们通过政治波普来表现批判性立场;作家们在虚构性作品中夹藏政治诉求……,在艺术领域中,本体和喻体彼此交融汇集而不是泾渭分明,隐喻对上述内容的包容则为审美迈向政治的暗度陈仓提供了准备,正是隐喻的存在才保证了艺术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而这也恰恰是艺术与游戏难以重合之处。可以说,隐喻打开了一扇政治的窗子,通过这扇窗,才使得审美超越于游戏。正如席勒将“游戏——艺术”这一过程描述为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过程,一个从“物质游戏”到“审美游戏”的过程,并坚持认为人的游戏冲动只有进入一种超越物质自然的自由形式的创造冲动时,才能称为真正的审美游戏。正如赫依津哈所说:“作为通例,游戏成分逐渐退至幕后,大部分被宗教范畴吸收,剩余的则结晶为知识、民间故事、诗歌、哲学或各种司法形式及社会生活。这样,原始的游戏成分就完全隐藏到文化现象的背后。”*[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政治性是艺术作品重要特征之一,正如先哲们把人界定成为“政治的动物”一样,政治在人类的一切行为中皆有所表现,艺术自不例外。就像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隐喻一样,也同样存在着无所不在的政治。而且借助于隐喻、象征等手段,在艺术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政治景观更为复杂多样,但其核心依然是权力问题。只是在艺术场域中存在着复杂的资本置换,而非如现实的政治斗争一样唇枪舌剑或者血流成河。一方面,在艺术场域内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以图谋艺术领导权;另一方面,艺术品往往与实际政治斗争呈现出映射关系,经过变形的权力问题以隐喻的方式普遍存在。但是,在游戏中政治问题则是另外一重面貌。应该说,游戏无论就其本体还是其历史来说,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要逊色于艺术,虽然席勒在其《审美教育书简》之中将游戏与艺术置于同样的高度,但不可忽视的是,席勒将游戏认定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的产物,但艺术却并非如此,它是一种具有恒定性的存在。这样,政治在游戏中的分布就呈现出一种正态关系,随着游戏从物质层次过渡到审美层次,其政治存在也愈加丰富和多样。
批判性几乎是政治性必然的产物,人类对恒定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的追求,导致了艺术成为一种观念表达和价值判断的路径,批判性暗示着衡量正义、良善追求的伦理指向与激烈程度,于是,艺术在与态度、立场捆绑在一起的同时,也同公平、正义、平等捆绑在一起。正如艺术内在地有美的追求一样,它同样也有善的追求,前者极力使其形式化,后者极力使其工具化。这两种取向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艺术的组成部分,而批判性也如影随形,不可抗拒地附着于艺术之上。艺术本身的开放性导致其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存在着激烈的博弈,这就为批判性的存在提供了可能。而在游戏中,批判性就比较罕见了。盖因游戏的伦理诉求相对较弱,尤其是在所谓“物质游戏”的阶段,想象以及模仿所起到的作用远大于隐喻,游戏内在的矛盾张力不足,难以拓展到伦理层面,这自然而然地就削弱了游戏的政治性和批判性。而在“审美游戏”阶段,游戏与艺术之间的重合度愈加提高,其批判性就更为强烈了。
而“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庞然大物,毫无疑问地覆盖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艺术和游戏自不待言。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都与利益相关,无论是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还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亦或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理论,都是围绕着“利益——思想”这一结构建立起来的。于是,游戏、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转换为它们与利益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利益问题上,游戏与艺术各有不同。对于游戏而言,由于想象压倒了隐喻,愉悦压倒了权力,游戏中的“利益”通常都是想象性的,与现实利益的关联不大,“它是一种与物质利益无关的活动,靠它不能获得利润”,*[荷]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第15页。尤其是“物质游戏”,在席勒看来往往是自然而然的精力发泄和从属于人的动物性生活。相对而言,艺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与利益存在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裂的联系,一方面,在于艺术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围绕着利益和权力建立起来的复杂体系,它就没有可能自外于其他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围绕着艺术世界内部的权力与利益结构建立起自身的意识形态,虽然有其自身结构上的特殊性(如布迪厄所言之“颠倒的经济世界”),但是在本质上并无特殊之处;另一方面,由于艺术与现实之间强大而紧密的隐喻关系,艺术深深地楔入了现实之中,而现实也深刻地影响了艺术,于是现实世界中的权力与利益问题也同样成为艺术中的问题,“尽管在文学(等)场内部进行的斗争在原则上是极其独立的,但在起源上,无论是幸福的起源还是不幸的起源上,总是依靠它们与外部斗争保持的联系和这类人或那类人能从中找到的支持。”*[法]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艺术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同构化的力量,这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阐释。
游戏在批判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方面的匮乏揭示了它与艺术的重大差异,而前面提到的席勒对“物质游戏”与“审美游戏”的划分表现出了他对整合两者所付出的努力——“自然从需求的强制或物质的严肃开始,再经过剩余的强制或物质游戏,然后再转入审美游戏。”*[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0页。他认为“只要这种幻想游戏一点也不受到形式的干预,它的全部魅力都是由无拘无束的形象交替组成,那么这种游戏虽是人所特有的,但它仍仅仅属于人的动物生活,它仅仅表明人已从一切外在的感性强制中解放出来,但还不能由它推断出在人身上已有一种独立的创造力。这种观念自由交替的游戏还是物质性的,用纯粹的自然法则就可以说明”*[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0-231页。在这里,必须首先对参与游戏和艺术的主体详加区别,个体性的游戏、审美与非个体性的游戏、审美存在着重大差异,构成群体是产生政治性、公共性的前提所在,只有在群体中才涉及到权力的独占、分享、认同、制衡、博弈;才涉及到权利的争取、保障、捍卫,因此,参与到游戏活动中的游戏者数量是非常关键的,它决定了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是否可能。
在唯一个体参与游戏活动和艺术审美的时候,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往往更容易是匮乏的,但同时也是更为自由的。在“单一游戏者—游戏”和“单一审美者—艺术品”之间,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社会性这一影响因素,使得游戏行为和审美行为所开辟出来的新世界仅仅由这两者构成,正如圣·埃克絮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和星球上的唯一一株玫瑰,在这样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暴力和非暴力的争斗被最大限度地摘除,权力问题遭到悬置和取消,批判的对象与批判本身就烟消云散,意识形态作为权力控制机制无需存在,更加复杂综合的政治更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而在多个个体参与游戏活动和艺术审美的时候,其焦点所在、运作机制、影响范围无不与前一种情况大相径庭,权力问题在游戏与审美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持续性地对整个游戏和审美的主体、对象、场域产生影响。也正是因为权力的介入,游戏与审美渐行渐远,艺术品作为人工的造物,不可避免地拥有更为广大的隐喻空间,这也导致了权力之流更大范围地渗入和淹没艺术品,使得几乎所有的艺术品都不无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意味,使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能得到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阐释。而在游戏领域内,由于其运作机制往往相对而言更多地仰赖于生理的、物质的条件,这样对于权力问题的容纳就会大打折扣,其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
三、游戏王国与政治王国
游戏与政治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相拟相斥的关系。一方面,游戏中普遍存在着对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角色、政治权力话语的摹拟;另一方面,游戏又普遍地被宣布超越于政治之上,拥有某种非功利、超现实的特质。席勒所努力追求的,恰恰是以一种“整一”“和谐”的终极性境界为指向,试图达到游戏王国与政治王国的完美对接与融合。对于游戏的初级阶段,席勒的态度是贬抑的,“因为感性冲动以其我行我素的习性和粗野的欲求不断地进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初级趣味抓住的首先是新奇、光怪陆离和稀奇古怪以及粗野激烈,惟独一遇到质朴与宁静就逃避了。这种趣味创造的形象荒诞不经,它喜欢急速的转变、浮华的形式、鲜明的对照、耀眼的光线、激昂的歌唱。”*[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2页。这种“物质游戏”无法构建起他想象中的游戏王国,而只有当另外一种美好的必然性把“盲目力的放纵”和“形式的胜利和法则的淳朴威严”*[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4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使另外一个王国,即审美游戏的王国得以诞生。
席勒想象的游戏王国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其法相庄严,席勒进一步将其与群体、公共、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惟独美的沟通能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感性的快乐,我们只能作为个体来享受……认识的快乐,我们只能作为族类来享受……惟有美,我们是同时作为个体与族类来享受的”,*[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7页。而相对于初级阶段的、物质的游戏则是不屑一顾,“赤裸裸的物质需要有损于自由精神的尊严,趣味给它罩上一层它自己的柔和的面纱,使我们在可爱的自由幻影中看不到它同物质的可耻的亲缘关系。”*[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9页。显然,在席勒的美学世界里,审美游戏所带来的政治格局是匀称、整一、和谐的,通过审美游戏,人才能够获得自由,建构良好的政治秩序、保障——“在审美王国中,一切东西,甚至供使用的工具,都是自由的公民,他同最高贵者具有平等的权利;知性本来总是强行使驯从的未成形的物体屈服于它的目的,但在这里也得征询未成形物体的意见。因此,在这里,即在审美的假象王国里,平等的理想得到实现,而这种理想,就是狂热者也很愿意看到它得到实现。”*[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39页。也就是说,席勒的政治关怀——自由、平等只有在这一审美王国中才能得到实现。
在此,席勒设想和描述了一个完美卓绝的状态,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十六到二十六封信中,席勒提出了一个阶段论式的发展图景:感性的人—审美的人—理性的人,在这一进程之中,审美的价值被置于极高的位置,而游戏既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其自身的发展亦与审美重合。“他将生命主体性与生命和谐性统一起来,将审美目的论与生命目的论统一起来。于是,审美游戏论被提升到生命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高度,并作为一种审美自由理论而被充分肯定。”*李咏吟:《解释与真理》,第342页。席勒对于审美游戏的推崇是高昂的,但审美游戏自身也分为两个阶段“最初以外界事物为乐,最后以自己为乐,而这又分为两步:开始是通过属于人的东西,最后是通过人本身。”*[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226页。宏观来看,在从物质游戏到审美游戏的发展变化之中,其政治诉求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的运动过程。游戏的政治作用就范围而言由外在的公共世界逐渐隐入个体的内心领域,就影响力而言逐渐由一种权力虚无转为一种权力主张,这一内在的运动轨迹颇值得玩味探索。
前文曾经说过,在所谓“物质游戏”阶段,在游戏内部,无论是其利益诉求、权利主张还是权力争夺,都是比较有限的。游戏自身由于其利益的虚幻性、权利的想象性和权力的非实存性,致使游戏很难在政治层面有较大的影响。这也是被席勒所认定的。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当把游戏纳入整个社会全局中进行思考的时候,不难看出,游戏本身具备相当的政治消解作用,这种先天的消解功能在某些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尤其显得力量强大,别开生面。
无论是席勒所处的300年前还是当今时代,专制权力的杀伤力都并未减小。虽然与席勒的时代相比,专制力量的施展空间已经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禁锢、伤害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更易而改变。相反,借助于技术的进步,专制力量对个体的行为、思想的控制反倒比若干年前更为强大。专制的力量会深深嵌入每个个体的生活,不仅控制人们的政治选择,也控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中,这种无所不在的专制权力和普遍遭到权力辖制的私人生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也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游戏的作用往往能够得到更为明确的凸显。当专制权力全面控制了个人的私域时,人对于游戏的参与、投入甚至痴迷往往意味着在专制范围以外另开辟一个自由的空间。而这一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专制权力的拒绝和消解。正如茨威格笔下的象棋、昆德拉笔下的性爱、王小波笔下的数学……,它们都是专制权力的软化剂、专制秩序的破坏者,尽管他们采用的都是非常“非政治”的态度。也就是说,游戏凭借其“非政治性”的特性达到了一种政治性的后果。无论是席勒所言之“物质游戏”,还是“审美游戏”都能起到以上的作用。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敏锐地写到了“浪荡游民”,他们可能是文学家,可能是密谋者,也可能是捡拾垃圾的人,他们“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骚动中,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而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动摇这个社会根基”*[法]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这种浪荡者和席勒笔下游戏的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说,“浪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化的游戏。“对于个体而言,美学经验成为一种合法的表达,积聚了反社会的趋向和冲动。”*Hilde Hein,“Aesthetics Consciousness:The Ground of Politics Experience”,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of and Art Criticism,1976,No.2.
游戏的这种功能为通往尊严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虽然游戏往往不能甚至不可能对政治产生直接的、有力的影响,而政治本身所要求的权利与权力也并非游戏所能承当。但在抵御专制权力对个人生活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压制时,游戏几乎是不二之选,在通往自由、正义的路途上,游戏所起到的作用功不可没。
游戏既是想象的,也是权力的,席勒对游戏理论的使用,海涅的分析或可作为恰当的注脚,他“以惊人的洞察力指出,在德国,由于一开头就缺乏实际行动的可能,所以出现了一个升华的过程:没有见诸行动的社会积极性,把它的光芒折射到幻想上面,折射到由音乐、书本和绘画所表现的艺术形象上面,由各种思想原则构成的精巧花纹上面去了。”*[苏]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64页。游戏与审美的合一是构筑席勒诗性政治的基本法则,“理性说:美的事物不应该是纯粹的生活,不应该是纯粹的形象,而应是活的形象,这就是说,之所以美,是因为美强迫人接受绝对的形式性与绝对的实在性这双重的法则。因而理性做出了断言: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第123页。也就是说,通过对人、美、游戏三者之间关系的确认,使诗性政治的逻辑框架得到巩固,最终使整个诗性政治的逻辑得到确立。
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13DB04)。
张秀宁(1978-),女,文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期刊社编辑(南京 210042)
——冯至《蛇》的一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