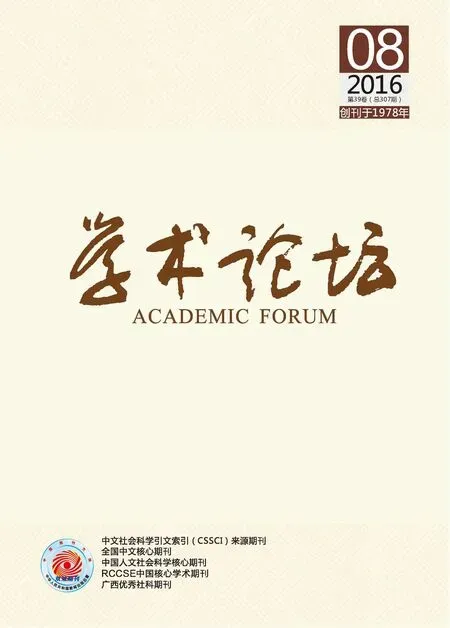论先秦“心性”范畴理论内涵的嬗变
朱金发
论先秦“心性”范畴理论内涵的嬗变
朱金发
先秦时期,与“心性”范畴相关的思想认识,起源甚早,这一点在西周初期的文诰和诗歌中,有明确的反映。殷周金文资料中,将德看作人心所蕴涵的道德属性,这种思想就是“心性”范畴理论内涵的最早形态。战国中期的儒家学者对此有更加系统的论述,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性是人禀受于天地、蕴涵于内心的基本属性,这种思想观念充实了“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易传》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逻辑论证,认为人的道德属性是人对天地之道的体悟;《孟子》一书更进一步认为,道德品性和人的生理本能一样,都是蕴含于内心、先天而来、可以通过尽心尽性而实现的道德自觉,完善了“心性”范畴的理论认识。
“心性”范畴;道德品性;理论内涵
一
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主体,“心性”范畴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儒学是中国传统的综合性学说,涉及伦理、政治、教育、文艺等,“这些学科的内容……互相联系的,互相配搭才构成这么个系统的儒学思想体系”[1](卷四,P97)。其以探求天人之道为根本旨趣,把人作为理论思维的中心,集中探讨人的本性、人性的善恶等问题,为政治理论服务。因此说,“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和天人关系问题一起,贯穿中国哲学的始终,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2],这说明,“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3](P4),重视对人心、性、情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4](P13)。然而时下还有人认为,心性论思想到战国中期的孟子时代才开始提出。我们通过传统典籍、金文资料及出土文献的梳理,发现这种观点是需要修正的。在西周早期,关于“心性”范畴理论内涵的思想意识,就已经出现了。
清代以前,《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被作为“心性”范畴理论内涵提出的最早根据,特别是宋明心
性之学,以之为“尧舜禹三圣传心之要旨”[5](59册,P47)。南宋以后,传统的性理之学对此多有阐发,朱熹说:“尧舜禹所传心法,只此四句”[6](P2017)①另外《陈氏尚书详解》见[5],胡士行《胡氏尚书详解》卷十三、王樵《尚书日记》卷三也有相同说法。,认为尧舜时代已经提出了心性之学的理论。但也有人对此并不认同,如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力辩古文《尚书》之伪,认为“虞廷十六字‘心经并不是尧舜禹三代之辞,而是魏晋间人檃栝《荀子·解蔽篇》文字而成,认为心性论的起源是战国时代的事情②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以为这些话乃荀子所引《古道经》之文。王先谦亦谓《荀子·解蔽篇》所引《道经》“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来也”(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3页)。。我们认为,虽然尧舜禹时代不可能提出如此完整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心性“范畴理论内涵的提出还是很早的。如《尚书·盘庚》:“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7](P170-171)这里商王盘庚晓谕臣民,要他们服从迁徙的命令,责怪他们不与自己同心,不能体恤自己的良苦用心。“不宣乃心”,心字意为忠诚之心;“迂乃心”,意为心灵受到蒙蔽,思想邪僻不正。这里所言的“心”,基本内涵为情感、愿望和意志,是关于人的精神方面的概念。特别是“迂乃心”之义已经初步具有了“作为道德观念,便表示人通过认识和修养而具有的伦理道德精神”[8](P26),是“心性”范畴理论内涵的基本内容。《盘庚》是可信的今文《尚书》的篇章,其中关于心性论的思想,是殷商时代的思想观念。
到西周初期,“心性”范畴的理论认识更为成熟,“明德”说便是这种认识的体现。如《诗经·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9](P587-589)诗歌前四句颂扬文武之德,即能够勤谨政事,有光明之德。孔颖达认为诗歌“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抚民不倦之事也”[9](P587)。“单厥心,肆其靖之”,“单”,《毛传》:“厚”也。这两句是说文王、武王能够宅心仁厚,才使得天下太平。诗歌中的“心”,指的是通过践履而实现的内心道德精神。马端临《毛诗传笺通释》认为诗歌“作于成王之时”[10](P1051),王国维《周大武乐章考》以为是周公所作《大武》乐章首章所用之诗歌[11](P105-111)。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考证此诗为成王初期郊祀天地所诗歌:“周公在洛邑南郊祭天,歌奏《昊天有成命》之诗。”[12](P220)不管哪种说法,这首诗歌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这说明西周建立之初,心性论的观念已经成熟。
西周初“心性”范畴的思想认识,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如《尚书》中周初的几篇文诰,是西周建立之初,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为维护新政权而创作的,其中多有关于道德建设及“心性”范畴的内容。如《康诰》《酒诰》《梓材》是周公平定武庚和三监叛乱后,册封康叔于卫时所作。据《史记·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13](P1565)再如《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13](P1518)说明西周之初,管叔、蔡叔为争夺政权,纠合武庚发动叛乱,淮河流域的东夷诸部落也参预乱局,对刚建立的王朝形成严峻的挑战。因此周公果断地兴兵平定了叛乱,并册封康叔封在卫地建立侯国作为周室屏障:“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13](P1589)富于雄才大略的周公认识到道德文化建设对于稳定人心政局的重要性,在册封康叔的同时,作“《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13](P1590)。如《梓材》要求康叔封“勤用明德”,宽厚爱民,勤谨政事;《酒诰》告诫康叔不可酗溺于酒,要借鉴殷商灭亡的教训,在卫地推行文王的教化,重视农耕、敦厚亲族人伦,“教为纯一之行。其当勤於耕种黍稷,奔驰趋走供事其父与兄”[7](P206),以此来推行道德教化。这些文告中,周公反复强调心性的重要性,如《康诰》说:“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7](P203)其中“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据《尚书》孔传,是让康叔“当大远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则知训民”[7](P203),告诫康叔要遵循文王的德行政教,牢记商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往尽乃心,无康好逸,乃其乂民”[7](P203)。这是周公告诫康叔不要贪图安逸放纵的享乐生活,“当尽汝心为政”,“乃其可以治民”[7](P203)。并进一步指出,政治不平静是因为人心不安:“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要求康叔“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7](P205)。周公告诉康叔,要恭敬从事,“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谋、非常之法,惟断以是诚,大法古人之敏徳,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徳,远汝之谋,宽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14](P90)。这些都是关于人思想、情感和情志的内涵,与道德精神修养有关。特别是所谓的“丕则敏德,用康乃心”,说要康叔努力效法“敏德”才能“康乃心”(即安心),这就涉及到道德修养问题,是“心性”范畴的主要内容之一。
上述这些思想中,肯定了人的道德品性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没有提出心性概念,但这些将人心与德性等同起来的认识,就是“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
和西周初期不同,西周中、晚期,很少有周初文诰那样直接历史记录和文献流传下来。有幸的是,历代出土的金文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记载,这些是西周中期、后期关于“心性”范畴思想认识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据《殷周金文集成》一书著录,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资料中,关于“心性”范畴的资料很多,如:
2.《师望鼎》:太师小子师望曰:丕显皇考宄公,穆穆克明厥心,哲厥德[15](卷二,P378)
5.《大克鼎》:克曰:穆穆朕文祖师华父,悤命厥心,宇静于猷,淑哲厥德,肆克恭保厥辟恭王[15](卷二,P409)
6.《师訇簋》:敬明乃心,率以乃友,捍御王身[15](卷三,P482)
8.《散氏盘》:实余有散氏贼心[15](卷六,P135)
(以上铭文均为节选,标点为笔者所加)
这些西周彝器上的铭文,是西周时期思想观念最原始的记载。据《金文集成释文》,1-4器为西周中期的器物,5-8器为西周晚期的器物,其中1、2、6、7诸器,所谓的“克明厥心”、器5的“悤命(同聪明)厥心”,内涵相同,一个“明”字说明这些“心”指的是通过个人主观努力才能够实现的道德伦理精神;具体而言,即铭文中的“帅祖考”“帅型皇考”“哲厥德”“淑哲厥德”等事项,即遵循祖先显赫的德行,要有明智仁厚的德性。器8《散氏盘》铭文中的“贼心”一语,更是明显地表现出了关于“心”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基本内涵。这些思想内涵和《昊天有成命》一诗中“单厥心”即宅心仁厚的思想是一致的。上述铭文中的明心,是指通过道德实践和主观努力实现的道德精神,这和后代的心性论理论内涵中的道德自觉精神一致,都是和道德精神相关的“心性”范畴的基本内涵。
周代的金文和殷商甲骨文不同,甲骨文为占卜而作,是占卜时命龟及占验之辞,和人的道德心性无关。周代金文是周人为表彰功德、颂扬祖先而作,有固定的程式内容,所谓“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9](P316)。这样颂扬功德的铭文,和道德教化深切相关,是君子“德音”体现。因此说,制作这些铭文,是为了“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因此这些金文中的道德心性内涵,体现了西周的人文精神,是西周道德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西周中后期的金文资料,参照《诗经》和《尚书》中周初文诰,正好可以反映出整个西周时期人们关于人自身道德心性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自身修养和道德心性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是成熟的“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这些理论内涵就是“心性”学说的理论源头,西周以后的心性论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来的。
二
春秋以后,心性论思想逐渐丰富完善起来,认为人的道德品性蕴涵于人内心,人的外表言行就是这种道德品性的外在表现。如《诗经·閟宫》:“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济济多士,克广德心”,认为鲁侯能够“敬慎威仪”,是“敬明其德”“克明其德”的表现,这些都体现了鲁侯的道德实践精神。特别是“克广德心”一语,体现了周代重视人内心道德品性的思想观念。
孔子开创儒学,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人文精神。据《论语》一书看,孔子较少谈论抽象的“心性”概念,注重具体的道德实践,只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对“心性”范畴的理论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孔子以后的学者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很热烈,据《论衡·本性篇》:“周人世硕①班固《汉书·艺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根据后天教育会向不同方向发展。见《论衡·本性篇》。,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②班固《汉书·艺文志》:“《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贱。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据《韩非子·显学》谓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漆雕之儒。司马迁《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谓“漆雕开,字子开”,以为孔子弟子。然王应麟以为漆雕开为孔子弟子,名启字开,《宓子》一书为开之后人所著。王说见中华书局版《二十五史补编·汉书艺文志考证》,第二卷第1407页。班固《汉书·艺文志》:“《公孙尼字》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16](P132-133),这些都是儒家后学关于人道德心性的理论。这一时期的学者中,特别是子思、孟轲对“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有集中而系统的论述,并讨论《诗》《书》及礼乐教育对德性修养的作用。宋人所谓“圣以道化,贤以学行”[17](P472),即是指子思、孟轲主张的通过《诗》《书》、礼、乐进行的道德心性的培养,这些被称之为思孟心性之学。上述世硕等人的著作已经无法看到,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中,集中论述到“心性”范畴的是《孟子》《荀子》及《礼记》中的《中庸》《乐记》等。新文化运动以后,《礼记》中讨论性情的著作多被定位为汉代儒生之作。随着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证明这些著作都是孔子之后七十子之徒的学说,特别是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思孟学派性情论著作的发现,更加证明传统观点的可靠。
如前所述,孔子只是提出了性相近的命题,孔子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才开始对“心性”范畴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如朱熹说:“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说得详。”[6](P129)又据《史记·孔子世家》:“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13](P1946)另据《隋书·经籍志》,南朝梁沈约《奏答梁武帝问乐事》劄子:“《中庸》《表记》《防记》《缁衣》,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18](P288),也肯定《中庸》为子思的基本理论。据《荀子·非十二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19](P59)
荀子所驳思孟理论的核心是“五行”,其理论方法为“案往旧造说”,荀子认为这是十分乖僻、隐晦和无法解释的理论。荀子不遗余力所攻讦的思孟“五行”理论,应该是因为这种理论及方法与荀子提倡的法后王、治当世的政治主张相矛盾。思孟“五行”是什么,历来争议不休①可参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梁涛《思孟学派考述》,《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第27-34页;谢耀亭《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0页。。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为解开历史迷雾提供了文献依据:思孟所谓“五行”,是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是和道德人心相关的内容,和《中庸》中心性论思想一致。如果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以后,关于思孟学派“五行”理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②赵光贤《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十四辑)、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299页)都否定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是子思学派的著作,否定思孟学派的理论。,《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的出土,就使人再也无法找到任何否定思孟学派及其“心性论”内涵的藉口了。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一大批战国中期以前的竹简,其中有很多内容和《中庸》《乐记》一致,是孟子之前、七十子之徒的学术著作。其中关于“心性”范畴的论述自成体系,是孔子之后思孟学派心性论哲学的著作。这些竹书中《五行》《性自命出》《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缁衣》是一组,简长32.5厘米[20](P149),约合周尺一尺七寸③据吴承济《中国度量衡史》,周尺为19.78厘米,郭店简约折合周尺一尺七寸。(吴承济:《中国度量衡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2页)。,是这批竹简中最长的,说明在当时人的心中,被认为是仅次于经书的著作(据先秦简册定制,“以策之大小为之尊卑”,王国维语)。《语丛》各篇都抄写在长度最短的那种简上,内容由类似格言的文句组成,其体例与《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形似,集中解释了情、性、严、敬、欲,仁、忠、智等十几个范畴的基本含义和这些范畴之间的相生关系,这些范畴,应该是竹书作者对儒家心性学说思想体系中基本范畴的总结和整理,是为《五行》《性自命出》等哲学专论作资料准备的,《五行》《性自命出》中提出的仁义礼智圣,就是《语丛》诸篇中众多范畴的中心。
简本《五行》将人内心的道德品性作为“君子”的基本要求(以下引文均用通行文字,方括号内文字为整理者校补):“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④据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4页,此处无德字,然庞著是以帛书烂漫的距离推断阕文字数以校补,此处当从郭店楚墓竹简本《五行》文本。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20](P149)正如庞朴所言,《五行》“是一篇探讨道德哲学”[21](P10)的论文,认为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性是君子所应该具有的,只有这五种品德成为人内在的道德情感时,才是真正的德行,简文说:“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据郑玄《周礼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22](P730)。即简文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善弗为无近,德弗志不成”[20](P149)。简本《五行篇》通过揭示砥砺德性的心理过程,指出需要进行自觉的主观努力,用心思考才能实现这些道德性,即“德弗志不成”[20](P149)。不仅要“闻君子道”,还要“知而行之”“安而敬之”[20](P150),表明人需要使这些德性沉潜于人的内心之中,表现在人的行为之上,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本质。
郭店楚墓竹简中,另一篇系统论述“心性”范畴的是《性自命出》,其中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20](P179),认为人性是相近的,教育使之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凡性为主,物取之也”[20](P179)等重要命题,探讨外物、心性、情感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一种潜能,当受到外界刺激时,便会产生喜怒哀乐之情,人心的喜好是这种情感的内在动因,人的本性就是在这种喜好中培养起来的。这种观点,解决了对人的心性进行陶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其观点和《礼记·乐记》中“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的看法一致,并且篇中“心”“性”连言,如其开篇说:“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20](P179),认为人的内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情感和思想意识,外物的刺激和长期的实践,是人本性形成的基本条件,即“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奠”读如定,即是说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可以形成固定的本性,认为人的道德品性和人的生命本质是一致的,是人的生命本质和道德品性相互渗透形成的,即简文所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种观点和《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3](P1625)的说法一致,认为教育是培养人道德品性的重要手段:“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是从“心性”角度对教育和人德性之间关系的探讨。因此这篇文章中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即简文所谓“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20](P179)。简文作者认为这种教育和修习的过程,就是“生德于中”过程。因此说《性自命出》和《五行篇》篇都是探讨心性哲学的论文,“其内容在学理或说思想逻辑上,几乎完全符合我们今天对古典文化精神内涵的认识或思维定向的顺序”[24](P215)。这些思想就是思孟心性之学的五行学说,解决了人的道德心性是什么的问题。和西周时期的思想比较,这些学说将仁义礼智看作人心蕴涵的德性,“心性”范畴理论内涵中空泛的德,就被具体到仁义礼智之上,“心性”范畴的理论获得了具体的逻辑内涵。
三
上述先秦儒家心性论思想中,认为仁义礼智圣是蕴涵于人心的道德品性,至于道德心性是怎样产生的,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周易大传》及《孟子》书中,这些问题才得以解决。
《易传》以理性思辨方式论证人的道德心性来源,将人的心性放在天地之道的理论背景下进行讨论,认为万物是在天地阴阳精气氤氲交感中产生,是“精气为物”(《系辞传》上第4章);其中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传上》第1章),其实是在探寻天地万物产生的原理,而不是探讨万物及男女产生的现实原因。《易传》认为据自然阴阳之理,可以探知“刚柔相推”及“三极之道”的根源。如《系辞上》第五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传上》第5章)这里《易传》认为物性源于自然阴阳之气,由刚柔阴阳相次而成,所成即为物性,这也包括人的道德心性,即“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仁”“智”是人的道德精神,是“心性”范畴的基本内涵,《易传》认为“仁”“智”蕴含于“一阴一阳”之道,是继此阴阳之道而成,此阴阳之道也就是通过这些“仁”“智”的道德品性体现在人的道德生命状态之中的。换句话说,《易传》认为人的道德品性就是从天地阴阳之道中产生出来的,和天地之道是一体的,人就是在体悟天地之道的过程中,实现道德属性的。如《说卦传》第一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先秦时期观象制器思想,天地人之道是在“顺性命之理”也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易传》认为,仁智是人的道德属性,这种道德属性是天地阴阳之道的自然延伸,体悟天地之道而实现人道,通过仰观俯察大千世界,弄清楚天地万物和社会道德的准则,即“顺性命之理”。
《易传》中认为人的“仁”“智”之德性来源于天地之德,道德精神的实现是由天地之道直指道德人心,这就从理论思辩的角度解决了人心中蕴涵的仁义礼智诸德性产生的逻辑过程,是儒家学说对“心性”范畴理论内涵的逻辑论证,解决了人的道德品性来源问题。笔者有另文专论①参见拙文《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此不赘述。《易传》将人的仁义之性与天地阴阳刚柔之道混同起来,认为仁义为人道,人道来源于天地之道,属于人之恒德,是天地恒常之性的延伸。此说引仁义入天地恒常之性,是儒家学说中对道德心性观念的理论充实和提高。
先秦儒家学说中,将人的道德心性与天道混同起来论述的,除了《易传》以外,还有《孟子》一书及《大学》《中庸》等。我们首先看《中庸》,其中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命题,将人的道德属性和天命联系起来。《中庸》中天命说,和宗教天命不是一回事,孟子的性命思想也是这样。这种思想认为,人的道德属性是仁义礼智等内容,来自先天禀赋,这就将人的道德品性与天地之性联系起来,这与《周易·系辞》中的说法相近。因此有人认为《中庸》的性命观和《易传》相通,如熊十力《原儒·下卷》中说:“《中庸》本演《易》之书。”[25](P177)这也是清代学者中比较流行的看法。然而二者实质上还是不同的。《易传》中主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主张通过对天地自然阴阳刚柔之性体察感悟,实现人自身道德属性,达到道德自觉。而《中庸》强调道德属性的本质,认为德性存在于人内心,是禀受自天地、通过尽心来实现。《易传》主张通过体悟天地之性化成天下,重视人道德实践的外化及其建设作用;《中庸》重视人内心道德修养功夫,主张由天道到性命的内化及尽心全性成为圣贤。《易传》侧重于人对天地阴阳刚柔之性的体悟和模仿,而《中庸》等则将仁义礼智圣等道德属性完全内化为人的道德本质,更重视人本身的道德属性。
这种更重视人道德属性的理论倾向,在《孟子》一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就是《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观点。孟子认为人的道德属性是人禀受于自然的习性,人的生理本能和道德心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孟子认为人的生理本能就是性:“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26](P87),是人的生理本能,“四肢之于安逸”,是人共同的心理习性,即“人心所同然者”。孟子认为这些是先天而来的,都是接受人心控制的,是人心能够接受和容纳的因素,具有普遍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孟子认为这些心所同然的生理本能,和仁义礼智等道德品性一样,都是人心所同然、心所固有的东西。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6](P86)这是孟子著名的仁之四端说,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性的四个基本方面,这四个基本方面不是从外部通过习惯形成才进入人内心,而是“我固有之也”的。因此,孟子以人的共同心理判断与取舍标准为认识论基点,将仁义礼智圣等道德品性与人的耳目口鼻的生理本能等同了起来,将它们归入人的自然禀赋之列,人的道德属性自然就是由天命而来,就是秉赋于自然的了。
自汉代赵歧到清代阮元,都以道德自觉精神来解释孟子的性命两个范畴之间的伦理关系,特别是阮元又将孟子的观念和《尚书·召诰》的“节性”思想相联系,申明了节性敬命的思想。但孟子主张的尽心、尽性,是充分扩充、发扬和实现人内心所具有的善性,通过求其放心、尽心尽才性之美,从而实现正命、立命的。对于怎样节制人的生理欲望,怎样不超过礼命的规定、不从事僭越活动,对于孟子的理论来说,是等而下之,不关紧要的内容。孟子是要通过性命一体两面关系的论述,印证人性是禀受天地自然而来的,是蕴涵于人心的仁义礼智圣等道德品性,这就充实了“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完善了道德心性论理论体系,其核心和落脚点是人性善。
和孟子的性善论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荀子思想中的心、性两个范畴,和孟子理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将人性看作秉赋于自然而来的因素,是先天具有的。不同的地方是,孟子的思想中,性、命和心三个范畴的内涵是一致的,生理欲望和仁义礼智圣之性都蕴含于内心,人性是这些因素的整合体。而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是人的生理本能,是人与生俱来不需要学习的,而人的道德情感是后天学习和道德实践中培养起来的;同时荀子认为人心是控制和驱使人身体的中枢,可以控制和调节人的喜怒情感,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通过长期的实践和修养功夫,形成现实的德行,从而实现人道德品性的提高。这就将人的生理本能、欲望、道德情感从人心中剥离了出来,将心和性两个范畴明确的区分开了,性成为心之外的、被人心认知的独立客体。以此为基础,荀子自然的得出了性恶的结论来。荀子的理论,更符合人类思维的实质,但不是先秦儒家以仁义为中心的心性论思想的主体。
[1]庞朴.中国儒学[M].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2]蒙培元.浅论中国心性论的特点[J].孔子研究,1987,(4).
[3]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5]陈经.陈氏尚书详解[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6]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孔颖达.尚书注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8]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9]孔颖达.毛诗正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10]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Z].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赵逵夫,贾海生.先秦文学编年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蔡沈.书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16]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7]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9]王先谦.荀子集解[M].上海:上海书店,1986.
[20]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1]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0.
[22]贾公彦.周礼注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23]孔颖达.礼记正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24]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
[25]熊十力.原儒[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6]朱熹.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戴庆瑄]
朱金发,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古典文学文献学博士,河南南阳475061
I206.2
A
1004-4434(2016)08-0111-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诗经》学范畴研究”(11BZW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