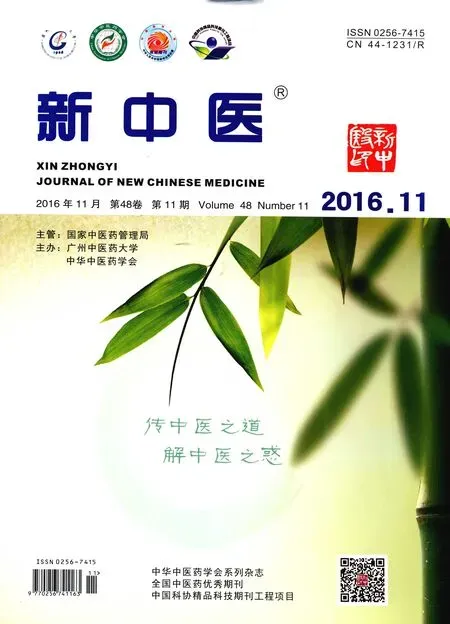王仲青论治危重疑难病医案5则
葛健文,马小军,王争胜
天水市中医医院,甘肃 天水 741000
王仲青论治危重疑难病医案5则
葛健文,马小军,王争胜
天水市中医医院,甘肃 天水 741000
喘症;猝心痛;水肿;瘿气;中风危证;王仲青;医案
王仲青主任生前是我国第一批老中医药师带徒指导专家,曾任甘肃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名誉顾问,天水市中医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王主任从医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内科疑难病症的辨治得心应手,尤其在伤寒、温病、中医临证思维方法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王主任在六十多年的医海生涯中,因屡起沉疴而声名遐迩,许多危重、疑难病患者慕名前来求诊,这其中包括许多当今医学公认之顽疾,如重症中风、肺性脑病、急性心梗、晚期糖尿病、甲亢等。对这些中西医均感棘手之病,王主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同时配合西医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现整理其部分医案,以飨同道。
1 喘症(肺心病、肺性脑病)
白某,男,72岁,1985年6月19日会诊。患者咳痰喘已数十年之久,每于冬春加重,诊为肺心病,经常服药。此次发病加重已近半年,经服中西药未能控制,住院后经用抗炎、强心、止咳、吸氧等无效,近日更趋严重,西医诊断为: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心衰III度,肺性脑病。医院予病危通知,乃邀王主任会诊。症见神识朦胧,卧床不起,面唇晦暗而紫,喘促抬肩,气短,呃逆不止,饮食不进,手足冰凉,爪甲紫绀,尿少,下肢浮肿。舌紫、苔白而黄燥,脉结促而乱,沉候隐约不见。辨证:心肺阳气虚衰而欲脱,中气馁败,痰瘀互结,病属喘症危候。治以益气强心、活瘀化痰之法,以观其变。处方:人参(另煎兑服)15 g,当归、炙五味子、炙甘草、丹参各9 g,茯苓12 g,远志、制附片各6 g,公丁香4.5 g。1剂,阴阳水各半,浓煎频饮。
6月21日二诊:上药服后,患者精神稍好,气喘息促稍见缓和,颜面四肢紫绀略转,能进食3~4两,呃逆未止,大便未行,小便每天2~3次,量稍增,色赤,下肢仍肿,舌紫苔黄稍退,脉促细数,仍守前法,以观其效。处方:人参24 g,熟地黄15 g,茯苓12 g,炙五味子、麦冬、远志、丹参、当归、炙甘草各9 g,制附片6 g,公丁香3 g。2剂,阴阳水煎频饮。
6月24日三诊:上药服完2剂,患者精神大振,喘促大减,气息平稳,能起坐,纳食尚可,颜面及四肢紫绀转为红润,下肢肿减,乃仍以前法加减服之,饮食调摄,逐渐好转。
8月11日随访,患者精神、食纳可,日常活动正常,时有咳嗽,活动上坡时稍觉胸闷、喘促,颜面、下肢无水肿。
按: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云:“肺虚为微寒所伤则咳嗽,嗽则气还于肺间则肺胀,肺胀则气逆,而肺本虚,气为不足,复为邪所乘,壅痞不能宣畅,故咳逆,短乏气也。”故咳痰喘肺气本虚,病久则肺虚及肾,肾气失于摄纳,肾阳失于温煦,则喘促抬肩、气短、呃逆不止、手足冰凉、尿少、浮肿;肺肾气虚,不能鼓动血液运行,血郁为瘀,“血不利则为水”,致痰、瘀、水错杂,治疗以培补肺肾,化瘀祛痰,标本兼治。
2 猝心痛(急性心肌梗死)
胡某,男,59岁,1991年6月6日初诊。以“腰腿疼痛”收治入院,经治腰腿疼痛减轻。6月23日下午6点半,患者突感胸骨下缘及上腹剧痛难以忍受,查血压(BP):110/70 mmHg,心率(P):70次/分,律齐。先后给强痛定、杜冷丁缓解。24日查心电图示:电轴右偏+120°,V1~V6呈QS波形,V1~V6导联T波呈弓背抬高,II、III、avF导联ST段水平下移,西医诊断: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中医诊为胸痹(心血瘀阻证)。西药给极化液静脉滴注,口服消心痛等,中医予血府逐瘀汤。24日晚8时许,患者又诉心前区剧痛,查P:96次/分,呼吸(R):20次/分,BP:80/20 mmHg,急予止痛、吸氧、抗休克治疗,至9时心前剧痛又作并出现呼吸困难、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呕吐痰涎,P:140次/分,R:24次/分,BP:100/45 mmHg,心律不齐,心尖区可闻III级收缩期粗糙如吹风样杂音及舒张期杂音。舌淡红苔薄白,脉细数疾。西医诊断:冠心病、急性广泛前壁心梗、心源性休克、心律失常,西药抢救同时针刺人中、内关、涌泉,浓煎人参30 g顿服。实验室检查:血白细胞(WBC):25.0×109/L,中性粒细胞(N):0.85,淋巴细胞(L):0.15,血沉(ESR):40 mm/1h,血糖:8.7 mmol/L,钠:129 mmol/L,钾:3.7 mmol/L,余未见异常。至26日,患者仍胸痛时作,心悸气短,精神极差,并先后出现心房纤颤、频发房性早博,西药抗心律失常药治疗未见显效。6月27日请王主任会诊,症见心前区疼痛,尿少,舌淡红苔白,脉虚数,BP:80/65 mmHg,心电图示,急性广泛前壁心梗,心房纤颤,房性早搏。证属心气大虚、元气欲脱、瘀血阻络之“猝心痛”,治拟补气益阴以防厥脱,少佐活血药物。处方:西洋参(另煎兑服)、麦冬、炙甘草各9 g,炙五味子、远志、降香各6 g,郁金3 g,陈皮4.5 g,大枣3枚。2剂,每天1剂,水煎分2次服。
6月29日二诊:心前隐痛,剧痛未作,心悸气短,神疲乏力,言语低微,汗多,纳差,尿少,无大便,苔白,脉缓结代,BP:80/60 mmHg,心电图示:急性广泛前壁心梗、窦性心动过缓、房性早搏、Q-T间期延长,辨证同前,前方继服3剂。
诊11次后,胸前剧痛未作,隐痛减轻,惟癫痫时作,头痛,或挟大肠湿热而便血,均予随症加减,而补益气阴之法则始终用之。共服药80余剂,诸症基本消失,心电图示有陈旧性心梗波形,BP略低。于1991年10月3日痊愈出院。
按:王主任认为冠心病虽有心血瘀阻表现,用活血化瘀治法可缓解,但往往短期内反复发作,且常见气短、心悸、自汗等,此皆因心气不足所致。但阴阳互根,心气虚久致心阴亏耗,故临证中气阴两虚者居多,治疗上以补益气阴为主,辨证论治,较之单用活血化瘀疗效为优。此例患者,虽用活血化瘀法加用西药治疗,仍不能控制病情,乃因病机重在气阴两虚,因剧痛而致元气欲脱,大汗又耗伤心阴,若用活血化瘀之法,不顾气阴大亏元气欲脱之根本,本末倒置,势必更加耗伤正气,恐病未除而人先亡矣。王主任紧扣病机,补气益阴生脉以防脱,少佐活血理气之品,随症加减,终使此危重患者安渡险期而病愈。本方以补为主、补中寓通,紧扣冠心病本虚标实、因虚致实之病机特点,充分体现了王主任一贯主张的“补而不壅滞、滋而勿黏腻、活瘀勿耗血”的观点。临症加减:如气虚甚可加炙黄芪,人参可代以西洋参、党参;胸痛较剧加桂心、丹参;胸闷憋痛加瓜萎、薤白、枳实;心悸少寐加炒枣仁、柏子仁、茯神;心阴虚加生地黄、玄参;小便不利加茯苓、泽泻、木通等。
3 水肿(重症糖尿病)
卫某,男,72岁,1991年11月21日会诊。患者患糖尿病已20多年,双腿疼痛,行动不便2年,加重半年。入院经中西医治疗,效不显。诊之症见口渴舌燥,心悸气短,咳嗽,纳呆,大便干燥,小便量少,因双腿痿弱不能行走,而半卧于床。双下肢、臀部水肿,足肿如穿靴,阴囊肿大如拳,腹部胀大如鼓,叩之如鼓,情绪悲伤。察其舌质红、有裂纹、苔焦黄,脉弦数应指有力,腹部移浊(+)。尿检:尿糖(++++),尿蛋白(+++),血糖12.0 mmol/L,上一个医生用济生肾气丸加西洋参、炮姜、芡实等治疗。王主任认为病人素有内热,且本虚标实,虽有水肿,但不宜温阳,亦不宜过于利水;兼有纳呆,大便燥结,数日不行,也不宜消导。治宜滋阴利水,方用六味地黄丸加味。处方:熟地黄15 g,山茱萸、山药、泽泻各12 g,茯苓、牡丹皮、肉苁蓉各9 g,玉米须30 g。
此病人服用王主任这一处方,略施加减,达30多剂,同时配合西医支持治疗,水肿显著减轻。1992年1月16日随访,患者午后双下肢时有水肿,经休息后晨起水肿消退。
按:王主任认为此病西医虽诊为糖尿病,但从中医的消渴病来看,现无“三多”之症,而以水肿为主,故治疗上亦应抓住这一主症,抓住阴虚燥热这一病机关键,兼症可不予多考虑,使药性力专。处方中加重泽泻以泄浊,并加玉米须30 g,认为此药利水而不伤阴液,且性味甘淡,无伤胃之弊,加肉苁蓉以润肠益肾而通燥结。
4 瘿气(甲状腺机能亢进)
段某,女,37岁,1991年5月23日初诊。诉脖项肿大14年之久,目前口服他巴唑5 mg,每天2次。常心慌头昏,多食乏力,烦躁,目珠突出,目光炯炯少瞬,口干多饮,多尿,大便每天2~3次,成形。甲状腺肿大III度,触之坚硬如石,面赤手颤,舌尖红赤、苔根部薄黄,脉细弦,证属痰气胶结,蕴热伤阴,治以养阴疏郁、软坚化痰散结。处方:玄参、生牡蛎各15 g,麦冬、海藻各12 g,赤芍、天花粉、浙贝母、茯苓、夏枯草、昆布、制香附各9 g,青皮、黄药子各6 g,生甘草3 g。3剂,每天1剂,水煎温服。
5月28日二诊:服后诸症均有减轻,已停服西药他巴唑,脉舌同前,仍宗前法加减治疗。处方:玄参、海藻、生牡蛎(先煎)各15 g,昆布12 g,浙贝母、香附、夏枯草、赤芍、海浮石、泽兰叶各9 g,山甲珠6 g。3剂,每天1剂,水煎服。
6月1日三诊:药后诸症续减,惟目突手颤,瘿瘤大小坚硬如前,脉舌同前,上方去香附、泽兰叶,加炙鳖甲9 g,蓬莪术4.5 g,薄荷3 g。3剂,每天1剂,水煎服。
6月18日七诊:以6月1日方加山慈菇6 g,服9剂后瘿瘤边界较前明显(原弥漫不清),硬度亦有所软化,项部压迫感有减,今日能骑车10公里来诊,仍守前法继服。
6月29日九诊:瘿瘤近日逐渐缩小,比前又缩小1 cm左右,质地稍软,左侧明显缩小,舌红苔根部薄黄,脉左弦数略大、右小数。仍守前法加蒲公英12 g,黄药子6 g,5剂,每天1剂,水煎服。
7月24日十四诊:上方加减共服18剂,并外敷海藻、蒲公英各60 g,风仙花30 g,黄药子15 g,为末水调外敷项部,并于20天后方中减去海藻,瘿瘤又有所软化,前方加柴胡3 g。5剂,每天1剂,水煎服。
8月3日十五诊:瘿瘤已缩小十之七八,质坚硬已软,其他症状如发热心慌等均减轻,舌红苔少,脉数。此后一直坚持服中药,病情稳定。至9月11日因足癣,而外擦碘酒,右侧甲状腺又触之坚硬,治疗同前。
9月28日二十二诊:瘿瘤左侧大消,右侧仍肿大略硬,下肢酸软,浮肿,按之凹陷,舌尖红苔薄白,脉细略数,指甲凹陷,治守前法加养血平肝渗湿之品。处方:玄参、牡蛎各15 g,夏枯草、蒲公英、海浮石、决明子各12 g,当归、泽泻、赤芍、浙贝母、鳖甲各9 g,香附、穿山甲各6 g,白芥子4.5 g。5剂,每天1剂,水煎服。
1992年1月4日三十一诊,西药已停服半年余,心率84次/分,近因经常感冒,而间断服药,症状不明显,甲状腺左侧质软接近正常,右侧仍肿大稍硬,目突右轻左甚,咽痛,身痛,四肢有轻度压痕,舌尖红无苔,根部薄白苔,脉沉细。予清热解毒配散结之品服之,并告以前方加量配散剂常服以资巩固。1993年底随访,病情稳定未发展。
按:此例甲亢患者因甲状腺肿大严重,目突亦甚,外地某大医院曾建议手术,因患者不同意而改服中药,王主任抓住阴伤热甚、痰凝气郁之病机,始终坚持以滋阴清热、软坚化痰散结之法而收功。
5 中风危证(蛛网膜下腔出血)
张某,男,58岁,1986年3月2日会诊。患者因头痛头晕,恶心呕吐半天,于1986年2月28日11时收住某医院。发病前因劳累、心情不舒,精神一直较差,2月28日晨起时自觉头痛头晕,恶心,呕吐黄水2次,精神紧张,欲解大便,神志清,语言清楚,无肢体偏废及黑便。入院查体温(T):35.6℃,脉搏(P):90次/分,呼吸(R):20次/分,血压(BP):200/100 mmHg,颜面苍白,精神差,神清,对答切题,双瞳等大圆,对光反射存在,咽轻度充血,颈部强硬,心肺(-),肝脾未及,腹软无压痛,四肢活动尚可,生理反射迟钝,病理反射未引出,初诊为高血压。经甘露醇及降压药等治疗,患者转入昏睡状态,经查眼底示:视网膜动脉硬化(高血压II期),余未见异常。
3月2日患者仍处昏睡状态,精神极差,目闭,烦躁不安,怕光,颜面潮红,颈项强,生理反射迟钝,巴氏征(+),夏道克氏征(+),戈登征(+),10点左右做腰穿,脑脊液压力偏高,如洗肉水样脑脊液,化验后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122 g/L,红细胞4.30×106/L,白细胞1.74×108/L,中性粒细胞:0.77,淋巴细胞:0.29,酸性0.01,二氧化碳结合力:67.2 mmol/L,西医予吸氧、镇静、脱水等治疗,均无效果,患者转入深度昏迷,乃邀王主任会诊。症见患者昏迷不醒人事,痰鸣漉漉,鼾声大作,烦躁不安,颜面潮红,颈项强直,对光反应迟钝,小便失禁,膝腱、提睾反射均消失,巴氏征(+),舌边尖红、苔黄,脉弦大。综观脉证,系肝风内动,痰热胶结,蒙蔽清窍,暂拟平肝熄风清热、涤痰通络和血为治,以观其变。处方:钩藤12 g,胆南星、天麻、菊花、羚羊角(锉粉冲服)、竹沥(兑服)、赤芍、白芍、橘红各6 g,姜半夏、石菖蒲、秦艽、仙鹤草各9 g,全蝎、桃仁各4.5 g,生甘草、鲜姜汁各3 g。1剂,水煎频频少量灌服。3月3日,1剂药尚未服完,患者烦躁不安,气短而促,昏不知人,汗多,哈欠,鼻鼾,BP:160/90 mmHg,又作腰穿,见红色混浊脑脊液,压力高,诊为蛛网膜下腔出血,下病危通知。家属急告王主任,王主任细作分析,认为药服1次,未达病所,应鼻饲将昨日药服尽,以观动静。
3月4日二诊:病情略为稳定,神识较昨稍清,烦躁稍减,双瞳反射较昨灵敏,仍畏光,自述头痛,喂流食能咽,喉间痰鸣,舌如前,脉弦大略减,药已中病,继守原方加减,去白芍、菊花、仙鹤草、桃仁、橘红,加生地黄12 g,牡丹皮6 g,红花2.4 g,茯苓9 g。2剂,水煎2次,混合后分服(羚羊角粉另冲)。
3月5日三诊:药后病情基本稳定,仍嗜睡,面赤,时鼻鼾,咳嗽痰多,咯之不爽,稍能进食,四肢可稍活动,大便通畅,舌边尖红、苔黄燥兼黑,脉左弦大。各症虽然大减,但肝风尚未痊熄,痰热胶结尤甚,守前方加重化痰之品。处方:瓜萎15 g,钩藤、生地黄各12 g,胆南星、法半夏、茯苓、石菖蒲、竹沥(兑服)、菊花各9 g,牡丹皮、天麻、赤芍各6 g,橘红4.5 g,全蝎3 g,鲜姜3片。2剂。
3月7日四诊:药后诸症续减,惟咯痰量多不爽,头痛,嗜睡,舌苔如前,脉弦大较前略缓和,血压波动不大,效不更方,上方加海浮石12 g,以化顽痰,再服2剂。
3月9日五诊:诉头痛大减,痰量明显减少,神识清楚,能进饮食,吸氧停止,二便如常,惟视物模糊不清,舌质略红、苔黄,黑苔已退,脉弦而缓,BP:160/70 mmHg,此时痰热已清,而肝风未熄、肝阴不足,治以平肝熄风、滋阴清热。处方:石决明(先煎)、瓜萎各15 g,玄参、丹参、草决明、茯苓各9 g,赤芍、菊花、秦艽、天麻各6 g,酒黄连、生甘草各3 g,竹茹4.5 g。2剂。
3月12日六诊:饮食增加,疲乏无力,视物成双,且模糊不清,舌略红、苔中黄糙,脉弦而缓。将上方赤芍改为焦栀子,酒黄连改为麦冬,竹茹改为桑叶。3剂。
3月19日七诊:复视有所减轻,视物仍模糊,已能起坐,纳食大增,咯痰爽利,大便干燥,舌苔薄白略带黄,脉缓和。患者已进入恢复阶段,乃以上方或加生地黄、夏枯草,或加天冬、牛膝、潼蒺藜、泽泻,连服4剂。
3月22日八诊:患者恢复良好,头目清爽,复视消失,视物清楚,能下床活动,纳佳,小便正常,大便干,3天未解,舌质转淡,苔黄已退,脉缓略弦,拟益气通络活血,予补阳还五汤加减。处方:生黄芪30 g,生地黄、石决明各15 g,天冬、当归、白芍各9 g,川芎、牛膝、天麻、菊花、元明粉(冲服)各6 g,桃仁4.5 g,红花2.4g,生甘草3 g。
3月25日九诊:药后大便已解,仍感起则头眩,疲乏,余无所苦,脉舌如常,乃以上方去元明粉,加草决明15 g,服5剂后,停药,调养而愈。
按:经云:“阳气者,烦劳则张”,患者年近花甲,本体弱气虚,复因劳累,阳气张扬,阴血暗耗,更因气郁不疏而化火,致阳升风动,挟痰挟火上逆而见头晕头痛,项强面赤,挟胃气上逆则呕恶。初治肝风未熄,痰火未清,气血上逆痰热胶结,蒙蔽清窍而成中风中脏腑之危证。神昏、目合、痰鸣、鼻鼾为神机内闭之症;遗溺欲大便、汗多呵欠为元气欲脱之兆;病危变速,恐内闭外脱,有阴阳离决之势,则危甚矣。然本案虽有年老体弱,元气欲脱之象,但脉弦大,舌红苔黄,故风动痰热内闭、气血逆乱才是本案病机之重点,王主任紧扣病机,予以羚羊角、天麻、钩藤、全蝎、菊花、白芍平肝熄风清热,胆南星、半夏、石菖蒲、橘红、姜汁、竹沥以涤痰开窍醒神,妙在本病早期即抓住气血逆乱失和之病机,使用了和血之桃仁、赤芍,为以后康复打下了基础。虽药尚未服毕而病更危殆,亦坚守法度,不改初衷,终使药后神识渐清,转危为安。其后谨守病机,步步为营,随症变化加减,或补益肝肾,或益气阴、通腑气,而清热化痰、平肝熄风、和血通络则贯串始终,直至病愈。
(责任编辑:冯天保,郑锋玲)
R249
B
0256-7415(2016)11-0167-04
10.13457/j.cnki.jncm.2016.11.073
2016-06-09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308RJZE298)
葛健文(1955-),男,主任医师,研究方向:神经内科疾病及内科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马小军,E-mail:maxiaojun@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