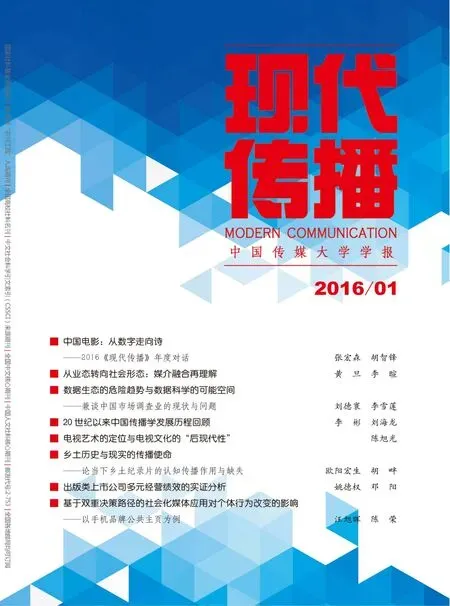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
■ 张志安 吴 涛
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
■ 张志安吴涛
【内容摘要】 伴随着互联网用户的激增和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新闻业的深层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互联网改变了中国新闻业的产业结构、受众结构、股权结构和权力结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生产实践的变革,呈现出生产主体从专业化到社会化、生产机构从封闭性到透明性、生产周期从周期性到循环性等变化趋势以及软性新闻主导的特点,使得在中国本就碎片化、局部呈现的新闻专业主义又面临新的重构挑战。而在新的重构过程中消解与促进、挑战与机遇因素并存,新闻业的公共性面临新的隐忧。
【关键词】互联网;中国新闻业;新闻生产;公共性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新闻业:变革与演进(1992—2012)”(项目编号:1209087)的研究成果。
过去10余年,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乃至重塑着中国新闻业。以新浪、腾讯等为代表的商业门户网站,以东方网、南方网等为代表的重点新闻网站,和以人民网、新华网为代表的媒体新闻网站,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传统报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危机,网络新闻业无论是用户规模还是媒体市值都相当可观。以整体的用户规模而言,根据CNNIC第36次报告,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68亿,中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25.6小时,网络新闻的用户规模达到5.54亿人,也就是有5.54亿人通过互联网获取新闻;从媒体市值来看,截至2015年6月15日,腾讯的市值已高达11480亿人民币,网易也高达1184.9亿人民币。
伴随互联网用户规模的扩大和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从产业结构、管理制度到生产方式,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中国新闻业的深层结构和整体生态。本文试图从新闻业的结构(structure)、行动者(agency)的生产实践、传媒的公共性(publicity)三个维度来总结和探讨互联网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
一、中国新闻业市场和权力结构的双重变化
新闻业的结构,包括用户结构、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和管制结构等不同维度,主要体现在市场和权力两个层次。互联网的日益应用和普及,使中国新闻业在结构层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互联网用户增长改变受众结构
受众结构的变化直接表现在传统媒体受众的减少、网络用户规模的增长,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趋向于“不看报纸、少看电视”的使用习惯,更加依赖通过手机、Pad等终端来随时随地的上网,移动网民规模日益扩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6次(CNNIC)报告显示,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年底的85.8%提升至88.9%。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趋完善、手机终端的大屏化以及手机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手机作为网民主要上网终端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为满足新型受众的移动化阅读需求,各大媒体纷纷发力移动互联网,推出大量新闻App。根据人民网研究院2013年1月对国内1486份报纸的统计显示,推出新闻App的有170家,占报纸总数的11.4%(1)。2015年,在澎湃新闻的引领下,传统新闻媒体更是掀起新一轮建设新闻客户端的高潮,并读、无界、上游、封面、猛犸、九派、南方+等纷纷亮相,据清华大学沈阳发布的《未来媒体趋势报告》统计,110家官方媒体中60%已拥有自己的客户端。
(二)互联网产业收入改造产业结构
从传媒产业的市场结构看,互联网已经远超报业,成为第一大传媒产业。2014年,互联网业务(包括网络加移动增值)规模达到传媒产业总体市场的47.2%,几乎占据了传媒产业的半壁江山,而传统报业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5.1%。(2)
自2012—2013年传统报业出现“拐点”以来,在互联网行业的猛烈冲击下,传统报业持续衰退,2014年更是呈现“断崖式”下滑局面。据清华大学发布的《2015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大趋势》显示(3),2014年全国报纸印刷用纸量约为270万吨,比2013年减少了近1/4,报纸发行量事实上下降了25%。作为传统报业收入主要来源的广告市场,也连续4年负增长,2014年的下降幅度达到15%,2015年报业广告则普遍下降20%以上,个别报纸甚至降幅高达30%。与传统报业广告市场的惨淡相比,2014年网络广告的收入规模则超过了1500亿,增长了40%。
(三)互联网产权突破改变股权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双轨制,产权结构比较单一,始终坚持国家控股。进入2000年以后,政府加快了传统新闻业融资政策、产权结构的改革步伐,允许报业集团上市进入股票市场,比如2004年12月《北京青年报》在香港上市,但仍规定非国有股权不得超过49%,以保持国家的控股地位。(4)此后,尽管陆续有粤传媒(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新华传媒(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等在国内上市,但报业集团的产权结构始终是国家主导。
但是,以腾讯、网易、新浪、搜狐为代表的IT企业,其创业资本主要来源是海外基金,加上在美国纳斯达克等海外资本市场整体上市,这些商业新闻网站的产权结构实质上已经突破了中国新闻业必须“国有”的传统。以腾讯为例,南非的两家外资集团MIH 和ABSA分别占有34.27%和6.32%的股权,以马化腾为首的创业团队占有剩余股权。考虑到商业新闻网站在当下中国新闻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某种程度上看,中国新闻业的“事业单位”的性质已被彻底改变,形成了传统媒体坚持国有、网络媒体国有与私有并存的全新格局。
(四)互联网管制体系改变权力结构
过去,报刊和广电的准入门槛和行政管理归口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而互联网业务的牌照多年来主要由国务院新闻办来管理,而整体的舆论导向皆由宣传部门主导。如今,互联网新闻业务的归口管理已经从国务院新闻办转至2011年成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办公室”。而且,随着网络成为舆论调控和管理的“重中之重”,2013年国信办与国新办正式分家,成为互联网的主要监管机构。加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已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总体上看,网络新闻业的监管呈现出集中化、升级化特征。
再具体到新闻审查的机制看,互联网新闻业跟传统新闻业最主要的不同有三点:第一,监管主体的“联动性”更强。由“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办公室”来主导,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参与协同治理,过去网络新闻业“多龙治水”的局面得以根本性改观。第二,管理权限更加集中。过去“互联网的管理规则虽然出自于北京,但是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管制规定,甚至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方性自治条例,结果在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很大的政策、法规、服务和价格的变异”。(5)现在,由于主流的商业网站和媒体网站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尤其在北京特别集中,由此导致网络新闻的监管呈现“属地化”特征,其监管效率更高。第三,“事先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强化。过去,传统媒体采取的是审看制、追错制,而网络媒体采取的则是过滤制、纠错制,主要体现在:建立防火墙,将脸书、推特等一些国外网站内容屏蔽过滤于国内网络媒体之外;采用关键词过滤技术,将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关键词和谐掉,使受众无法搜索到与该关键词相关的内容(6);及时有效地纠错,将出现问题的违法或敏感内容尽快删除乃至全部从网络上清除干净。据称,我国的互联网管制在5—30分钟内可以将接近30%的“违规内容”删除,接近90%的“违规内容”在发表后的24小时内会被删除(7)。总体上看,过滤制提高了新闻发布事先审查的效率,纠错制一方面能快速消除网络上负面、敏感信息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也给新闻网站在敏感议题上“打擦边球”提供了一定的机会。
二、传统新闻业生产变革与网络新闻业实践特点
Mitchelstein和Boczkowski(2009)指出(8):以往对网络新闻的研究中缺乏历史性视角,对于网络新闻业的研究需要超越新闻编辑室和新闻业的层面引入新的研究视角以便更好地理解“谁开始生产了网络新闻,生产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怎样的故事在这样的动力机制下被生产出来”。下面,我们试图引入一定的历史性视角,对传统新闻业与网络新闻业的生产方式进行简要对比,总结传统新闻业的生产变革和网络新闻业的实践特点。
(一)传统新闻业的生产变革
在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下,传统媒体利用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互联网技术平台对其已经形成的新闻实践“惯习”进行再造,通过流程重构、机制调整和形态融合等方式进行了显著的生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生产主体:从专业化到社会化
从行动者的角度来说,由于采集新闻信息的高成本,传统的新闻生产的行动者是由新闻组织机构雇佣的职业的新闻从业者(记者、编辑)进行,是一种专业化组织化的生产行为。而在“人人皆是记者”的互联网时代,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介入新闻生产领域,通过个人微博、微信等发布自己目击甚至调查的新闻。当下,“公民新闻”主要有三种形态:一是目击新闻,即重大事件目击者快速发布现场照片和滚动播报所见所闻;二是网络爆料,以知名爆料人周筱为代表,主要接受匿名消息源对公权力机构或官员进行网络舆论监督;三是社会动员,即普通公众为了激发网络情感、形成网络舆论而进行的“网络抗争”,其主要目的在于发起环保、维权等社会运动。再加上传统媒体对用户生产内容(UGC)的吸纳和整合,越来越多的公众有机会参与到原先的专业化新闻生产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业从专业化组织化到社会化生产的转变。新闻生产不再仅仅是一个专业组织的封闭生产形态或者机制过程,而是共同参与、协同生产的活动,新闻业的把关人逐渐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合作、广泛参与的方式进行新闻生产活动。
2.生产机构:从封闭性到透明性
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是相对不透明的,新闻生产被置于后台,很少有机会为公众所见。但在互联网语境下,新闻线索的发现、与信源的联系、阶段性报道的发布,使得新闻把关的控制过程更加开放、直接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在这种新闻生产“可视化”的新生态中,受众既可以了解新闻生产的过程,还可以频繁地参与互动(9)。由此带来传统媒体组织透明性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向公众说明”和“邀公众参与”两个层面,“透明意味着在新闻报道中植入一种新的意识,说明新闻是如何获得的以及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表达”。(10)比如:新闻行业的争议性话题,会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激烈讨论,强化了公众对新闻伦理和规范的认知;调查记者利用微博等进行采访突破,尤其当遭遇地方政府和官员阻挠时进行的滚动直播和在线动员,拉近了职业新闻人跟受众之间的距离;大量媒体人开设实名微博,利用微博等新媒体手段来服务于新闻生产、转载和发表报道……这些都大大增强了新闻机构的透明性。
3.生产频率:从周期型到循环型
互联网语境下,传统的截稿时间不复存在,24小时滚动循环成为常态。比如传统媒体在报道地震等突发性事件时,利用微博等24小时不断滚动发布地震救灾进展,并对已经刊发的纸质报道内容进行补充修订,突破了截稿时间的限制。为了保证24小时滚动循环生产的运行,媒体机构也必须在组织制度上做出相应调整,采用新的生产流程和考评机制。以人民日报的微博运营为例(11),报社将微博作为“独立的媒体”来运作,微博的发起、筹备、运营统一交由《人民日报》编辑采访的总枢纽——新闻协调部负责,打破部门限制,人民日报社的全体编辑、记者包括评论员都要参与到微博内容生产当中。生产频率从周期型到循环型的转变,使得针对重大事件的“直播”成为一种常态,而与之相对应,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也会显著提升。
4.生产资源:信息源结构的多元
传统的新闻生产,在信息源的筛选过程中,新闻记者主要靠日积月累的人际关系网从信息源那里获取新闻线索,而且对不同类型新闻线索的依赖和习惯背后是新闻作为社会建构的“框架”,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再现”。正如塔奇曼所言(12),“新闻从业者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信息源,而不是普通人提供的信息”,造成了政府部门官员、专家、精英人士更多地成为记者的信息源,出现在新闻报道中。遇到特殊情况,新闻记者则依赖于深喉等线人的报料,如水门事件。而互联网的兴起,至少从两个层面在改变传统的消息源权力结构。一是,机构消息源具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设置议题的能力,比如大量的政务微博(薄熙来案中济南中院的直播)、企业微博(农夫山泉和《京华时报》事件中的企业微博);二是普通草根的声音更多在网络新闻中占据明显位置,以及更多地被传统媒体的报道所吸纳。
5.生产压力:网络民意的影响扩大
过去,控制新闻的力量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商业利益和专业主义,受众的兴趣和需要主要通过市场化的商业驱动来发挥作用。如今,由于公众舆论在传统媒体的话语空间中很难生成,因此,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舆论场的核心平台,甚至中国的网络舆论已经呈现“微博化生存”的态势。
由此导致网络民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一方面,传统媒体的调查报道借助互联网迅猛传播,快速激发的网络民意和社会影响对公权力机关会造成监督压力,从而形成网络舆论监督和传统媒体批评报道的合力,有利于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另一方面,职业新闻人边进行报道,边进行微博直播、实时掌握网络民意。而整体上,相对民粹化、非理性、群体极化的网络民意对记者的价值判断和报道立场会产生负面影响。总结来看,网络民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是利弊共存的。
(二)网络新闻业的实践特点
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表现在传统媒体利用门户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互联网技术平台产生新的特点,还表现在以新浪、腾讯为代表的商业网站自身新闻生产所呈现的新特点。
1.从记者主导转向编辑主导
传统新闻生产的主体行动者是记者,主要负责现场采访和快速写稿,稿件编辑虽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审核、编辑和排版,但稿件的关键部分却受制于记者的供稿。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条例,新浪、腾讯等商业网站只有新闻编辑和刊载权,而没有原创新闻采访权,因而其生产主体主要是编辑。目前,网络新闻多数是非原创的,供稿来源主要还是传统媒体,编辑为吸引网民点击或扩大稿件影响,往往需要对标题做深加工。由此,传统新闻报道中记者主导的高成本原创被“复制/改编+聚合(草根新闻)+少数原创”的编辑主导所取代,记者在场的offline research(线下观察)被编辑不在场的online research(在线观察)所取代。网络编辑对新闻的选择、整合和挖掘决定了新闻产品的质量,以及能否吸引更多的受众,编辑的素质高低越来越多地决定了网络新闻的传播效果。
2.从作为产品到作为过程的新闻
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是由记者主导,严格遵循截稿和发稿周期,在规定时间内集中采集、合成和分发。新闻报道是社会化的产品,由编辑部主导,以中心化的机制一天一次刊发,实现一对多的单向传播。同时,新闻作为产品,衡量其优劣的标准主要是专业品质。网络新闻则不同,依托海量、开放的发稿平台和聚合空间,商业网站的传稿和发稿不再有严格的截稿时间,可以实现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滚动发布和即时更新,制作和发布的新闻专题也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动态进展而不断更新和补充,作为过程的新闻可以只有开始、永不结束。此外,基于相对平等和开放的公众参与性,网络新闻具有内在的“去中心化”的偏向,其传播和扩散由链接促发,是一个不断整合、加工和添加的动态过程。
3.新闻生产的偏向从硬变软
传统新闻生产的新闻内容以整体、深度、一次性、文本性的方式呈现,在新闻形态上强调事实至上,在新闻价值上崇尚由快至深,不断逼近真相的努力和公众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使其对“硬新闻”的社会意义更加看重。对于网络新闻生产来说,其对用户需求的满足、对技术表达的注重、对点击量的追求,使其在新闻形态上更加重视视觉至上而非事实至上。由于娱乐化、碎片化、视觉化的文本,最适合通过移动互联网的载体和工具进行发布和传播,也最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爆炸式、病毒式的传播效果,所以商业网站的新闻内容逐渐趋向速度而非深度、强调体验而非质量。
总体上看,伴随着网络新闻的日益规模化和主流化,软性新闻业(soft journalism)开始兴起,具体体现在从传统的提供公众需要的(needed)转向提供公众想要的(wanted),从硬/软兼顾的公共利益偏向转向逐渐偏软的用户兴趣偏向,从读者口碑驱动的质量至上评估转向用户点击率驱动的影响至上标准,其背后是商业主义的强化和专业主义的弱化。
三、社会控制的新趋势与传媒公共性的隐忧
我们探讨互联网对中国新闻业的整体影响,归根结底要回到两个关于新闻业的核心问题:自主性和公共性。前者强调的是新闻生产的独立性,即互联网能否为中国新闻业“赋权”,创造更大的报道空间和传播自由;后者追求的是,在转型社会的中国,新闻业能否在更大程度上承担其公共责任,以更好的公共性来服务和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总体上,从社会控制的新趋势和互联网新闻业的公共性角度看,值得关注的变化和趋势主要有三点:
(一)过度的商业控制导致专业伦理的失范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传媒市场化,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媒体的“自主性”发挥着“解放性”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将媒体在拉向市场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为受众服务,并通过调查报道和深度时评等实践舆论监督、进行公民启蒙和推动社会进步。但过去10余年,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正在都市报、电视娱乐节目等方面体现出利益至上、过度煽情等商业主义的问题,市场化所扮演的“压制性”的消极作用,正在逐步体现出来,同时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网络新闻实践中。因此,对过度市场化的反思正成为审视网络新闻业的重要命题。如有学者指出:“媒体的市场化进程培育了一种新型的媒介—受众关系,使得媒体更倾向于对受众的市场需求做出回应。媒体的改革使得中国的新闻业从意识形态到专业主义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从毛时代的政党—媒体模式转变到改革时代的市场—受众模式……互联网更是加速了这一模式转变的进程。”(13)
从新闻生产的自主性看,互联网行业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促使传统媒体在转型和自救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采取“事业部制”、实施整合营销等理念和做法,从而导致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之间的“防火墙”崩塌,由此,对新闻生产的专业原则和独立性产生极大损害。而以商业网站为代表的网络新闻编辑部,尽管在吸纳用户生产内容(UGC)和探索原创新闻报道上有一些专业主义的努力,但整体上,受制于“市场导向新闻业”的公司文化驱动,其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和自主性整体上均比较弱。而且,这些商业公司运营新闻网站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直接盈利或服务于公司的品牌和利益,而非通过披露真相来满足公众利益,因此资本力量主导下的商业控制会对编辑部产生更加严苛的约束机制,甚至导致新闻网站实际上扮演着商业公司的“公关部”的角色。
此外,新闻寻租、有偿不闻等伦理缺失也是网络新闻业让人痛心疾首的现象。据媒体报道披露,不少商业网站的财经频道通过对准备IPO的企业进行报道,抓住和放大企业存在的问题,通过敲诈勒索来获取高额广告或“封口费”;一些商业新闻网站内部存在“大客户保护名单”,只要大企业每年给网站投放一定额度的广告,网站就可以协助这些大企业屏蔽负面新闻,这种“有偿不闻”的做法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极大伤害;一些侵犯公民隐私权、名誉权的新闻或“爆料”,在网络上被轻易地广泛传播,而相关的把关机制却形同虚设……这些专业伦理缺失的现象,在当下和未来的网络新闻业可能会愈演愈烈。
(二)政治控制的内化导致自我审查的强化
一方面,传统的行政管理和权力控制,无论对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的影响都在不断加大。伴随着互联网监管力度的强化和管制结构的调整,对网络新闻的监管和舆论治理正在走向“行政化”和“法制化”合力的趋势。另一方面,外部政治控制的强化,再辅之以关键词过滤和审查技术的不断升级,导致网络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笔者关于网络新闻从业者的一项调查显示(14),对“新闻网站编辑记者应当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的信息”的态度上,受访者的得分均值为3.07分,倾向于较为肯定。可见,网络新闻从业者面对行政控制的压力感知比较强烈,外部政治控制容易内化,致使其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主动规避风险。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15),即便是比较善于突破的调查记者群体,在强有力的权力管控和组织规范之下,调查性报道生产过程中自我审查普遍化,调查记者主要通过使用微博等互联网技术提升新闻生产效率,进行新闻突破、社会动员乃至职业抗争只是非常规情境下的极少数偶发事件而已。
(三)网络舆论的极化导致公共空间的弱化
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对媒体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由民意造成的社会压力往往只有在极端事件中才能引发,常规新闻生产中记者和编辑部受到民意的影响并不大也不直接。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以论坛、博客、微博为主的平台给网民提供了活跃的表达空间,由此也容易针对热点事件形成汹涌的网络舆论。不过,当下的网络舆论场却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由于敏感言论的有效管制,导致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公共事务的意见无法充分表达,致使网络舆论对真实民意的体现有所不足;由于公民社会的不成熟和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局部失控,导致网络舆论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倾向明显;由于微博等技术平台碎片化、爆炸式传播的特点和效能,导致事实和观点的割裂、难以在网络上形成真正持久的深入对话,因而也难以形成理性的社会共识;由于“结构性怨恨”和“普遍不信任”的社会心理机制,网络舆论很容易走向“群体极化”甚至“对抗性”文化的方向。
尽管财新网等少数专业性的网络平台,尝试在每条新闻下方将本站跟帖、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等不同渠道的评论“抓取”在一起,试图建立一种基于事实基础上观点表达的互动机制和表现形态,但这种在提供准确真实事实、汇聚不同渠道的言论方面试图推动理性网络空间形塑的努力,总体上仍然非常稀缺,其作用也相对较小。基于网络舆论的分化、舆论的割裂、舆论的极化等上述特点,很难真正从理性、积极的方向持续推动中国新闻业的进步和发展,相反,可能会导致作为传媒的互联网变成更加弱化的公共空间。
四、结语
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从未像西方新闻业一样“已经形成了阐述这些专业特征和理念的一套话语,并且有相对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专业规范机制”(16),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是未完成的进行时。当下,在互联网重塑中国新闻业的整体语境中,本已局部化、碎片化呈现的专业主义又面临新的重构可能,其中既包含着有利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因素,也包含着不利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因素。从行动者如何影响结构的角度看,无论是传统媒体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新闻生产实践,还是商业网站自身的新闻生产,以记者编辑为代表的职业新闻人和以草根新闻为代表的普通公众,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直接影响着新闻专业主义建构。
首先,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原则,主要是针对职业新闻人而言的。网络新闻生产实践中,职业新闻人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职业新闻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把关人角色,而是利用博客、微博等互联网技术工具试图超越它”(17),在传统媒体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新闻生产实践中,职业新闻人“参与者”角色在不断强化。在大量公共事件中,记者利用微博进行的在线报道和网络动员,增强了其直接参与事件的几率和风险,由此对其“记录者”的专业角色造成偏差。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参与者”的角色使得职业新闻人自身的情感和情绪很容易被表达出来。这种将自我置于新闻的中心舞台,将情绪裹挟在新闻报道中的倾向,容易产生如石扉客所概括的“社运型”记者现象(18);二是在商业新闻网站新闻生产中,作为职业新闻人的网站编辑,过度迎合公众对视觉、娱乐、煽情新闻的偏好,生产和推送过度碎片化、娱乐化的软新闻,造成网络新闻“标题党”现象盛行,使得商业主义驱动的生产机制完全主导,而新闻专业主义则更加缺失。
其次,普通公众在网络新闻业的专业主义建构中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他们既是职业新闻人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效助力,也以一种去“专业化”话语挑战着职业新闻人对传统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和对自我作为职业权威的捍卫。一方面,普通公众已经更加广泛地参与到新闻生产实践中。他们的参与扩大了新闻报道的空间,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内容,也改变着传统的消息源权力结构,有助于职业新闻人摆脱对于体制内信息源的依赖。另一方面,新闻作为“一种诠释现实的权力实践”,在传统媒体时代,原有的新闻场域是由组织内的新闻专业人士主导确立的,而在互联网语境下,这种诠释现实的权力实践和话语权威正面临普通公众发起的严峻挑战,比如:技术赋权使得新闻生产工具资料社会化、全民化,专业人士面临场域内新入者、即普通公众的激烈竞争;过去,新闻从业者依靠专门训练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及与大众绝缘的方式获得专业资本,如今在改编、复制和聚合为主的网络生产模式之下,传统新闻专业的核心能力被边缘化(19);大众不仅能够通过市场对新闻加诸间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参与干涉新闻生产,职业新闻从业者在新闻场域内的专业资本在缩小;此外,网络民意汇聚形成的“去专业化”话语要求新闻业体现与普通公众的联系,既要代表公众、反映底层人民的疾苦,又要参与社会行动、帮助底层人民解决实际问题(20)。于是,大量的网络传播实践都采取了情感宣泄、反讽戏谑、悲情化、标签化等话语方式,这种易走向极端化的、去专业化话语,不仅与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客观性”格格不入,而且在专业话语和去专业话语之间也很难形成理性对话的空间。
回到社会控制新趋势和传媒公共性的关系,我们大体可以这样总结互联网对中国新闻业的结构性影响:其一,政治权力的强势介入和有效监管,未能为互联网新闻业带来比传统媒体更大的报道空间和独立性;其二,市场驱动的利益短视和逐利倾向,导致互联网新闻业很难在商业网站建立专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品质追求,整体上的煽情主义、商业主义影响了网络新闻的品质和水准;其三,互联网技术的传播赋权和信息突破,给少数公民和机构带来了提升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机会,但非理性的网络舆论又可能会对新闻生产的自主性造成负面影响,“去专业化”的话语也会导致职业新闻人的自我认同感趋于弱化。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中国新闻业面临着“双重尴尬”:一方面,在传统媒体时代,专业主义的启蒙和共识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碎片和局部的新闻专业主义又面临新的重构,而在新的重构过程中消解与促进、挑战与机遇因素并存。未来中国新闻业的走向,需要媒体管理者在宏观政策上有更积极的改革、机构所有者在组织制度架构中有更合理的设计,以及新闻从业者在生产实践中有更专业的追求和更理性的自觉。
(本文为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的成果之一。)
注释:
(1) 唐绪军:《中国新媒体年度报告(2013)》,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2) 参见《2015年中国传媒产业报告谁才是赢家》,来源:http://www.yejibang.com/news-details-10779.html,2015年7月2日。
(3) 中国社会科学网:《清华大学研究报告:2015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大趋势》,来源:http://www.cssn.cn/dybg/dyba_wh/201506/t20150615_2035014_9.shtml,2015年6月15日。
(4) Stockmann D.Race to the Bottom:Media Marketization and Increasing Negativit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11,28(3),pp.270.
(5) Yang G.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Preliminary Assessmen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03,12(36),p.457.
(6) King G,Pan J,Roberts M.E.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3,107(02),pp.326-343.
(7) Tao Zhu、David Phipps、Adam Pridgen:The Velocity of Censorship:High-Fidelity Detection of Post Deletions,//22nd USENIX Security Symposium.2013:11.
(8) Steensen S.:Online Journalism and the Promises of New Technology:A Critical Review and Look Ahead.Journalism Studies,2011,12(3),p.321.
(9) 周葆华:《从“后台”到“前台”: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总第25期。
(10) [美]比尔·科瓦奇:《新闻业的十大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11) 涂光晋、陈敏:《媒体微博的内容特色与生产机制研究——以三家报纸的官方微博为例》,《现代传播》,2013年第3期。
(12) [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3) Tai Z,Sun T.Media Dependencie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the Case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in China.New Media&Society,2007,9(6),pp.991-992.
(14) 张志安、陶建杰:《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审查研究》,《新闻大学》,2011年第3期。
(15) 吴涛、张志安:《调查记者的微博使用及其职业影响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6)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1期。
(17) Yu H..Beyond Gatekeeping:J-blogging in China Journalism,2011,12(4),pp.379-393.
(18) 石扉客:《“社运型”记者的特征和行事边界》,《南方传媒研究》第30期,http://www.southcn.com/nfdaily/media/cmyj/30/04/content/2011-07/01/content_26239520.htm,2011年7月1日。
(19) 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伦理和评价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新闻记者》,2013年第2期。
(20) 谢静:《民粹主义:中国新闻场域的一种话语策略》,《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
(作者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吴涛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公共传媒管理方向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