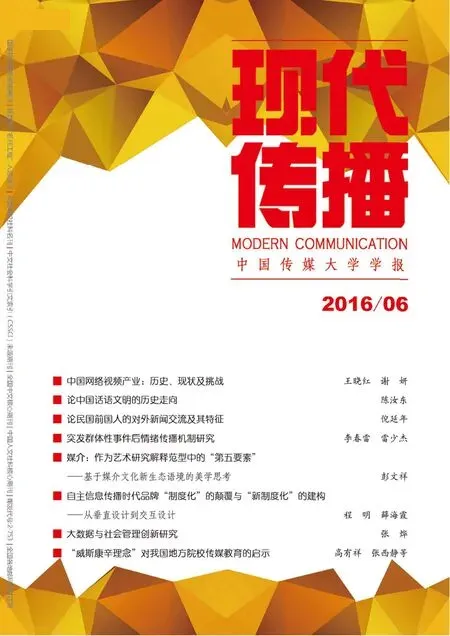论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
■ 朱奕亭
论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
■ 朱奕亭
口述是最古老的历史言说方式,从“口头传述”到“口述历史”,历史的传承方式从文字记录发展到影像传播。近年来,以“影像”为书写方式的口述历史节目在电视荧屏上大放异彩,《口述历史》《大家》《我的抗战》等节目的热播见证了史学与影像的融合。经过电视媒介的包装和拓展,口述史突破了精英和文字的双重限制,成为可听、可视的大众化的影像文化,为受众带来“身临其境”的历史体验。毫无疑问,影像的介入使口述历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形成一道独特的电视文化景观,而这种“转向”背后的原因、意义及随之而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影视艺术、历史学及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从三个方面探讨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
一、转向:历史记忆的影像表达
让克丽奥(Clio,历史女神)走向坊间,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民众的呼唤。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非印刷文化”①,因此,人们不再单一从纸媒上认知历史,而更倾向于在丰富多彩的影像空间寻找记忆。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主要通过录音、摄像、电视、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来实现,它大大拓展了传统史学的叙述范围,使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变得触手可及。摄像技术的普及为口述历史活动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使得口述史向影像传媒的转变成为可能。
从思想源流上看,影像史是由“新史学”孕育而来的。新史观主张“自下而上地看历史”,从精英中心转向关注草根民众,以个人命运来折射社会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话语权”意识逐渐觉醒,大众传媒开始将镜头转向普罗大众,并利用“口述历史”这种颠覆性的治史方法来丰富历史影像。事实上,“口述历史类电视节目正是史观变迁在媒介生产领域的一种表征”②。比如,纪录片《我的抗战》聚焦抗战时期的普通人,透过个体的生命故事展现特殊的社会背景,通过电视媒介将话语权赋予零散多元的个体,使得“小写的历史”进入公共领域。小人物、小道理登上历史舞台,这打破了上层社会对话语权的垄断,使平民百姓通过电视亲近历史,解读历史。
此外,口述史与影像媒介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正如马克·费侯所言,“以历史的观点来解析影像,或以影像的叙事策略来解释历史”③,历史与影像是彼此互惠的。一方面,历史有助于拓展影像的意义空间,历史题材使得电视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影像能够弥补文字描述的不足,真实生动地再现历史原貌。主人公在口述历史时,会伴随着表情、神态、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影像以视听手段再现当时的情境,完整地捕捉历史记忆和细节信息,让受众感受到叙述者的情感变化。此时,原生态的口述史与电视观众追求真相的需求不谋而合,历史记忆自然而然地实现其影像转化。
二、融合:历史的艺术再创造
口述历史与影像的结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录在案,它有“更高的意图”——把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艺术再创造。④“有机”是指两者相互碰撞,激发出全新的艺术魅力,此时,影像不再只是一种记录工具,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意义。
其一,全息式的历史场域的建构。口述史一向强调鲜活性和互动性,历史的影像书写建构了一种近乎全息式的历史“场”,营造一种重回历史现场的特殊感受。所谓“场”是电视纪实语言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指一个场面内相关事件、行为的动态关系,以及形象、声音、环境、心态、情感等共同积累出一个丰厚多元的信息时空。《往事》《大家》等纪录片就是这种艺术再创造的产物,多元话语的记录、群像面孔的展现,口述者的语调、眼神、表情、姿势等多种视听元素的融合,消除了影像与真实生活的间隔,消解了“不在场”的矛盾,打造出立体真实的审美艺术。
其二,个性化、故事化的表达。受新史观的影响,口述历史摆脱了宏大叙事,转而关注小人物的个体生命记忆,通过记录一部分被掩盖、遗忘或缺失的历史,来丰富整个社会历史图景,这种讲述带有浓厚的个性色彩。比如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节目选取的口述者主要是某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有着独特而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或喜或悲、或光明或灰暗……片中常常是主人公绘声绘色地讲述个人经历,真实地流露个人情感。这类影像作品充满故事性和人情味,使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其三,“群言”与“群像”的多元复合。口述历史“通过两种途径给人传达信息,一个是视觉,完全靠阅读当事人的面孔来获得信息,另一个则靠当事人的话语来判断文字,来获得文字的具体的所指”⑤。显然,“群言”是由差异性个体的讲述建构“众声喧哗”的话语空间,形成观众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多元认知,而“群像”则是汇聚叠合多种感受,观众经过自我分析得出最贴近历史真相的认知。当下的口述历史节目大多采取“多点探析法”,选择不同的人物进行讲述,这使得史观的表达不再是片面的“一言堂”,而是全方位完整地展现客观原貌,进一步增强影像艺术的真实性。
三、困境:“影像转向”带来的思考
如上所述,口述历史依托影像媒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多元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然而,在当前功利而喧嚣的媒介生态格局下,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遭遇新的瓶颈。
首先,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大众文化的狂欢与历史真实的隐退已成为一个普遍问题。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口述历史纪录片中获取历史认知。为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口述历史节目以多元化、故事性的影像表达来制造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实现更高的收视效益。此时的影像空间,娱乐性多于严肃性,感性宣泄多于理性记录,群众的“口述”俨然成为一场话语狂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狂欢式的影像表达消解了历史的真实性,阻碍了观众通过媒介来认知和解读历史,也削弱了节目在历史建构方面的意义。
其次,口述历史的主体更加复杂化,话语权的下放使得不同观念相互碰撞,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在场叙事与个体记忆不可避免地走上异化之路。一方面,口述者在媒体面前,受“霍桑效应”的影响而带有“表演”性质,有意夸大或遮蔽某些历史细节,使“真相”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口述者的讲述受到记忆、情绪、文化等的影响,所呈现的历史是他们选择的“脑海图像”,其真实性亦让我们无从考究。由于“口述记忆的内容是不完整的、有限的、流动的、易逝的、未定型的、不稳定的”⑥,通过个体记忆进行补充的历史文本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不可忽视的是,口述历史的影像转向有赖于视像艺术的革新,如何将口述史转变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态,是影视行业一直以来探索的问题。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导演的专业水平、摄像团队的能力、后期剪辑制作的技术等因素都影响着“转向”的成功与否,从而制约对“过去”的建构。而今,虽然不乏《我的抗战》这样精良的团队,但影像的成功输出离不开每一个环节的精心制作,这就对我国的人才和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综而观之,口述历史作为历史与影像联姻而生成的艺术形态,其在场性、故事性以及草根的价值取向,拓展了历史文化的意义空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探索色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影像历史的建构并不全然是理想化的,它受到大众文化、个体记忆及传播技术的制约。因此,如何摆脱困境,追求历史真相与传播效果的共振,实现口述历史与其他媒介记忆的互构,从而丰富和发展口述史的影像空间,这一问题值得学界与业界共同探讨。
注释: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② 蔡骐:《影像传播中的历史建构与消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法]马克·费侯:《电影与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3页。
④ 赵蕊:《影像·记忆与认同——口述史纪录片的历史真实》,《电影文学》,2013年第9期。
⑤ 肖平:《“过去的声音”:一个说者的视角视点及其影像写作》,《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⑥ 陶涛、林毓佳:《口述历史:在回忆中制造过去》,《现代传播》,2015年第6期。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责任编辑:李 立】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口述历史的影视传播”(项目编号:13YBA23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