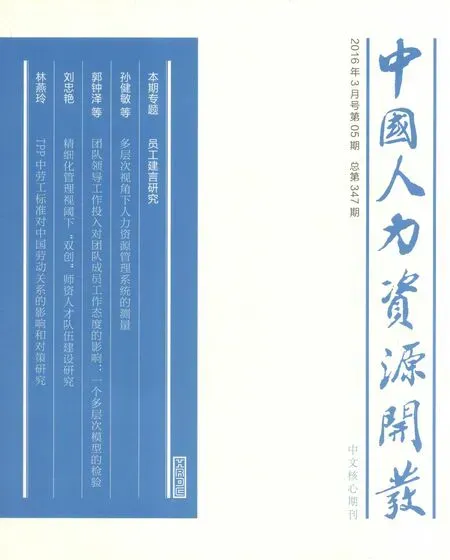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机制及其反思
● 何伦坤
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机制及其反思
● 何伦坤
内容摘要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机制是指国家基于劳动争议多发化、群体化的维稳压力,运用政策手段,对多元化、社会化的调解机制实施国家统合的结果。该机制整合不同调解资源,形成调解合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劳动争议的控制。但是由于过度追求维稳功能、以国家代社会,损害了调解的本质属性,模糊了不同调解机制的界限,阻滞了国家与社会并治的多元劳动解纷模式的建构。矫正该机制的不足,应坚守开放式、社会化、多元化的基准思路,坚持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解纷思维,着重加强调解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着力培育民间调解机制的权威基础。在此基础上,秉持“多元、效能、竞争、开放”的原则,针对不同调解机制的特点和不足,采取具体化对策,做强做大劳动调解体系。
关 键 词劳动争议 联动调解 国家统合 弊端 对策
何伦坤,重庆文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电子邮箱:helunkun@126.com。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5YJC710071)资助。
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机制是在“大调解”构建背景下,一些地方为应对劳动争议的多发化、群体化,通过政策手段,对以往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等多元调解予以整合,而建构的一种多部门参与联动的新型劳动大调解模式。从实践来看, 该模式已逐渐被推广,理论界和实务届对其点赞较多①,但对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不利于劳动调解体系的理性发展。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反思的立场,通过解析联调机制的演进,深入剖析其运行中的弊端,在此基础上建构重塑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公正性、规范性的基准思路和具体对策,做强做大多元调解体系,促进劳动争议的及时有效化解,维护劳动关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机制的演进及其特点
从实践看,作为一种新型的大调解模式,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机制是伴随劳动关系市场化、多元化,劳动争议的多发化、群体化而逐步建构起来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企改革、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劳动争议不断增多,国家就开始引导用人单位建立以基层工会为主导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就近及时快捷化解劳动争议,其专门法规为1993年《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后随着劳动争议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企业劳动调解委员会的实效不足,国家于2007年出台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专门法律的方式,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之外,又赋予“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乡镇街道具有调解职能的调解组织”之法定调解者角色。2009年人社部《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又进一步将“乡镇街道具有调解职能的调解组织”明确为: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站)调解组织,工会、企业代表组织设立的调解组织,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双方代表组成的调解组织。这可以视为劳动争议调解机制的首次做“大”,其核心标志是将单一民间调解(企业调解)拓展为开放性的多元民间调解模式,重构了民间调解与官方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的地位,使得民间调解的地位显著提高(王全兴、林欧,2012)。这表明随着社会矛盾凸显、劳动争议多发,国家挖掘社会资源,着力发展多层次的民间调解机制,以弥补国家强制解纷资源有限性的思路。
但实践显示,这种多元化、社会化的努力并没有达成预期效果,调解机制分流劳动案件的能力有限,仲裁、司法的压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且由于矛盾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大规模劳动群体性事件频发,劳动争议从经济问题逐渐向危及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演变,劳资纠纷也逐步成为社会冲突的首要问题②。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为了应对日益激增的劳动争议,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的多元化、社会化调解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政策资源,对不同性质的调解机制及其背后的组织机构进行统合, 形成多部门参与、相互衔接配合的一体化联动调解体系。和以往分散的多元调解体系比,联动调解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以国家力量,对以往彼此分割、各自为战的多元调解机制一统化,强化调解的合力和国家权威性。即通过地方党政主导,运用政策手段,将从属于不同权威的“行政调解、企业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解、”等多元异体的调解机制,整合为多部门参与、彼此紧密结合、协调互动的一体化联动联调工作平台。有些地方,如广州市、江苏南通、上海金山等甚至设立了实体性的联合调解中心,实施联合办公,联合接案,联合调处。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由于主导机构、参与力量不同,联调机制又存在多样化的形式及组织结构模式。比如,宁波北仑区的党政主导、总工会牵头,人社局、司法局、信访局、法院等参与的联合调解中心模式;北京市的党委领导、市总工会牵头,社保局、司法局、信访办、高院、企联参与的六方联动机制;四川省的省高院主导,省总工会、人社厅参与的三方联动调解机制,以及山西省的人社部门主导,司法行政部门、工会、企联(企协)参与的联合调解模式,等等。
其次,强调调裁对接、调审对接,大力实施仲裁庭外联调、法院诉前联调。仲裁机构对未经调解组织调解,直接申请仲裁的案件,应引导当事人到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组织调解。人民法院要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坚持调解优先,在受理阶段,积极委托工会、调解组织等先行调解,在审判阶段可以邀请调解组织成员,协助人民法院调解,尽可能以调解方式结案。
其三,积极引导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实施仲裁置换和司法确认,强化调解协议的强制性效力。所谓仲裁置换,即对民间调解协议经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依法审查,可置换为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的仲裁协议。其主要规范是《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第27条。所谓司法确认,即对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经法院审查、确认,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其主要规范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解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及2011年《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这种间接赋予调解协议国家强制力的做法表明,劳动争议调解实效的力量源泉还在于国家性权威,而非社会权威及当事人合意的伦理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在劳动争议联调机制构建过程中从促进者、培育者向统合者蜕变的角色逻辑。一方面,面对日益暴增的劳动争议,国家理性认识到,在国家解纷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培育以社会权威为依托的民间性劳动调解机制,以缓解国家机制的压力,促进劳动纠纷的快速化解。但是由于多元化、社会化调解体系权威性、有效性难以确立的严峻现实,无法实现“以调解方式化解大部分劳动争议”的目标。这又迫使国家放弃社会化、多元化的建构思路,向国家回撤,利用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对原本分散、多元并行的调解机制整合,使之一统化、国家化,试图以国家权威的加赋对调解机制“强筋健骨”,从而提升调解的实效性和权威性。一体化的联动调解体系的国家统合,在事实上淹没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的社会化、多元化调解机制的建构思路,使得多元民间调解机制被国家化、行政化。从动因上看,国家这种前后逆转的逻辑主要基于劳动争议多发化、群体化产生的维稳压力。
二、检讨与反思:劳动争议联动调解机制的弊端分析
尽管实践显示,劳动争议联调机制,通过整合不同调解资源,实施多方衔接联动,注入国家元素,提升了调解机制防控劳资冲突的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地方在建构、实施劳动争议联调机制后,劳动仲裁、诉讼受理的案件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但是,深入检视,联动调解并没有真正达成案结事了、化解劳动争议、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甚至造成了新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广东在建立联调机制之后,反而在2011年、2012年出现了多场大规模的民工骚乱(庄文嘉、岳经纶,2014)。这说明以国家统合为基础的联调机制,虽能借助国家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提升调解机制的权威,但由于过度强调国家统合,过于追求维稳目标,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
首先,过度强调“调、裁”衔接和“调、审”衔接”,变相延长了劳动争议处理的链条,加重了劳动者维权成本。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机制彼此独立、各自终局化解劳动争议,是多元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设计的理想目标。但联调机制过度强调“调解与仲裁、诉讼”的衔接,要求仲裁委员会对未经调解组织调解而直接申请仲裁的案件,和已立案但认为可以委托调解的案件,通过《调解建议书》或委托调解的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基层调解组织调解;要求法院按照调解优先的原则,对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劳动案件,在立案前或立案后未开庭审理阶段,积极通过委托调解、邀请调解、联合调解等方式,尽可能予以调解结案。③这种反复调解、过度调解的做法,不仅有拒绝裁判之嫌,而且变相将选择性的调解机制运作为强制性程序,成为仲裁、诉讼的前置,从而在“法外”将“裁→审”机制异化成“调→裁→调→审”机制,在事实上大大延长了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链条,增大了劳动者维权成本。这种以国家力量推行的过度“衔接”逻辑不仅违反了调解、仲裁和诉讼之间的法定程序,而且悖离了多元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效率要求,必然导致调解在实践中被劳动者抛弃。
其次,过于追求调解的维稳工具价值,损害了调解的公正性、规范性和合法性。从劳动者视域来看,选择调解机制的主要动因在于,利用其自愿、灵活、柔性特点,更快、更经济的救济自己的劳动权,并维系劳动关系。而联调机制的国家统合逻辑,旨在利用调解的程序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快速化解劳动争议,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目标。在维稳目标的驱使下,各地在运作中不可避免地忽视调解的规范性、公正性,侵害劳动者在调解中的自主选择权和自主决定权,强制调解、胁迫调解屡现,由此导致调解机制在维稳与维权关系的内在紧张。比如一些地方,为实现调解结案,采取夸大仲裁(诉讼)风险、威胁性劝导等各种手段,强迫劳动者调解,并且在结果上,将劳动者的法定权益大打折扣,胁迫劳动者接受,以实现劳动争议的快调快处(郑广怀,2010)。有些地方,“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的维稳观,已成为各类调解组织(甚至法院)及其人员调解劳动争议心照不宣的指导思想。在此背景下,调解的维稳目标也就自然压倒了维权。
而现代调解是一种以法治、自治为基础的,注重将程序公正、实体公正贯穿始终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它不仅追求结果层面的“纠纷解决”,更关注纠纷的解决是否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决定,是否实现了当事人在法制上的权利和义务。它不过分强调当事人通过牺牲自己的权益来苟且求得对纠纷的和平解决(汤维建,2009)。而如前所述,联调机制的国家统合逻辑,强调调解的维稳工具价值,追求调解的社会控制功能,必然导致对劳动者法定权益的压制,悖离现代调解机制的合法性、自愿性等根本原则,最终必危及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也正是“大调解”实施后,一些地方的劳动争议出现越调越乱局面,以及全国法院系统劳动争议受案率不降反升的一个重要原因。④
第三,过分强调国家整合,模糊不同调解机制的异质性、独立性,不利于国家与社会共治的多元劳动解纷机制的生成。作为一种替代性解纷机制,调解是一种依托社会资源的自治性解纷机制,具有非国家、非强制的特点。因此,调解机制的体系做大和实效做强,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源的增加、社会权威的培育和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
而劳动争议联调机制的统合逻辑,通过加载“党政领导”、注入“国家强制”、连接“国家权威”,着力将原本从属于社会的人民调解、企业调解、行业调解与从属于国家的司法调解、仲裁调解,整合起来,使之彼此借力、互相混同,成为一体。不仅造成其中的民间性调解机制(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工会调解、协会、商会调解)向国家靠拢,其社会性、自治性等本质属性不断褪色,其背后的社会权威的成长受到抑制,引发国家对社会的吞噬;而且,另一方面,还模糊了司法与调解机制的差异性、独特性,损害司法的基本价值,最终不利于国家与社会共治的多元劳动解纷模式的生成。比如,一些联调机制明确要求法院发挥司。
法能动性,积极探索诉前联调,推动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室,与人民调解委、工会等调解组织对接,更多通过调解方式快速化解劳动争议,服务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贯彻调解优先的原则,法院系统内部通过设置调解结案率考核指标等司法管理手段,勒令各级法院调解。还有些地方,为应对群体性劳动争议,甚至要求法官走出法院、法庭,赶赴劳动争议现场,与政府职能部门、司法所、街道办、人民调解委沟通交流,实施联动调解,稳控局面。这种片面、过度追求调解结案的做法导致司法裁判功能下降,角色错位,司法的被动性、裁判性、终局性等本质属性由此被颠覆。此外,在我国调解协议普遍基于劳动者非完全自愿地作出低于法定底线利益让步而达成的现实背景下,联调机制要求积极“引导”(实践中在一些地方已经异化为“强制”)当事人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不仅在事实上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而且还可能将调解过程中并没有化解的劳资对立,转化为劳动者与司法权之间的对立,从而进一步损害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而依法治原则,司法作为纠纷解决的“底线”,事实上承担着对调解协议监督审查的责任。如果法官在劳动争议处理中,常常以调解者的身份主动介入,甚至与工会、劳动部门一起联合“坐堂”调解劳动争议(汤碧琴,2010),司法作为劳动争议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将失守。当作为“底线”的司法出现信任危机时,劳动者只有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比如暴力、跳楼、堵路、罢工等尖锐激烈的方式抗争维权,引发社会震荡,劳资矛盾反而扩大化、政治化。
三、矫正与重塑:做强做大劳动调解机制的基准思路和具体对策
基于上述检视,劳动争议联调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危及了其正当性,不利于劳动争议调解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应予以矫正。其基准思路是:首先,应坚守《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确立的开放式、社会化、多元化调解机制发展方向,祛除联动调解的国家统合思维,变统合为培育和规范,尊重不同调解机制的特质,维持调解机制的多元性、独立性、竞争性,确保不同类型的调解机制在各自的轨道上发挥自己的优势价值;其次,加强调解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着重塑造调解机制的自治性、公正性、合法性,⑤杜绝强制调解、胁迫调解;其三,摒弃以国家代社会思维,坚持国家与社会并重并治的劳动解纷机制理路,着力培育调解体系中民间性多元调解机制的社会权威基础,提升其实效性,使之成为劳动大调解体系的支柱。在此基准思路的指导下,秉持“效能、竞争、开放、规范”的原则,分别针对不同调解机制的特点和不足,采取具体对策,做强做大多元劳动调解机制。
第一,强化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化能力建设。尽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人民调解组织加载了调解劳动争议的法定职能,但由于传统人民调解的特点是乡土性、情理性,而非法律性。其化解解纷主要仰赖调解人员的威望、情理技术、熟人社会的人情因素,而非专业化知识和技能。使得传统的人民调解在面对专业化、复杂化的劳动争议时,力不从心。这已为人民调解较低的劳动争议受案率所证明。尽管人社部曾提出,到十二五末期,50%的劳动调解员要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王永,2011)。司法部也于2010年下发《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意见》,要求加强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但由于缺乏专门性制度保障,这些目标远没有落实。为此,当下应该以落实2015年人社部《关于加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为契机,抓紧制定专门性的《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争议专业能力建设办法》,明确、固化建设责任主体,健全工作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完善人民调解员选聘条件和考核制度,加大培训力度,落实培训经费,提升人民调解员的劳动法规知识水平与能力,从而做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劳动调解专业能力。
第二,做实企业调解,做大行业调解。企业调解最大的优势在于贴近劳动一线,能够就近快速化解劳动争议。但是,由于企业工会的单位主导、独立性差,以及缺失第三方性,导致实践中企业调解基本失灵。这也是理论界主张废除或将其改造为劳资协商委员会的原因。但是,国家在“大调解”体系建构中,仍然
将其作为重要机制予以塑造。这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中体现明显。因此,应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针对企业调解的缺陷,一方面,通过强化企业代表组织、地方工会以及行业性调解组织,对企业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培训和监督,以提升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从根本上看,应着眼于企业工会的体制弊端,通过民主化改革和集体劳权建设,从根本上建构工会代表性和行动能力,从而增强工会在劳动争议调解中的话语权威。
行业调解主要包括行业工会调解、行业协会(商会)调解组织,及以行业工会与行业组织联合设立的调解组织。相对于企业调解,行业调解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超脱性,权威性较高。相关数据也显示,行业调解的调成率远远高于企业调解(尹民生,2012)。这表明行业调解应该成为社会性劳动调解体系建构的主要方向。实践中,行业调解的问题在于:基层企业代表组织(如企联、协会等)不健全、覆盖率低,经费紧张,一些行业组织对其应担负的劳动关系协调职能认识模糊,参与劳动调解的积极性不高等等,影响了行业调解功能的整体发挥。对此,应通过政策引导、经费保障;推动基层行业组织(特别是中小企业行业组织)的组建,并明确其劳动调解职能;加快在劳动争议多发领域的行业协会(商会、工商联)设立劳动调解组织等举措,以做大行业调解体系。
第三,扩展政府购买服务,进一步拓展民间性调解机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指政府通过市场化手段,将社会力量引入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以减轻政府压力。这不仅有利于政府改革,也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体成长,推进社会建设。劳动争议本身有很强的公共性、私人性,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劳动争议,能够减轻政府压力,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劳动纠纷带来的政-劳对立,有利于政府以中立者、监督者身份协调劳资纠纷。
从目前情况来看,民间力量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基本上还没有纳入到国家购买社会服务的视野。这不利于社会化解决劳动争议思路的实现。而事实上,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不少民间服务性组织基于劳动争议化解的现实需要,积极介入劳动争议调解,取得了良好效应。比如,广东、北京等地的农民工NGO,通过调解农民工劳动争议,赢得了劳资双方的认同。天津市大胆创新,开掘社会资源,以人力资源经理俱乐部为平台设立了该市首家民间性劳动调解中心,充分发挥了民间资源参与劳动调解的作用(徐永革、陈思,2015)。北京市在构建“六方联动”劳动调解机制中,尝试通过地方工会出资购买律师参与调解,提升了调解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郭隆,2011)。这些经验表明民间力量参与劳动调解有其自身优势,应该成为我国多元化、社会化劳动争议体系发展的方向。因此,应尽快健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政策法规,利用竞买、委托等方式,将那些威望高、专业能力强的公民调解人、劳工NGO、律所、法律工作者、其他具有调解能力的公益性服务组织等吸纳到劳动调解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做大做强民间性劳动调解机制(何伦坤,2013)。
第四,塑造行政调解的公正性、公益性。行政调解即政府主导设立的调解组织,实践中主要有乡镇(村)、街道劳动服务所和司法所劳动调解室、工业园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外来工劳动调解委员会、基层综治办劳动调解窗口等形式。在我国社会自治能力和资源等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行政调解不可放弃。
行政调解依靠国家行政权力作后盾,以国家公信力作担保,相比于社会性调解,更能得到劳动者的信任。这也是不少学者极力主张着重发展劳动行政调解的原因。实践中的问题是,基层政府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和维稳思维,偏离了其公正角色,将行政调解异化成压制劳动者权利的工具,破坏了调解的自愿性、合法性。此外,对行政调解的公益性性质定位不清,也削弱了其公正性。比如,在广东汕头就出现了基层干部在调解劳资纠纷过程中,逼迫工人向老板下跪并扣取“调解费”的事件(李迪,2012)。
因此,应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劳动争议行政调解办法》(杨广,2010),从制度上将行政调解定位为公益性解纷机制,杜绝收费,明确劳动行政调解的主体、职责、控制程序和责任追究。尤其要规定不得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的程序、问责机制,防止其被扭曲为压制性的维稳工具。同时,应借鉴国外的普遍经验,将其职能范围限定为主要调解集体劳动争议,避免其利用强势资源,争夺、垄断劳动调解服务市场,抑制其他调解机制的发展,从而确保劳动行政调解与其它社会性劳动调解在各自的职能领域内发挥作用,维护调解体系的层次性、开放性、多元性。
第五,对于劳动仲裁调解和司法调解,应该回归角色本位,着力树立其裁判的权威性、公正性。相对于调解组织而言,仲裁和诉讼的主体性角色是裁判,而非居中协调、促进和解。过于践行调解功能,易导致其本位功能异化。而且,从前述的人民调解、工会调解、行业调解、基层调解以及其他社会化的调解来看,我国劳动调解调解体系已非常庞大,在此背景下还一味强调仲裁调解、司法调解,将形成繁复的调解局面,不利于专门调解组织的功效发挥,浪费制度资源和社会资源。尤其如前所述,在联动调解过程中,仲裁员和法官在调解和裁判环节的角色同一性,还将对当事人形成事实上的压迫,担心不同意调解而在裁判环节会对其不利,而被迫接受本不情愿的调解结果,造成不公。因此,从多元劳动解纷机制的本真意义出发,应取消取消劳动仲裁调解和诉讼调解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刘诚,2006)。
四、余论:回归社会为主的多元建构理路
劳动争议联调机制是国家基于劳动争议多发化、群体化的维稳压力和社会化、多元化调解机制实效不足的情势,对分散的多元调解机制进行国家统合的结果。它试图以国家性元素的植入和加载,对多元化的调解机制进行重新编排和一体化,做强调解机制的权威,通过调解把大部分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实现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社会和谐。但由于过于倚重国家统合,过于追求维稳目标,缺失规范性制度的管控,国家权力失范,反而危及了调解机制的自治性、合法性、公正性。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自治的解纷机制,劳动调解机制的效能和权威,根本取决于社会的高度自治、劳资力量的制衡和劳动主体的道义水平,而非国家权威的直接加载。而我国劳资力量严重失衡、企业诚信水平普遍较低、劳资自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以社会权威为基础的多元劳动调解机制,在短时内难以立威。这也恰恰成为国家统合的理由。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向社会还权、赋权,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主体的成熟,以及多元劳动治理模式的形成,国家统合主义的思维必将消解,国家强制性解纷机制与社会柔性解纷机制并举并重的格局必将确立。因此,作为一种柔性解纷机制,劳动争议调解的做大做强,最终还是得回归社会为主的多元建构理路。在社会得以成长成熟的前提下,凭籍国家的引导、支持、培育和规范,着力发展以社会权威和公共理性精神为依托的多元、竞争的调解机制。当下社会权威的缺失和社会性调解机制的孱弱绝不能成为向国家回退、以国家代社会的籍口,反而应该成为国家自我革新、自我限权,以更坚定的意志推动社会建设、塑造社会权威、培育社会性解纷机制的动力,从而为多元劳动调解机制的发展奠定社会治理体制基础。
注 释
①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篇名“劳动争议联动联合调解”,得到33篇相关文献,均为积极宣扬联动调解机制经验、成效。学术界系统研究联动调解机制的文献甚少,仅有的若干文献也以点赞为主,如孙晓萍、吴式兵:《劳动争议联动联调机制探微》,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67-70页。
②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劳资纠纷是导致千人至万人群体性事件的主因,占群体性事件的36.5%,领跑社会矛盾冲突排行榜。参见李林、田禾:《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2月版。
③具体参见《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2009]124号)、《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中央综治办,2010年)、以及四川、天津、福州、江苏等地的劳动争议调解规范性文件。
④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4年全国法院系统新收劳动争议案件38.7万件,比去年上升5.4%。这表明联动调解并没有真正发挥拦截劳动争议案件的作用。数据来源参见黄彩相:《全国法院收结案数量再创新高 审判工作取得新进展》,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4月30日。
⑤其针对性措施有:明确法院、仲裁机构在实施委托调解、邀请调解过程中,向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客观全面地释明调解程序的选择权,及其法定权益、妥协让步的内容和法律后果的义务;健全法院在司法确认过程中,对调解协议的程序合法性、实体合法性审查的标准和程序规范;建立对违法调解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从而确保调解的自愿性、合法性。
参考文献
1.王全兴、林欧:《劳动争议民间调解协议的效力及其加固》,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2012年第5期,第37-46页。
2.庄文嘉、岳经纶:《从法庭走向街头——大调解何以将工人维权行动挤出制度化渠道》,载《中山大学学报 社科版》,2014年第1期,第145-157页。
3.郑广怀:《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27-38 页。
4.汤唯建:《中国调解制度的现代化转型》,载《检察日报》,2009年07月20日。
5.汤碧琴:《工会劳动司法联合“坐堂”当“娘舅”》,载《宁波日报》,2010年4月8日。
6.王永:《今后的劳动争议将有半数以上在基层以调解方式化解》,载《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6期,第9页。
7.尹民生:《区域性、行业性劳动争议制度研究》,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5-30页。
8.徐永革、陈思:《大调解视域下民间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功能与实践》,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年第12期,第83-87。
9.郭隆:《六方联动把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载《北京观察》,2011年第8期,第18-20页。
10.何伦坤:《劳动争议实效的软法求解》,载《理论探索》,2013年第3期,第119-123页。
11.李迪:《汕头内衣厂大火调查:讨薪很普遍 干部调解让讨薪者下跪》,载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07/c70731-19823049-2. html,2015-8-25日访问。
12.杨广:《构建劳动争议行政调解制度》,载《中国劳动》,2010年第5期,第18-20页。
13.刘诚:《国外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及其启示》,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108-102页。
■ 责编/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Linkage Mechanism and Its Reflection
He Lunkun
(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Abstract: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labor dispute linkage mediation is based on the pressure of multiple and mass labor disputes, and the lack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mediation system, to take a national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The logic of excessive emphasis on maintenance of stability of medi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of the state instead of the society, damages to the nature of mediation, confuses the boundaries of different mediation mechanisms, block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labor dispute pattern of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Correction of integration logic, should adhere to open, socialized, diversified benchmark ideas, adhere to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dispute resolution thinking,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the mediation mechanism, efforts to cultivate the social authority of civil mediation mechanism. On the basis of this, should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 pluralism , efficiency, competition and opening-up",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different mediation mechanisms, and take concrete measures to make them stronger and bigger
Key Words:Labor Dispute; Linkage Mediation; National Integration Logic; Defect;Counter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