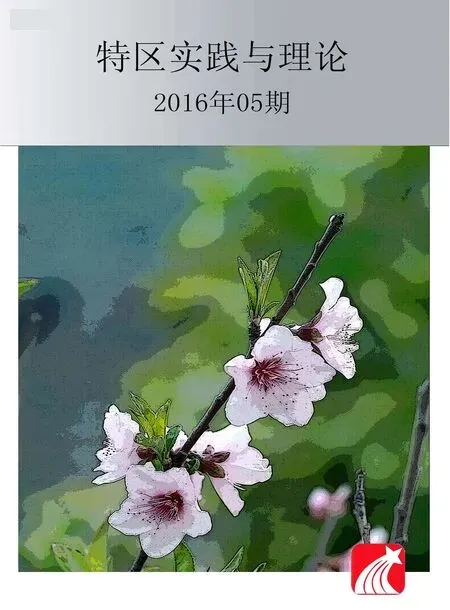孟子悲悯情怀外化的困境与通途
关万维
孟子悲悯情怀外化的困境与通途
关万维
从心到气,孟子的悲悯情怀实现了从心、到气、到浩然之气、到勇气,打开一条由自省到“为政”的通道。孟子在内心与外在之间,由义气打通向世俗释放之路。孟子对于仁政的布施,在于劝慰,走向类宗教情怀,而心、性等,走向知识论,走向世俗。孟子生于心、成为仁的悲悯情怀,向外释放的过程,没有走向崇拜、走向神秘主义,而是走向志气、义气、浩然之气,是一种高尚人格的树立和孔、孟二人的悲悯情怀,最终没有走向虚无而是诉诸政治,这是儒家思想最后没有走向宗教而是走向世俗的重要原因。
孟子;心气论;道德劝慰
儒学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中外思想学派有如此漫长的延续性的学派几乎不再有第二例。但传承也必然有偏差,譬如有子的“孝悌无犯上”之论,与孔子对《尚书》阐释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偏差。有子这样一种言论还被置于《论语》之首,近在“学而”一章之后,可见是有不少学生对此是认同的。又如,《尊德义》云:“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1]这句话与《礼记·曲礼上》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论书面还是意思都基本相同。可见《礼记》思想的来源的确有很多很早的思想。但也有一些后学很好地阐释了孔子的理想,比如《礼记·礼运》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的观念,将孔子政治理想更明确化、理论化。但从孔子到孟子之间,完成得最好的似乎是理论上的建树而非思想上的拓展。以其思想论,从《论语》到《缁衣》的变化,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出现一些偏差,从这些变化中也大致可以反映孔子思想在重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郭店简所见《缁衣》文,十分强调君主对于民众的引导作用,李零校本二十三条文本,近二十条是讲君主对民众的表率作用的,而且是非常工整的先“子曰”后“诗云”的格式。
其理论建树上则有所不同,子思学派开启了一些新的气象。如《五行》云:“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不敢唯;诺,莫不敢诺;进,莫不敢进;后,莫不敢后;深,莫不敢深;浅,莫不敢浅。”[2]似乎是第一次提出了“心”的概念,虽然以其与耳目口鼻相提来看,这个“心”还是生理层面的。但不管是哪个层面的,都已经进入了儒学理论视野,成为一个重要名词,可役六官,说明它的重要性。又如《性自命出》云:“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3]“性”与“心”一起出现并且在理论上形成相互阐释的模式,开启了孟子心性论的先声。
一、孟子仁政的劝慰色彩
从郭店楚简儒家文献中不难看到孟子思想的一些来源,但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理想来自孔子;向孔子学习,也是孟子的主观愿望。事实上,从孟子的政治思想中,也可以看到其对于孔子政治思想的主动继承。在学生问及伯夷、伊尹、孔子是否同一类人时,孟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将孔子放到极高的地位,即“圣人”之位。对于孔子的处世法则,孟子也附和。对于孔子的一些思想,孟子也作非常具体的隔代回应,如《孟子·离娄上》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论语·子路》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思想来源清晰可见,但孟子给出具体的原则,即“惟义所在”。但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主要在于其核心的思想,尤其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的“仁”,孟子全部继承,也同样推到一个极高的位置。
《孟子·公孙丑上》云:“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赵岐注云:“为仁则可以长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则安。”赵氏对孟子之“仁”的含义作功利化理解。朱熹章句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故曰尊爵。”朱子所谓“四者”即仁、义、礼、智。杨伯峻译云:“仁是天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最安逸的住所。”[4]即孟子常以政治利益为目标引诱诸君主施行仁政,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但就对“仁”的这一理解而言,是很纯粹的。因此,杨伯峻之译,最为中肯。孟子将“仁”放到“天之尊爵”的位置,也深信“仁者无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
《孟子》全书涉及“圣”者约五十次,大多指“圣人”,且主要指孔子;涉及“圣王”仅三四处,如“先圣后圣”、“圣之君”、“圣王”,《论语》中那个作为“仁”的外在政治理想的“圣”不见了。《孟子》谈“圣”的其他意义者极少,仅一二处。
在《论语》中,“圣”有两层意义,其一为至仁至德的人,其二为至高的政治实现。孟子这里,圣主要是第一层意义,《孟子·尽心下》云:“圣人,百世之师也。”而孔子对于“圣”的第二层意义,到孟子这里,变成“仁政”。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话有丰富的信息。首先,“地方百里而可谓王”,可见这个“王”有治理者的含义,并非“王霸”的含义。作为这个百里之地的治者,孟子给出其“仁政”的具体内容,在孟子这些政治思想中,不难看到孔子的影响。其一,如“省刑罚”,《论语·为政》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孔子是反对刑治的,孟子同。其二,孟子主张“薄赋敛”,《论语》未对“赋”有明确的看法,但《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季孙打算改变赋制时,三次向孔子咨询。孔子曾提出“敛从其薄”的思想。此外,孔子极少涉及税赋之政。但他关心百姓的足与不足。税赋问题没有引起孔子重视,在《论语》中没有很突出的论述,却引起孟子重视,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出年代之差异。孟子之际,各国经过赋税改革,诸侯之间对百姓的盘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因此“薄税敛”成为孟子的政治思想内容。“薄税敛”可以让百姓勤耕作,“深耕易耨”,收成可涨,带来税赋的增长,形成社会的良性循环。其三,《孟子》反对滥用民力,让精壮劳力有时间修养孝悌忠信之道,居家则孝敬父兄,“出以事其长上”,那么百姓即使是手持棍棒都可克秦楚之坚甲利兵之师。而孔子提出过“节用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观点。
孟子所谓仁政,首先就是保证民众物质利益。这与孟子反对“道在尔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的思想也是相吻合的。孔子的“圣人之政”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而孟子的仁政,在他看来却是切实可行的。这是儒家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重要一步。我们说孟子走向“现实主义”,并非说孟子是个现实主义者,而是他将儒家的政治理想具体化。但事实上孟子的很多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对于“民”的政治价值,至少自西周以来就是政治主流的共识。“民”因此也成为儒家政治家价值观的根本。孟子以“得天下”为诱饵,推行其仁政。孟子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商鞅变法之后50年左右。法家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战国间的秩序,孟子所谓“得其民,斯得天下”的理论,在急促的兼并战争中几乎难以立足。孟子的依据是什么?《孟子·梁惠王下》给出成功的例证:“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文王之所以能立业,靠的是对鳏寡孤独的关照,这是文王之德,也是西周立国之本,因此,孟子认为: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明知“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孟子·滕文公下》),却又指望如此乱世,可以用柔和的仁政来平乱。孔子之世,世道将乱。孟子之世,世道已乱。孔子可以指望通过对秩序的肯定,来重新回到天下太平的局面,孟子对此,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
这是孟子较为完整地阐释他的仁政的“施行办法”。孟子之政,看似轻松,但施行起来并非“仁政”二字可以解决。别的不说,仅“俊杰在位”一项,就已经是一个古今难题。孟子对具体的政策操控,显然缺乏深入的体验。甚至,孟子的“仁政”,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孟子以宽松得近乎“无为”的政策,吸引士、商、农、贾,以求壮大生产力、凝聚人心,从而达到国家强盛。这与“小国寡民”的“无为”不同,但与“无为而无不为”之“无为”是颇为相似的。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颇有古公亶父的风采。在齐人即将加强薛地城墙之际,滕文公感到不安,问计于孟子。孟子认为,从前太王居于邠,狄人侵犯,太王放弃邠,迁徙到岐山脚下。这不是故意选择,而是不得已,但是周室因此而以兴旺。因此,君主行善政,即使未能当世成事,也将为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
从孟子以古公亶父的故事给滕文公“献策”之事看,说明几个问题。其一,孟子对的局势的判断是明白的。藤作为小国,夹于齐楚之间,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藤文公的不安。孟子搬出古公亶父的故事,显然已经明白地意识到藤国并无任何对抗的策略,任何顾虑都是徒劳的。孟子并没有异想天开,认为仁政能够直接抵御强敌,故而讲古公亶父、讲子孙,而不讲现在。其二,孟子推行仁政,表面上是以成王业为诱饵,实则有明显的无条件施行仁政的意思。这是藤文公唯一的策略,施行仁政,行善积德,为子孙计,此外没什么更好的选择。这一点颇有劝行德积善的意味,有一点淡薄的宗教色彩,即无条件性。这是孟子思想流露出来的微弱的宗教意味。就这而言,孟子有着比孔子更明显的迹象,当然这并不等于可以过度解读孟子思想的宗教色彩,不论孟子还是儒学,无疑都是典型的世俗思想。其三,孟子并没有找到政治与道德之间可能存在的切实可行的强国办法,只能以古代圣王的事迹为模本,其仁政更准确地说,就是一种劝慰方式,好似布道施教,而非真正的政治策略,这也是儒家思想在特定时期所必然存在的局限。仁义道德都是柔性的,在暴利和丛林法则之中,儒学思想往往缺少现实主义的力量。
孟子推崇的政治手段并不能拯救王权。《荀子·非十二子》如此批评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姑且不论荀卿是否能客观地看待孟子,但其所指责并非空穴来风。思孟“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意指孟子虽然强调法先王,但忽略先王的政治手段;一味强调德治仁政,却不知道先王如何治政。荀子耳闻目睹法家苛政的成功实现,有所启发,故自认深谙治道,自然感觉以奉仁政劝慰君主的孟子实为“才剧志大”。荀子的批判不一定能说明其他问题,但能从侧面证实孟子学说的理想主义色彩。
孟子和孔子一样,对财富抱有藐视的态度。《孟子·告子上》云:“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没有将孔子较为复杂的“仁”的含义继续复杂化,而是简单化和具体化。孟子将“仁”这一道德、伦理色彩浓重的概念归结到政治思想之中,以“仁”行“政”,也符合儒学的一贯思想。在王权时代,“仁”是最能体现对“民”的关怀的一种观念甚至也是一种技术。孟子将孔子核心的“仁”简化归结到政治理想中,而在“心”里,阐发自己的更复杂的思想。这于思想史而言,也是一种必要的理论推进。
二、心气论:悲悯情怀之外化通途
孟子思想理论的复杂化,主要来源于他对人和人生的思考而非对社会的思考。这一点,首先从他对于“仁政”的具体策略的空想色彩可以看得出来;其次,孟子反躬自省,其思想直指内心,提出一个比“仁”更接近人的核心的概念“心”,进而做更深入的思考,提出或赋予一些概念更具体的含义,如“气”、“性”、“义”、“志”等等,这些概念尤其“心”、“性”等,启发了后来的宋明理学。从“心”到“性”到“义”再到“志”,孟子比孔子更自觉、更多地思考人的自身。这是儒家生命哲学内省历程的重要一环。当然,这一环并非始自孟子,而是在孔子门人中就已经出现这种理论上的自觉。
儒家内省这一取向,在孟子这里实现一次较大的飞跃。“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这样的自省主要在于行为和表象,而孟子自省的核心含义,在于对人格更自觉和更进一步的思考。而“性善论”是其中核心思想之一。陈荣捷认为,孔子至多隐含人性是善的,而孟子前进一大步,认为人性本善。[5]孔子对于人性,至少是人的本性善恶属性,并没有形成自觉思考。孟子内省,反观自心,由“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坚信“性本善”。但是,不能简单地将性善论理解为孟子个人的“心”的经验,事实上,孟子对人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如《孟子·离娄下》云:“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句话可以给孟子“性善论”予以重要补充,更真实地反映性善论的复杂含义。人与动物之异无几,说明孟子对人作为天地天物之一员的兽性一面的肯定。而且,对于人的这一面,保持其本质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君子”:可见“庶人”对人性的理解是错误的。对于“仁”,孟子更多将其整体价值外在化、具体化,体现于政治理想之中。
《孟子·尽心上》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对内心自省、自觉性,超过了前代儒家。思想家的自省的自觉,多少会笼罩上一点宗教色彩。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论述高级宗教与低级宗教的差别时认为,“某种宗教高于其他宗教,是因为它发挥了更高层次上的心理功能,激发了更加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包含着更多的概念,这些概念中感觉和意像的成分很少,而且安排得更加合理”。[6]这个观点对于一般思想的宗教色彩的判断有一定参考价值。或者说,伦理思想具有天然的宗教情怀。儒家早期思想家的思想因此具有这种两面性:一种思想,源自自我反躬自省而诱发的人类的崇高本能,德、性、善、仁等思想因为具有某种悲天悯人强烈倾向而具备宗教色彩。一种思想,源自对社会焦虑和对民权、时局的积极进取,孟子思想虽然较之于孔子思想有种种理论上的自觉化与一定程度上的纯粹化,但政治、时局依然是其自省的重要的原动力。
在孔子看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是“为政”。孔子修身、养德,便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孟子亦同,孟子宣扬“仁政”,至德之仁,与政治紧密相连。于孟子而言,其近乎宗教般的仁慈之心,也与政治发生了关系,“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不论是仁、是孝、是义、是德,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孟子继承孔子“仁”的思想,但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孟子》单独谈“仁”并不太多,更多是“仁政”并提。由“仁”而及“仁政”,意味着“仁”这一在孔子看来是最为核心的品质,在孟子这里走到了尽头,外化为一种求诸政治的悲悯情怀,比“仁”更为核心的因素是“心”:“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由此可知“心”比“仁”更加广大,“心”是比“仁”更彻底的人格要素,而“仁”只是“心”所负载的各种要素之一。
从“仁者爱人”到“仁者人心”,“仁”从动态的“爱人”到静态的“人心”,因此似乎也可以说“人心爱人”。因为“性本善”,因此“心”也具有一定先天性“仁”的判断。但是“性本善”不等于“性必善”,因此,既有“仁”也有“不仁”,因此有“人”也有“非人”。,孟子虽然做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这是孔子所未曾尝试的。孟子也给孔子所谨慎触及的“仁”,赋予更多的道德价值。仁者人心,有爱即荣,无爱即辱。将爱的存无当作人格的重要内涵,仁成为荣辱观的重要标准,孟子给“仁”注入了直接和明了的道德判断。为什么“仁则荣,不仁则辱”?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强调的“仁”,是一种非常确切的人格含义,没有任何神格色彩,因为“仁”的动力就在于人的内心,即“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孟子对“仁”的具体化理解,则是人伦化、情感化。“性本善”是孟子对人格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而“仁”是“善”之本所衍生出来的外在因素,缺乏仁,即对人格的亵渎和侮辱。孟子甚至还曾将仁与义归结为孝与悌:“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这是在浓郁的孝文化背景之下,孟子最可能自然形成的一种思想。孝是一种比儒学更早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价值。孟子此论,似乎将孝悌居于全部思想价值的核心(同等于仁义),而且是“智”的体现,是礼的本质,是乐的本质。传统孝文化的形成,目前可考与周文王推行的德政有关,而儒家早期思想家则将孝视为仁爱之心的立足根本,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原则与远近亲属原则的衍延之后,可达成普天下之爱,从而实现其他政治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社会理想。
但孟子显然意识到仅靠“孝悌”是不足以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因此孟子并没有局限于孝,更多时候是将“心”放在一种广泛的理论形态中。《孟子》中关于“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多元的、中性的属性,不具备“仁”那样天然的价值倾向。因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孟子之所谓心,有赤子之心、不忍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等。“心”的多种属性,似乎又将这原本比孔子“仁”更本原的“心”推向外在,这也让笔者对孔子之“仁”与孟子之“心”,哪一个更靠近人的核心,产生一些疑问。甚至“气”也是中性的,因此必须强调“浩然之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
这是孟子对告子观点的评价。告子认为,如果不能成于语言,则不必求诸思想;未成于思想,则不必求诸意气。孟子认为,前者不可,而后者可以。因为思想意志主宰着“气”,而“气”是与体魄具在。意志来到,“气”也到来。因此,保持自身意志,勿滥施意气。勿使滥施意气,以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对“气”的唯一理解,似乎没有涉及是否有其他类型的“气”。“浩然之气”是什么?
杨伯峻在译《孟子》这一整段话时作如是解:孟子说:“告子曾经说过:‘假若不能在语言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思想;假若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必求助于意气。’(我认为)不能在思想上得到胜利,便不去求助于意气,是对的;不能在语言上得到胜利,便不去求助于思想,是不对的。”笔者认为,“不能在语言上得到胜利”这样的理解或有悖于孟子原意,“言”与“心”应类似于现代西方的“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只不过是告子对于“言”与“心”的先后问题,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主流观念正好相反。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就像老子莫可名状于道,孟子也深感“浩然之气”其“难言也”:首先气“至大至刚”,以“直”即正义来滋养且勿使受害,那么它可以充斥天地无所不在;其次,气要与“义”与“道”合,否则“馁”;第三,必须是持续的坚持而不是投机的。“气”也不是孟子所发,《左传》、《礼记》中已有过“气”的论述,如“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左传·昭公元年》),又如“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左传·昭公九年》)、“节嗜欲,定心气”(《礼记·月令》)等等。
因为“浩然之气”加之有了自省精神,凡是认定正确的事情,就勇往直前。孟子的勇气论来自孔子。《论语·子罕》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论语·卫灵公》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将这种杀身成仁的勇气,诉诸政治,于是就有“诛一夫纣”、“诛其君而吊其民”(《孟子·梁惠王下》)的勇气,直接对王权提出挑战呈现出思想家为民所计的无畏精神。正气因此得道义,其勇气外在,可以杀不道之君。
当然,孟子之心、性、气,也有普遍性的一面。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赵岐注云:“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为正。人能尽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知其性,则知天道之贵善者也。能存其心,养育其正性,可谓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无亲,惟仁是与,行与天合,故曰所以事天。”这里所谓“事天”,简单地说,即践行天命。再如《孟子·尽心上》之所谓“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在这里,孟子的政治热情完全被忽略了,而更强调个人的修养。当然这种修养与政治热情之间不存在任何沟堑,甚至是浑然一体的。更重要的是,个人的道德仁义的修养,是比政治热情更接近本原的一种素养。
三、概述
纵观孟子的仁之策,对于现实政治而言没有多少策略的含量,自然不为王者所接纳。孟子推行的是其道德理想,虽然这是禹汤文武屡试不爽的成功法则,但显然解决不了短兵相接时代的问题,孟子的理想遭冷遇是必然的。对此,孟子自云“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这更证明孟子的“仁政”思想,很大成分是个人生命理想的自我释放。劳思光认为,“孟子对于形躯、情意中诸种险扰,论之不详,未免令学者有太简之感”,这是孟子的独特的理想主义。他虽然试图将孔子的“圣”之政付诸实施,但是显然其走向现实的同时,也没有摆脱其理想主义,甚至比孔子的政治理想更显得缥缈,与其说是治国之策,毋宁说是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劝慰甚至是道德因果。
《孟子·告子上》云:“仁,仁心也;义,人路也。”仁与义互为表里。从心到气,孟子的悲悯情怀实现了从心、到气、到浩然之气、到勇气,打开一条由自省到“为政”的通道。孟子在内心与外在之间,由义气打通向世俗释放之路。悲悯之心是宗教情怀,浩然之气为世俗情怀,前者为里,后者为表。孟子对于仁政的布施,在于劝慰,走向类宗教情怀,而心、性等,走向知识论,走向世俗。孟子生于心、成为仁的悲悯情怀,向外释放的过程,没有走向崇拜、走向神秘主义,而是走向志气、义气、浩然之气,是一种高尚人格的树立和孔、孟二人的悲悯情怀,最终没有走向虚无而是诉诸政治,这是儒家思想最后没有走向宗教而是走向世俗的重要原因。
[1][2][3]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2;103;136.
[4]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82.
[5]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66.
[6][法]爱弥尔·涂尔干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
责任编辑:周修琦
B222.5
A
1673-5706(2016)05-0123-06
2016-07-07
关万维,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