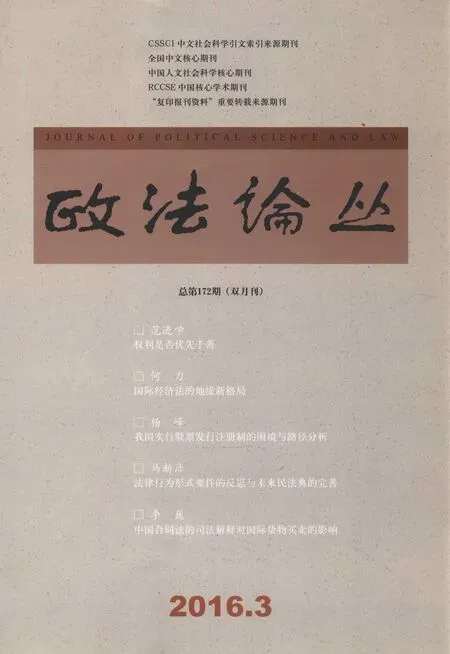论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
王志祥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论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
王志祥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内容摘要】从立法原意的角度看,“杀害被绑架人”应包括对死亡结果发生的要求。“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不适当地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而“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则合理地限缩了死刑的适用范围。立法者在对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中对限制死刑刑事政策的贯彻可谓有得有失。基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立场,对“杀害被绑架人”应当解释为“杀死被绑架人”,对“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应以处无期徒刑为原则,以处死刑为极其罕见的例外。
【关 键 词】绑架罪绝对确定的死刑杀害被绑架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限制死刑
继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之后,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死刑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本文将对其中所涉及的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予以法理上的评析,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一、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过程
绝对确定的死刑,是指法定刑所包含的主刑类型只有死刑而没有其他主刑的情形。1997年系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绑架罪、劫持航空器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拐卖妇女、儿童罪、贪污罪以及受贿罪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其中,1997年《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由此可见,在实施绑架犯罪的过程中,只要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法定刑的种类就是唯一的、确定的,即死刑。
不过,在1997年《刑法》的修订过程中,立法机构并非从一开始就对绑架罪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就绑架罪的法定刑来说,1996年8月8日的刑法分则修改草案规定,对于本罪的基本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从实践中看,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还是存在的。为适应各种轻重情节不同的绑架犯罪,立法工作机关在1996年8月31日的刑法修改草稿中以上述8月8日稿的写法为基础,为绑架罪增设了情节较轻情形的法定刑,即“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而,后来由于受当时正在开展的“严打”斗争的影响,1996年10月10日刑法修订草案(征求建议稿)不仅删除了情节较轻情形的法定刑幅度,而且对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该草案的这一写法最终为1997年刑法典所沿用。[1]P459
由此可见,立法者为绑架罪确立绝对确定的死刑的目的,是严厉打击后果严重的绑架犯罪。但是,为绑架罪确立绝对确定的死刑,剥夺了法官在是否适用死刑方面本应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一旦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法官在确定基准刑时就只能以死刑作为惟一的选择,而没有另行选择其他种类刑罚的余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并由此有悖于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此外,“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这两种情形下的主观罪过形式有截然不同:前者系行为人的行为过失引起的,而后者则系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这两种情形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不加区分、不加衡量地对这两种罪过形式截然不同的情形均配置绝对确定的死刑,是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尽管如此,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却并未对绑架罪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作出修改。1997年刑法典实施后,从实践中看,刑法对绑架罪设定的刑罚层次偏少,而且法定最低刑就是10年,不能完全适应处理情况复杂的绑架案件的需要。有鉴于此,《刑法修正案(七)》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对绑架罪增加规定了情节较轻情形的法定刑,即“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P459-460而绑架罪的绝对确定死刑的规定则在《刑法修正案(七)》中仍然得以原封不动地保留。
对此,有论者指出,尽管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之中,很多学者都对1997年《刑法》中绑架罪的加重构成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应当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杀害被绑架人”这两种情形予以明确区别,并将无期徒刑作为此两种情况下的选择刑以取消此处绝对死刑的规定,刑法修正案最终还是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这固然可以有诸如打击犯罪的压力过大、绑架罪本身是严重犯罪、特别是要尽量在立法上体现对于人质安全的政策考虑等理由,但终究还是令人遗憾的。在这样的崇尚死刑威慑的观念和政策的名义下,被告人的权利受到了当然的侵犯。[2]P73有学者认为,不论是从限制、慎重适用死刑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罪刑设置的科学性着眼,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杀害被绑架人”这两种情形都不应设置绝对确定的死刑。在今后对绑架罪的立法修改中,应以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代替绝对确定的死刑,如可以规定“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3]P327上述意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的过程中得到了回应。
2014年10月27日至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稿)进行了第一次立法审议。在一审稿中,并未涉及对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改。在此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稿)印发各省(区、市)和中央有关部门、部分高等院校、法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征求意见。中国人大网站全文公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同时,还到四川、新疆、山东、安徽等地进行调研。在此过程中,有的部门、地方和专家提出,《刑法》第239条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杀害被绑架人”这两种情形规定绝对死刑的刑罚,司法机关在量刑时没有余地,不能适应各类案件的复杂情况,有的案件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除致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以外,对于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也应当根据其犯罪情节规定相应的刑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公、检、法等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将犯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的规定修改为:“故意伤害、杀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4]P367-368这一建议在2015年6月24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第14条中得以反映。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审议的过程中,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部门提出,对于犯绑架罪,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无论是否得逞,是否造成重伤、死亡的后果,都应当严厉惩处,以切实保护公民生命安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二审稿第14条修改为:犯绑架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4]P353该建议在2015年8月24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审稿)第14条中得以反映。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保留了三审稿第14条对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改。这样,1997年《刑法》第239条就被修改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由此,“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替代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成为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的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
二、“杀害被绑架人”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第14条的表述排除了“杀害被绑架人”要求造成重伤结果的误解。而且,按照立法原意,“杀害被绑架人”也不要求造成死亡结果。也就是说,“杀害被绑架人”只是对故意杀人行为的规定,而并不包括对死亡结果的规定。不过,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后出版的刑法著作中,对此则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绑架罪,只要有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即使杀害行为未遂甚至中止,也应当适用修正后《刑法》第239条第2款的规定。[5]P126立法工作机关在解读“杀害被绑架人”的立法原意时指出,“杀害”只需要行为人有故意杀人的故意及行为,并不要求“杀死”被绑架人的结果。[4]P10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杀害被绑架人”应当限制解释为“杀死被绑架人”。[6]P195实际上,关于“杀害被绑架人”是否包括对发生死亡结果要求的问题,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的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即均颇有争议。在刑法理论中,有学者指出,杀害被绑架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绑架杀人,而是指杀死被绑架人,即俗称的撕票。因此,杀害被绑架人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结果:是一种包含死亡结果的杀人行为。[7]P208有论者则认为,“杀害被绑架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故意杀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在绑架犯罪过程中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而已。而故意杀人存在杀死与未杀死两种结果。因此,“杀害被绑架人”也就存在杀死与未杀死的问题。这样,“杀害被绑架人”就应当是指“杀害”的行为,而非“杀死”的结果。[8]
笔者认为,虽然从立法原意来看,修正后的《刑法》第239条第2款所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并不要求必须造成死亡结果,但从学理上看,则应当认为,修正前后的《刑法》第239条所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应当均包括对发生死亡结果的要求。
首先,在法律未对条文用语的含义作出特别规定时,解释“杀害”一词的含义不能随意脱离人们日常所能理解的范畴而滥作扩大或限制解释。这也是法律解释所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杀害”一词在日常用语中的含义不仅仅包括“杀”的行为,更强调出现“害”即“死”的结果。[9]P96
其次,如果认为“杀害被绑架人”并不要求必须造成死亡结果,而只要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即可,那么,“杀害被绑架人”就既涵盖了将被绑架人故意杀死的情形,也包括了针对被绑架人实施杀人行为而被绑架人未死亡的情形。前者属于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即既遂形态,后者属于故意杀人的未完成形态。这样,就出现了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均在“杀害被绑架人”这一加重罪状中加以规定的现象。但是,在同一个罪状中对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均作出规定,是以二者的犯罪构成完全一致为前提的。这是因为,罪状毕竟是对犯罪构成的描述;在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在犯罪构成上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在立法技术上无法实现将二者在同一罪状中加以描述的目标。而事实上,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在犯罪构成层面的差异是无法否认的。具体而言,与故意杀人的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相比,故意杀人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多出了死亡结果这一为前者所排斥的构成要件要素。由此,如果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均能够涵盖在“杀害被绑架人”这一加重罪状中,就意味着死亡结果时而蕴含又时而被排除在“杀害被绑架人”的规定中,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再次,如上所述,认为“杀害被绑架人”并不要求必须造成死亡结果,而只要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即可,就意味着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均涵盖在“杀害被绑架人”这一加重罪状中。由此,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就共用《刑法》第239条为“杀害被绑架人”所配置的同一个法定刑。而我国刑法总则中关于预备犯、未遂犯的处罚规定中“比照既遂犯”处罚这种字眼,则意味着对预备犯、未遂犯等犯罪未完成形态比照既遂犯的刑罚标准处罚。这样,既遂犯的刑罚标准就是一个独立的基准,刑法分则条文没有为预备犯、未遂犯等犯罪未完成形态设置独立的法定刑,否则,“比照既遂犯”进行处罚就无从谈起。而在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共用同一个法定刑的情况下,既遂犯的刑罚标准作为独立的基准并不存在,刑法总则中关于预备犯、未遂犯“比照既遂犯”处罚的规定就无法落实。据此,认为“杀害被绑架人”并不要求必须造成死亡结果,而只要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即可,就会与刑法总则中关于预备犯、未遂犯“比照既遂犯”处罚的规定相抵触。
最后,如上所述,认为“杀害被绑架人”并不要求必须造成死亡结果,而只要有故意杀人的行为即可,就意味着故意杀人的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共用同一个法定刑。这样,只要行为人针对被绑架人实施了杀人行为,无论是否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在处罚标准上便无法实现区别对待。一方面,这会鼓励行为人一旦针对被绑架人实施杀人行为,就要将杀人进行到底,直至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由此,上述立法者所追求的“杀害被绑架人”不要求必须造成死亡结果“以切实保护公民生命安全”这一立法目的就不但显然会落空,而且会起到鼓励将被绑架人杀死的严重负面后果。另一方面,在行为人针对被绑架人实施杀人行为的情况下,是否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显然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会发生很大影响。无论是否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的结果,都坚持适用同一个处罚标准,会导致罪刑失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由此便无法实现。
在确认“杀害被绑架人”包括对发生死亡结果要求的情况下,对行为人针对被绑架人实施杀人行为而最终未造成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形如何处理,便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对此,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前后出版的刑法学著作中,均有不同的观点。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前,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杀害被绑架人”的刑罚为绝对确定死刑的前提下,不存在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而在被绑架人未死亡的情况下,适用死刑会导致重罪轻判,并且与我国刑法典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规定中限制死刑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因此,只有将“杀害被绑架人”理解为杀死被绑架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绑架他人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仍应按照绑架罪基本犯的犯罪构成处理,并且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不能作为所构成的绑架罪要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这就同样可以实现罪责刑相一致。[3]P321-32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绑架杀人未遂的,依然适用《刑法》第239条“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的规定,同时适用刑法关于未遂犯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10]P796实际上,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前的刑事司法实务中,对于绑架杀人未遂的处理,也有不同的做法。在“李城、杨琴绑架案”中,裁判要旨指出,《刑法》第239条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形并列,就是指在绑架的过程中,被绑架人死亡的,都应当判处死刑。被绑架人没有发生死亡后果的,只能定绑架罪,最多判处无期徒刑。[11]P524这与上述前一种观点是一致的。而在“王建平绑架案”中,裁判要旨则指出,将“杀害被绑架人”理解为包括杀害被绑架人未遂这一情形在内,绝不等于说,对所有绑架并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都必须一律判处死刑。在具体量刑时,还要贯彻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杀害被绑架人手段特别残忍且已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考虑判处死刑。但造成的后果并非特别严重,如没有造成特别严重残疾的,并非不能从轻判处,如有的可考虑判处死缓。杀害被绑架人未遂,并非绑架罪未遂,因此,不能作为独立的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在没有其他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如根据案件特殊情况,确需要在法定刑(死刑)以下量刑的,则应依照《刑法》第63条规定的特别程序来解决。[7]P210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后,一种观点认为,绑架杀人未遂、中止的,直接在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幅度之内量定刑罚。[6]P19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就构成绑架罪的既遂,至于杀人行为是否造成被绑架人死亡或者伤害后果,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因此,行为人犯绑架罪,杀害被绑架人的,即使杀害未遂甚至中止的,也应当认定为犯罪既遂。[5]P126
就对上述观点和刑事司法实务中的不同做法进行评价而言,需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在“杀害被绑架人”的刑罚为绝对确定死刑的前提下,能否依据不存在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排除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以绝对确定的死刑为基准法定刑进行处罚的可能性?对此,笔者认为,在“杀害被绑架人”的刑罚为绝对确定死刑的情况下,从轻、减轻处罚并非没有实质意义。应当看到,依据经《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的1997年《刑法》,有三种死刑方法可供对犯有绑架罪的被告人加以判处,即死刑立即执行、普通死缓以及限制减刑的死缓。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如果法官决定予以从轻处罚,可以判处普通死缓甚至限制减刑的死缓;如果法官决定予以减轻处罚,可以低于法定刑的下限(死刑)判处无期徒刑。当然,如果决定对这种情形不予从宽处罚,则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在“杀害被绑架人”的刑罚为绝对确定死刑的前提下,以不存在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为依据排除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以绝对确定的死刑为基准法定刑进行处罚,并不妥当。
(2)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以绑架罪基本犯的法定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为基准法定刑进行处罚,是否妥当?对此,笔者认为,《刑法》第239条将“杀害被绑架人”规定为绑架罪加重犯的构成事由,这就意味着,绑架罪基本犯的构成中不可能包括故意杀人的行为。由此,以绑架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为基准法定刑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进行处罚,就意味着以在犯罪构成中本不包括故意杀人行为的基本犯对在犯罪构成中包括故意杀人行为的“杀害被绑架人”这一加重犯进行评价,这不仅混淆了基本犯与加重犯之间的界限,遗漏了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中所包含的故意杀人行为的评价,而且会导致将《刑法》本来为基本犯配置的法定刑错误地适用于加重犯处罚的结局,会造成罚不当罪的结果。具体而言,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以绑架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为基准法定刑进行处罚,最高也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这就与故意杀人罪的处罚显得很不协调。因为,在一般的故意杀人未遂的情况下,还可以在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一定的刑罚。而《刑法》第23条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宽处罚的规定,意味着对于极少数的未遂犯而言,如果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并不亚于既遂犯时,那么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出发,就应适用与既遂犯相同的法定刑。由此,就不能排除对一般的故意杀人未遂的情形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情形除了故意杀人未遂以外,还包含了绑架行为。这样,对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处罚理所当然地应当重于对单纯的故意杀人行为未遂的处罚。而如果对前者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对后者则不能够排除判处死刑的可能性,那么,就显然会导致对前者的处罚出现罪刑失衡的局面。
(3)“杀害被绑架人”的未遂是否属于绑架罪的未遂?对此,上述裁判理由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里的潜在的支持否定回答的理由是刑法理论中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加重犯不存在未遂”。但是,加重犯的犯罪构成与未遂犯的修正的犯罪构成之间存在交叉关系,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在刑法学理论中,普通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是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作的划分,而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则是根据犯罪构成所依赖的犯罪形态是否典型而作的划分。这两种划分是依据不同的标准所作的平行的、彼此并不排斥的划分,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我们不能把普通的犯罪构成等同于基本的犯罪构成,而把派生的犯罪构成等同于修正的犯罪构成。实际上,普通的犯罪构成既可以是基本的犯罪构成,也可以是修正的犯罪构成;同样,作为派生犯罪构成类型的加重犯罪构成和减轻犯罪构成既可以是基本的犯罪构成,也可以是修正的犯罪构成。[12]P352具体就“杀害被绑架人”而言,虽然其属于加重构成的事由,但这并不妨碍其存在未遂的修正的犯罪构成的情形;之所以认为未遂只能适用于绑架罪基本犯的犯罪构成而不能适用于其加重犯的犯罪构成,是由于将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仅限定在基本犯的犯罪构成这一狭小的范围内所致。
(4)“杀害被绑架人”的既遂与否是否对绑架罪既遂的评价不发生影响?对此,上述有的观点给予肯定的回答。这实际上是以绑架罪基本犯既遂的评价当作绑架罪既遂评价的全部内容,从而否定了绑架罪加重犯既遂评价的独立性,将绑架罪基本犯的既遂标准与加重犯既遂犯的评价标准混为一谈。应当看到,在我国刑法中,虽然绑架罪的基本犯与加重犯共用同一个罪名,但这并不能否定二者在犯罪构成层面的差异。而既遂是以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为评价标准的。在绑架罪基本犯与加重犯的犯罪构成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二者的既遂评价标准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够以绑架罪基本犯既遂的评价代替对其加重犯既遂的判断;绑架行为的完成仅仅是绑架罪基本犯既遂的评价标准,而不能成为其加重犯既遂的评价标准。
笔者认为,“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构成由绑架罪的犯罪构成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组合而成。依据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杀害被绑架人”的既遂标准就应当是绑架罪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和故意杀人罪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前者的标志是绑架行为的完成,即被绑架人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后者的标志是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杀害被绑架人”既遂的标志就应当是绑架行为的完成加上死亡结果的发生。这样,在行为人针对被绑架人实施杀人行为而并未发生被绑架人死亡结果的情况下,就形成“杀害被绑架人”的未完成形态(未遂或中止)。就对“杀害被绑架人”未完成形态的处理而言,应当以《刑法》第239条为“杀害被绑架人”所规定的法定刑为基准法定刑进行处罚,并同时适用刑法总则第23、24条关于未遂犯、中止犯从宽处罚的规定。
三、“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评析
“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这一由《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替代“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和“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这两个事由。“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可以包含在原来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这一加重事由中加以评价,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前者并不属于新增的加重事由,而“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则属于纯粹新增的加重事由。
就“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这一新增的加重事由而言,其是否存在不适当地扩张绑架罪死刑适用范围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具体而言,绑架罪是继续犯,其客观行为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绑架人质阶段和绑架状态持续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均有可能发生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行为。在前一个阶段所发生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行为是为了排除被绑架人的反抗以达到将其置于控制之下的目的,因而实际上属于绑架罪中暴力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实质上属于一行为触犯两个罪名(故意伤害罪、绑架罪)的想象竞合犯的情形。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的处罚原则,对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绑架罪基本犯中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并在该罪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在后一个阶段所发生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行为实际上属于在绑架罪之外独立实施的故意伤害罪。对此,本应根据刑法总则中数罪并罚的规定进行处理。《刑法》第234条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行为配置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9条为绑架罪基本犯配置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样,无论是依照想象竞合犯的“从一重处断”的处罚原则,对于“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行为以绑架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作为基准法定刑进行处罚,还是依照刑法总则中的数罪并罚的规则,对于“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行为以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和绑架罪基本犯的法定刑进行并罚,最高可能判处的刑罚均为无期徒刑,而并不存在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而《刑法修正案(九)》第14条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配置的法定刑则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从学理分析的角度看最高可能判处的刑罚仅为无期徒刑的“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配置法定最低刑为无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法定刑幅度,固然凸显了立法者对于被绑架人重大身体健康的关注,因而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同时也存在人为拔高法定刑、不适当地扩大死刑适用范围的突出问题。实际上,要在体现对被绑架人重大身体健康关注的同时又不人为地拔高绑架罪的法定刑并避免死刑适用范围的不适当扩大,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可以考虑采取将“故意伤害被绑架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规定为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的加重事由的方式。具体而言,根据《刑法》第234条的规定,纯粹的故意伤害他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行为的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故意伤害被绑架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则属于包含了绑架因素的故意伤害他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为体现对既严重侵犯被绑架人人身自由又严重侵害被绑架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以更严厉的否定评价,对于“故意伤害被绑架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可以将其法定刑的下限提升为无期徒刑,法定刑的上限规定为死刑。这样,就一方面与纯粹的故意伤害他人,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行为的法定刑以及未致人重伤的绑架罪的法定刑实现了区别对待,另一方面也在提升对严重侵犯被绑架人身体健康的绑架行为的打击力度的同时,保证了对死刑范围的合理限制。
将“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作为绑架罪的加重事由加以规定,还存在着与其相并列的“杀害被绑架人”这一加重事由不相协调的问题。本来,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之前,“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就因其与“杀害被绑架人”在社会危害性上不能相提并论却被并列规定为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而备受诟病。而在《刑法修正案(九)》中,随着“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这一加重事由的删除,旧的绑架罪加重事由之间在社会危害性程度方面不相协调的局面消失了,但“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增设导致绑架罪加重事由之间在社会危害性程度方面出现了新的不相协调的局面。如上所述,一般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行为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规定,一般的故意杀人行为的法定刑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很显然,一般的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行为的法定刑与故意杀人行为的法定刑相比,相差悬殊,由此反映出二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有重大差异。将如此在法定刑上相差悬殊、社会危害性程度有重大差异的行为并列规定为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显然会导致绑架罪的加重构成事由之间在社会危害性程度方面失去协调性。
就《刑法修正案(九)》第14条所规定的“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这一加重事由而言,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这一原有的加重事由相比,其显然缩小了绑架罪死刑的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前,“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系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的加重事由。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场合,行为人对于被绑架人死亡结果的主观心态系出于过失,这是毫无疑问的:“若是出于故意,则直接属于‘杀害被绑架人’而不属于‘致人死亡’;而若是不具有过失,则也欠缺以被害人的死亡来追究行为人之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6]P193而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场合,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在主观上也系出于过失。而“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既包括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的情形,也包括故意伤害以外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情形。这样,将“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规定为替代“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加重事由,并将原来的绝对确定的死刑调整为“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就适度地限缩了绑架罪死刑的适用范围。
笔者注意到,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前,即有学者指出,由于绑架罪加重构成的法定刑是绝对的死刑,从罪刑均衡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角度出发,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应该限制解释或曰严格解释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而不能包括对于被绑架人不具有伤害故意的、纯粹出于过失(甚至不具有过失)的致被绑架人死亡。[2]P74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可取的。问题是,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解释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意味着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之外增加了“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由此,就存在着在现行法的规定之外基于实质合理性的考虑而随意添加构成要件要素的问题。应当说,《刑法修正案(九)》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替代,是实现罪刑均衡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妥当做法。
在合理限缩绑架罪死刑适用范围的同时,“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替代,还使得绑架罪的加重构成事由之间在社会危害性程度方面实现了协调。如上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九)》颁行前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规定为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的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导致绑架罪的加重构成事由之间在社会危害性程度方面存在不协调的局面。而在《刑法修正案(九)》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替代“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成为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的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根据《刑法》第232、234条的规定,“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死亡”和一般的故意杀人行为的法定刑幅度分别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二者的法定刑种类除了排序有所不同之外,并无其它差异。这反映出二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可谓旗鼓相当。由此,将二者作为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并列加以规定,就是妥当的。
总而言之,《刑法修正案(九)》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替代,一方面不适当地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而另一方面则又适度地缩小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因而可谓是利弊互见的。
四、结语
《刑法修正案(九)》“总结我国一贯坚持的既保留死刑,又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做法”[4]P358-359,采取了废除死刑与限制死刑并举的做法,在大幅削减死刑罪名的同时,也通过将贪污罪、受贿罪以及绑架罪的绝对确定的死刑修改为相对确定的死刑的方式限制死刑的适用。但是,通过本文对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修订的分析,可以看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目标并未能够在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中完全得以实现。从学理分析的角度看,“杀害被绑架人”应包含对死亡结果发生的要求,而从立法原意上看,则并不要求死亡结果的发生。但这一方面不利于对被绑架人生命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造成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形与未造成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形实现区别对待,进而不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因此,“杀害被绑架人”不要求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一立法原意应备受诟病。而“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增设则一方面有利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另一方面则又不适当地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由此看来,立法者在对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中对限制死刑适用刑事政策的贯彻可谓是有得有失。由此导致限制死刑的适用与扩张死刑的适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在同一个条文的修订中得以并存。
尽管在对绑架罪绝对确定死刑规定的修订中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但这并不妨碍在学理层面对绑架罪加重构成的事由进行合理解释,以体现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精神。就此而言,对于“杀害被绑架人”,应当解释为“杀死被绑架人”;在“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的场合,应当解释为“以处无期徒刑为原则,以处死刑为极其罕见的例外”[6]P193。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付立庆. 论绑架罪的修正构成的解释与适用——兼评修正案对绑架罪的修改[J]. 法学家,2009,3.
[3]赵秉志. 刑法分则要论[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4]臧铁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5]喻海松. 刑法的扩张——《刑法修正案(九)》及新近刑法立法解释司法适用解读[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6]陈兴良. 刑法各论精释(上)[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
[7]陈兴良. 判例刑法学(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8]曾亚杰. 如何理解“杀害被绑架人”[N]. 人民法院报,2004-09-20(3).
[9]祝铭山. 非法拘禁罪·绑架罪[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10]张明楷. 刑法学(第4版)[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1]陈兴良,张军,胡云腾. 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要旨通篡(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2]王志祥. 犯罪既遂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黄春燕)
On the Revis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Absolute Death Penalty of the Crime of Kidnapping
WangZhi-xiang
(Research College of Criminal Law Science, Beijing 100875)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gislative intent,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result of the death occurs should be included in“killing the kidnapped person”. The applicable scope of death penalty is expanded unduly by “intentionally inflicting bodily injury upon the kidnapped person,causing severe bodily injury to him” and appropriately limited by “intentionally inflicting bodily injury upon the kidnapped person,causing his death”. As far as the revis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absolute death penalty of the crime of kidnapping is concern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limi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by legislators can be described as gains and losse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position of limi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strictly, “killing the kidnapped person” should be construed as “slaying the kidnapped person” and as far as “intentionally inflicting bodily injury upon the kidnapped person,causing severe bodily injury to him” is concerned, to be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rinciple and to death penalty an extremely rare exception.
【Key words】crime of kidnapping; absolute death penalty; killing the kidnapped person; intentionally inflicting bodily injury upon the kidnapped person,causing severe bodily injury to him or his death; limiting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文章编号】1002—6274(2016)03—09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13-006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项目(2012WZD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志祥(1971-),男,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F624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