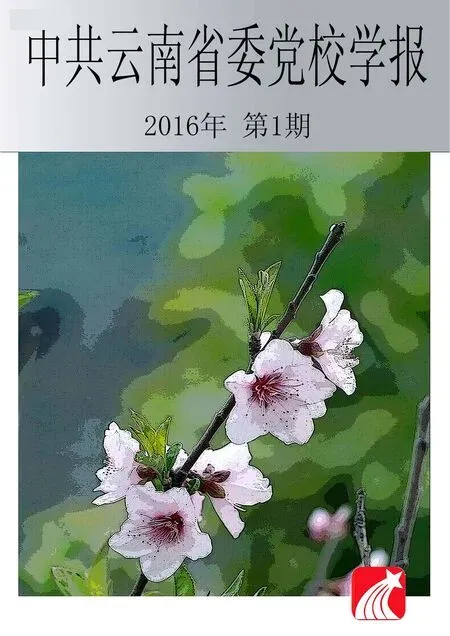从创世史诗看彝族傣族审美追求的异同
杨立新
从创世史诗看彝族傣族审美追求的异同
杨立新
(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摘要:彝族和傣族是生活在云贵高原的两个不同民族,在共同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范围内,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交流与共融,这使他们在文学的审美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之处。然而,生活在相同地区的民族,由于生活背景的不同,主体文化的差异,也使得他们在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心理具有许多个性。将彝族傣族文学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比较,可从更深层次挖掘山地民族和水稻民族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魅力,探讨文学多元化的审美内涵及审美价值,促进民族文学及文化的交汇融合。
关键词:彝族;傣族;审美比较;多元化;文化的交汇
创世史诗是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和傣族拥有不同数量的创世史诗。其中《勒俄特依》流传于四川凉山,《查姆》 《梅葛》流传于云南楚雄,是彝族创世史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巴塔麻嘎捧尚罗》是傣族目前整理出来的最完整的创世史诗。这些创世史诗作为彝族、傣族两个民族的“根谱”和“百科全书”,都已成为各自文化体系中的经典之作。从文化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沉淀于其中的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方向的审美心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挖掘彝族和傣族审美共性及审美个性。
一、勤劳、善良、智慧、团结的审美共性
由于共同生存在西南这一大的生态环境中,彝族和傣族形成了具有相对一致的审美共性。表现在创世史诗中,就是彝族、傣族都塑造了自己的一个力量非凡的巨人群。巨人群是最初的劳动创造者,他们劈山开河,制造日月星辰,犁耙大地,播种五谷,捏人捏兽,传宗接代。但是,这种劳动的过程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他们的功绩不亚于汉族传说中的燧人氏和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劳动,体现出早期人类的才能、智慧、品德、意志的美的特性。通过这些巨人群与大自然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彝族和傣族人民共同的审美追求。那就是彝族、傣族两个民族所塑造的天神群像和始祖英雄群像,都能反映出彝族和傣族对勤劳、善良、智慧、团结的共同的审美追求。
(一)崇尚顽强、勤劳、智慧和坚韧
在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的开天辟地中,我们看到,远古时期,由于生存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人与自然的斗争便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为了与自然界抗争,彝族先民们凭借想象,在史诗中把自己祖先创造成了形体硕大和具有巨大威力的巨人。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大自然在人类面前所呈现出的狂暴和肆虐,以及人所感到的恐惧和渺小。不过,最终的结果,在历经艰难困苦之后,巨人们凭借着自身的勇敢和智慧,开天辟地,征服了自然。它充分体现了早期彝族先民们改造自然及创造生活的顽强、勤劳、艰辛以及崇尚勤劳、智慧和坚韧的审美追求。
黑格尔说:“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生活在诗的气氛里,他们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成认识的对象。”[1]傣族先民和彝族先民们一样,在知识贫乏、抽象思维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必然会以经验直观为依据,用简单类比的方式进行思维。在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2]中说,远古的时候,在空旷无际的太空里,只有烟雾、气浪和大风。在烟雾气浪的下面是白茫茫的一片水。气浪、烟雾和大风在呼啸、翻腾、动荡。经过一千亿年后,气浪慢慢地凝结起来,像一包蜂窝,又在大风和烟雾中漂浮了十万年,而后变成了有头有身、模样像巨人的神,这就是太空中的第一位天神英叭。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傣族先民为了生存,要与大自然作斗争,需要高大健壮的体魄。从英叭身上,我们可看出傣族和彝族一样以高大为美的审美特征。英叭诞生后,造天造地,造江河湖泊。尽管大自然在傣族先民面前呈现出狂暴和肆虐,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傣族人民心目中的始祖在历经艰难困苦之后,用顽强和智慧征服了自然。“起源---创造(包括战胜各种艰难困苦)---胜利”是彝族、傣族创世神话的基本模式。巨人群的劳动,体现出了彝族、傣族先民在才能、智慧、品德、意志、情感等方面的共同的审美追求。
(二)肯定真善美,崇尚善良和团结
哈耶克指出:“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还是一种遵守规则的动物”[3]人类的进化是漫长的。通过一次次的进化,人类逐渐净化了自己的心性,确立了社会行为规则,那就是肯定真善美,崇尚善良、团结,这成了彝族、傣族两个民族创世史诗共同的审美追求。
如彝族创世史诗《查姆》[4]的叙述,最早的人是龙王的姑娘造的独眼睛人。由于独眼睛这代人不知道种粮食,不讲道理,不分长幼,又懒又凶心不好,所以,天神要换掉这代人,要找好心人来重新繁衍子孙。于是,直眼睛人取代了独眼睛人。但直眼睛这代人还是经常吵嘴打架。天神商量还要重换一代人,并派一位神到人间查访好心人来传宗接代。这位神骑着龙马到人间,假装跌了一跤,折断了腰和腿,请人给人血医治。大户人家回答不仅人血不给,人尿也不给。只有庄稼人阿扑独姆兄妹,用金针刺出手上血给这位神,于是,天神用洪水洗大地。我们说,洪水考验是人从神的创造物到自身的结果这个过程所必须经历的考验。只有通过这个考验,人类才是脱离了原始状态的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人类。通过考验,人面对的就是人类自身,也就脱离了先前的种种不正常状态,比如形体怪异、没有道德规范等,而进入一种正常状态。又懒又凶心不好,是独眼人被换掉的原因。而从阿扑独姆兄妹身上,我们则可看到彝族祖先从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善良的赞美。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说,“人越来越多,人多心也多”,“有了黑心人,心黑起暗算”,其中有一人,“眼睛竖着生,皮比土层厚,说话酸又馊,他忘了父辈,他忘了人规,邪恶吞吃他,头昏眼变花”,这“惹怒天上神”,“一起开口骂,这代人不好,美丑都不分”。水神更愤怒,他一声吼,“大海像决堤,海水扑过来,把宗补淹没”。“第二代人种,毁于洪水中”。[5]从史诗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洪水泛滥的情节,并不是洪水灾害记忆的保存,而是作为毁灭不良世界的手段来设置的,是为了重整世界、再造人类。实际上,是人类的邪恶和不善,最终招致了人类的毁灭。当然,从中也可看出傣族人民的审美追求。
(三)贯穿着民族同根、同源、同宗的情结
在创世史诗中,紧接着洪水泛滥之后,人类总是要繁衍。在叙述人类的繁衍时,彝族和傣族总是会贯穿着一个共同的审美主题,那就是民族同根、同源、同宗的情结。
如彝族创世史诗《梅葛》[6]叙述的,格滋天神因人心不好,要换人种,使洪水泛滥,只剩下兄妹二人。后来兄妹成婚,生下葫芦,锥开葫芦,戳开第一道,出来是汉族,汉族住在坝子里,盘田种庄稼,读书学写字,聪明本领大。戳开第二道,出来是壮族,壮族种出石榴花。戳开第三道,出来是彝族,彝族住山中,开地种庄稼。……戳开第九道,出来是傣族,傣族盖寺庙,念经信佛教。出来九种族,人丁兴旺了。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人类大兴旺”中也有类似的叙述。“从此人类啊,就分出了一百零一伙,有一百零一个帕雅,产生一百零一个民族,分居在四大洲,说着一百零一种话。由于天下四大洲,神安神宝石,一洲有一颗,光芒不一样,人的肤色就不同,可是他们啊,同是一个母亲生,都是葫芦人种。他们的祖先,同是召诺阿和萨丽捧,他们的大王啊,也只有一个,他是神种嘎古纳,智慧的桑木底腊扎”。[7]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强烈的地域习性,群体间强烈的对抗与协作、共同防御以及大公无私总是相生相伴,缺一不可。团结协作的群体,最终总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于是,这种协作精神逐渐浸润到人类的心灵深处。这也反映了彝族、傣族人民崇尚团结的共同的审美追求。这正如博厄德所说的:“尊奉习俗,相互仿效的文化传播机制为人类团结协作的精神提供了至少一个无可辩驳的理论依据,从经验论点观点来看,同样合乎情理。它解释了人类有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的协作行为,不管是否与自己的利益相抵触,人类都能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同类进行合作”。[8]
彝族和傣族的创世神话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包含了人类和大自然斗争及大劫难后的人类再造,充满了人类对大自然、对自身繁衍的顽强斗志和信心;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内聚力,也通过创世史诗得到很好的表现。当然,这类作品也表现出彝族、傣族人民对勤劳、善良、智慧、团结的共同的审美追求。
二、独特的生存环境造就独特的审美个性
创世史诗是先民对自己和生活认识的一种通过想象的艺术反映。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9]由于彝族、傣族生存的环境不同,造成了他们的不同的审美个性。
(一)征服自然的斗争美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生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0]原始人类就是由开始的匍匐于大自然的脚下而一步步由弱到强,改造了大自然,成为了世界的主人。彝族先民大多生活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山高坡陡的山区和半山区,地形高低不平,环境十分复杂而险恶。这就使得彝族先民要改造整治这样的天地,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并发展,必然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劳动。所以,在彝族创世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心理,大多都是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
比如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说,格滋天神用九颗金果化为九子,七颗银果化为七女。五子造天,四女造地,造好了,请飞蛾丈天,请蜻蜓量地。一量,天小了,又叫三对麻蛇绕着地边箍紧,把地往小里缩。可这一缩,周边便不整齐了,只好放三对蚂蚁啃地边,直啃得整齐溜圆。但还没有完,又放三对野猪和大象来拱地,直拱出高原、山箐、平坝才罢休。之后,为了测试天地牢不牢,又打雷试天,地震试地,天开了裂,地出了洞,又以蜘蛛网为线,云彩为补丁,缝补天隙。又以老虎草为针,酸绞藤为线,地公叶做补丁,补地窟窿。还有像《勒俄特依》中的支格阿鲁,也是寻找天空,寻找地面,丈量田,丈量地,后来,历尽艰辛,射掉五日六月,扫尽毒蛇害虫,终于完成了天地改造。
从上述开天辟地的复杂过程,可看出彝族先民生存环境的艰辛恶劣。即便是神,要想征服这样险恶的环境,对环境进行改造,也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格兹天神们尽管被描述得无所不能,但面对这样的环境,他们几乎到了战战兢兢的地步。他们在造天造地时表现得那样的精心和细腻。当然,他们在征服自然的活动中,尽管历经艰苦劳动、备受折磨,但我们也可从中看出他们征服自然的决心和毅力。
(二)依赖自然的和谐美
傣族则不同,他们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平坝地区。这里河流平缓,土地肥沃,森林茂密,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正因为傣族生存的自然环境非常优越,所以,在他们的创世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傣族先民对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创造和依赖的和谐的关系。如《巴塔麻嘎捧尚罗》的创世神话中所叙述的,在若干亿年之前,有一个气体滚动的真空,气体千变万化出一个有着无穷生命力的天神英叭。“英叭体大吓人,污垢附体十万层,随着他不住的搓擦,又黑又厚的污垢啊,势如山倒地陷,密似倾盆大雨,哔哔滚落下来”。[11]傣族始祖英叭用身上的污垢搓成了天地,搓成了人类,还搓出了能顶天立地的神像。用身上的污垢创世,除了表现出傣族先民对生命创造的赞美和崇拜之外,还可看到傣族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比彝族要相对优越,所以,创世的劳动也较彝族相对容易而简单。
由于生存环境的优越,所以,傣族创世史诗还处处表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心理。和谐是人本身或人与自然之间互相谐调和融合的关系。人必须要获得物质和精神的满足,才可能获得心理的内部和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在人内部和谐的基础上产生的。傣族在山清水秀的平坝地区生活,这种自然环境为人的生存提供了较为富足悠闲的生活条件。他们不需体验生活的艰辛,他们更多感受的是百花的艳丽和芬芳,野果的甜蜜和馨香。这样的生存环境,使得傣族人民性情平和、心地善良。反映在审美心理上,就是他们处处追求一种和谐的状态。而创世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人对自然的依赖之情,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的审美心理在傣族创世史诗中比比皆是。
如在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第三代人繁殖起来后,通过观察雀屎和鼠屎的现象受到启发,学会了种谷子。由于谷子是从雀屎和鼠屎里长出来的,所以,傣族先人立下诺言:“让鸟吃饱谷,让鼠吃饱谷,以吃饱为数,雀鼠屙的屎,归人类所有。这个诺言啊,十万年不改,千万年不变。一直到今天,所以自古来,有人就有鼠,有谷就有雀争吃。从那时起,谷物诞生了,谷种是神给,它从天飞来,它是生存果,专养活人类,归人类所有”。[12]这一诺言表明,因为人依赖自然的恩赐才得以生存,因此,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所谓千万年都不改变,表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应当伴随人类的始终。在这里,我们可看出,傣族人民的审美心理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对自然的崇敬、感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巴塔麻嘎捧尚罗》中还叙述天神把天分为若干层,每层都有相应的神进行管理。他们各司其职,各管其事,以保证天地万物的正常运行。有了谷之后,天王玛哈捧为了人类的生存,要划分四季。于是,派天神到人间给人们划分四季,以利耕作。结果,因为天神疏忽,划分中出了差错,结果受到惩处。从这可看到,违反了自然界的规律,连神都要受到惩处,更不用说普通人了。所以,傣族人民世代维护着这种规律,按自然界的规律办事,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阳刚美与吉祥美
原始社会的人认为,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与本氏族有血缘关系,于是,就把这种动物或自然物作为本氏族的标志。创世史诗中,彝族表现出征服自然的斗争美,傣族则表现出依赖自然的和谐美。但是,由于彝族、傣族所生存的环境不同,文化不同,使得他们面对具有神灵的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心理也不同,那就是彝族通过鹰、虎所表现出的阳刚美和傣族通过象所表现出的驯良美。
彝族生存的环境较为恶劣。彝族先民要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中生存,原始崇拜物必须拥有无上的力量和无畏的勇气。这种对力和勇的崇尚,表现在对动物的感情上,就是他们所崇拜的动物必须是力的化身,勇的化身。而透过彝族动物崇拜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心理,总体呈现为一种阳刚的风格。比如在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的英雄支格阿鲁,就是在人间抑强扶弱的鹰的孩子。史诗中贤美的姑娘濮嫫妮依,当她织布时突然出现了一件怪事,飞来的鹰滴下三滴血,恰恰滴在妮依身上。一滴落在头部,穿透九层发辫;一滴落在腰部,穿透九层披毡;一滴落在下身,穿透九层褶裙。结果,濮嫫妮依怀孕了,后来生下了鹰的孩子支格阿鲁。从这则神话,可明显看出支格阿鲁的形象带有彝族先民早期鹰图腾的色彩。而在另一部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天地万物则是虎的化身,虎的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胡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气变雾气,虎肚做大海,虎血做海水,大肠变大江,小肠变成河,虎皮做地皮,排骨做道路,硬毛变树皮,软毛变成草。
这些彝族创世史诗中,彝族先民所崇尚的动物,都是充满了抗争的具有阳刚之气的虎、鹰,这实际上显示了彝族人民独特的审美心理,那就是力量、勇气的英雄审美情结。
而傣族的村寨依山傍水,远处是茂密的森林,近处是成片的庄稼,这里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人们早晚相见,人情浓厚,所以,在傣族的审美心理中,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和谐宁静。表现在对动物的感情上,就是普遍崇拜和喜爱大象、蛙、雀一类的驯顺的动物。比如在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由于英叭的福气,由于英叭的神力,污垢架落到水面,变成一只大神象,它威武高大……英叭看着它,心中万分喜,他给神象取了名,叫掌月朗宛。掌月朗宛大象,显现出无比神力,它全身光芒闪耀,把朦胧的太空照亮。数天下的动物,算它最有威望,它的功劳无法估量,它是镇住天地的神象”。[13]在傣族文化中,象所承载的是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种无穷尽的力量和智慧,以及衍生出来的吉祥、庄严及高贵的美的象征,透露出傣族人民的审美心理,那就是没有强硬的张力的驯良、善和吉祥,以及傣族人民对这种驯良吉祥之物的依赖。
从这些最具代表性的彝族、傣族创世史诗中我们可看出,审美追求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彝族和傣族在与自然的斗争和劳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审美共性及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将他们的文学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比较,可以更深层次地挖掘山地民族和水稻民族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魅力,更好地展示两族文学特有的风采,从而更深层次探讨文学多元化的审美内涵及审美价值,促进民族文学及文化的交汇融合。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
[2][5][7][11][12][13]岩温扁译.巴塔麻嘎捧尚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236、430-431、17:262-263:33-35.
[3][英]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C〕.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232
[4]郭思九、陶学良整理.查姆[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6]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搜集翻译整理.梅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
[8]刘珩译.美德的起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195.
[9]沙马拉毅主编.彝族文学概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6:3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5.
责任编辑:刘建文
中图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16)01-0173-04
收稿日期:2015-12-17
作者简介:杨立新(1966-),女,云南昆明人,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艺术与文化。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云南彝族、傣族民间长诗审美比较研究》(2013Z09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