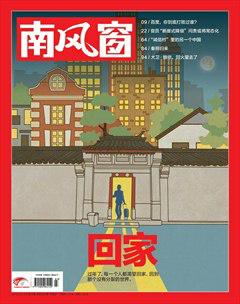康熙与教皇使者的一次交锋
张国刚
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康熙最后的处置,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维护中国传统的态度,亦无可厚非。罗马方面干预在华教务,夹杂着权力与利益考量,难辞其咎。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罗马教皇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请路易十四多派传教士来华,请罗马教皇允许传教士遵照利玛窦规矩继续留在中国。
17世纪末叶,耶稣会内部正为中国礼仪之争,闹得不亦乐乎。核心内容是,中国教徒可以祭祖祀孔吗?康熙也被带进去了,为此还与罗马教皇及其使节有一次激烈的交锋。
徐日升、张诚、白晋等在华传耶稣会士,是曾经帮助大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功臣,也是康熙皇帝在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上的老师。他们焦心于罗马教皇对于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干预,特请示康熙帝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请皇帝证明,中国人祭祖祀孔之礼仪,无关乎宗教信仰。康熙慨然应诺,特颁发谕旨,确认耶稣会士理解正确。此谕旨被翻译成拉丁文,送到梵蒂冈,教皇大怒:我们宗教事务,岂容一个异教君王判断!并派出特使铎罗到中国去检查教务。

插图/ 陈恒春
铎罗1705年4月到达广州,同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12月31日首次觐见康熙皇帝。虽说是礼节性的,但双方为一些人事问题有不同意见。铎罗提出在北京设立总主管,管理全体教士。康熙当时没有答复,后来答复说,这位宗教事务主管,必须从在宫廷中服务了10年以上的传教士中选择,这不符合罗马教皇的意图,教皇之意要夺回在华传教的主导权。康熙提出在铎罗使团中选一人出使罗马,以报聘教宗。铎罗推荐的人选,康熙也已同意,后来发现此人不通中文,提出由宫廷耶稣会教士白晋为正使,铎罗推荐的人为副使。白晋曾撰写《康熙传》,深得皇帝信任。对此,铎罗很是不爽。由此可见,康熙意识到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很可能会坏了大清与西方关系。
半年多以后,即1706年6月29日,康熙第二次接见铎罗,对于铎罗的目的已经有所警惕。康熙很关切教皇对他那道谕旨有什么回应。铎罗支支吾吾,不愿意正面回答。康熙不得要领,邀铎罗次日游览畅春园。
次日,即6月30日,在畅春园会面。康熙开门见山警告特使,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习俗,天主教须与儒学和谐共处,若反对祀孔祭祖,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铎罗无法回避,说天主教与儒学之间的冲突,他本人没有能力解释,福建宗座代牧阎珰,精通中国文献,可作详细解答。
阎珰是法国人,主持福建教务,不满葡萄牙耶稣会士在华垄断地位,此时奉铎罗之命早已来到北京,并被要求从儒家经典中摘录出,他认为与天主教相抵触的内容。阎珰硬着头皮从“四书”“五经”中摘录出一些章句,分列为48个命题,说儒家“太极”或者“理”不可能指天主教的神,中国皇帝祭祀天地、星辰、山岳等行为与天主教相抵触。
康熙特地在热河召见了阎珰。阎珰摘录的文字,错误百出,康熙断定,阎珰完全没有能力解释中国书籍。现在他要当面测试阎珰,看看他对“四书”的熟悉程度,并指着御座后的几个汉字,要阎珰识认。阎珰只会讲几句福建方言,既不能从“四书”中翻出皇帝要求的内容,几个汉字也只认得一个,见驾时全靠翻译。
这水平与康熙身边的传教士,差别太大了。康熙指斥阎珰“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说阎珰不谙中文,却把不伦不类的译作发往欧洲,导致教宗误解中国教义。阎珰辩称他的中文的确不够熟练,但儒家经典也的确有不符天主教之处,他挑出这些内容寄给教宗,是将疑难问题都提交教宗裁定。
阎珰这种冥顽态度,使皇帝不再有容忍之心,于是很快就下令驱逐他。皇帝同时通知留在北京的铎罗,他的国家里不需要任何唱反调的传教士。康熙命各地传教士进京接受审查,发誓永居中国,发誓遵从利玛窦规矩,即尊重中国文化和风俗,否则,请立即出境。
这次的事件后来愈演愈烈,到雍正、乾隆时期发展成为一场禁教活动。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康熙最后的处置,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维护中国传统的态度,亦无可厚非。罗马方面干预在华教务,夹杂着权力与利益考量,难辞其咎。设想当年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如果“娘家人”也如此的颟顸干预,恐怕也会中途夭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