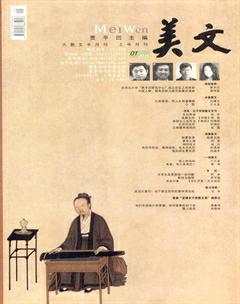青春,有几条尾巴?
黄海
丁小龙为什么要给自己的青春纪念命名为《纸上的岛屿》?
我不喜欢这种无妄的修饰。
好在每个人完成青春的体验各自不同,于他的是一次从阅读的A面到B面的阅读,或者是纯粹的一次私人的心灵交错,意义近无,无需试金石。
一代人不尽相同的脸,对他而言,不过是没理有想的虚无,却写成了夜晚的哀伤和歌唱,白昼的枯燥和无聊。但他有真诚的表达,生于1985后,他们有别于我们生活晚熟的一代。承受对于他们来说不那么必要,青春这张脸不再苦逼,没有一种力量把我们压抑和窘迫。但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感受我还没有感受到。
丁小龙这张青春的脸又如何呈现给我呢。
2012年1月3日凌晨3点的脸、2011年3月21日的脸、2012年5月27日夜晚的脸、2012年6月29日的脸。在这些时间的刻度,他和这些人在一起构成一个个时间的节点,有些面孔是寂静的,有些是鲜明的。他尽管在虚实变幻镜头,特写的生活之境依然不够清晰。有时,喊出来的声音,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这是阅读不能抵达的。
在巨大的生活场中,我们必须置身其中。
要不然青春显得无足轻重。
丁小龙的焦灼有些突然,也许是一种无聊,无非被“我”悲壮化了。这样也是生活的一种,但写作不是对己的一次性的失落和满足,也不是单薄如纸的穿行。我想说的是假以佛身和假以人道都是借尸还魂,或者说假以先哲和假以道具一样是道貌岸然。青春需要撕开给人看,这才是血淋淋的,不能掩饰给我们看。
青春不会因为你有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变得与众不同,痛与不痛,冷暖自知,有什么不可呢。写作不是一种抵达,写作就是有话要说啊。青春卖萌也说愁,只要活生生,还要生扯的什么意义吗。
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讲到,讲述了一个刚满十八年的“我”离家远行的故事,他远行到哪里,为了什么要远行?其实“我”根本不清楚。青春在接近一种虚无的状态下,“我”完成了一次旅行。我想这大概是所有人类似的青春吧。
写和不写对于青春无非是多了一种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多了一种情绪表达。我们能宣泄一切吗,青春没可能例外。
如果喧声嘈杂,即便读再多圣贤之书,知多识少也是可能,青春变成无迹可寻的假面具。对写作而言,众乐乐不如独享享。
阅读是纸上舞蹈,哑剧的一种,读者只是配音员,从心底发音的。
而低下头生活,日常荒诞不经,写作者要做那个魔术师,生活逼真(不是逼真生活),这样的荒诞就在我们的身边。刻意虚构,写作会成为表演的一种,有人以为是想象的力量,给自己插了个翅膀。写实是最大的想象,因为在我的身边,每天有太多不可想象的事发生着……
不可想象是作家无法想象的。作家的写实就在身边,大事小事,每个人都是这个世道的扮演者,我们就是记录他们。
现在是该割掉青春这条尾巴的时候,虽然它看起来漂亮而诱人,但是割掉它们,我们可以站起来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