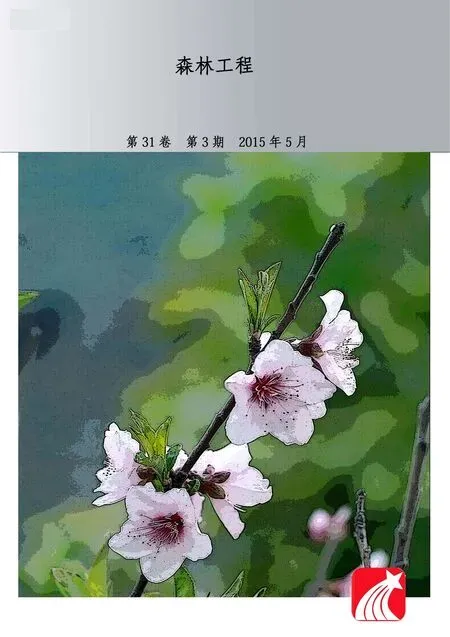大兴安岭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研究
大兴安岭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研究
陈璐,辛颖,赵雨森*,刘邵宇,李昂
(东北林业大学 林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要:为了探讨森林火灾对土壤抗冲性的影响,以大兴安岭地区三种不同火烧强度的火烧迹地为研究对象,采用原状土冲刷法对土壤抗冲性进行测定,并结合枯落物蓄积、持水性能及植物根系差异变化进行综合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火烧迹地的土壤抗冲性显著低于未过火地段(P<0.01),随着火烧强度的增加,土壤的抗冲性能逐渐减弱,抗冲系数总体变化趋势为:重度火烧迹地<中度火烧迹地<轻度火烧迹地<未过火天然林。四种样地类型的枯落物蓄积量总体趋势为轻度火烧迹地<中度火烧迹地<重度火烧迹地<未过火天然林。4种样地类型的枯落物最大持水率及有效拦蓄率皆表现为重度火烧迹地<中度火烧迹地<轻度火烧迹地<未过火天然林。在浅层土壤中,重度火烧迹地的根密度及根系总长度均值皆为四者中最小。研究表明:未火烧天然林的土壤抗冲性表现最优,重度火烧迹地的土壤抗冲性能最弱,应与及时治理与植被恢复。
关键词:大兴安岭;火烧迹地;火烧强度;土壤抗冲性
中图分类号:S 7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05X(2015)03-0021-04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orest fire on soil anti-scourability,the burned areas under three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in Greater Xing’an Mountains were selected.Soil anti-scourability was determined through original soil scouring method.Furthermore,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made through the difference of litter accumulation,water holding capacity and the change of plant root.The results showed that:Soil anti-scourability of burned area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unburned areas(P<0.01).As fire intensity increased,the overall trend of soil anti-scourability was severe Keywords:Greater Xing’an Mountains;burned areas;fire intensity;soil anti-scourability 收稿日期:2014-11-11 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D08B02);东北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1310225017) 作者简介:第一陈璐,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通讯作者:`*赵雨森 ,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E-mail:zhaoys1957@163.com Study on Soil Anti-scourability of BurnedArea in Greater Xing’an Mountains Chen Lu,Xin Ying,Zhao Yusen*,Liu Shaoyu,Li Ang (School of Forestry,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Harbin 150040) 引文格式:陈璐,辛颖,赵雨森,等.大兴安岭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研究[J].森林工程,2015,31(3):21-24. 土壤抗冲性是指土壤抵抗径流对其机械破坏和推动下移的性能,是土壤侵蚀机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定的径流作用下,土壤的抗冲性大小反应了土壤抵抗径流冲刷侵蚀的能力,土壤抗冲性越大,土壤抵抗径流侵蚀的能力就越大[1]。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北方森林集中典型分布区,在改善和维持森林生态平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保持我国森林覆盖率和木材生产方面功不可没[2],同时也是森林火灾的高发区[3]。林火导致森林生态环境剧烈改变,对土壤产生很大的扰动,不仅影响土壤的渗透性能[4]、容重等物理性质[5],也显著地改变了土壤的化学以及生物学特性[6-11]。在1987年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后,不同地段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土壤侵蚀[12]。因此,深入研究大兴安岭地区火烧对土壤抗冲性的影响十分有必要,有利于保护大兴安岭地区的水土资源,为火烧迹地植被恢复提供理论依据。 1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大兴安岭北坡的阿木尔林业局,南与呼中林业局、内蒙的满归林业局接壤,西与图强林业局毗邻,北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地理坐标为北纬52°15′~53°33′,东经122°38′~124°05′,平均海拔高为500~800 m。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长而严寒,夏季短暂而湿热,年平均气温为-5℃,年降水量约432 mm,年无霜期为90~120 d。本区地带性土壤为棕色针叶林土,此外还有暗棕壤、草甸土、沼泽土、泥炭土等。乔木树种主要有兴安落叶松(Larixgmelini)、樟子松(Pinussylvestrisvar.mongholica)、白桦(Betulaplatyphylla)、山杨(Populusdavidiana)等。灌木主要有兴安杜鹃(RhododendrondauricumL.)、越橘(Vacciniumvitis-idaeaL.)、刺玫(RosadavuricaPall.)、杜香(Ledumpalustrevar.dilatatum)等。 2研究方法 以2011年发生火烧的落叶松天然林为研究对象,选取毗邻的立地条件基本一致的未火烧天然林作为对照。2013年8月,按照火烧程度的不同分别选取轻度、中度和重度火烧迹地,分别设置3块面积为20×30 m的临时标准样地进行样地调查(表1)。火烧时地被物基本烧毁,重度火烧迹地地表裸露,植被无恢复;中度火烧迹地有少量草本生长,主要为小叶章(CalamagrostisangustifoliaKom.)、羊胡子苔草(CarexcallitrichosV.Krecz)等;轻度火烧迹地草本植物已更新,草本多为小叶章、羊胡子苔草、大叶柴胡(BupleurumlongiradiatumTurcz.),有少量兴安杜鹃、越橘等灌木矮小幼苗生长。 表1 试验样地基本概况 Tab.1 Basic situ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field 土壤抗虫性试验采用原状土抗冲槽冲刷法,抗冲性样品采集工具为矩形取样器,其规格为20 cm(长)×3 cm(宽)×4 cm(高),配有活动上下盖,取样器下端开有刃口,以方便取样[13]。每个标准地内用采样器采集4~6个0~10 cm层原状土试验样品,冲刷架为可调节坡度支架,根据试验地坡度将冲刷坡度设置为10°,通过特制供水桶控制流量,冲刷流量为1.7 L/min,为保持压力恒定,供水桶内水面高度不得低于桶高的三分之一。土壤的抗冲性用土壤抗冲系数(K)来衡量,定义为每冲走单位干土重(M)所需的水量(Q)和时间(t)之乘积,即 K=(Q/M)·t[14]。 土壤抗冲性实验结束后,将剩余土样置于孔径为0.25 mm的土壤筛中冲洗,将洗出的根系置于105℃条件下烘干,测量不同径级的根系数量,总长度及干重[15]。 在每个标准地内分别设置3个50 cm×50 cm的样方,测量并记录每个样方内枯落物未分解层和半分解层厚度,并分别收集样方中的枯落物。枯落物带回实验室后即刻称重,然后在80℃下烘干至恒重,再次称重。以干物质质量推算不同火烧迹地枯落物的含水率及蓄积量。采用室内浸泡法,将烘干后的枯落物装入网袋,并浸入盛有清水的容器中浸泡24 h,称重后计算其持水量。根据枯落物的最大持水率和平均自然含水率计算最大拦蓄率,公式为: 最大拦蓄率=最大持水率-平均自然含水率 有效拦蓄率=0.85×最大持水率-平均自然含水率 有效拦蓄量公式为: W =(0.85Rm-Ro)M 式中:W为有效拦蓄量(t/hm2);Rm为最大持水率(%);Ro为平均自然含水率(%);M为枯落物蓄积量(t/hm2)[16]。 3结果与分析 由图1可知,不同强度火烧迹地的土壤抗冲性差异极显著(P<0.01),随着火烧强度的增强,土壤的抗冲性能明显减弱,综合四种土地类型对比分析:重度火烧迹地的土壤抗冲性最弱,其次为中度火烧迹地,轻度火烧迹地为再次,未火烧天然林土壤抗冲性为最优,且显著高于火烧迹地。重度火烧迹地土壤的抗冲系数最小,只有0.40 L·min/g。未发生火烧的天然林土壤抗冲系数为10.29 L·min/g,是重度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的25.5倍。中度火烧迹地土壤抗冲系数为0.51 L·min/g,稍强于重度火烧迹地,是其抗冲系数的1.3倍,但仍极显著低于未发生火烧的天然林(P<0.01),仅为对照样地的1/20。轻度火烧迹地的土壤抗冲系数为2.03 L·min/g,分别为重度火烧迹地和中度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的5倍和4倍,但是仍远远小于对照样地,其抗冲系数为对照样地的1/5。 图1 不同强度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 Fig.1 Soil anti-scourability of burned areas under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高强度的火烧不仅将地表植被烧毁,使其化为灰分,地下火也同时将浅层土壤中的根系、土壤动物及微生物燃烧殆尽,土壤失去地被物的覆盖变得裸露,根系无法固结土壤,从而使土壤的理化性质发生了改变,因此土壤的抗冲性能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轻度火烧对森林植被的烧毁程度较轻,只烧毁了地表枯落物、草本植物及部分灌木,一部分植物根系并未化为灰烬,对土壤仍然起着一定的固持作用,降低了雨水击溅及径流冲刷对土壤的侵蚀。而轻度火烧下土壤中存活下来的土壤动物及微生物,能够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促进地表植被更新,从而减轻林火对土壤抗冲性的影响。 森林火灾将林地原有的枯枝落叶全部烧毁,只有火烧后新凋落的枯落物,枯落物的组成、厚度和储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表2可看出,未发生火烧天然林内枯落物的厚度、含水量与总蓄积量均高于过火地段。对照样地枯落物蓄积量分别是重度火烧迹地、中度火烧迹地、轻度火烧迹地的3.1、7.5及9.4倍。由于林火发生时火焰未将所有高大乔木的树冠烧毁,火烧后第二年调查时,大量烧死木的枯枝凋落到地表,形成未分解枯落物层,导致重度火烧迹地的枯落物蓄积量为三种火烧迹地中最大。未火烧天然林枯落物层较厚实,含水量较大。 表2 不同强度火烧迹地枯落物蓄积量 Tab.2 Litter storage capacity of burned areas under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枯落物的持水能力一般用干物质的最大持水率、最大持水量表示。枯落物最大持水量是由其最大持水率和蓄积量决定的,反映了林分的持水能力。从表3可看出,未发生火烧天然林枯落物持水能力高于火烧迹地,其最大持水率分别为重、中、轻度火烧迹地的2.9、2.7和1.9倍。火烧使林地枯落物储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影响了枯落物有效拦蓄率。火烧程度越大,火烧迹地枯落物有效拦蓄率越小。虽然重度火烧迹地的枯落物最大持水率,最大拦蓄率及有效拦蓄率却为最低,分别为对照样地的0.35、0.36和0.37倍,但是由于其枯落物蓄积量大,导致最大持水量、最大拦蓄量及有效拦蓄量也为三种火烧迹地中最大。 表3 不同强度火烧迹地枯落物持水能力 Tab.3 Water-holding capacity of burned areas under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林下枯落物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抑制水流对土壤的冲刷。枯落物可以通过改良林地土壤结构、影响植物根系含量强化土壤的抗冲效应。林火发生时,地被物被烧毁,枯落物层被碳化为灰烬,成为火烧迹地地表碳层的主要成分。当枯落物失去其作用时,雨水直接接触地表对其冲刷。碳层疏松多孔且拦蓄能力极低,易于冲走,使得雨水与土壤直接接触,造成土壤侵蚀。 植物根系的固土机制,是植被抑制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功能。植物根系通过对土壤缠绕、固结,阻止土粒分散,并改善其理化性质,来提高土壤的抗冲性[17-18]。在土壤表层中,细跟分布较为广泛,其主要来源于矮小灌木及草本植物[19]。林火发生时,地表火将枯落物层及表层细小根系烧毁,导致表层土壤中根含量较少,对照样地的根密度显著(P<0.01)高于火烧迹地(见表4)。由于土壤中细小根系更容易被烧毁,因此未火烧样方内的小于0.2 cm径级的根系生物量及总长度均高于火烧迹地。 表4 不同强度火烧迹地植物根系特征 Tab.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roots in burned areas under different fire intensities 在表层土壤根系分布中,四种样地类型的小于0.2 cm径级的根生物量及总长度均大于0.2~0.5 cm径级。通过4种样地类型的不同径级根系含量百分比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细根须根比粗大根系更能起到固持土壤的作用。其中重度火烧迹地中小于0.2 cm径级的根生物量占根总生物量百分比最低,仅为88.49%,而其他3种样地类型的百分比都在90%以上。虽然中度火烧迹地的小于0.2 cm径级的根生物量占根总生物量百分比最高,达到93.93%,但是其小于0.2 cm径级根总长度占总根长度均值百分比较低,由于较长根系在林火发生时被破坏,短小根系对土粒的盘绕作用较弱,导致了土壤的抗冲性能降低。在小于0.2 cm径级根总长度占总根长度均值百分比中,重度火烧迹地的比值与中度迹地基本持平,但仍低于轻度和未火烧样地的1%左右。在表层土壤中,无论是火烧迹地还是未火烧林地,主要都是由广布分散的细根、须根通过对土壤的盘绕固结来起到固持作用,从而增强土壤的抗冲性;而未火烧天然林内的表层土壤中根系分布更为紧密,根密度、总生物量及总长度也高于火烧迹地,因此土壤的抗冲性能更加优异。 4结论 森林火灾发生后,土壤的抗冲性能显著降低,重度火烧迹地的抗冲性能最弱,抗冲系数仅为0.40 L·min/g,未火烧天然林的抗冲系数为10.29 L·min/g,是重度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的25.5倍。林火使地表枯落物层被烧毁,蓄积量减小,其对降水的拦蓄作用也随之大幅度减弱,使地表土壤失去了枯落物未分解层和半分解层的有效保护,变得裸露、易冲刷。土壤浅层根系遭到破坏,使总根系生物量和总长度减小,导致对土壤的盘结、固持作用降低,削弱了土壤的抗冲性能,加大了土壤侵蚀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森林火烧迹地应予及时的治理与植被恢复,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邹翔,崔鹏,陈杰,等.小江流域土壤抗冲性实验研究[J].水土保持学报,2004,18(2):71-73. [2]康文发,张建云.关于对大兴安岭林区森林资源管护问题的商榷[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04,27(1):36-38. [3]白爱芹,傅伯杰,曲来叶,等.大兴安岭火烧迹地恢复初期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J].生态学报,2012,32(15):4763-4771. [4]Horton J S,Kraebel C J.Development of vegetation after fire in the chamise chaparral of southern California[J].Ecology,1995,36(2):244-262. [5]胡海清,刘洋,孙龙,等.火烧对不同林型下森林土壤水分物理性质的影响[J].水土保持学报,2008,22(2):162-165. [6]王雨朦,高明,董希斌.大兴安岭火烧迹地改造后土壤化学性质研究[J].森林工程,2013,29(1):21-25. [7]胡海清.林火与环境[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0. [8]罗菊春.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2,24(5):101-107. [9]蔡文华,杨健,刘志华,等.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区火烧迹地森林更新及其影响因子[J].生态学报,2012,32(11):3303-3312. [10]孔繁花,李秀珍,尹海伟.大兴安岭北坡林火迹地森林景观格局的变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9(2):33-37. [11]王绪高,李秀珍,孔繁花,等.大兴安岭北坡火烧迹地自然与人工干预下的植被恢复模式初探[J].生态学杂志,2003,22(5):30-34. [12]张洪江,关君蔚.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后水土流失现状及发展趋势[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88,10(1):33-37. [13]赵雨森,王克勤,辛颖.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实验教程[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3. [14]景小元,张淑莉,张爱国.土壤抗冲系数测时标准问题探讨[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26(2):91-93. [15]陈晏,史东梅,文卓立,等.紫色土丘陵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抗冲性特征研究[J].水土保持学报,2007,21(2):24-27. [16]胡淑萍,余新晓,岳永杰.北京百花山森林枯落物层和土壤层水文效应研究[J].水土保持学报,2008,22(1):146-150. [17]王库.植物根系对土壤抗侵蚀能力的影响[J].土壤与环境,2001,10(3):250-252. [18]熊建平,熊建红,郑育桃,等.营林用火对针叶林地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研究[J].江西林业科技,2014(4):8-14. [19]唐小智,孙泽平,兰立达,等.炼山对华西雨屏区杉木采伐迹地土壤理化特征的影响[J].四川林业科技,2013(5):29-36. [责任编辑:李洋]
2.1 样品采集

2.2 土壤抗冲性测定
2.2 植物根系测定
2.3 枯落物蓄积量及持水量测定
3.1 不同强度火烧迹地土壤抗冲性的差异

3.2 不同强度火烧迹地枯落物持水性能的差异


3.3 不同强度火烧迹地植物根系状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