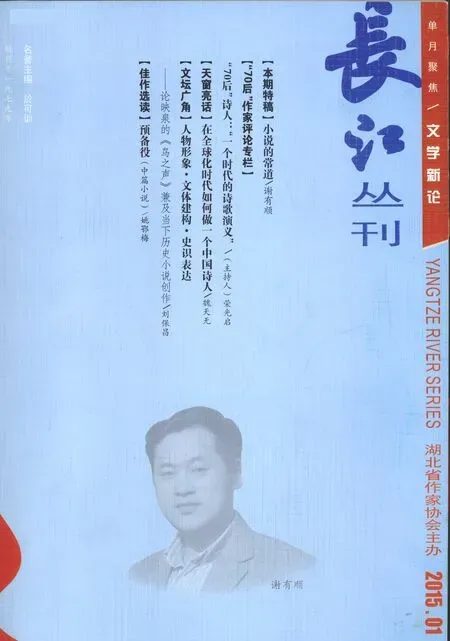朵渔:最“干净”的“下半身”诗人
巩瑜
朵渔:
最“干净”的“下半身”诗人
巩瑜

巩瑜,23岁,山西晋中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写作理论与实践硕士研究生。喜欢用相机记录一路的风景,喜欢尝试与分享美好的食物,喜欢在咖啡馆里安放天马行空的幻想……年轻的时候空气天真,我们都无所不能。
朵渔,原名高照亮,1973年出生于山东,1990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9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2000年与朋友们发起了“下半身”诗歌运动,影响巨大。新世纪以来,朵渔广泛参与了各种民间诗歌运动,主编民间诗歌刊物《诗歌现场》,并曾获得过多项民间诗歌奖项。他是中国“70后”一代的代表诗人,是民间诗歌写作的中坚力量。
谈起朵渔,“下半身”似乎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标签。大学时代的朵渔就曾创作出《高原上》、《河流的终点》等佳作,但却是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广为人知的。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下半身”诗歌的评价仍然毁誉参半,而且似乎批判、嗤之以鼻的态度更多,“下半身”诗人就像是背负着一个不良记录,但事实上“下半身写作”其实昭示了世纪之交以来“身体观念”的苏醒与转变。20世纪90年代似乎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诗歌不再是时代的号角也不再是艺术家的实验工具,更多的是慰藉自身的“精神怀抱中的乐器”、更多的是诗人感受自我和想象世界的一种心灵活动和语言能力,但此时的诗歌也恰恰回到了其本来的位置。于是一批“70后”诗人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在语言运用上也开始倾向于“口语”化,最受诗坛关注的尤数世纪之交的“下半身写作”。
在沈浩波、尹丽川等众多的“下半身”诗人中,朵渔看上去像是最“干净”的一个。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下半身就是指性的话,我的确是‘最不下半身’的”。虽然他的语言一样直指下半身,作品中同样不乏“做爱”、“阴茎”、“操”等直白的“下半身”字眼,但似乎并不会引起我们的反感,因为我们可以感受的到里面暗藏的人性的跳动,一种直指我们内心深处的力量。比如在《野榛果》中,作者主要写的是青春期“小兽般的冲动”:“在越省公路的背后,榛子丛中/我双手环抱?她薄薄的胸脯/一阵颤抖后,篮子扔到地上,野榛果/像她的小乳房纷纷滚落/她毛发稀少,水分充足/像刚刚钻出草坪的蘑菇”,充满诱惑、不可捉摸的青春冲动让人心跳加快,“而快感却像/地上的干果,滚来滚去/坚硬但不可把握”。这首诗写出了身体的隐秘冲动与无限激情,这不仅仅是经验的书写,更是对世界无穷的原动力的体现,让人内心不禁为之一颤。
用朵渔的话来说,“下半身”写作就是不再为“经典”而写作,而是一种充满快感的写作,一种从肉身出发,贴肉、切肤的写作,一种人性的、充满野蛮力量的写作。通过对身体和感官的书写,抛弃宏大题材的遮蔽,寻求一种在场的肉感,重新发现我们人性的灵光。朵渔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做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轻轻的爱抚,静静地回味,深刻但不骄傲,散发着真切而充沛的“感性”。虽然他不是最“下半身”的诗人,但却是最贴近“下半身”精神的诗人。
“民间知识分子写作”
在一次访谈中,朵渔曾说:“在‘民间’和‘知识分子’最为对立的那两年,有人问我属于哪一派,我说我是‘民间知识分子写作’。”想来也确实只有“民间知识分子写作”才可以代表诗人朵渔的身份与立场。
真正的诗人应该具有民间立场,只有书写“中国的、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避开权力的笼罩与异化,才能具有悲悯之心、温润之爱,写出具有生命力、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作品。朵渔没有局限在“下半身”诗歌团体对原始欲望毫无节制的追求,而是侧身转向了对生活本身的体查与领悟。他曾说:“诗歌绝对不是一项喧嚣的事业。它可以在某些时候属于广场,在某些时候属于咖啡馆,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时刻属于‘前排’、‘头条’,但更多的时候,它属于一个人的黑暗世界,属于‘钟的秘密心脏’。”
而同时诗人与知识分子也有着微妙的关系,诗人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朵渔,如果你只把他混同于现实和底层问题的揭示者显然是不够的,他的写作的精神性命题也足够大,足够“知识分子”。正如朵渔自己所言:“只要在这个时代还有那么多苦难和不公,还有那么多深渊和陷溺……那么,诗人的任何轻浮的言说、犬儒式的逃避、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就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于是,当我们看到《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今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这首诗如此刺痛神经,不是因为什么技巧,而是朵渔站在社会乃至生命的立场上,对诗歌在灾难面前的无力感的揭示和反思,诗人不该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诗歌现场》
“民间知识分子写作”是朵渔对于自身的清醒的准确的定位,同时更是一种自我要求与追求。在他的诗歌中,口语与书面语、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反叛精神和传统意识总是能够驾轻就熟地随意布阵。在论争过去的十多年后,我们发现朵渔确实是青年诗人中有“大才”之人,他的诗也逐渐彰显大格局与大气象。
为人生的写作

朵渔
朵渔将自己近二十年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8年到2008年。从1998年大学期间开始,朵渔写出《河流的终点》、《高原上》等短诗,高原上那“忧郁的眼神和孤傲的心”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写照,那时的他对文字、对诗歌有一种魔力般的神秘感。结识沈浩波、杨志等人后,于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作为一个最不“下半身”的诗人和最具“下半身”精神的诗人,他写出了《暗街》、《野榛果》、《我梦见犀牛》等短诗,可以看出他在诗歌新精神方面的自由探索,这是一个自我觉醒的初始阶段。“下半身”的写作阶段持续了两三年,他开始关注现实性、批判性的写作。这与身体意识的觉醒是一脉相承的,自我觉醒必然带来这种批判与反抗。2006年的短诗《妈妈,您别难过》就是这个批判现实阶段的代表作,给人触动至深,但他说:“这让人只是认识到了自己的分裂,却认识不到自己的罪。”
第二个阶段便是08年到现在,朵渔的自觉性变得更强,有了一些更深入的思考:一个诗人应该承担什么,应该为世界留下什么,应该怎么来完成自己的一生。从2013年出版的诗集《最后的黑暗》可以发现,朵渔的作品就比早期要急促许多,读者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危机感在内,这也印证了朵渔自己所言,“诗歌是生活的内分泌,有其自身的节奏和意绪”。
而在70年代出生的众多诗人中,朵渔是少数几个能用文章来表达诗歌观念的诗人,他从柏拉图、苏格拉底、中世纪的神学,一路读到近现代的哲学,同时撰写了许多文史随笔,出版了《生活在细节中》、《说多了就是传奇》等随笔集。他说:“阅读是为驱赶内心的黑暗,是为擦亮空气以便看得更远,也是为建构个人的诗学土层……研究历史可以改变你的时空观念,可以将你的目光拉远。很多诗人没有现实感,其实是因为缺乏历史感。”朵渔通过大量阅读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明确立场,通过文史随笔抒发社会担当,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一直在他所信奉的“为人生的写作”的道路上前行,正如他自己所言:“老老实实,不要输掉一颗心,这是为诗人的本分”。
“他坚守自由、真实的言说伦理,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尊敬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并试图由此重建诗歌的悲剧意识和现代汉语的尊严。在一个崇尚轻浅、速度的时代,朵渔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量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9年度诗人朵渔授奖辞)。朵渔的写作,就像是一朵渔火,渺小却固执,一点一滴擦亮黑暗,用诗歌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爱和光明,给人以拯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