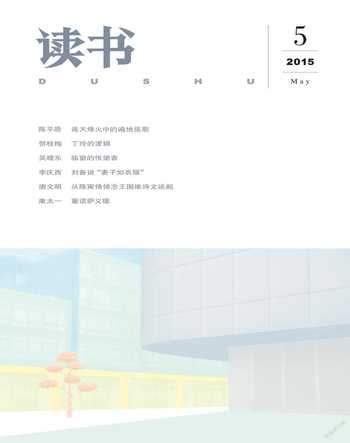俞平伯“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
袁一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俞平伯以为“目前南去并不明智,南方局势亦不平静”,“而且对人们说来,北平在不久的将来将是最安全处”,劝老友朱自清等待、观察一段时间。其任教的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同人纷纷南下,他正值轮休,便以侍奉双亲为由留居北平。一九三八年夏,休假期满,俞平伯收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寄来的聘书,又以父母年事已高,自己体弱多病为由婉拒,同年受聘于私立中国大学。一九三九年元旦遭狙击后,周作人准备接受伪北大的任职,想把他在燕京大学的教席让渡给俞平伯,俞婉言推辞。
沦陷时期俞平伯虽然没有出任伪职,在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上却不时可以见到他的名字,如柳龙光主持的《华北作家月报》,周作人挂名的《艺文杂志》,沈启无编辑的《文学集刊》及背靠汪伪政权、由龙榆生组稿的《同声月刊》等。但其发表的几乎都是纯文艺或考证性的札记,如《杜陵自比稷契申杜臆说》、《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左传震夷伯之庙一条非左氏旧文说》、《音乐悦乐同音说》、《词曲同异浅说》等。这些多半“不含政治色彩”的自娱之作,有的却可读出作者的心事怀抱,仅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为例。
一九四二年春,隶属于武德报社,有日伪背景的《万人文库》旬刊向俞平伯约稿,其《文园》专刊的编辑登门拜访,俞氏赠以考据之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 (《辛巳文录初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出自《论语·宪问篇》,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人矣”。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对此句的解释,称“久要旧约也,平日犹少时”,将“久要”理解为往日的约定。朱熹《集注》依从孔注对“久要”之解,仅把“平生”改释为“平日”。
按朱熹的说法,“久要”果为“旧约”,则与“平生之言”文义重复,俞平伯指出此句之疑点不在“平生”而在“久要”。受江绍原的启发,他引扬雄《法言·问明篇》中蜀庄“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与《论语》此处比勘,以为句式相似,不妨将“久幽”看作“久要”之注脚。“久幽”之“幽”,《法言》释作“沉冥”,俞平伯解为离群索居之义,并举“苏武之抗节异域”为例。“不改其操”则与“平生之言”相对,在内为操守,向外发为言辞,操守居常不变,言辞而冠以“平生”,在他看来,“皆平居暇日所养而验诸仓卒者也”,验而不应,怎可谓之“成人”?
俞平伯将他对“久要”一句之新解求正于其父,俞陛云赞同以“久幽”释“久要”的读法,但以为将“久幽”释为离群索居,仍不免被孔注“旧约”二字所缚。《论语》这三句乃“明修身行己之大端,非关于朋友间之要约信誓”。同样用《法言》与《论语》对勘,俞陛云着眼于句子间的结构关系而非字词之对应:“三句似平实侧,却分宾主”。换言之,“见利思义”与“见危授命”为并列关系,“久要”一句为前两事之实践,所谓“平生之言”,即指上文之“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同理,《法言》之“不改其操”即落实在“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上。两书勘合,词例相同,不然泛说“平生之言”,则没有用力处。
俞平伯以《法言》释《论语》,反驳孔注“旧约”之说,训诂学者杨树达则试图从《论语》中寻求内证来解释“久要”二字(《论语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积微居小学述林》)。其据《论语·里仁篇》“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一句,谓“要”与“约”同,“久要”即“久处约”也,“约”乃穷困而非期约之义,故“久要”一句应释为“虽久居困约而能不忘其平日之诺言”。
杨树达自认为以《论语》释《论语》比俞平伯之读法更为直截了当。且不论谁的解释更贴近原义,杨树达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是单纯的训诂考证,与具体的历史情境无关,而俞平伯的考据文章中却暗藏着他的心事怀抱,其对“久要”二字的新解与他沦陷时期的生存处境及随时可能面临的胁迫有关,所以应当将落在纸上的繁琐考证与此文发挥的社会功能—言志同时也是婉拒—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