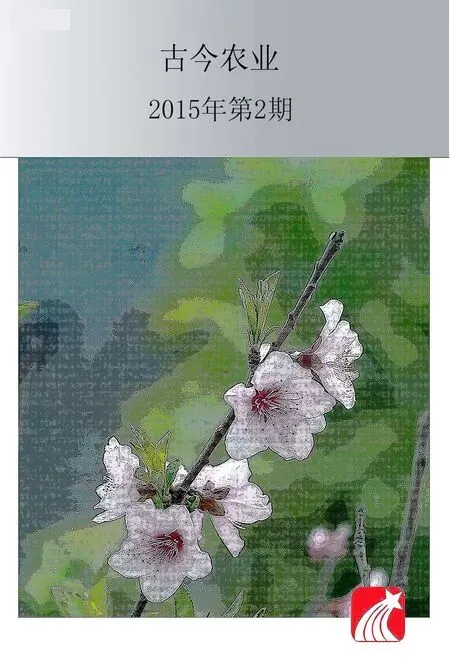黄河河道变迁对黄淮流域城市的影响
——以安徽省砀山县为例
李 娜 卢 勇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黄河河道变迁对黄淮流域城市的影响
——以安徽省砀山县为例
李 娜 卢 勇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迁”称著于世,北宋之前,以北流为主,南宋时起,改道南泛,淸咸丰五年之后,复北流。南泛期间,在黄淮大平原上来回滚动,对砀山河段变迁的考证,印证了河道多次变迁。黄河河道在黄淮地区的变迁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水灾频繁、摧屋毁稼,沙灾伴之、破坏环境,淹没城市、城址变迁,治理黄河、建设河防。
黄河;河道变迁;城市;砀山;影响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称为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五长河。它发源于我国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碦拉山脉北麓,流经黄土高坡,携带大量泥沙,水性重浊,以“善淤、善决、善迁”称著于世,“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就是黄河变迁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不同于其余河流的显著特征[1]。黄河决口泛滥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就多达1590余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黄河》一书提出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影响巨大的有6次。①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黄河》.1959年版.
砀山县坐落于安徽省最北部,处于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四省七县交界处,自秦设置砀郡及砀县以来,“为砀郡、为砀县、为梁国、为梁郡、为辉州,沿革多以代异,而封域亦尽变矣”②乾隆《砀山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于隋朝开皇十八年最终改名为砀山县,沿用至今。“芒砀山雄峙于前,黄河襟带于后,古为汴京唇齿,徐淮门户,素有九州通衢、天下要冲之称。”③砀山县政府网·砀山简介.http:// www.dangshan.gov.cn/class.php?classid=35.虽就目前的地理位置看来,与黄河并无关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砀山水系与黄河自古存在渊源关系,北魏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一书中就有明确的记载④郦道元著、史念海、曾楚雄等著,《水经注》卷二十三获水,华夏出版社,2006,第459页.,黄河南泛期间,砀山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关键部位,为徐州等重要城市的上游,一旦决堤,黄淮流域将大面积受灾,康熙、乾隆等皇帝尤为重视砀山河段的治理,曾数次亲自参与该地政策的制定,可以说这里是黄淮流域著名的黄泛区。
对于黄河河道的变迁,先贤多有研究,但多数是站在宏观的立场上,研究黄河主体,例如谭其骧对黄河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岑仲勉深入研究了黄河变迁史、程有为、姚汉源等专门研究了黄河尤其是其中下游地区的水利史、邹逸麟撰文分析了黄河河道的变迁以及其造成的影响、方建华探讨了黄河下游河道改道问题。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某一特定区域的黄河河道变迁研究,例如肖扬探析了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对徐州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李涛浅析了黄河河道变迁及其对商丘的影响。然而,关于黄河砀山河段的研究较少,稍有零星,也是侧重于黄河河道的开发和利用。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砀山为主体,厘清黄河在砀山境内的河道迁徙,深入分析河道变迁对当地产生的影响。
一、黄河河道砀山段的变迁
徐福龄指出所谓河道变迁,是指黄河大徙,或称大改道。即大河在沿河某处决口改道以后,不再回归原来河道,而是全部另由他道入海,其经流的时间较长,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比较严重。[2]他将黄河河道变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西汉初年(前206年)到宋靖康二年(1127年),黄河变迁范围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二是自宋建炎二年(1127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变迁范围皆在现行河道以南;三是自清咸丰五年(1855年)至今,为现行河道的演变过程。这三个阶段中,本文主要针对第二个阶段进行研究。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极其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北宋之前,黄河河道比较固定,以北流为主,“直至北宋末年黄河仍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3]。据明史记载:“黄河,自唐以前,皆入北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济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馀里。”①《明史》卷八十三《河渠一·黄河上》.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金兵占领了今河南安阳、濮阳和山东鄄城一带,为了阻止金兵继续南下,宋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扒开河堤,决河东流,经豫鲁之间,至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由泗入淮。②《宋史·高宗纪》.这次改道,是黄河变迁史上一次重大的变迁,掀起了其南泛720余年的开端。此后数十年间,社会动荡,堤防不坚,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③《金史》卷二十七《河渠·黄河》.。
在砀山境内有两条著名的河道,一条是贾鲁所开的“老黄河”,位于砀山城南,是明清时期所称的黄河故道,一条是潘季驯治理的“大黄河”,位于砀山城北,是现在所谓的黄河故道。黄河流经砀山以后,在砀山境内有数次河道变迁,黄河开始流经砀山城北,后又城南城北几经变异,最终固定在城北“大黄河”河道上。根据史料记载,笔者整理出黄河流经砀山期间,在境内变迁的过程,如表1所示。
金代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黄河决口于李固渡,开始分流,其中一股便是由单县之南,经虞城、砀山之北,由萧县至徐州入泗,这是黄河流经砀山的开始,在城北形成了最初的河道。此次分流之后,黄河“南流”占全河的十分之六,“北流”仅有十分之四[4]。金朝政府担心“骤兴大役,人心动摇,恐宋人乘间构为边患”⑤《金史》卷二十七《河渠·黄河》.,对黄河缺乏治理。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决口于山东省曹县白茅堤,淹没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十多个州县。此后几年,黄河又多次决溢泛滥,两岸百姓背井离乡,苦不堪言。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受命治理黄河,他采取了“疏通、开凿”双管齐下的策略,一面疏通黄河故道以及支流河道,一面开凿新河道,分流河水,贾鲁治理的河道成为“贾鲁河”,也称作“老黄河”。经过贾鲁治河,黄河改道流经砀山城南,《方舆纪要》云“黄河在城南三十里,即元贾鲁所开,由虞城入境,经狐父达杼秋城凡九十余里,又东出萧县小桥入泗”①乾隆《砀山县志》卷二《河渠志》.,狐父的地理位置即在砀山境内。这是黄河河道在砀山境内的第一次迁徙。
根据县志记载,自黄河改道城南之后的两百年间,虽有数次决溢泛滥,但不曾大规模迁徙,直到嘉靖时期,由于泥沙淤积严重,贾鲁河道逐渐废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河流变迁,将其经行一带淤塞,北徙距县二十里戎家口出徐州茶城入漕。”②乾隆《砀山县志》卷二《河渠志》.这说明,黄河河道此时由城南又迁徙至城北。③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编纂的《黄河水利史述要》中图文记载,金、元两代的河道位置与县志中记载一致,不过,明代前期的记载却与县志记载大相径庭,该书记载明代自洪武至正统年间,黄河河道一直在县北。然而,据乾隆年间本县县志记载,当时黄河河道应在县南。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春,山东巡抚黄克缵于蒙墙掘开黄河,“决口广八十余丈”④《明史》卷八十四《河渠二·黄河下》,后河决朱家旺口,“黄河故道已复”⑤《明史》卷八十四《河渠二·黄河下》,此黄河故道即是位于城南的老黄河,可见再次改道城南。“黄河原在砀山县南。因明大学士沈鲤奏称黄河水经凤阳恐惊皇陵,且入海迤远,议定将黄河自虞城东之黄堌坝堵塞,改开新河于砀城之北。”⑥乾隆《砀山县志》卷二《河渠志》.于是,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黄河再次改道城北。至此,黄河河道在砀山境内的迁徙告一段落,河道基本固定在砀山之北,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在河南省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决口,河道北徙,离开砀山,穿大运河由山东夺大清河入渤海,这也是清末黄河河道的一次大变迁。
二、黄河河道变迁对砀山的影响
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是淮河流域的几个重点省份,自黄河南下夺淮入海以来,成为了黄淮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长期遭受黄河决溢之害。首先,洪涝灾害频仍,推屋伤稼,人口损失严重,河南开封,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淮河流域内的黄河一次决口造成的人口损失就高达数十万⑦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其次,地形地貌改变,河流湖泊消失,13至19世纪期间,黄水荡涤过的广大平原和冈丘,数万平方公里地域普遍淤积厚4米左右,个别城市地带淤厚达10米以上;⑧卢勇:《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据考古工作者发现,开封龙亭东侧潘湖湖底以下一米,距地面约四米的地方,挖出了明代周王府的房舍,经研究就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黄河在开封决口所淤埋[2];历史上有记载的诸如圃田泽、菏泽、巨野泽等许多湖泊,均被淤积成平陆。此外,土壤沙化、盐碱化严重,导致土地流失,甚至耕作改制,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为避免水患影响,趋利避害,当地耕作制度发生了嬗变”⑨卢勇:《明清时期淮河水患与生态社会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还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粮食产量的普遍降低,使得昔日富庶的徐淮地区成为有名的贫瘠之乡。
史料显示,黄河流经砀山之前,砀山是个物产丰富、人民富庶之地。例如《史记》记载:“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①《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就是说的梁孝怀在砀郡为王的情形。明刊《徐州志》中说:“古徐州物产之饶,甲于寰宇”②《徐州志》,这正是包括砀山在内的整个徐州的情况。然而,黄河水患彻底颠覆了当地的优势,导致“今疆土非昔,而洪水岁复为殃,水陆之产皆萧索而失生”③《徐州志》。总之,河溢在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等多个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一)水灾频仍,生产生活受损
说到黄河造成的影响,首当其冲,应属黄河决溢造成的洪涝灾害,河道淤积是决溢的主要原因之一。北宋欧阳修曾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游,下游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游之低处,此势之常也。”④《宋史》志四十四《河渠志一·黄河上》清代靳辅也认识到:“河决于上者,必淤于下,而淤于下,又必决于上。”⑤(清)靳辅:《治河方略》.自黄河流经砀山以来,“砀罹水患数矣”⑥乾隆《砀山县志》卷一《舆地志·星野·附祥异》.。笔者根据地方志和相关文人笔记等史料记载,对自金大定八年至清咸丰五年的决溢情况进行统计,金元、明、清三个阶段的数据呈递增趋势,其中金元期间5次,明朝时期12次,清朝达到顶峰,有21次之多,详情见表2。

表2 金大定八年至清咸丰五年间砀山境内河溢情况统计表⑦表中资料来自乾隆《砀山县志》和1985年《砀山县志》

(续)
有学者分析,此间水患逐渐增多,原因之一是治水技术的限制,二是治水思想的牵绊,对此本文不作详述。但“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庐,坏禾稼,百姓已罹其毒”①《元史》卷六十五《河渠二·黄河》.的严峻事实不容忽视,黄河决溢给砀山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据元史记载:“至正四年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②《元史》卷六十六《河渠三·黄河》.当时有人写下了一首诗歌,内容就是反映这次灾情,其中有这么几句“季来河流失故道,垫溺村墟决城堡,人家坟墓无处寻,千里放船行树杪”③元道贤《新堤遥》,见《诵芬室丛刊·金台集二》.。
但是表中数据仅仅是根据方志等相关史料中对砀山水患有着翔实的记录整理的,实际上,史料中也没有将当时水患情况完全记载,尤其是金元至明代前期,而且有些记载也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泛滥范围,只是提到某地区、某城市等,其实根据地理位置及灾情推测,可以看出辐射范围不仅仅是史料中提到的地方,例如,对于文献中“开封等州县”的记载,虽然只能作为开封一个地区统计,事实上不止开封一处,可见,当时造成的灾害远比表中统计严重得多。
明清时期黄淮流域的水患,常常导致多灾并发,蝗灾、瘟疫随之而来,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人口损失。以明朝崇祯年间为例,自崇祯四年(1631年)以来,经历过大雨、大水以后,作物减产,粮食欠收,“民饥”④乾隆《砀山县志》卷一《星野》.,而后,几乎连年蝗灾,民不聊生,终于十三年(1640年)冬,“土寇群起”⑤乾隆《砀山县志》卷一《星野》.,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大饥,先食树皮及各草子,渐至食人,初犹避忌,后且公然不为异,甚有父子、兄弟、夫妻相食者”⑥乾隆《砀山县志》卷一《星野》.,“冬复大疫,田野荒芜”⑦乾隆《砀山县志》卷一《星野》.,当年全县人口“二万三千九百零三十丁,死于饥、死于疫、死于寇凡一万七千六百零三丁,仅存六千三百二十七丁。”⑧乾隆《砀山县志》卷五《赋役志·户口》.。由此,笔者认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固然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然而由于灾情严重,致使粮草供应严重不足,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荡没城址,县治数次变迁
砀山在秦汉时就为郡,其城历史悠久。然而后世多次城毁,据史料记载,砀山县城一共六次城毁,其中三次是因为兵事及火灾,但是没有城址迁移的记载,只是在原址上重建,而另外三次则全部是因为水患。笔者根据史料记载,整理了砀山县城城址变迁记录。如表3所示。

表3 砀山县城城址变迁统计表①表中数据来自于乾隆《砀山县志》和1985年《砀山县志》.
如上表所示,砀山县城城址第一次为洪水所毁是在金兴定五年(1221年),砀山罹患水灾,县城被洪水荡没,县城迁至虞山保安镇(今永城县保安镇),清乾隆年间“其地时刻‘砀山县'三大字及儒学棂星门石柱犹存。”②乾隆《砀山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元宪宗七年,方还旧地下邑,尚未建城。明正德八年(1513年),知县李金创筑土城,后来因为河患稍有坍塌,嘉靖中副使王梃令重修,植柳其上,二十六年(1547年)知县王绍元又请增筑,重植柳以为障。不幸地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河决陷没,城堤仅存遗址”③乾隆《砀山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县治迁于小神集。后于嘉靖四十四年,县治迁回原址。隆庆年间,知县王廷卿重创筑土城,建五门。可惜万历二十六年(1600年)秋,“又为水没,基址当然无存”④乾隆《砀山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县治复迁至小神集。知县熊应祥改迁旧城,于城西三里秦家堂筑新城,仍为土城,万历二十八年(1602年)竣工,始有规模,后又经几番改建、修筑,即为今砀城所在之地。
另外,黄河流经还影响了砀山县的政区隶属关系,据金史志记载,“单州砀山县,兴定元年以限河不便,改隶归德府”⑤乾隆《砀山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金末为河水荡没,元初复置时已改隶河北的济宁路。可见,黄河决溢对砀山县城城址变迁造成的影响之大,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三)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更迭
黄河多泥沙,“河水一石,其泥六斗”⑥《汉书·沟洫志》.,自古便有“浊河”⑦《战国策·燕三》.之称。陈潢指出:“平时之水,沙居其六,一入伏秋,沙居其八。”⑧(清)靳辅,《治河方略·湖流地五》.黄河携带的大量黄沙流经砀山平坦之地,黄沙日益沉积,且黄河多次改道和决溢,导致砀山大面积遭受河患,河水退去,黄沙却留在了河水经过的地方。因此,黄河决溢给周边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洪涝灾害,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沙灾。正如邹逸麟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每次决口后洪水泛滥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自不待言。洪水过后,大量的泥沙沉积在平原上,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致使自然水系紊乱,比如原来的湖沼被填平,天然的河流被淤浅,宣泄不畅的地方又将原来的洼地改变成了湖泊,大片的沙地、沙丘和岗地、洼地留在了平地上。[3]
首先,黄沙淤平了原有的河流,造成了当地水系的更迭。“河道之系于民生大矣。”⑨乾隆《砀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砀山县河道图记》.据记载,黄河流经砀山之前,砀山境内有多条河流,但在黄河流经之后或逐渐淤塞消失,或易音改名为它。县东七十里有盘岔河,今淤;县西南五十里有夹河,为元末刘福通迎韩林儿为帝之处,今淤;县西九里有九里沟河,今淤;县东北二十余里有羊耳河,今淤;县南五十里有雎水,县东南有徐溪口,雎水自永城县经徐溪口,又下东南入萧县界,明嘉靖中自徐溪口至永城俱成平陆;还有白川河、新岔河、李河、桑叶河等数条河流也无处可考;而新泽汇或指为小神湖,雁池或指为华池。①乾隆《砀山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天子巡幸江南,“亲见淮徐上下汙莱弥望,岁警水荒,恻然深念”②乾隆《砀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砀山县河道图志》.,命重臣循流溯源,大修河道,“砀邑得河道七”③乾隆《砀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砀山县河道图志》.。其一自县西北经虞城、夏邑、永城入淮为减水河,也就是老黄河;其二自毛城铺南经萧县入淮为洪沟河;其三自西北经县城北入减水河为利民河;其四自县南有小神湖入减水河为永定河;其五自毛城铺东北沿堤入萧县为文家河;其六自吕公堤顺流入萧县为顺堤河;其七在大河之上,北承西水以入于丰铜沛达于微山湖为华家坡河。其中,洪沟、减水、华家坡三条为干流,其余四条均为支流。④乾隆《砀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砀山县河道图志》.至此,砀山境内水系“经纬井然,脉络连贯,淫潦之水得有所归,无横溢弥漫之患。”⑤乾隆《砀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砀山县河道图志》.
其次,由于地面上沉积的黄沙结构比较松散,一遇大风起,便会出现黄沙漫天的沙尘暴现象。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县志中出现有关沙尘暴的记载,“黑风起,自西北黑气疑云,有声渐近,日色全晦,白昼如夜。反刀枪之属有火光。约三四刻,北风息,黄沙满地,厚寸许。”⑥乾隆《砀山县志》卷一《舆地志·祥异》.黄沙浊水还可以改变当地的土壤性质,来自河水的沉积物在一定的时间内对土地有一定的肥力,但是如果沙质过粗,尤其是长期排水不良而引起的盐碱化,则给农业带来很大的损害。[3]“河流甘淡,井泉斥卤,白坟十九,赤埴十一。”⑦乾隆《砀山县志》卷一《舆地志·水土》.可见,盐碱地竟多达占了十分之九。
(四)黄河治理,建设河防系统
砀山河段在《中国水利史》一书中被郑肇经称“为第一要害之地”,如若砀山北岸决堤,水入南四湖(今微山湖),沿线丰、沛、铜等遭灾,漕运也会受阻,若南岸决口,洪水就会进入洪泽湖,沿线及淮扬一带受灾,“此水下注,不特凤徐淮属县漫淹,而水全归洪泽湖,撼掣高家堰,高家堰一有不支,则全淮东泄,黄蹑其后,而清口淤,运河垫,清水潭等工皆不可保矣。”⑧乾隆《砀山县志》卷二《河渠志》.于是,地方政府和民间都十分重视治水防河,尤其是到了清朝,政府更是把砀山河段治理多为黄河治理工程的重中之重,史上多位皇帝如康熙和乾隆曾亲自数次参与规划砀山河段的治理工程,上有天子的亲力亲为,下有治河大臣的不懈努力,使得河防体系日益完善。
自古“水为中国患”⑨《元史》卷六十四《河渠一》.,是因为“其患之不可测”⑩《元史》卷六十四《河渠一》.。既然不可测,只有时刻加强防范。砀山位于黄河之滨,是丰、沛两县的上游,关乎下游的安危,故“防河为最急”⑪乾隆《砀山县志》卷二《河渠志》.。砀山境内修建的河防体系主要有黄河两岸大堤、毛城铺坝、石林口坝等。元、明两代在治河上,以保漕运为主,堤防方面,重北轻南。元至正三年(1343年),河决曹县白茅堤,八年后,方堵和决口,修筑了从白茅至砀山北岸堤防,明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治河,又在黄河北岸修筑了遥堤,上至河南胙城(今延津县),下至江苏丰县,以防大河北犯漕运,名曰太行堤。明代初期,砀山南岸没有大坝,“丰沛萧砀黄河南岸地形高仰,水发出岸无忧,不必堵遏。”①傅泽洪,《行水金鉴·河水》.中国水利要籍丛编第一集,文海行印出版社出版.明隆庆年间“创筑南堤,工始自祥符,下迤于砀山治北,而砀山以下之南岸,尚空之弗堤,六以为涨水回旋之余地”②《河史述要》.,又修筑黄河北岸大堤,高一丈二尺,顶宽三丈,西自山东单县界,东至丰县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修筑黄河南岸大堤,“高一丈二尺五寸,宽六丈乌尺,顶宽二丈,西从河南虞城界东至萧县界,缕堤长一万四千四百十六丈八尺”。③乾隆《砀山县志》卷二《河渠志》.毛城铺石坝用于调节和控制黄河决溢时的南岸之水,是一项重要枢纽工程,关系到下游多个州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石林口坝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宣泄黄河盛涨之水,防止北岸漫溢决堤,保障下游地区丰、沛、铜山等地的安全。④曹天生,《砀山黄河故道文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河防工程不仅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患,减轻了洪水对当地生产和生活的影响,还影响了当地村庄的命名,反过来,也可以发现村庄的命名特征正式反映了当时河防的建设影响。据统计,砀山县内带“堤口”的村庄有十五个,如刘堤口、官堤口等,像马路口等带“路口”的有九个,带“河套”的有七个,带“坝堰”的有五个,另外还有四个黑龙潭、五个夹堤湾,还有一些用“圩”、“台”等相关词进行命名的村庄。[5]
三、结语
黄河南泛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对周边城市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由黄泛平原城镇地方志可以看出,每座城镇的建设史都是一部应对黄河洪涝灾害的城镇变迁史,每座城镇都有被黄河冲决、淹没或被迫迁移的历史记录。[6]在黄河流经砀山近700的时间里,记录在册的共有38次决溢,三次毁城,使得水系更迭、城址迁移、环境恶化,给砀山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为了抵御黄患,砀山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筑起黄河南北两岸大堤,修建多处闸坝,疏导河水,助清刷黄。黄河虽然北徙离开了砀山,可是黄河故道依然存在,县内河道全长46.6公里,河道面积277.8平方公里⑤砀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砀山县志》.方志出版社,1985:118.,是砀山县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梳理黄河河道变迁过程,分析对周边城市的影响,笔者认为,黄河迁徙无常,难于治理,不仅要了解黄河河道的历史变迁规律,还要研究今后的演变趋势,多层次全方位综合治理,以保障沿河地区安全无虞,正所谓“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应及千里之外;治目前之河者,推算应在百年之后”[2]。而且从黄河南泛的历史教训中发现,即使现如今不流经的地区,依然要加强防范,做到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基金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以来的淮河水灾与治淮思想变迁研究”(编号: 13BZS07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时期淮河水灾与救灾机制研究”(编号:11YJC770034);3、校人文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方志内容挖掘及知识组织研究”(编号:SKZD201401)。]
[1]贾国静,二十世纪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8(03):146-155.
[2]徐福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概述.人民黄河,1982,03:46-49.
[3]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S1):12-24.
[4]孔祥淮,薛春汀,刘健,1128-1855年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对中国东部海域的影响.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11(05):25-36.
[5]张超男,明清黄河堤防技术及管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0.
[6]许继清,韦蜂,胡泊,黄泛平原古称“连环湖”与城市防洪减灾.人民黄河,2011(9):3 -4.
The impacts on the Huang- Huai cities caused bychanael shifting of Yellow River——Taking Dangshan County,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Na Lu Y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The Yellow River is well- known for being good at siltation,outmigration and burst in the history.Befor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main stream is in the north. After Southern Song,the channel changed to the south until the fifth year of Xianfeng in Qing Dynasty,and from then on,the channel shifted to the old course.During Yellow River flowing in the south,it rolled back and forth on the Huang Huai great plain.The research on the channel change in Dangshan confirms that the Yellow River changed many times in the history.The changes caus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area,such as the frequent floods destroying house and crops,sand disaster caused environment destruction,cities emerged and changed,Yellow River control and construction of Hefang.
Yellow River,channel shifting,city,Dangshan
李娜,女,(1985-),安徽宿州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史;卢勇,男,(1978-),江苏泰州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水利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