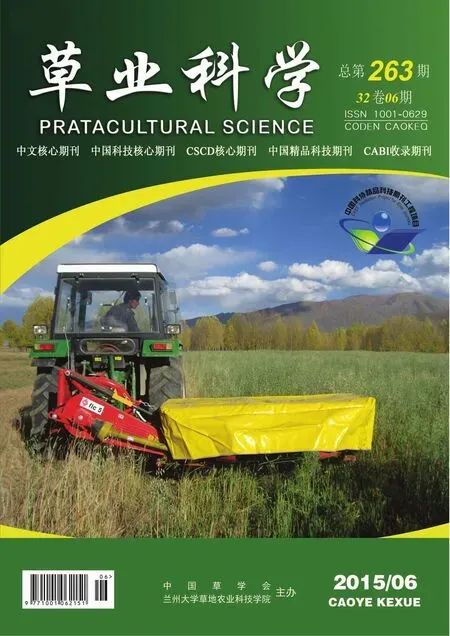羊年再谈放牧
任继周
草业琐谈之五十三
羊年再谈放牧
任继周
12年前的羊年,正是禁牧之风盛行全国的时候,我写了《羊年谈禁牧》一文,反对禁牧。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透彻一些,当时接着又写了几篇文章,呼吁紧急刹住禁牧的历史倒车。祸及全国的禁牧、杀羊之风似乎逐渐有所收敛。
时光流转不息,12年后,羊年又来了,笔者有所感触,再来谈谈放牧,话题聚焦两件事,即羊的放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和对羊的伦理关怀。
首先要问,源自原始社会的放牧利用草地的方式,不但没有被淘汰,反而进入发达国家的第一方阵。为什么?原来放牧方式在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原始粗放型放牧制度与社会同步发展,它随着社会工业化,历经300年左右,最终实现了放牧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转型涉及大农业系统的重构,绝非偶然,也绝非易事。在传统的游牧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化的人居-草地-畜群放牧系统单元。有些地区,进一步将其中部分草地辟为农田,迈入农牧业结合的现代草地农业系统,即草业系统。这个现代农业系统的核心是以划区轮牧为基础的农牧区规范化。我们说农牧区的规范化,不只是把现代化科技手段纳入新型轮牧系统,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境按照科学规律连续放牧而不被间断;它还有另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将农区与牧区的结构性分异逐步弥合而渐趋消失。因此尽管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都有类似我国传统牧区的生态地境,但他们并不存在像我国这样农区与牧区的结构性鸿沟。于是铸造了全社会的农业现代化时代,进入社会发展的第一方阵。放眼国际,不少现代化国家正是通过放牧把栽培业和畜牧业连为一体的。即使荷兰那样寸土寸金,与海争地的小国,放牧地也随处可见。原来现代化农业不但不能摒弃放牧,还把放牧作为土地合理利用的必要元素。这里一个关键词是放牧的现代化转型。
我国工业化利用了大约30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现代化路程。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速度完成放牧畜牧业的现代化转型?关键是我们对放牧系统的转型这件事根本没有察觉,更谈不到下功夫做系统性改革了。几十年来花了许多钱,做了不少事,但都是零敲碎打,没有触及放牧系统现代化转型的本质,绝大部分做了无用功。浪费了人力物力,尤其难以挽回的是浪费了时间,而这段时间正是全国农业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期!真是历史的遗憾。
禁牧的结果只能是舍饲,舍饲需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甚至牧民连年亏损。当人力物力难以为继时,牧民忍痛杀羊,不少地区羊只锐减70%。这里反映的首先是经济问题,但不只是经济问题,其深层蕴含伦理的缺失。
这就进入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生态系统的伦理学向我们揭示,草地的初级生产,必然转化为动物生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即所谓天道。一切草食动物生存的食物源都来自放牧,而羊是与人类关系渊源最为久远而密切的草食动物。羊是完成放牧这一生态伦理环节的主角。尽管有个别类型的羊,如湖羊,在长江三角洲局部地区适应了舍饲,但就羊的总体而言,放牧还是羊群自由觅食于草地的基本方式。把羊群与草地隔离,搞禁牧,一如强使幼童离开母亲,是违背生态伦理的。
食物链是任何自然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驱动力。羊是人类食物链中美好而普遍存在的一环。羊与鱼搭配产生称为“鲜”的人间美味;羊羔是调制“羹”的主料;“大”和“羊”组成“美”字,表达令人欣喜的精神境界。战国时以独角羊“獬豸”作为秉公执法的象征,成为后来历代执法者之官服 ,绵延两千多年直到清末。羊与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友好互动,使羊获取社会的美好感情。而感情是道德的母体和源泉。华夏古文,羊、祥通解,羊本身成为吉祥的象征。以羊为主体构建了表达美好德行的“善”,这是羊在人类社会中美好意念的升华。羊的美好德行的表征不仅流行于华夏,古埃及卢克索的卡纳克神庙,营造了一条300 m的长廊,称为公羊之路,两侧排列32座羊首狮身像,蔚为壮观。这是以羊表达智慧与狮的威猛的结合。把羊来表达智慧的善德,与老子以水来表达善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河流域的乌尔王陵出土一对《金山羊与圣树》,表达了对羊的崇敬。在欧洲金羊毛充满美丽的传说。羊已经熔融入人类社会的道德范畴。
至于“亡羊补牢”意指对失误的补救;“羝羊触藩”比喻进退两难的处境;“羚羊掛角”比喻诗文意境超脱不凡等等,这些成语故事都表达了羊与人类社会在不同情景中的多样精神融合。大量史前岩画提供了远自洪荒时代人类与羊共存的记忆(图1)。及至历史时期,商代的“四羊方樽”(图1)、“三羊铜罍”(图1)等记录了羊在华夏早期文化中的显要地位,汉代金羊灯为华夏文化初成时的标志(图1)。此后历代都有大量的金属或陶瓷羊的图像遗存。

羊在中国已经走下12生肖的神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善待种类繁多的羊。在英语中各类羊都有单独的名称,譬如绵羊,他们称为sheep,山羊称为goat,公羊称为ram,母羊称为ewe,羔羊称为lamb等,就是没有对各类羊的通用名称。我们的“羊年”怎么称呼?使他们为难了。几经苦思冥想,他们把羊年称为sheep/goat year,即绵羊/山羊年。在这里我想顺便指出,一个“羊”字,显示了汉语长期演化的语言成就,正如汉语草原/草地一词可以概括世界各地、多种类型的草地,而西方却因地而异,给以多种名称一样。
不论羊的种类有多少,作为羊的生存主旋律,还是要尽快完成放牧系统的转型,给羊以接近自然的伦理回归,也使华夏农业文明走向现代与世界接轨,这是我们面临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