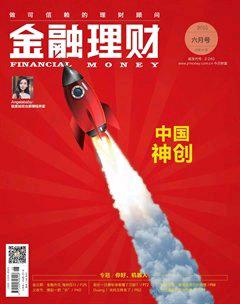机器人时代的中国制造
江玲

5月20日,李克强总理再一次在中国北车制造的新列车上为中国制造站台,这也被认定为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破题之举。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签署,中国制造意图打造的工业强国美好图景似乎就在对岸,一步之遥。五年之前,中国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这距离上一次登顶已经过去了150年之久,未来三十年,中国将努力在机器人时代跻身制造业强国第一阵营,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家命题下的一场攻坚战,中国制造业接到的命令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失败的代价实在太大。
“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在于运用网络化、数字化的手段实现智能化制造。据家电产业观察家梁振鹏介绍,目前主流家电企业纷纷利用互联网、工业信息化手段改造自身制造流程,引入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等生产工具,以提升生产效率,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一步之遥,遥不可及
然而这一步之遥却似乎遥不可及。虽然在中国有无数的企业和精英在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努力着,奋斗着,但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是,在国内大型工厂和重装备生产车间,德日系的机器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工业机器人只能从事“搬运、焊接”等基础性工作,无法进入核心产品的生产流程,这可能是让中国制造业感到最尴尬的故事。
另外,研发能力偏弱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老毛病正变得越来越棘手。据权威数据显示,工业机器人领域,97%的研发成果无法转化,整个制造业领域可转化的科技成果也不足10%。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的新松机器人一度作为中国最早242家行业研究院所转制为企业的代表,但却在最近的调研中,工信部表达了失望:“在关键技术研发方面,有的已经萎缩,有的甚至不搞了。”大量的科研成果,沉寂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更为棘手的是,原本为了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采用海外并购方式“曲线救国”,却由于长期的模仿和引进惯性,让中国企业失去了研发的动力和土壤,很多企业甚至“根本就不具备研发成果的沉淀和转化能力”。
刚刚突破智能数控机床技术瓶颈的沈阳机床鼓励更多“跨法人组织协同研发”,即鼓励不同部门的研发合作,特别是企业对科研单位长期的研发投入支持。这是中国制造业为获得未来竞争中的主动权,寻求升级的“超能陆战队”的又一尝试。
为此,沈阳机床核心技术的突破总共耗时7年,各项资金投入超过11亿元。这有利于在企业和研发机构之间建立“纯洁且相互信任”的关系,使大多数特别是国有企业避免戴上涉嫌“利益输送”的帽子。
造好一款舒适的马桶盖
吴晓波曾经以“到日本买马桶盖”来折射中国制造与德日制造的差距,在吴晓波看来,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逻辑非常简单,就是“造好一款舒适的马桶盖”。
而在中国企业寻求变革的过程中,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张瑞敏带领的海尔公司从经营理念的变革、组织架构的调整以及生产线上的小幅度变化被认定为是告别旧有生产模式的开始。
张瑞敏尝试把公司的层级打乱,把垂直式的管理模式变更为分布式,即公司内部布满“小微公司”。所谓的“小微公司”,即指公司内部“由传统串联的部门组织变成了共同面向用户的一个个小微,”按照张瑞敏的布局,“公司小微和用户小微是并联的,如果用户小微不能创造用户价值,那么这些采购小微或者制造小微就也没有价值”。
这是张瑞敏为海尔这家传统的制造企业寻找的智能优化路径,也是中国制造业升级路径的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日益个性化的消费市场,而这也许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最简单逻辑。
无独有偶,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倒闭潮蔓延,多数企业主苦苦寻求出路未果后离开时,东莞制造业协会会长曾经尝试用机器替换产业线上的工人,使得车间工人由4500人下降到1500人,显著提高了产品质量,也被认定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部分。这一尝试正好符合吴晓波“造好马桶盖”的观点。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朱森第认为,“中国制造业由于发展不平衡,内部层次结构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工业2.0要补课、工业3.0要力争普及,即从电气化过渡到自动化生产这一环节,而工业4.0要有示范模式”。
但朱森第也担心,如果国内一窝蜂搞智能制造,导致国内产业发展跟不上,只能买国外设备,采购以后,至少十年不会更换,反过来可能会导致国内的智能制造产业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也正是《中国制造2025》面临的最大隐忧,资源过度集中到高端装备产业,产业升级没有做好,就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尴尬的“两头镂空” 境地:新的产业尚未建立,旧的产业已经倒下。
对此,划司副司长李北光称要加快对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使现有传统制造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尽快地降下来成为当务之急。

前景是光明的,道路是坎坷的
尽管距离工业强国的彼岸只有一步之遥,但路途却布满坎坷。对于中国工业人来说,在自身做出改变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做出迅速反应,争取为自己通往彼岸的努力赢得更大的时间窗口。
制造业升级需要处理的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关系的互动模式。《中国制造2025》坚持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两种力量互动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十年以后,中国制造业能否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下在制造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改变对相关产业态度的结果使得制造业开始重新回流 ,但是如果产业升级的节奏过快,超过了企业和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很有可能演化成新一轮投资泡沫。
更为忧虑的是,实体经济持续的资金失血拷问着继续升级的可能性。东莞的机器换人潮中,就有超过190家企业因为资金缺乏不得不终止升级的进程。对此,李北光认为,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国家应该在政策方面做出创新,例如鼓励制造业重点领域的大型集团开展产业和金融结合的试点,就是可以开办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大部分制造类企业,都是这一博弈中的弱者,但是博弈的结果,却关乎到中国制造业能否获得升级的时间窗口。
此外,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的用工荒就透露出中国廉价劳动力消耗殆尽和高端产业工人结构性用工荒同时困扰着中国的宏观经济。能否在十年间培养一批适合制造业升级的下一代产业工人也成为制约中国企业升级的关键。苗圩强调,“要实现制造业的升级,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劳动力红利,来补充我们的发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