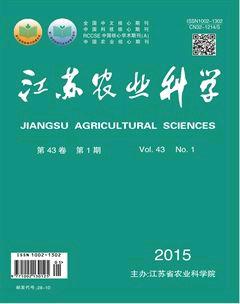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
徐敏 黄江



摘要:运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对2006—2012年新疆82个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不同,南疆地区基础效应高于北疆地区,增长效应更加明显;部分农户收入高增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均出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呈负效应的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和金融体系结构与功能矛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优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环境,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创新性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满足不同金融需求,提高监管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等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性金融;农户收入;变系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2.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01-0427-05
收稿日期:2014-08-12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高层次人才项目(编号:RCSX201109);石河子大学兵团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基金(编号:BTJR201305)。
作者简介:徐敏(1971—),女,四川盐亭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通信作者:黄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E-mail:125179320@qq.com。“普惠金融体系”最早于2005年联合国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提出,之后便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大力推行。普惠金融被定义为“获取金融服务是天赋人权”,即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力获得金融服务。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同时提出“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可见,普惠金融的发展已经成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而面向“三农”的金融服务则是普惠金融发展的根本所在。
普惠性金融与收入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发展普惠性金融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获得金融服务,尤其是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个人或组织,让其拥有公平的机会去获得金融产品和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而有机会参与经济发展并享受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从理论角度看,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收入的影响效应主要有4个:(1)门槛效应。客户得到金融服务是须要支付成本的,即金融服务门槛。在金融约束条件下,穷人由于资本积累限制无法支付这一成本,进而享受不到金融服务,高收入人群则因自身财富优势能够支付成本享受到金融服务,进而提高资本收益[1]。(2)减困效应。除了储蓄、汇兑、支付等基础金融服务手段外,发展低交易成本的新型金融组织,提供小额信贷等服务,把被排斥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个人或组织(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纳入金融服务范围,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使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改善,从而提高收益摆脱贫困[2]。(3)排斥效应。金融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复合概念,包括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自我排斥等6个维度[3]。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金融空白造成的金融可及性障碍,以及农村地区缺乏有效抵押品、农业生产高风险性等诸多原因,导致许多农户被传统金融机构排除在外,使其无法享受到所需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从而影响农业生产,制约收入增长。(4)涓滴效应。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影响农民收入。一方面农村金融通过储蓄动员、资源配置等金融功能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高收入者投资需求增加,利率上升,低收入者将钱贷出从而获得较多利息收入,减缓贫困[2]。
总的来看,在不同金融发展阶段,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近年来,中国通过金融机构调整和改革,在发展农村普惠性金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和尝试,这些努力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须要被综合分析和评价,以便构建更有效的农村普惠性金融制度,实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有关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主要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探讨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改善农民收入的影响。普惠金融的早期研究者杜晓山认为,小额信贷的实质就是普惠金融理念的实践[4]。在此基础上,董晓林等[5]、周孟亮等[6]认为推行无抵押、无担保的微型信贷产品,可以提高贫困者的自身扶贫能力,改善收入状况。王曙光等[7]、刘七军等[8]认为,推行社区发展基金、农民扶贫互助资金等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此外,王修华等从金融宽度的角度分析了包容性金融门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排斥效应、涓滴效应等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2]。田杰等通过构建农村金融普惠指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正效应[9]。另一方面,对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定量测度和评价也是有关研究的主要方面。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测度方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建立农村金融服务覆盖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测度农村金融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10-11]。二是利用金融普惠指数或金融包容水平,如田杰等[9]、徐敏[12]利用Mandira等[13]结合金融排斥概念提出的包含地理渗透性、使用有效性、产品接触性等3大维度的金融普惠指数测度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三是从普惠金融的对立面入手研究金融排斥程度,如高沛星等利用变异系数法从地理排斥、价格排斥、评估及条件排斥、营销排斥评价金融排除度[14]。
上述研究为分析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借鉴,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运用面板模型进行分析时,仅凭经验选择面板模型,没有对其进行检验,会造成模型拟合效果不佳,直接影响分析结果;二是对于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和评价,国内学者并没有一致的观点,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三是由于较难获取数据,鲜有文献对县域、多民族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多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对区域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建议较少。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2年新疆82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应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进行研究,以期为进一步提高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提出政策建议。endprint
1研究方法及模型检验
1.1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是指具有三维(截面、时期、变量)信息的数据结构。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成:
yit=αit+β1,itx1,it+β2,itx2,it+…+βk,itxk,it=αit+βitXit+μit(i=1, 2,… ,N;t =1, 2,… ,T)。(1)
式中:yit是被解释变量;Xit是解释变量;μit是随机误差项,μit~iid(0,σ2);αit、βit是待估计参数,代表引起个体和时期之间差异的“潜变量”的综合影响,即所谓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划分为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变系数模型等3类。
1.1.1混合模型假设截面成员无个体影响和结构变化,即模型中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都不存在,则:
yit=α+βXit+μit(i=1, 2,… ,N;t =1, 2,… ,T)。(2)
1.1.2变截距模型假设截面成员上存在个体影响而无结构变化,且个体影响可以用截距项αit的差别来表示,则:
yit=αit+βXit+μit(i=1, 2,… ,N;t =1, 2,… ,T)。(3)
1.1.3变系数模型假设截面成员既存在个体影响,又存在结构变化,即个体效应或时间效应同时影响模型的截距项αit和斜率βit,则:
yit=αit+βitXit+μit(i=1,2,…,N;t=1,2,…,T)。(4)
1.2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1.2.1模型构建传统的总生产函数可被用于分析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综合温涛等[15]、余新平等[16]、田杰等[9]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将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和其他收入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引入总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Yit=αit+βitIFIit+γitZit+μit(i=1,2,…,82;t=1,2,…,7)。(5)
式中:Yit表示农户收入水平;IFIit表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Z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IS)、政府财政支出(GOV)、就业率(EMP)。
1.2.2变量选择
1.2.2.1金融普惠指数采取金融普惠指数(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IFI)评价2006—2012年新疆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表1)。Mandira等提出包含地理渗透性、使用有效性、产品接触性等3个维度的金融普惠指数[13],为测度普惠金融水平提供了一个综合方法。
IFI指数将3个维度的信息合并为一个单一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IFI=Ir[Ar(x1,m1,M1),…,Ar(xk,mk,Mk)]=1k∑ki=1(xi-miMi-mi)r。(6)
式中:r取值0.25、0.5或1。 IFI指数值为0~1,0表示完全的金融排斥,1表示完全的金融普惠。IFI是一个具有单调性和同质性的递减函数,Ar(xi,mi,Mi)100/(kIr)被称为维度i对总普惠性金融的贡献。
表1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指标
维度项目指标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机构网点X1: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金融服务人员X2: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服务人员数金融服务可得性存款服务X3: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额贷款服务X4:农村居民人均贷款额金融服务使用度
存款服务
X5:农村地区储蓄存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贷款服务X6:农村地区贷款占GDP比例
本研究从3个维度出发,选择6项指标计算金融普惠指数,来测度2006—2012年新疆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服务渗透性主要从为农村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数和人员数衡量。普惠性金融就是要让被排除在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个人或组织获得足够的金融产品和有效的金融服务渠道,用万人拥有金融机构数和金融服务人员来评价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状况;在普惠性金融服务体系下,农户很容易获得基础的金融服务,所以用人均储蓄和贷款衡量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此外,在普惠性的金融体系下,农户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使用程度也非常高,本研究选用农村地区储蓄存款和贷款占GDP的比例来表示金融服务的使用度。
1.2.2.2农户收入选用各县(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Y)代表县域农户的收入水平。
1.2.2.3其他控制变量考虑到除金融发展水平外,产业结构、财政支持、就业水平等都会对农民收入水平产生影响,本研究选择产业结构(IS)、政府财政支出(GOV)、就业率(EMP)作为控制变量。采用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当期GDP的比例表示产业结构,即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从而反映非农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该比例越高表示农户可能获得越多的收入。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是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影响农民收入,本研究选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当期GDP的比例表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力度。此外,充分就业将会使农户获得更多的收入,由于农村就业人员数据不完整,本研究采用各县(市)总人口中乡村与城镇从业人员总数占比来表示农村地区就业率。
1.2.3数据来源本研究选取2006—2012年新疆88个县(市)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为对象,分析7年间新疆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测度农村金融普惠指数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公布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其他变量数据来源于2007—2013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2007—201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县(市)社会经济主要指标部分。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本研究最终选取了82个县(市)作为样本数据,占新疆总县(市)的93.2%,能够代表新疆农村地区。将新疆划分为北疆地区和南疆地区,北疆地区样本包括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州以及塔城、阿勒泰、吐鲁番、哈密4个地区40个县(市);南疆地区样本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及阿克苏、喀什、和田地区42个县(市)。endprint
由表2可见,新疆农村金融普惠指数平均值为0.296,整体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较低。农村金融普惠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北疆各州和南疆巴州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和县域,如奎屯市、昌吉市、伊宁市、阿克苏市、库尔勒市、若羌县等,说明普惠性金融发展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主要集中在南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理位置偏远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疏勒县、疏附县、叶城县、柯坪县、巴楚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南疆、北疆地区农村金融普惠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338 3和0.256 3,说明南疆、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表2样本统计分析
项目YIFIISGOVEMP平均值0.5310.2960.6620.4090.382中位数0.4780.2640.6470.3320.360最大值2.1700.8610.9612.1773.359最小值0.1160.0150.3420.0230.063标准差0.2750.1530.1500.3090.232注:各指标观测数均为574个。
1.3模型形式设定检验
选择正确的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可以减小模型估计结果与现实经济情况之间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有效性。本研究选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确定样本数据符合的模型形式,用Hausman检验法判定模型影响形式。
1.3.1协方差分析检验协方差分析检验通过计算F统计量来检验假设,从而判定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根据模型设立2个假设H1和H2,分别为:H1:β1=β2=…=βN,γ1=γ2=…=γN;H2:α1=α2=…=αN,β1=β2=…=βN,γ1=γ2=…=γN。相对应2个F统计量为:F1=(S2-S1)/[(N-1)k]S1/[NT-N(k+1)]~F[(N-1)k,N(T-k-1)];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式中:N表示截面个数;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T表示观测时期总数;S1、S2、S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计算表明,残差平方和S1为0.851 5、S2为13.468 9、S3为30.769 4;统计量F2为14.227 7、F1为7.500 4;在5%显著水平下,相应临界值F(324,164)为1.256 3,F(405,164)为1248 0。由于F2>1.248 0,所以拒绝H2假设;又因为F1>1.256 3,所以拒绝H1假设。因此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
1.3.2Hausman检验法利用Hausman检验法确定模型的影响形式,即选择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17]。该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影响模型,用H表示Hausman统计量,H=256.3253,对应概率是0.000 0,说明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因此应选择固定影响模型为模型的影响形式。
2结果与分析
2.1北疆地区分析
新疆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北疆地区各县(市)截距项平均为-2.366 6,昌吉市截距项最高,为8.923 5;其次是玛纳斯县和阜康市;伊宁市截距项最低,为-34.875 1;其他地区截距项较低,且大部分为负数。截距项不同说明农村普惠性金融性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效应不同,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户收入水平匹配程度不同。截距项越高,说明基础效应越强,匹配程度越高。如截距项低的伊宁市和哈密市,该地区农户收入在新疆属于中等水平,但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却处于较高水平。
除巩留县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北疆地区农民收入均影响显著,其中16个县(市)具有正效应,24个县(市)具有负效应,IFI系数平均值为-0.311 8。对于具有正效应的县(市),说明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发挥了其减困效应,效果最显著的是奇台县和伊吾县,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户收入分别提高4.8%、3.9%。负效应较显著的尼勒克县、昭苏县、察布察尔县等,属于伊犁州直属县(市),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偏远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在新疆前列,而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负效应与农户收入快速增长相矛盾,说明该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支持力度被严重弱化。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昌吉市、博乐市等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却对农户增收产生负效应,究其原因是这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对资金的高需求,农村金融机构在自身逐利动机的驱使下,使农村资金向非农领域外流,同时农村金融服务的高交易成本和低收益性也加深了金融排斥效应,造成资金错配,使农村资金“偏农离农”,进而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差异,最终影响农民收入增长。虽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实质上其并没有发挥支农作用,反而加剧农村金融排斥。说明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减困效应易被弱化,排斥效应易被强化,同时也说明一定程度上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间接影响的涓滴效应是潜在而非现实的,对该地区贫困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并没有明显促进作用。
表3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新疆北疆地区农户
2.2南疆地区分析
新疆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由表4可见,南疆地区各县(市)截距项平均为0.020 9,尉犁县最高,为8.881 8;喀什市最低,为-10.960 5。南疆地区平均截距比北疆高,说明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基础效应优于北疆地区。同样,截距最低的喀什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处于新疆中下水平,但其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却处于较高水平,说明近年来该地区普惠性金融的发展并没有明显发挥其减困效应。endprint
除轮台县和莎车县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均对南疆地区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其中23个县(市)具有正效应,19个
表4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收入
增长效应的回归分析
县(市)具有负效应,IFI系数平均值为0.104 2。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促进作用最明显的有疏勒县、若羌县、拜城县等,如疏勒县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4.9%。疏勒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均较低,巴楚县、柯坪县、疏附县、叶城县等与其水平相近地区的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增收促进明显,说明这些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支持还远远不够。近年来若羌县、拜城县等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迅猛,尤其是若羌县的IFI值7年间增长超过1倍,与此同时,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增速也位居新疆第1位。对于疏勒县、巴楚县、柯坪县、疏附县、叶城县等多民族聚居、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虽然整体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但近年来在不断改善,这些地区通过宣传、支持、推广农户使用“惠农卡”,发放小额贷款,积极为农户授信,银政合作支持特色农业产业,引进和成立以服务“三农”为方向的新型金融组织(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措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减少地理、评估、条件、营销等方面的金融排斥效应,加深了普惠性金融服务的深度,明显地促进了农民增收。这些地区农户收入的快速增长与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紧密联系,也说明普惠性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地区农户具有很好的减困效应。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是同时进行的,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普惠性金融的发展在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减少金融排斥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增加农民收入。
此外,阿克陶县、塔什库尔干县等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较低的贫困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负效应,其偏远的地理位置、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多民族聚居、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等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该地区存在金融排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北疆地区分析结果一致,库尔勒市、阿克苏市等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却存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负效应的现象。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本研究表明:(1)北疆地区和南疆地区的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的基础效应不同,南疆地区的平均基础效应高于北疆地区。(2)北疆地区和南疆地区部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北疆、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存在较大差别,南疆地区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北疆和南疆地区均出现部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负效应的情况。(3)部分地区出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产生负效应,分为3种情况,一是尼勒克县和昭苏县等地,即使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产生负效应,农户收入依旧增长迅速;二是部分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昌吉市、库尔勒等,却存在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负效应的情况;三是部分贫困地区(如阿克陶、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出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产生负效应情况。
3.2本研究创新性
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分析内容上,从微观县域角度,利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结果,检验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减困效应、排斥效应、涓滴效应,深入细致地分析普惠性金融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第二,在分析对象上,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多民族聚居、地区差异明显的新疆各县(市)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地区多为贫困地区,有大量的中低收入甚至贫困人口,这正是发展普惠金融须要重点惠及的地区,发展农村普惠性金融对农民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协方差分析和Hausman检验选择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避免依据经验选择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提高了分析准确性,同时利用金融普惠指数对2006—2012年新疆82个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3.3政策建议
3.3.1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环境,缓解农村金融排斥如在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的基础效应高,促进增收效果更明显,但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普遍低于北疆地区,应该侧重加强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将普惠性金融服务向更贫困的弱势客户和地区延伸,进一步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然而在偏远贫困地区,经济密度、人口密度无法满足网点盈利水平,设立和运营新机构的成本较高,这种矛盾造成一定程度的农村金融排斥。所以要鼓励设立低成本、灵活的新型金融组织,如社区型合作金融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作为金融机构向农户服务的中介,缩短金融服务距离,降低交易成本,缓解农村金融排斥。同时,还须积极推动征信,完善区域信用评价,改善信用环境,使客户信息透明有效,优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3.3.2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提供创新性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有效功能支撑新疆部分地区出现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呈显著负效应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存在金融体系功能和结构上的矛盾,应该通过差异化监管,对目前存在的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信用社、小贷公司在市场准入、税收、财政补贴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创新性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如在北疆地区尼勒克县等地,旅游资源丰富,属少数民族地区,多以放牧为主,近年来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其中经营性收入增长尤其突出,这就要求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机构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农民收入来源情况分析市场,调整市场、业务、产品、客户的定位,推出个性化差异服务,通过金融创新增加金融服务层次,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产品。
3.3.3提高监管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在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积极作为对涉农的金融机构,在严格准入标准、清晰服务对象、规范服务行为的同时,尊重其业务策略与市场需求,通过市场自身调节和差异化政策,使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对于经济发展快、农村普惠水平较高却存在农户收入增长呈负效应的地区,应该给予一定的调控和干预,监督支农资金的流向,减少农业贷款资源错配等“脱农”现象,同时建立金融保险机制,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和借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金融支农效果。endprint
参考文献:
[1]张立军,湛泳.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23(12):73-81.
[2]王修华,邱兆祥.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1(2):71-75.
[3]Kempson E, Whyley C . Kept out or opted out?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ulsion[M]. London: The Polity Press, 1999.
[4]杜晓山. 小额信贷的发展与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J]. 中国农村经济,2006(8):70-73.
[5]董晓林,杨小丽,胡睿.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约束与农信社小额信贷——基于对江苏睢宁县的农户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2):27-34.
[6]周孟亮,李明贤,孙良顺. 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研
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4):1-7.
[7]王曙光,胡维金. 社区发展基金与金融反贫困[J]. 农村经济,2012(2):10-14.
[8]刘七军,王海明,李昭楠. 对甘肃省贫困村互助资金发展的调查与思考[J]. 开发研究,2012(5):30-33.
[9]田杰,陶建平. 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中国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1877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财经论丛,2012(2):57-63.
[10]孙翯,李凌云.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状况分析——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经验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1(4):131-137.
[11]李明贤,李学文. 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的现实考量与分析[J]. 调研世界,2008(8):17-22.
[12]徐敏. 农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J]. 开发研究,2012(5):104-107.
[13]Mandira S, Jesim P.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0, 23(5): 1-16.
[14]高沛星,王修华. 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1(4):93-102.
[15]温涛,冉光和,熊德平.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经济研究,2005(9):30-43.
[16]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 中国农村经济,2010(6):77-86.
[17]徐敏. 财政金融投入的农业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变系数模型分析[J]. 科技与经济,2010,23(1):51-54.陈轶,张衔春,周方睿,等.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2015,43(1):432-43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