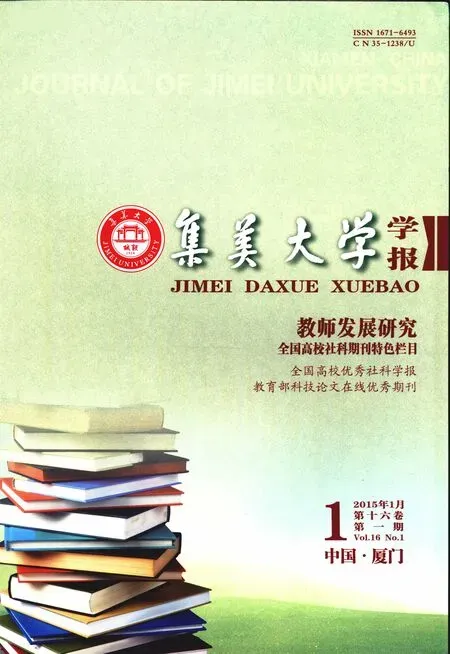明代历史教育述论
孔 华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安徽 池州247000)
明代是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历史教育在其中也体现出鲜明特色。研究明代历史教育,对于拓展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探索明代社会史、史学史、文化史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明代历史教育的具体表现做一述论,以丰富研究内容。
一 宫廷教育中的历史教育
明代的宫廷教育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对诸皇子的教育开始的,宣宗以后,尤其是英宗以冲年登极,宫廷教育逐渐形成经筵、日讲。宫廷教育中包含有历史教育。
(一)帝王重视历史教育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历史知识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过清醒的认识,他曾说“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 “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不仅如此,朱元璋在征战之际于戎马之暇还和儒臣们“讲论经史”。对掌握历史知识重要性的充分认识使得朱元璋十分重视对其子孙进行历史教育。
朱元璋重视教育机构的设置。在创立以金陵(今南京)为根据地并自立为吴王之后,朱元璋就在宫中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明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1]3549洪武元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登极称帝,仿唐制,设东宫为太子居所,其衙署称詹事院(府),下辖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等机构,统称府、坊、局。其官为詹事,“掌统府、坊、局之政事,以辅导太子”; “凡入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番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 《贞观政要》诸书。”[1]1783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对诸子进行历史教育有了固定的场所。
朱元璋通过“言传身教”对诸子进行历史教育。吴元年(1367 年),朱元璋命太子朱标省临濠墓时,就以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事例来教育朱标,他说到:“商高宗旧劳于外,周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俭,为守成令主。儿生长富贵,习于晏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其因道途险易以知鞍马勤劳,观闾阎生业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1]3547
朱元璋还通过“敕撰史书”对诸子进行历史教育。《明太祖实录》卷八十记载:洪武六年三月乙丑,命大臣“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者”编为一书,“赐名曰《昭鉴录》,以颁赐诸王。”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庚子,又敕撰《永鉴录》, “其书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颁赐诸王。”
朱元璋之后的明代帝王同样重视对子孙进行历史教育。以朱棣为例, 《明太宗实录》卷三十记载:太宗朱棣曾“命侍臣辑自古以来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一书,以授太子。”书名为《文华宝鉴》。又,《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三曰:太宗命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采古名臣直言,如张良对汉高、邓禹对光武、诸葛孔明对昭烈及董贾、刘向、谷永、陆贽奏疏之类汇录,以便观览。”名为《历代名臣奏议》。朱棣还重视对武臣子弟进行历史教育,《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三记载:“武臣子孙袭职者,未守之前人建功之难,而骤享厚禄,鲜不覆坠。……安于豢养,武艺不习,礼仪不谙,古今不通,将来岂足为用?其申明武学旧规,严其课绩。毋为具文应故事耳。”“古今不通,将来岂足为用?”。
(二)经筵、日讲中的历史教育
经筵,是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座。讲席除研读经史外,还联系朝政实践,切磋时务,这一活动既是皇帝接受历史经验,研讨治国安邦之道,学习治国平天下之策的讲坛,也是从理论高度研究朝政的专门会议。史载,汉宣帝曾令儒生于石渠阁讲《五经》;唐玄宗置集贤殿书院,选耆儒侍读,日讲经史[2]。宋代,开始有“经筵”一词的出现,当时还规定了入侍讲读的时间:“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冬至),遇双日入侍迩英阁,轮班讲读。”[3]元中叶,“经筵之制大备,以勋旧大臣知经筵,次至同知、讲读以下,大略如今日(指明代)之法。”[4]由此可知,明以前之“经筵”,始终未能形成制度。经筵成为国家一项制度开始于明中叶初期。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 年)九月癸亥,原晋王府长史桂彦良,上“太平之要”奏议,曰,开经筵是“自昔圣王贤臣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具载六经,垂法万世,不可以不讲也。……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遇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敷陈大义,使上下耸听,从警省,兴起善心,深有补于治化也。”但是,这一建议未被明太祖采纳。永乐至宣德时期,尽管有“每视朝毕,无日不御文华殿或便殿,召大臣或儒臣讲读”的记载,但经筵时续时断,还是未能经常化、制度化,直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 年)二月,“从大学士杨士奇之请”[5],始开经筵,经筵作为一项制度才延续下来。史载:“(经筵)明初无定日,亦无定所。正统初,始著为常仪,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1]1405经筵之外,还有日讲。日讲被称为“小经筵”,只有讲官侍班,礼仪逊于经筵。史载:“经筵有二案,而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6]日讲有讲章是崇祯时才有的事。日讲时,“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扣头礼后,东西分立。先读书,次读经,或读史,每伴读十数遍后,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讲读后,侍书官侍上习字毕,各官扣头退。”[7]
从经筵和日讲的内容来看,均有对历史知识的讲授。经筵开讲时,“司礼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置御案,皆《四书》东,经、史西。”[1]1406日讲“先书,次经,次史”[1]1407,同样有对历史知识的讲授。隆庆六年(1572 年),还订立了午讲制度,“每日早讲毕,帝进暖阁稍憩,阅章奏,阁臣等退西厢房。久之,率讲官再进午讲,讲《通鉴节要》及《贞观政要》。”[1]1407
贯穿于经筵、日讲中的历史教育同样受到大臣的重视。《明孝宗实录》卷一八○曾记载这样一件事:孝宗曾一度在日讲中停止对《贞观政要》一书的讲授,这引起诸大臣的不满,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刘健等立刻上言:“今日进讲间,传旨将《贞观政要》暂且停讲,切缘《贞观政要》所载唐太宗议论行事之迹,于帝王为治之道最为切要。……伏望圣明少留顷刻,俯垂天听,容臣等仍将此书照旧进讲,以裨圣治之万一,岂为臣等之幸,实宗社无疆之幸也。”人称“救时宰相”的张居正更是看重贯穿于日讲中的历史教育,《明神宗实录》卷四记载:张居正曾专门拟出《日讲仪注》,其中写到:“上午讲的内容为《四书》中的《大学》和《五经》中的《尚书》……午讲的内容侧重于史,讲读的内容为《通鉴节要》,讲官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为了更好的引导教育小皇帝朱翊钧,张居正等大臣还于正史中广泛取材,慎重选择,以短篇故事的形式编成《帝鉴图说》一书,此图书展现出从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到北宋止的3000 余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帝王形象。隆庆六年(1572 年)十二月,张居正进《帝鉴图说》,自称: “臣等尝考前史所载治乱兴亡之迹,……谨自尧天下之君,撮其善而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鉴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册,以辨淑慝。”[8]
(三)宫廷女教和内书堂读书中的历史教育
中国自古就重视对女子的教育,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成为后来正史中“列女传”的模本,自此之后,专门用于对女子进行教育的教科书相继出现,如东汉班昭《女诫》、唐太宗长孙皇后《女则》以及唐宋若华《女论语》等。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熟阶段,对宫廷中的女子教育十分重视,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宫廷女教。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命儒臣修《女诫》,告谕到: “治天下者,治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卿等其纂《女诫》及古贤妃事可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1]3503太祖马皇后也十分重视女教,她曾问女史:“自唐宋以来,何后最贤,家法何代最正?”女史曰:“惟赵宋诸后多贤,家法最正。”马皇后遂命录其贤行,令女史诵而听之,并且说:“不徒为今日法,可为子孙万世后妃法也。”[9]成祖仁孝徐皇后同样重视宫廷女教,曾著《内训》和《女诫》。明世宗也很重视宫廷女教,他曾“以章圣太后所著《女训》一卷示辅臣,其首即献帝为之序,次即太后自序,为目十有二。已,复以慈孝高皇(后)传及仁孝(徐)皇后《内训》同示,欲与《女训》并刊行。”[10]87统治者重视宫廷女教,其本意并不是要普及历史知识,对女子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但宫廷女教所用的教材都是“采古为可法者”编集而成,其在客观上确也起到历史知识普及的作用。
明代宫廷内有一种对内臣进行文化教育的专门性教育机构——内书堂。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内侍毋许识字”,但当其曾孙宣宗朱瞻基即位后,竟公然于内府设内书堂,选派外廷官员入内,专授小内侍读书。明代,内书堂读书有涉及历史知识的教育,这从其所用教材即可看出,内书堂所用的教材有《四书》、《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关于《神童诗》,明人朱国桢有这样的记载:
汪洙,字德温,鄞县人,九岁善诗赋,牧鹅黌宫,见殿宇颓圮,心窃叹之,题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鱼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上官奇而召见。……世以其诗铨补成集,以训蒙学,为《注神童诗》[11]
有些地方官员还为内书堂编写教材,《明神宗实录》卷二五○记载:礼部复:“四川佥事张世则奏进《貂珰史鉴》,曰评、曰考、曰论,为箴、为赞、为诗。善可为法,身享令名,国亦受福,读之令人慕;恶可为戒,国将受害,身先诛夷,读之令人畏。夫祖制,貂珰识字有禁,宣德以后始立内书堂,教以《忠鉴录》,世则所进,宜俱定为课程,庶几口诵心维,可以迁善改过。”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传记类第九十八册著录有《貂珰史鉴》一书,可查阅。
二 官学教育中的历史教育
明代,学校教育分为两大系统:官学、私学。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是国子监,地方官学主要有府、州、县儒学。历来认为,明代官学不注重历史教育,史书不受重视,顾炎武曾感叹到:“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12]如若仔细的考查一下明代官学的教育内容,我们会发现,历史教育在其中同样受到重视。
(一)国子监
国子监属中央官学,最早设置于龙凤十一年(1365 年),“以故集庆路儒学为之。”洪武十五年(1382)又改学为“监”,扩大规模于鸡鸣山之阳:“……中为彝伦堂,分两厅(博士厅、绳愆厅)、六堂、三十二班,左庙(先师庙)右学,亭庑厅厢,肄业有所,会馔有堂,以主廪库庖隔,靡不毕备。”[13]卷7《》永乐元年(1403 年),明成祖营建北京,以北平府学为北京国子监,永乐十九年(1422 年),迁都北京,南京成了陪都,其国子监则称“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成了“大明国子监”,后人分别称之为南监、北监或南雍、北雍。
关于明代国子监生员所习课程,《明史》有记载:“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1]1789以“诸史为业”说明有对生员进行历史知识的传授。
明人黄佐记载国子监生员读书内容时说:“(国子监)各堂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13]“每日诵读书史”,也是国子监重视历史教育的表现。 《明宣宗实录》卷五八曰:宣德四年(1429 年)九月乙卯,北京国子监助教王仙说到:“……学校教养人材,固当讲习经史。”同样表明,官学教育中对历史知识教育的重视。
(二)府学、州学、县学
明代地方儒学之设开始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 年),朱元璋立地方儒学诏曰:“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识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此最急务,当速行之。”[13]》《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曰:“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
明代地方儒学的课程设置在全祖望的《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中交待的最为清楚:“其所业自经史外,礼、律、书其为一科,乐、射、算其为一科,以训导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学正或教谕为之提调。经史则教授辈亲董之,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哺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版、传记之属。”[14]经史由“教授”亲自讲解,内容有“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充分说明了历史教育在明代地方官学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朱元璋在位期间经常命令礼部颁赐书籍给地方学校,从其所颁赐的书籍中,也可看出地方官学有对历史知识的教育。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六月戊寅,朱元璋命礼部颁赐书籍于北方学校,曰:“朕常念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学者,往往病无书读,向尝颁《五经》、《四书》,其它子、史诸书,未曾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颁赐诸书中,有历史类书籍,说明地方官学教育中贯穿着历史知识的教育。
三 书院讲学中的历史教育
(一)明代书院之兴盛
明初,政府在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州、县儒学,官学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书院因之衰落。但各地还是兴建和重建了一些书院,史书记载:“初,太祖因元旧制,洪武元年(1368 年),立洙泗、尼山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孝宗弘治二年(1489 年),以吏部郎中周木言,修江南常熟县学道书院。”[15]成化、弘治以后,书院开始复苏,至嘉靖、万历年间达到鼎盛。 《明史·东林诸儒传》曰: “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玠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顷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志,取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沈德符有言: “自武宗朝,王兴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10]1236
乡村书院也大量的出现,以安徽泾县为例,“自姚江之学盛行于水西(书院),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烤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岭则有蓝山书院。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故和则考德而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散则传语而述教,拳拳以善俗为心。”[16]
(二)历史教育在书院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教育在明代书院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明人刘宗周曾记姜士昌建秦中书院,书院讲会分为五部分,其中有“史学”一会:“仍分立五会,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古文词,四曰理学,五曰昭代典故。听诸生各占一会,或二三会。会之日,各以其学互相质难,收丽泽之益,渐底与成材。”[17]把“史学”单独作为一会,可见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明人吕高把是否知晓“古今治乱之迹”作为衡量是否为全儒的一个标准:“若曰读尽天下之书,穷尽天下之理,原无此等学术。但古今治乱之迹,是非得失之论,见证之下,迷而不达,亦不得谓之全儒。”[18]因此,在书院章程规定学员应读经书之外,吕高又为诸生开列了一系列书目,其中“史部”就有《左传》、《国策》、《通典》、《通考》和“二十一史”等,将这些书籍采备于书院,鼓励诸生恣情览阅,其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四 民间教育中的历史教育
明代的民间教育包括私人教育和半官方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半官方教育包括义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王凯旋认为社学是明代官学系统的最基础部分,[19]本文把社学列入民间教育进行考察。一般来说,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
(一)社学
“社学者,一社之学也。百又十户为里,里必有社,故学于里者名社学云。”[20]朱元璋在位期间除大力兴建国子监和地方儒学外,又于洪武八年(1375 年)在全国城乡推行元朝的社学之制。《明太祖实录》卷九六有记载: “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适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借建社学之机勒索民财,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 年)曾一度废止社学。洪武十八年(1385 年),朱元璋又诏令地方郡县“复设社学”。之后,社学普遍存在。史载:“凡在城坊厢,在乡屯堡,每一社立一社学”,“凡在城四隅,大馆统各社学以施乡校之教,子弟年八岁至十有四者皆入学,约正、约副书为一籍,父兄纵容不肯送学者,有罚有司。”[21]
从明代社学的教学内容中可窥见对历史教育重视,全祖望曾记载: “若乡里学舍(社学),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弟子则称为师训,在官府则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字文为首,继及经、史、律、算之属。”[14]清道光年间(1821 年—1850 年)撰修的《遵义府志》记载了明代社学生员读书作文之法:“先读《四书集注》、《孝经》、《小学》,次读《五经传注》、《周礼》、《仪礼》、《三传》、《国语》、《国策》、《性理》、《文选》、《八家文集》、《文章正宗》及应读史传、文集等书。……作文以经史发为文章。”[22]生员需读“史传”,历史教育受到重视。
(二)义学、塾学
义学,又称义塾、义馆,是为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义学不收束修,还提供膏火之费。明代义学有民办和官办之分。民办义学一般为富裕的民间人士置物、买田、捐资创办。例如,明代,徽州私人创办义学蔚然成风,歙县呈坎人罗元孙,“尝构屋数十楹,买田百亩,以设义学,以惠贫宗”;休宁人吴继良, “尝构义屋数百楹、买义田百亩,建名善书院、设义塾。”[23]歙县人汪光晃“设义馆以教无力延师者。”[24]官办义学如明万历年间的李贵和在祥符设立的义学:“在大梁门外丁字街路北,房共十二人间,后畦地三十余亩,岁租银十二两,供塾师束修之需,以教乡民子弟贫不能从师者。”[25]塾学,又称私塾、书馆,是在民间广泛设立的由私人经办的蒙养教育机构。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朱元璋下诏停办社学,徽州“乡民有乐教者”就“各自延师训诲子弟”[26],创办塾学。从设置情况看,塾学有族塾(村塾)、家塾之分。家塾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塾师在自家里设馆,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收附近学童就读,如明黟县人汪文宗, “建光德楼,读书其中,……常手录先贤格言以训乡邻子弟,一时志学之士,咸就正焉。”[27]一种是由富裕人家独自聘请教师在家设馆,以教子侄,如明末清初歙县人江之鳌,“课子延名师,朝夕敬礼。”[28]
对于义学、塾学中历史教育的考察,我们从分析其所用教材入手。明代的童蒙教育重视对《三字经》的教学,白寿彝先生在《从〈三字经〉谈到历史教育》一文中,从历史教育的角度认为,《三字经》“基本上是一种进行历史教育的书,其中包括历史知识的教育。”[29]明代还有一种对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童蒙历史读物《幼学须知》,其中就有对历史知识的介绍,如“朝廷”一门,书中写到:
姜后脱簪而待罪,世称哲后;马后练服以鸣俭,共仰贤妃。唐放勋德配昊天,遂动华封之三祝;汉太子恩覃少海,乃兴乐府之四歌。[30]35
在“地舆”一门中,书中写到:
尧有九年之水患,汤有七年之旱灾。
商鞅不仁而阡陌开,夏桀无道而伊洛竭。[30]20
明代学者程敏政曾专门为塾学编订《咏史绝句》,作为历史蒙学读物。在叙及撰写宗旨时,作者说到:“余家居,见塾师以小诗训童子,乃首以市本无稽韵语,意甚不乐。因以所记古七言绝句咏及史者,手书授之,上之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余年,以时比次,得数百篇,又以其猥杂而不便于一览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间世之治乱,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贤否,大抵略备。”[31]专门把咏史诗编订为一书,供童蒙阅读,可见作者对儿童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视。
五 结束语
明代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都有对历史知识的教育,且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1](清)张廷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欧阳修. 新唐书·卷47·百官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2.
[3](清)徐松. 宋会要辑稿·卷58·职官六[M],//神宗正史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影印.
[4](明)于慎行. 谷城山馆文集·卷1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2008.
[5](清)夏燮. 明通鉴·卷22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889.
[6](明)李清. 三垣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08.
[7](明)孙承泽. 天府广记[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345.
[8](明)张居正. 张太岳集·卷38·进帝鉴图说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78.
[9](清)傅维麟. 明书·卷20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0](明)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明)朱国桢. 涌幢小品·卷24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2](明)顾炎武. 日知录·卷16·史学[M]. 四库全书.
[13](明)黄佐. 南雍志[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4](清)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卷22·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M]. 四部丛刊.
[15](明)王圻. 续文献通考·卷50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6](清)赵绍祖. 赤山会约跋[M]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730.
[17](明)刘宗周. 刘子全书·卷21·亚中大夫江西政司右参政诰赠太常寺少卿养冲姜公墓表[M]. 四库全书,1996.
[18](明)吕高. 江峰漫稿[M] //赵子富. 明代的书院[J]. 中华文化研究,1996 (夏之卷):47 -52.
[19]王凯旋. 论明代社学与学校教育[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4):137 -142.
[20](明)冯应京. 皇明经世实用编·卷17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1](明)黄佐. 泰泉乡礼·卷3·乡校[M]. 四库全书,1996.
[22](清)郑珍,莫友芝. 道光遵义府志·卷44·艺文三[M]. 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
[23](清)赵吉士,等. 康熙徽州府志·卷15·人物志四·尚义传[M]. 康熙三十八年刻本,1988.
[24](清)陶澍,邓廷桢修. 李振庸,韩玖纂. 道光安徽通志·卷196·义行[M]. 道光十年刻本.
[25](清)李同亨修. 张俊哲,张壮行纂. 顺治祥符县志·卷2·学署[M]. 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
[26](明)彭泽,汪舜民纂修. 弘治徽州府志·卷5·学校[M]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27](清)吴甸华. 嘉庆黟县志·卷6·人物[M].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
[28](清)江淮椿. 歙北江村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故处士之鳌公传[M]. 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29]白寿彝. 白寿彝史学论集(下)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289.
[30](明)程登吉. 幼学须知[M],//中国古代蒙书精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1](明)程敏政. 簧墩文集·卷23 [M]. 四库全书,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