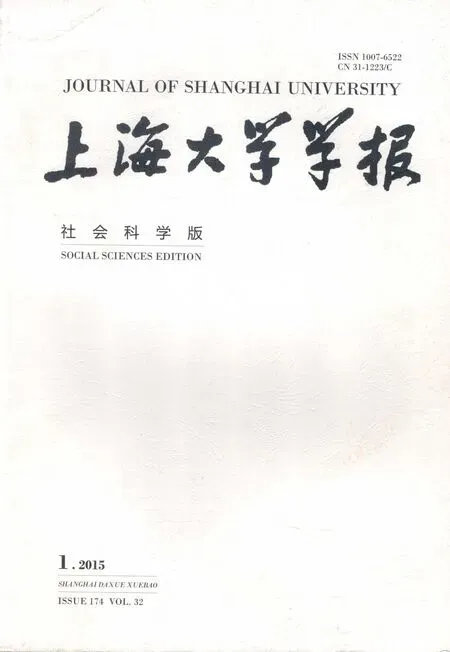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
张 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主持人语】
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
张 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宋代以降的近世诗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日常化、地域化及私人化倾向。清代的竹枝词、怀人诗及《感旧集》之类诗集的编纂、对昔日行迹图的题咏等,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其中伴生的巨量的非经典诗歌,有着经典诗学无法有效解释的价值。而从宋代以降诗歌发生、发展实际中提炼出的“情境诗学”,强调心灵史和生活史的层面,使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之中被重新赋予了意义。“情境诗学”不仅可以指向近世诗歌,也可以成为理解历代非经典诗歌的有效路径。
情境诗学;心灵史;生活史;日常化;地域化;私人化
一、问题的提出
《全唐诗》九百卷,多至四万八千首。精绝者亦不过三千首,可数十卷耳。(余久有《唐诗选》之意,约得三千首,此举至今未果。)馀则仅备观览,供采掇、资谐笑而已。虽不录无害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十
陈廷焯建构了相当完整的诗学和词学体系,有学者甚至言其文学思想是“传统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1]因此将他对唐诗的观点看作中国古典诗学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应该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全唐诗》除去三千首,另外四万五千首该如何对待?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更严重的是,这个问题在宋、元、明、清诗歌中愈加突出。按照陈廷焯的标准,或者中国古典诗学的标准,二十五万首宋诗、十三万首元诗、至少五十万首明诗、近千万首清诗①明、清诗歌的大致数量,依据罗时进的《清诗整理研究工作亟待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6日。,“精绝者”亦可能不过数千首,剩下的数十百万甚至上千万首诗歌怎么办?果能“不录”或置之不理吗?或者,充其量将其做为陪衬数千首“精绝”诗歌的“绿叶”来对待?
是诗歌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看待诗歌的眼光出了问题?
二、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
中国古典诗歌体式至唐大备,后世并没有产生出以往没有的新形式。在这相对稳定的形式中,唐诗和宋诗可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审美范式,元、明、清诗歌大体都可以划归到这两种范式中,如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所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2]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且研究成果丰硕②可参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戴文和《“唐诗”、“宋诗”之争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王英志主编《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这里不拟详说,但相较于唐诗,宋诗写作更具日常生活化的倾向,这是共识。仿佛所有高雅浪漫的题材被唐人挖掘一空,宋人大量转而向日常琐细生活要诗料,不仅咏劳动者的水车、秧马,也咏文人的笔墨纸砚,还咏人类共有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感受,如理发、洗足、服药、食粥、打瞌睡、肚子痛等。由于某些相对生新的题材在原有的诗歌遗产中较难找到对应的雅语,故吟咏中又常采用日常用语,从而造成了宋诗题材和语言的双重日常化取向③当然,宋诗的这种日常化倾向亦可说是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唐代杜甫开始,诗歌的题材与语言已有日常化的趋势,新乐府运动更加速了这种演变的态势,但宋人的日常化不仅更琐细,而且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而且这种日常生活化,愈至后代愈见全面和详细。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3]宋诗的日常生活化,可说是近世诗歌乃至近世文学的一个总体特征④在内藤湖南的论述里,除了诗歌史和语言学史内在发展的逻辑,近世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还和庶民社会的兴起、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印刷术的发达相关。。
近世诗歌除了日常生活化倾向外,还有一种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倾向。即诗歌不是追求建立普泛性和共享性的话语权力,而是呈现地域性甚至私人性的话语空间。地域文学的意识,一般认为自宋代开始,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即出现在宋代。明清两代进一步呈现出多元的文学格局和地域特征,蒋寅先生曾令人信服地指出:“明初开国,由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五粤派瓜分诗坛的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清代的文坛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4]近世诗歌对于私人生活及生命的体认也逐步加重,陈寅恪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5]“释古典”即释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考今典则是考作者本人的处境和心情。“古典”较之“今典”,更能跨越地区差异和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但近世诗歌的今典和自注现象却大大增多;不惟如此,近世诗歌的诗题,其时间、地名、事件的交代都更加明晰;近世诗歌的诗集后还常附入年谱,自传意味增浓等①参浅见洋二《文学的历史学——论宋代的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见《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另参周剑之《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一切都使其带上了私人生命史和生活史的意味②当然,从宽泛的意义看,一切诗歌均具有生活史和生命史的性质,如陶渊明的诗歌,就精妙呈现了其日常生活和生命感受。但近世以前更准确地说是中唐以前,无论是表现华美或是朴素生活、生命的诗歌,都经过了一种艺术美的过滤,因而显得有些诗化和抽象;而中唐和近世以降的诗歌,通过诗题细化、诗歌自注、自编年谱、题材世俗化等等方式,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和生命本身,虽显原荒杂芜,但血肉感也更强烈。。
清代诗歌,有几个现象值得玩味。一是几乎大部分诗家都或多或少地创作有竹枝词,而竹枝词是风土味很浓厚的一种诗体,似可反映清诗地域性的增强。二是怀人诗的大量出现,动辄数十甚至上百首,如陈用光有《秋暮怀人诗十五首》,朱珔有《岁暮怀人二十六首》,宋咸熙有《怀人诗四十首》、《后怀人诗三十首》,蒋攸铦有《雪鸿纪迹六十首》,朱文治有《再续怀人诗六十首》,金亚匏有怀人诗七十首,石椿有怀人诗百首,万慎子《南昌旅次怀人诗百首》(作于民国三年)等,以上仅是就道光以降诗坛略举数例而已。三是“感旧诗集”的编纂,即将师友诗作选编成集以兹纪念,如王士禛的《渔洋山人感旧集》收顺、康两朝与自己有交游的诗人333位,诗作2 572首;吴翌凤的《怀旧集十二卷续集六卷又续集二卷女士诗录一卷》仿王渔洋《感旧集》之例,取五十余年来所录前辈及同好中已往者之诗,编缀而成;张之洞亦辑有《思旧集》,选编十八位昔日友人诗作。怀人诗的写作与感旧诗集的编纂,其实都饱含着对昔日人事的感怀和眷恋。四是清人爱将值得纪念的经历绘制成图,并自题或索题他人诗词③此举宋人偶有,如孙觌《右丞相张公达明营别墅于汝川,记可游者九处,绘而为图,贻书属晋陵孙某赋之》,元明数量有所增加,但远不及清人泛滥。,如钟令嘉有《自题归舟安稳图》七首,毕沅有《自题慈闱授诗图》四首,长沙瞿氏《分灯课子图》载有熊少牧、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俞樾、曾纪泽、张之洞、王闿运、陈三立等诸家题咏,钱士青《机声灯影图》题诗者多达一百四十三人①“课读图”的意蕴,可参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第6章《绘图:“青灯课读图”与回忆中的母教》,三联书店2012年版。,章寿麟的《铜官感旧图》亦有百余人为之题咏,莫友芝的《影山草堂图》也索题友朋诗文甚夥,他还为老友陈锺祥的《十年鸿爪八图》册子题诗(诗题《息凡示〈十年鸿爪八图〉册子,各系一詩》),等等,图文并茂的方式,使生命的追忆和人生的品味更显华茂深情。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倾向,与近世诗学观念、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变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唐诗经典作家作品(即陈廷焯所谓的“精绝者”)高度推重的基础上,由此形成的评判优劣标准,如风雅、格调、神韵、意境、气象,乃至陈廷焯标举的“沉郁顿挫”等,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阐释传统,并能较为契合近代以来的“纯文学”观念,在今天文学史研究中占据主流位置,可称之为“经典诗学”。其中,“诗道高雅论”是“经典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诗,雅道也”[6],风雅、古雅、典雅、雅正、雅净,以及意义相近的脱俗、出俗、拔俗、避俗、超俗等术语,无不彰显着诗道高雅的传统[7]。面对宋代诗歌日常生活化或世俗化的创作实际,该如何调和它与“高雅”之间的矛盾呢?宋人的智慧是将“俗”暗暗统摄进诗道高雅的传统里。北宋梅尧臣论诗已有“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之语,经黄庭坚转述后影响甚巨[8],黄的“点铁成金”论即可视为此论的翻版;苏轼亦言“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镕化耳”[9],“街谈市语”本是日常生活的俗语,但经过“镕化”,方能转俗为雅。吴可《藏海诗话》谓陈子高“‘江头柳树一百尺,二月三月花满天,袅雨拖风莫无赖,为我系著使君船’,乃转俗为雅。”[10]亦同此意。经过如此创造性的转换,近世诗学观念中的“高雅”实际上已与唐代论诗标准貌合心离。
从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来看:近世以来下层文人的数量呈增加趋势,他们虽然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毕竟不在上位,并不迫切要求和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②其实即使是中上层文人,其诗文也不再局限于敷宣王言,还注意个性的表达。王汎森认为,至迟自明中后叶开始,士人和思想界“对普遍全天下的‘理’的兴趣趋于淡化,而对私的、情的、欲的、下的、部分的、个性的具有较大的兴趣”,见其《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他们中的部分人固然重视自己的诗人身份、诗歌使命和诗坛地位,但也有很多人并未将诗歌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圣事业③可参看蒋寅《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亦无意在诗歌上与前人较长计短,因此不必追求诗歌内容的崇高和艺术的创新。所谓渔樵耕读,各司其业,诗歌对于这些文人是份内之事,是其生活和生命的自然反映,或是消遣岁月的智力劳动。这样的诗歌不仅可以用来抒情言志,也可以用来干谒求助、交际酬应等,如我们从近世大量唱和诗,包括技巧上乏善可陈的唱和诗中,可以深刻体味到种种复杂的社交礼仪和人情世故。于是诗歌不仅在题材和语言,而且在功能上也趋于日常化或世俗化。诗歌变成了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了人际关系的一张美丽名片。社会性与文学性、俗与雅的界限在这里似乎消失了。
如果按照唐代“经典诗学”的标准,这些诗歌自然无单独讨论的必要,甚至宋以后直可谓无诗①宋后无诗论还受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可参张晖《元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其可能性》,《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太过单一,无疑会损害对文学整体性的理解。文学首先是人学,经典诗学只是人学也是文学的一个部分,人学和文学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经典诗学面对占绝对数量的非经典作品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它当然也不能有效解释宋以降诗歌发展的实际。我们该怎样激活那些沉寂或沉睡多年的巨量诗歌资源,使中国诗学焕发新的青春呢?
三、“情境诗学”与近世诗歌价值的开掘
毫无疑问,近世诗歌必须建立新的诗学话语及其评判标准,不能仅仅是经典诗学笼罩下的作家作品排座次。非经典作品在烘托陪衬经典作品的伟大价值的同时,应该另有其不泯的丰富价值。前述近世诗歌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倾向,还多是现象描述,有必要进一步提炼出一个更具概括力和涵摄性的诗学术语。笔者以为,“情境诗学”也许是一个可供讨论的选项。
因为无论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还是地域化和私人化,都必然落实为一种具体的人生情境。日常生活化指向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生情境,地域化指向空间细化后所感受到的人生情境,私人化则指向最个性化和内视化的人生情境。这里的“情境”不同于王昌龄《诗格》中所提出的“情境”,《诗格》的“情境”重“情”轻“境”,更多是将“境”视为“情”的后缀,两者并不对等,而本文的“情”与“境”则更具对举平行意味。“情”指的是一种主观化的感受,近于心灵史性质;“境”指的是一种外在境遇,近于生活史性质②“情”、“境”不论是单用还是联用,皆有多种复杂的含义,如不做具体的限定,则无法深入讨论问题。本文将“情境”大致限定在“心灵史”和“生活史”的范畴,这一思路,受到了廖可斌先生《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一文的启发。;以之类推,为了纪念和记录人生而呈现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近世诗歌,其“纪念”近于“情”而“记录”近于“境”。令人欣慰的是,近世诗歌和诗论中的“情境”虽各有不同意指③如宋晁迥《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中的 “情境”,是用于佛教意义上。明郝敬《艺圃伧谈》卷一:“汉魏人以情境为诗,多真逸;六朝人以辞彩为诗,多艳丽。虽艳丽而文生于情。若唐人以名利筌蹄为诗,限声偶,袭格套,如今之对股时文。”略同于《诗格》中所谓之“情境”。明卞永誉《书画汇考》卷四十六《仲姬雪梅图》:“是日微雪着红梅上,云栖子见示管夫人《雪梅》,与今日情境适合。”是将“情境”等同于“情景”。,但也不乏近于心灵史和生活史性质的可供借鉴的诗学资源。如“事境”的提出就强化了“境”的叙事意味。近世以降,诗歌的行为性、动态性、过程性的内容有所增加,叙事性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④参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周剑之《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增强叙事显然更利于人生境遇的记录,因此古人又常以“事境”视之,甚至以为“情”必借“事境”始能出之。如明张鼐曰:“古之人得于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达之。”[11]清翁方纲所论更为深刻,他对王士禛那些以神韵见长的诗作从“事境”等角度提出了批评:
若以诗论,则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于实际出之也。[12]
惟其须知渔洋于诗教总汇众流,独归雅正矣,而乃不得不析言其失。其失何也?曰:不切也。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实在于此其少为。[13]
在翁方纲看来,如非“切人切时切地”的亲身经历,事境便不能真切,“理味”、“性情”也不能出之,“神兴空旷”更无从谈起。王士禛那些不切事境的诗歌,不能算做“惬于人心”的佳作。翁方纲已看到“性情”与“事境”的统一性,可惜没有对“性情”与“事境”进行诗学理论上的再度提升,反而以“肌理说”统摄一切诗歌,又回到“经典诗学”的老路上。其实,近世诗歌和诗论文献中,较早将“情境”概念与“事”相联系的可以追溯到元代的陈绎曾,他在《静春先生诗集后序》云:
情发为诗而生于境。使诗真出乎是,而居苍莽、遇□莫,虽欲为富丽雄伟,不可得也。居顺境者反是。□其居而习焉者为主于内,即其遇而感焉者万变乎前,二者合而见乎辞,诗之体于是不一矣。十五国之诗,音声情态,往往不同,居使之然也。《周》变而《王》,《豳》易而《秦》,遇使之然也。夷考其衷,《王》、《周》、《秦》、《豳》,歌哭虽殊,本音犹在,欣戚虽异,故态未志。习之主于内,盖有不可得而变者矣。楚骚以降,家殊人异,情境之真,未尝求异古人,当有自能成家者。……清(情)境之遇,错然百变,而平和祥雅主于中者,固蔼如也。严古似建安,工致似三谢,娴冶似徐庾,冲澹似陶元亮,合数长而引之。于律度盖近取之王介甫,就其资与学而发之,于所居、所遇不失情境之真,斯可谓不求异古人而自成能家者矣。[14]
陈绎曾强调“情生于境”而“发为诗”,境之“遇”虽百变,而因境之“居”“主于内”,故有不变之“本音”。他的“境”虽包含静态之“居”与动态之“遇”,但无疑更看重静态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而较为忽视动态的“境遇”。明代何白的“情境”也值得注意,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
或持一说者,以为诗为心声,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无尽,吾诗亦无尽。当其目之所触,牛溲马通,无非上药,外无乏境,内无乏思。此论未尝不合作者之旨,但取材太杂,则有秽冗之讥,矢口成篇,复伤率易之病。究其归宿,不过词家一丛谈小说部耳。虽胸次如洗,殊少淘汰谨严之法。[15]
何白的“情境无尽”、“外无乏境,内无乏思”其实已有点接近生活史和心灵史,可惜他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说这段话的,对“情境”缺乏更深入的讨论。到了晚清的杨沂孙,终于在心灵史与生活史这一路向上,拈出一种明确而积极的“情境”来。他在《粤寇陷虞,予家与赵次侯避地崇川,同治元年十月,次侯检示家乡所作诗稿,读之不胜今昔之感,爰系以诗》中写道:
古人多悔少年作,每欲焚弃费搜索。我谓书画文章与年进,加以见闻阅历增开拓。是以中年以往所作始苍劲,不同少年初学犹薄弱。独是诗歌则不然,早岁亦复有寄托。因境生情写以诗,境遇诗留情有着。情留既难忘,诗留何必削。况乃性灵流露任天真,春水方生异冬涸。……朅来示我昔年诗,岂意清词未零落。因此昔年情境留不忘,朋辈平生寄欢若。卷中情境我亦与,惜无诗篇记隐约。我读君诗倍惘然,愿君莫把彩毫阁。渡江以来诗几何,不计妍媸记忧乐。此情此境如何过,由后视今如视昨。知君欲作诗史示后人,我先睹之引深酌。[16]
很明显,杨沂孙所说的“诗史”不同于赠誉杜诗的“诗史”,而更侧重于个人的生命史和生活史。正是这种个人化的境遇,使人触境生情,而以诗歌表现之,从而使“情”有了赖以附着的基础。情既借诗中之“境遇”得以不泯,诗亦有了存在的价值。诗歌只要能够再现“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具体历史情境,即能获得一种进入过程的在场感,达到“昔年情境留不忘,朋辈平生寄欢若”的目的。可以说,杨沂孙关于“情境”的论述是相当辩证和精彩的,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无独有偶,晚清周鹤立《匏叶龛诗存》自识也表达了相近观点:
诗不足存,存所遇也,所遇亦不足存,存夫师门之奖励、友道之切磋,即筮仕以后上交下交、相孚弗替,虽极艰难困苦、琐尾流离,几迫于颠踣,而卒能履险如夷者,未始非文字因缘默相维系也。……至于区别宗派,沿溯源流,则茫乎未有所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我所欲言而已,岂敢树坛坫、争敦盘哉。[17]
周鹤立甚至自谦说写诗不是为了纪念自己,而是为了纪念师友对自己的帮助,其间的因缘际会,诗歌也常扮演重要角色,自己因附丽于群体而得有存在感,并无在诗史上争一席之地的念头。杨、周的诗学主张完全不同于古典诗学兴象玲珑的审美理想,反而将诗歌看作人生的一种纪念,一段生命中的回忆,诗的日常化不仅是题材的日常化,而是功能的日常化,不是诗道高雅,而是日常应酬之道。于是,历史的感悟、日常的琐碎、生活的智慧、人生的回忆、情感的多变、心灵的深邃,共同交织成生命的复调。在生老病死面前,经典作家与非经典作家成为同样的存在。正像一百个人都同样努力工作,虽然最后成功者可能只有一个,但不能说另外九十九个就没有意义,过程中种种复杂的情境包蕴着无限的可能,价值和意义即在其中。近世诗歌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也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之中被重新赋予了价值和意义,“情境诗学”由此可以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观照诗歌的一种方法。如我们喜欢以流派区分诗人,但这些流派的标准显然是静态的、后设的,不能照顾到丰富的历史情境。于是清代中叶后诗人但凡言“性灵”必归诸“性灵派”,没有注意到“性灵”实可泛指内心世界,不同诗人所说的“性灵”内涵和外延并不一致,不尽属于“性灵派”的范围,即使是被文学史定位为“性灵派”主要代表的张问陶,其《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云:“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散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他根本不承认自己诗歌与袁枚之间的联系。同样,我们从其他被划归某派的诗人作品的具体情境中,也常会发现对诗歌流派的划分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一个诗人对待同一个对象的看法,在不同情境下也常有所变化。杨沂孙曾深刻批评过那些胶柱鼓琴地理解归有光评点的人:“震川先生治古文,自谓得力于《史记》最深。每下第,辄取《史记》重读而评点之,计传于世者不啻十数本,其见地用意,前后不同,各有所主也。夫一人之诣,阅数十年而不能同者,后之人乃据其一时之见,而以为精意在是,可乎。”[18]因此,从“情境诗学”的立场看问题,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问题本身的丰富性,做到不过分削足适履或厚诬古人。而且,即使站在历史学维度,“情境诗学”也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历史常被人讥讽为一部“帝王将相史”,梁启超《中国之旧史》即云:“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美国学者福尔索姆也说:“在中国史研究中,历史事件、制度和人物太多地散发着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气息。中国人的浓烈的温情和仁爱消失在职官名称、章奏和上谕的一片混杂之中。只凭变换那些著名官员的姓名就可以在实质上完成你对历史的叙述……传统中国史志和传记的特质,其中固然有我们需要的原始材料,但是通常却缺乏私人生活情况的记载。一个中国政治家的政绩会被详细记载下来,可他的生日却通常付之阙如。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从国家的观点来写的,因而,查寻历史人物的七情六欲的任何努力通常都会一无所获。”[19]但是大量别集的存在,如果从“情境诗学”的角度看,不正是活生生的个人之史么?尤其是诗歌,常被看作生活的结晶,也凝聚着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从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的生命活动和心灵呐喊。如韩崶的问梅诗社,其《还读斋诗稿》载社集次数达一百四十六次,似乎无关国计民生,却是地域文人密切交流及个人生活史和生命史的形象写照。不妨举一个例子:晚清常熟穷秀才翁苞封,授徒为生,又经商从事借贷,负债后避走山东,妻儿在家困苦万状,两儿不幸相继夭折,作者吁天呼地,写出《追悼亡儿》一诗:
忆昔我为山左游,两儿幼小不解愁。大儿髫龄方六岁,小儿才过岁一周。老妻含悲下楼送,强忍径走不回头。当时未拟长游衍,客怀日日思乡县。懒云倦鸟知有时,头角峥嵘会相见。不道一年长子殇,七龄弱息死痘创。得书痛定旋自解,尚有一儿两岁强。既非巢覆无完卵,一雏虽失犹未妨。况我时时动归思,得归只在少得志。一索再索瓞重绵,此后添一意中事。岂知落落寡世缘,飘泊天涯竟十年。鹪鹩一枝借方稳,恶耗千里惊来传。顿悟浮踪诚枉道,急趣归装装草草。顾外原非素位行,春梦醒时人已老。归来惨淡旧柴门,满目萧条见泪痕。自顾依然穷措大,抛书浪走吾之过。病妻瘦尽旧形容,孤苦伶仃人一个。妻言忍死盼天涯,为有征人未返家。大局还宜为君顾,苟延免使路人嗟。徐溯频年勤鞠育,始自孩提至入塾。八岁读竟四子书,十岁能书字盈幅。内而稼穑知艰难,外而庆吊走亲族。上而春秋入祖庙,奔走豆籩礼数熟。时而母忽病支床,兀坐床前不易方。侍汤侍药颇知谨,手能执爨口能尝。有时纳凉坐夜月,唐诗雒诵声琅琅。窥测人情度事理,出言辄中成人似。母抚儿喜儿亦喜,人言翁子真有子。子弟能佳事最良,境虽贫困亦寻常。不望阿爷归载宝,望爷归乐宁馨郎。何期生命薄于纸,奇疾忽撄来若驶。医言喉风不可为,十一岁儿三日死。一番听罢黯神伤,不是儿亡是我亡。此后诒谋竟安在,孽由自作何由悔。伯道虽知有命存,西河抱痛宁无罪。我离老父事远游,劝驾者谁歧路绐。本之不立末焉生,宜我块然如木瘣。君子达天无惧忧,穷通悟彻敢怨尤。妄想妄求前日事,吾生今始知行休。中夜忽然狂叫走,无后不孝伊谁咎。庙中何以对祖宗,地下无由见父母。浃背但觉汗流浆,抚膺频呼负负负。吁嗟乎!命在难从造物争,安贫守拙了馀生。堪叹迂儒不悟此,谬作牢骚鸣不平。[20]
此诗艺术上不能说很高明,语言也很朴素甚至有些粗糙,却如闻人当面泣诉命运的残忍和精神的绝望,“不是儿亡是我亡”的万念俱灰,“中夜忽然狂叫走”的惊狂失控,“地下无由见父母”的愧惧苦痛,仿佛场景就在目前,有一种进入历史情境的真切感,你能说他没有感染力和文学价值?
总之,当我们拿起逻辑与历史的“手术刀”,对这些精神密码予以解剖,在具有丰富意味的私人化和生活化细节中,分享其生命史、生活史、情感史和心灵史,使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年碎影”重新映入人们的视野,让那些芸芸众生的生命过程被人们真切感受。我们也因而可以勾连古今,修复正经正史与私人记忆之间的断裂和龃龉,使有限的人生得以无限的拓展,也使宏大政治与宏大文学叙事之外的世界得以逐渐丰润,历史和文学因而变得更加丰富迷人。“情境诗学”在这个层面上,使海量的非经典作品获得了更加堂堂正正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四、馀 论
“情境诗学”有可能面对的挑战与疑问,一是它如何与“情景”、“意境”相区分;二是它如何解决自身含摄的诗歌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三是作为属概念的“情景诗学”应该包含哪些可以逐层分级的种概念。
第一个疑问,需要概念上予以厘清,简言之,“情境”是“情感”与“境遇”的叠加,即“情”加“事”,重借事以传情,其事包括外在于情的一切事与物;“情景”是“情感”与“景象”的叠加,重通过外在自然景象表达情感,其面较“境”为窄;“意境”则是“情”与“景”的结晶,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21]。可以看出,“情境”较“情景”或“意境”更具动态和包容性。
第二个疑问,则需有一种理性和追问的态度,即日常生活是重复、单调、琐碎的,诗歌的日常生活化是否也会带来重复、琐碎和无趣感?而过于强调私人化的生命感受,是否会使诗歌趋于自闭,引起交流和共享的障碍?我们看古人诗歌,有时确有题材陈腐、千人一面的疲劳感和厌倦感;对于某些诗篇的意旨,有时也确有不知所云的茫然感。因为人类基本需要相同,在许多方面的情感体验与表现方式也相似,这本无可讳言。非经典作家的确难以同中见异,易于在文学表达上陷入模式化和套路化;或者走上另外一个极端,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自闭型情感传达。
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在我不在彼。为什么?古人已逝,留下的作品是静态的,如何组合、挖掘、运用,要看研究者自己的能力。即使是大量题材重复的作品,我们能不能从中提炼出共同的规律,并精准地解释这种现象?梁启超《中国之旧史》云:“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我们要力争成为那种“贵乎史者”,写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域或一个群体具有特征性的思想与情感。另外,诗歌是情感的密码,我们能否读懂文本,解开密码,进入作者色彩各异的生命世界和具体的历史情境?这就要看研究者自身功夫的深浅。
第三个疑问,涉及“情景诗学”体系的建立和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一个不容回避而本文确又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因为“情境诗学”涉及内容复杂,其体系的建立与成熟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积累。这里只能就其总体原则泛言一二:
首先是对待文献的态度应有其“淘汰谨严之法”,“情景诗学”虽然力求资料的详备,但学术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再详备的材料也无法真正还原历史,历史说到底仍是一种有着严格学术要求的书写。因此,“情境诗学”并不强求文献的巨细无遗,也不是无原则地堆砌材料,而是强调在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倾向的文献中,凭藉选取材料的眼光和分析材料的功力,发掘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呈现出个人的生活质感和生命情感,最终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其次,应该辩证看待“情境”。“情境诗学”不同于冷冰冰的历史事实叙述,而必须有活生生的人的情感投射,即他必须是以文学的形式很好地发挥感性的力量,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在场感,哪怕是一种游戏之作,也要求其事境能恰当真实地契合其情。如明末沈宜修、叶小鸾等人均有十题以上的《艳体连珠》;清乐钧《青芝山馆诗集》以《形体诗十二首戏创此题聊以叙怀》分咏心、发、眉、目、耳、鼻、口、肩、腰、腹、手、足;李福《花屿读书堂词钞》以《沁园春十二阕》分咏额、鼻、耳、齿、肩、臂、掌、乳、胆、肠、背、膝等,阅之颇能体会一种当时文人的生活情趣。此类诗作,不必因无深刻的社会意义而弃之如敝屣。
最后,对待“情境”必须有具体的分疏,如“情境”有作者真实经历的“情境”,也有代言或拟作的假设“情境”①笔者将之区分为“所历”与“所拟”,参《范浚诗歌的多元诗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2期。;而代言或拟作传统中既有古代诗歌的传统,至明清又发展出一种代圣贤立言的传统(由八股文浸染至诗歌,诗歌中有不合儒家诗教的表达常被删落或修饰);再进一步,不论是真实经历的“情境”还是代言或拟作的“情境”,历时既久,往往会形成一定的模式或套路,这些都会对情境的真实认知带来影响(如诗人的表达是否只是套式的借用)。再如诗歌的地域化和私人化存在,会形成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制约和其他诉求,使诗歌表达不能不考虑人情、利益等因素,其复杂关系该如何处理?又如对境或事的重视,会否使得这些非经典诗歌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史学方面而非文学方面?这一切,显然无法一蹴而就。
要之,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是近世诗歌的重要表征,而如果只能品尝到其模式化、自闭化的苦果,这种责任要由我们研究者自己来负。而“情境诗学”不仅不任其咎,反而是为了规避这种负效应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开拓,但是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这种努力和开拓,距离其成熟期或体系的系统化还遥远。我们只是提出一种不苛求修辞、章法、句法、字法、用韵、节奏,不同于经典诗学的另一种打量文学的眼光。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够推动“情境诗学”评价体系的初步建设,使其最终能够不仅适用于近世诗歌,也成为理解其他非经典诗歌的一条有效路径。
(本文承叶晔、王宏林、周剑之等友人慷慨惠示材料和心得,谨此致谢)
[1] 彭玉平.白雨斋诗话前言[M]//陈廷焯.白雨斋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26.
[2]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3]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10.
[4]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8-39.
[5]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
[6] 郎廷槐.师友诗传录[M]//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38.
[7] 易闻晓.诗道高雅的语用阐述[J].文学评论,2008(2):19-24.
[8] 陈师道.后山集[M]//四库全书:卷二十三诗话.
[9] 周紫芝.竹坡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354.
[10] 吴可.藏海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333.
[11] 张鼐.题孙叔倩百花屿稿叙[M]//宝日堂初集.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二年刻本:卷十二.
[12] 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1.
[13] 翁方纲.苏斋笔记[M].东京:日本古典刊行会,1974:卷十一.
[14]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M].清光绪吴兴陆氏家塾刻本:卷六.
[15] 何白.王伯度[M]//汲古堂集.明万历刻本:卷二十七.
[16] 杨沂孙.濠叟居士集[M].常熟图书馆藏钞本.
[17] 周鹤立.匏叶龛诗存[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3.
[18] 杨沂孙.读武昌张氏所刊归评《史记》[M]//观濠居士文集.常熟图书馆藏钞本.
[19] [美]福尔索姆,等.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前言.
[20] 翁苞封.井蛙鸣[M]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1]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M]//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191.
(责任编辑:梁临川)
Situational Poetics: Another Route to Understanding Modern Poetry
ZHANG Jian
(InstituteofLiteratur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The poetry since Song Dynasty has been characterized with the trend of routi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to some degree. Zhuzhici of Qing Dynasty, poetry expressing longing for friends and loved ones, the compilation of collections likeNostalgicCollection, poetry in memory of the past and so on made the trend all the more obvious. Among them, enormous concomitant non-classical poems have unique value hard to be explained by classical poetics. “Situational Poetics” in particular, which has been refined during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poetr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emphasizes psychic and livelihood levels, thus entrusting modern poetry with new meaning in terms of routin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oncrete life situations. “Situational Poetics” not only points to modern poetry, but also works as an effective route to understanding non-classical poetry through the ages.
situational poetics; psychic history; livelihood history; routinization; localization; privatization
2014-10-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ZW054)
张 剑(1971- ),男,河南遂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明清文献学研究。
10.3969/j.issn 1007-6522.2015.01.006
董乃斌
I206
A
1007-6522(2015)01-0092-11
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是贯穿中国文学史发展轨迹的两大传统。它们同源共生,互滲互竞,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消长起伏,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当代,以至未来。两大传统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各时代的存在状况与形态,实乃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大题目,既是一种宏观研究,又可以是在宏观指导下的中观或微观研究;既有较强的思辨性理论性,又可以是具体细腻的实证研究。但以往对两大传统的研究数量既不平衡,观念亦有偏差,或以为叙事传统仅与小说戏剧相关,或未能平视抒情叙事,甚至有意无意崇抒情而轻叙事,倡虚灵而贬质实,从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审美精神的特质,产生了种种偏见与误解。为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实际和中国审美精神的特质,有必要创新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首先就是要对叙事传统的研究进行认真补课。补课从哪里开始?我们特选择积习较深而亟须新变的关键部位,即文学研究中的历代诗歌研究入手。
我们的研究并非白手起家,前人的许多成果是我们立足的基础和起步点,外国的某些理论则给予启发和借鉴。无论古今中外,有关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都需要加以消化、理解、应用和转换,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创造。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就大致体现了我们的致力方向:从文学史实际出发,既重视提炼前人经验,也勇于学习外国理论,而以解决自身的问题为旨归。
本专栏隶属文学学科。本期为首刊,今后将不定期刊出。热诚欢迎广大读者关注、批评和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