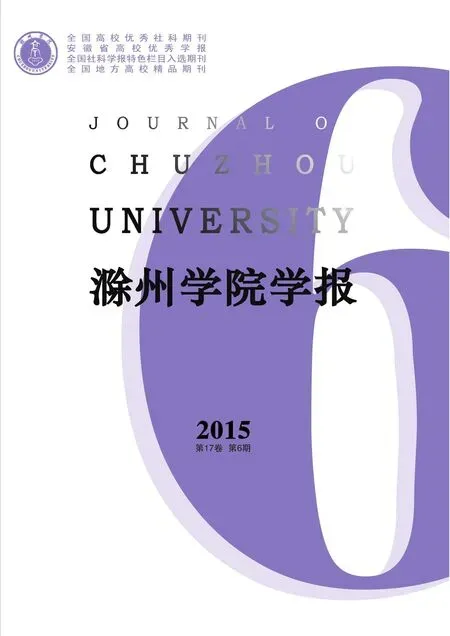“了”的句法位置及语义分析
吴胜伟,程家才,孙秀银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认为“了”是个助词,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表示动作或变化的完成;用在句中或句末停顿的地方,表示肯定语气。熊仲儒[1]认为当“了”还有“消除”、“了结”义,可作动相补语。也就是说,“了”至少有三个义项,那么这三个义项在句法的实现上有何差异?本文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下展开,为三个不同的“了”指派句法位置,并拟测其语义特征。为便于讨论,我们把作动相补语的记作“了1”,把表示动作或变化完成的记作“了2”,把表示语气的记作“了3”。
一、相关研究回顾
从文献来看,学界对“了”的范畴类别划分大致为时体助词、时制标记、语气词、补语词等四类。基本上,要么认为“了”是其中一个类别,要么认为“了”身兼两职。具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了”是个时体标记词
关于“了”的范畴属性,虽然学界观点不尽相同,但对其是时体标记基本上无异议。金立鑫[2]认为“了”能够表示时体意义,但在不同句法条件下所表示的时体意义并不完全一样,这些不同的时体义是由其所出现的句法条件决定的。朱庆祥[3]则认为“了”具有[+完结有界]特征,是个时体范畴,它出现与否,取决于其后补语的出现与否。吴福祥[4]认为“了”是时体范畴的标记,但其不能强制性地使用,其原因是汉语的完成体和进行体不是强制性范畴。税昌锡[5]虽然主张“了”具有“完结”和“起始”的两面性,承认其为时体范畴,但又说句中“了”和句末“了”在语法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因此他认为传统观念上对“了”的区分,仅具有句法分布的作用,在区别语法意义上价值不大。
(二)“了”既是时体范畴,又是语气词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了”即可表时体功能,又可表示语气。刘春卉[6]以确山方言相关歧义结构分析为基础,明确提出了有两个不同性质的“了”,前一个实际上是时体范畴的标记,后一个“了”是个语气词。彭利贞[7]认为“了”并不是时体范畴的标记,而是指向情态,是对情态敏感的指示性成分,表示情态的出现或变化。何文彬[8]认为“了”就是个语气助词,具有主观性的表意功能。崔立斌[9]通过对外国留学生的错误分析认为存在两上不同的“了”,一个用在动词后表示完成,是体标记,另一个用在句末表示变化,是语气词。
(三)“了”是时制范畴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了”是时制(tense)范畴的标记。李铁根[10]从汉语时间表达的角度对时态助词“了”的表时功能作了综合的考察分析,认为“了”是个时制范畴的标记。潘文国[11]通过对“了”字英译的穷尽性研究,认为“了”虽具有表时和表体的因素,但要承它一种“体标志”在技术上尚有难度。甚至潘泰[12]还认为“了”可以表示时体意义,也可以做补语。
综上所述,“了”的句法功能确实强大,可以做时体范畴的标记,可以做语气词等。有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自己的主张进行了论证,但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探讨“了”的句法位置和语义特征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至于“了”是不是时制范畴的标记,我们暂不讨论,因为汉语中是否存在时制范畴尚有争议。
二、充当动相补语的“了1”
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最早由赵元任[13]提出。梁银峰[14]认为动相补语能够给所表述的事件增加一种终结意义,可以把它处理成一种“准体标记”(quasi-aspectual marker)。
一般把句(1a)分析为中动句(middle voice sentence)或役事主语句。所谓中动句是指从语义上来看,句子表达的是一种被动含义,由于没有形态标记,从形式上来看采用的却是一种主动句的结构。句(1a-b)中的“了”表示的是“吃饭”这项活动的终结,是对“吃饭”这项活动结果或状态的说明,因此把它处理成补语有着语感上的依据。根据功能范畴假设[15],扩展主动词“吃”的是表示达成义(become)义的达成范畴(Bec),Bec的逻辑语义表达式为(2)。
(1)a.饭吃了。
b.张三吃了饭。
(2)[[BECOMEE:Y]BECOME[STATE:Z]]/BY[V]
从逻辑语义表达式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达成范畴Bec要为主动词选择两个论元,一个是Y,一个是Z,并分别为他们指派役事和状态/结果的题元角色。句(1a)可以用逻辑语义表达式(2)来实现。
(2)[[BECOMEE:饭]BECOME[STATE:了]]/BY[V:吃]
显然,(1a)中的“了”在语义上表示的是一种结果或状态,在句法上充当主动词“吃”的结果,所以可为句(1a)指派结构(3)。
(3)[BecP[Spec饭][Bec’[Bec][VP[V吃][RP了]]]]
结构(3)可以继续受表致使义(cause)的致使范畴(Caus)的扩展,同样致使范畴(Caus)可以为主动词选择一个论元,并为其指派致事(causer)的题元角色。一般来讲,致事应该是一种活动(ac-tivity 但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驱动下,句法通过转喻机制选择活动的参与者作致事。如句(4a),“张三走山路”就是活动作致事。同样也可以运用转喻机制选择活动的参与者做致事,如(4b),“那条山路”就是活动的参与者做致事。也就是说重动句是活动做致事的一种标准式。
(4)a.张三走山路走得满身是汗。
b.那条山路走得张三满身是汗。
句(1b)中,“张三”其实就是通过转喻机制转喻“张三吃饭”做致事,是语言经济原则的具体表现,当然也可以用活动做致事,如句(5)。关于句(5),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语感,有的认为可以接受,有的认为不可受,原因可能就是对经济原则的违反。
(5)?张三吃饭吃了。
句(1a-b)可以有如下变换。
(6)a.饭吃了。 a’.把饭吃了。
b.张三吃了饭。 b’.张三把饭吃了。
朱德熙[15]认为“把”是介词,其作用在于引出受事。熊仲儒[16]认为“把”是表致使义功能范畴Caus的语音实现,并不是介词。熊的分析可以避免“把”后没有名词性成分的难题,如句(7),维护了汉语禁止介词悬空的理论假设[17]。
(7)?茶碗,张三把摔了。
结合结构(3),可以为句(6b-b’)中的句子指派结构(8)。
(8)a.[CausP[Spec张三][Caus’[Caus吃了][BecP[Spec饭][Bec’[Bec吃了][VP[V吃][RP了]]]]]]
b.[CausP[Spec张三][Caus’[Caus把][BecP[Spec饭][Bec’[Bec吃了][VP[V吃][RP了]]]]]]
动结式是句法生成的合成词[1],它不同于词法生成的词。虽然我们在结构(8)中把它标注为VP,这仅仅是为了言说的方便,没有实质性意义。因为词汇性成分具有不可解释的特征,要强制性的受功能性成分的核查并为其各项特征定值后,才能够自由作句法成分。所以似类(8)中的动结式是词,不是短语。在结构(8b)中,Caus语音实现为“把”,由于“把”具有排他性,能够阻断受其成分统制的词汇核心向其移位。所以动结式“吃了”停留在Bec处。在结构(8a)中恰恰相反,Caus没有语音实现,出于音韵上的要求,Caus会吸引受其成分统制的动结式“吃了”移位到Caus处,满足Caus音韵上的要求。
综上分析,句(1)中的“了”是功能性成分为主动词选择的论元,并被指派了结果性题元角色,即在语义上表示一种终结状态,在句法上做补语。
三、时体范畴的标志“了2”
时体范畴(aspect category)即某一时间动词表示的行为是持续还是完成。“了”是由实词虚化,后又词缀化,逐渐形成时体范畴的标记[18]。
一般认为,时体助词“了”在语音上具有黏附性,需要附着在一个实词上。在这一点上,时体助词与功能性成分具有一致性。我们不妨假设“了2”就是时体范畴的语音实现。下面讨论该假设的可行性。
(9)a.饭吃完了。
b.张三吃完了饭。
根据功能范畴假设,可以为句(9a)指派结构(10)。
(10)[AspP[Spec饭][Asp’[Asp吃完-了][BecP[Spec饭][Bec’[Bec吃完][VP[V吃][RP完]]]]]]
在结构(10)中,“完”是由表示达成义的功能性成分Bec为主动词“吃”选择的论元,并被指派了结果性题元角色;“饭”是[Spec,BecP]处合并,是Bec为主动词“吃”选择的外部论元,被指派了役事题元角色。时体范畴“了”在句法上高于达成范畴,即时体范畴是扩展达成范畴的功能性成分。鉴于Asp的语音实现“了”在语音上的黏附性,根据开明的自利原则[19](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为满足“了”的黏附要求,句法合成词“吃完”核心移位到 Asp处,与之嫁接;同样,处于[Spec,BecP]处的“饭”被拖带移位到[Spec,AspP]处。当然,句法计算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9a)是典型的役事主语句,还可以受表致使义的功能性成分Caus的扩展,如句(9b)。同样,我们可以为句(9b)指派结构(11a)。
(11)a.[CausP[Spec张三][Caus’[Caus吃完-了][AspP[Spec饭][Asp’[Asp吃完了][BecP[Spec饭][Bec’[Bec吃完][VP[V吃][RP完]]]]]]]]
b.[CausP[Spec张三][Caus’[Caus把][AspP[Spec饭][Asp’[Asp吃完-了][BecP[Spec饭][Bec’[Bec吃完][VP[V吃][RP完]]]]]]]]
综合结构(10-11a),可以看出,处于 Asp处的“吃完了”在Caus音韵的驱动下,移位到Caus处;若Caus语音实现为“把”,则会阻止受其成分统制的成分“吃完了”向其移位,如结构(11b)所示。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句(12)的原因了。
(12)*张三把吃完了饭。
可见,把“了2”分析为表时体义的功能性成分,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因为我们可以为其找到合适的句法位置,能够使句法计算收敛;我们认为“了2”是时体性成分,在语义上表示“时体”概念,这也解释了母语为汉语说话人的语感。
四、语气词“了3”
黄伯荣、廖序东[20]认为语气词的作用在于表示语气,主要用在句子的末尾或句中有停顿的地方,它本身念轻声。由此可见,语气词不只是用在句末,还可以用在句中。
在句(13)中,有两个“了”,根据前文分析,前一个是“了1”,是动相补语,表示活动的结果或状态。后一个肯定不是“了1”,因为主动词的姐妹节点(补足语位置)已被“了1”占据;也不可能是“了2”,因为“了2”是时体范畴的标记,在语音上要黏附在一个实义动词上。那么,它可能是语气词或别的范畴。我们暂假定其为语气词(Mood),下面论证将其分析为语气词的可行性。
(13)张三吃了饭了。
朱德熙[15]认为语气词是后置虚词,永远读轻声。显然,从线性序列上来看,句(13)中的后一个“了”出现在句末;从母语为汉语的说话人的语感来讲,“了”轻声;从语义上来分析,“了”意义较虚,不像是意义较实在的词汇范畴。根据Ura[21]的词汇分解假说,语气词是C层的一个功能性成分,C是扩展T的功能性成分。我们把其记作Mo。我们据此为后一个“了”指派句法位置,如结构(14)。
(14)[MoP[Spec张三吃了饭][Mo’[Mo了][TP[T][CausP[Spec张三][Caus’[Caus吃了][BecP[Spec饭][Bec’[Bec吃了][VP[V吃][RP了]]]]]]]]]
从结构(14)我们可以看出,“了”是功能性成分Mo的语音实现,吸引整个TP移位到其指示语位置,得到句(13),其移位的动机是Mo的EPP特征。这里的移位与一般的核心移位不同,这里是短语移位,不是核心移位。另外,“了3”还可以出现在句中,如句(15)。
(15)张三吃了饭了啊。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认为“啊”是个叹词,基本等同于我们所讨论的语气词。学界对“啊”是具有表示语气的功能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既然句(15)“啊”是语气词,那么后一个“了”又是什么呢?可能是语气词,因为语气词也可以出现在句子中间。朱德熙[20]根据语气词出现的不同句法位置,把语气词分成三层,可见“啊”、“了”分属不同的句法层次。从句(15)可以得知说“啊”在句法上高于后一个“了”(了3)。我们为句(15)指派结构(16)。
(16)[Mo2P[Spec张 三吃了 饭了][Mo2’[Mo2啊][Mo1P[Spec张三吃了饭][Mo1’[Mo1了][TP[T][CausP[Spec张三][Caus’[Caus吃了][BecP[Spec饭][Bec’[Bec吃了][VP[V吃][RP了]]]]]]]]]]]
在制图理论看来,“了3”是个语气词,它是C层的一个功能性成分,它的EPP特征比较强,能够吸引受其成分统制的短语发生移位。另外,从句法位置上来看,“了3”可以出现在句中,也可以出现在句末,这是因为语气词的不同层级所致。
五、结语
“了”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具有不同的语义内涵。在生成语法看来,至少存在“了1”、“了2”和“了3”三个不同的“了”。其中“了1”在句法上出现在谓词性成分的后面,做动相补语,在语义上表示结果或状态,并被指派了“役事”的题元角色。“了2”是时体范畴,由于音韵上的原因,需要黏附在主动词后。“了3”表示的是一种终结或完成的语气,是语气范畴。在句法上把“了”区分为三个,有利于句法结构的指派和语义的拟测,并能很好的解释母语为汉语说话人的语感。
[1]熊仲儒.当代语法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金立鑫.“S了”的时体意义及其句法条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2):38-48.
[3]朱庆祥.从序列事件语篇看“了1”的隐现规律[J].中国语文,2014(2):134-148.
[4]吴福祥.汉语体标记“了、着”为什么不能强制性使用[J].当代语言学,2005(3):237-250.
[5]税昌锡.基于事件过程结构的“了”语法意义新探[J].汉语学报,2012(4):44-58.
[6]刘春卉.“了”的分类问题再探讨[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4(6):11-12.
[7]彭利贞.论一种对情态敏感的“了2”[J].中国语文,2009(6):506-517.
[8]何文彬.论语气助词“了”的主观性[J].语言研究,2013(1):10-18.
[9]崔立斌.韩国学生对“了”的误用及其原因[J].语言文字应用,2005(5):11-23.
[10]李铁根.“了”、“着”、“过”与汉语时制的表达[J].语言研究,2002(3):1-13.
[11]潘文国.从“了”的英译看汉语的时体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4):62-69.
[12]潘泰.现代汉语“没”与句中“了”的时体属性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09(3):286-290.
[13]赵元任著,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4]梁银峰.汉语动相补语“来”、“去”的形成过程[J].语言科学,2005(6):27-35.
[15]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6]熊仲儒.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17]Huang,J.,A.Li,& Y.Li.The Syntax of Chines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2009.
[18]王多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9]Lasnik.H.Case and Expletives Revisited:On Greedy and other Human Failings[J].Linguistic Inquiry,1995(26):615-633.
[20]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1]Ura,Hiroyuki.Checking Theory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Universal Gramma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