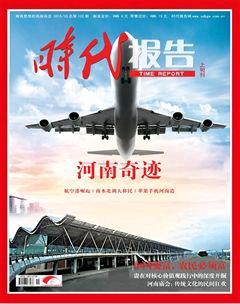脑瘫诗人余秀华
林迪
诗人余秀华,湖北钟祥乡下的脑瘫患者,默默写诗十五年,去年在《诗刊社》微信上的诗歌得到广泛传播。有人质疑这种传播是否是炒作,有人质疑她的写作是否有人代笔。这种质疑暴露了大多数人与诗歌隔绝得太久——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很多人读诗不是一件正常的事。爱读余秀华,没有问题,这也许是中国人真正热爱诗歌的第一步。
公众和诗歌“偶然相遇,绝不是什么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好事”,诗人余秀华在微信上刷屏那两天,诗人沈浩波如此说。沈浩波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余秀华凭借“脑瘫”这样的标签以及“穿过整个城市去睡你”这样耸动的诗歌标题,获得公众的意外关注,媒体亦蜂拥而至。在浮华与躁动背后,余秀华真正的光芒也许才刚刚显现。
2014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举办了一场名为“日常生活,惊心动魄”的诗歌朗诵会。五位“基层诗人”——余秀华、在私企上班的诗人小西、理发师红莲、送过快递的秦兴威、煤矿工人老井,是这场朗诵会的主角。他们每个人都有若干首诗被挑出,印在“诗刊号外”上。诗人及大学生次第上台,朗诵自己最喜欢的诗作。
朗诵会开始之前,《诗刊》主编商震发言说,“基层诗人”诗作中最可贵的品质是“可靠”:“关键不是成为别人,而是成为你自己。”
然而每一个“自己”都是立体的,不同的情境会流露不同的性情。商震说他从基层诗人的诗作中看到了士大夫情怀。
五位诗人最接近士大夫的是河南兰考县的80后诗人秦兴威。他现在是图书编辑,参加过诗刊社第27届青春诗会。在一首名为《地铁口失明的卖艺人》的诗中,秦兴威写道:“我们从他身边走过/我们冷漠地走过去/我们施舍,我们施舍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余秀华读的是自己的诗作《我养的狗,叫小巫》,其中有让人心头一凛的句子:“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在余秀华的诗里,这样的句子随处可见:“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我爱你》)。
《麦子黄了》的开头有大片气象:“首先是我家门口的麦子黄了,然后是横店/然后是江汉平原……”由此落笔写个人的际遇,个人的际遇不再廉价。顺着类似的句子往前往后看,却常有落差。余秀华的诗有佳句,但其“生态”杂芜,读者很难把佳句从其语境中连根拔起。
《苟活》不动声色,一眼望穿人间残酷:
每天下午去割草,小巫跟着去,再跟着回来/有时候是我跟着它/它的尾巴摇来摇去
这几天都会看见对面的那个男人割麦子/见着我一脸谄笑地喊着秀华姑娘/我就加快割草的速度/好几次割破了手指
这个上门女婿,妻子疯了20年了/儿子有自闭症/他的腰上总是背着个录音机/声音大得整个村子都听得见
我的一只兔子跑到了他田里,小巫去追/但是他的镰刀比狗更快/他把兔子提回去以后/小巫还在那里找了半天
“喜欢余秀华的诗,因为我也是农村长大的,也曾不管不顾,也被世俗抓住头发在墙上磕。更重要的是,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2014年11月,《诗刊》编辑刘年在编发余秀华作品的编后记中写道。
在诗歌中,余秀华借以完成自己的强,恰恰是美学上的弱。对弱的事物持久深入的关注,小狗小兔、花草白云都是她关注的对象,她说她“爱雨水之前,大地细小的裂缝/也爱母亲晚年掉下的第一颗牙齿//我没有告诉过你这些。这么辽阔的季节/我认同你渺小的背影/以及他曾经和将要担当的成分”(《爱》)。但她绝非小情小调地风花雪月一番的诗人,而是赋予这些事物她自己发现的世界观,让万物与她一起自足于、并承担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白、白色意象频繁出现在她的诗中。白是脆弱的、无辜的、甚至是贫瘠,却又是宽容的、接纳其他一切微弱或丑陋事物的。这似乎解释了她的诗为什么给予“大众”安慰,弱之力如水随势赋形,我们在余秀华诗中感到的那种“灵动”“即兴”也如此。
她的诗歌也并不雄辩,毋宁说那是一种“雌辩”,诉诸的是诗本身神秘非理性的逻辑,自有其妙。雄辩的诗歌向来为中国当代诗推崇,而余秀华的诗放弃辩论,放弃自圆其说,甚至放弃结论,因此与读者并不构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关系,反而联合读者一起面对世界之种种不如意,一起去对许多强悍的事物咄咄还击——即便为雄性思维的人所不喜。
余秀华与中国许多雄性诗人的不同,还集中体现在对情欲的书写中。且以她著名(但她也自认并非很好的)诗作《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与相似的男诗人普珉的《我穿过一座城市去肏你》相比就可以看出,普珉的诗也是好诗,但只能见我,而余秀华的诗,尝试见你,见众生(虽然并未完美)。普诗里的“你”是一个被抒情主体赋形的欲望对象,整首诗呈现的纯爷们攻性角度,并没有和传统诗歌里的那些性关系主宰者的强势抒情有什么本质区别。诗经时代的淫奔之诗,强调的是两情相悦、默契与暧昧,这点倒是余秀华的情欲诗有继承。
在性书写中,女性诗歌能抵达的高度如果超越男性,可能也是因为她放弃了进攻与索求。在余秀华这里这点更为显著,她的情欲渴求明显是虚构的、无望的,但正因为如此她得以不像大多数男诗人那样囚于自身欲望,被荷尔蒙驱动着疯狂;而是基于无望、无所求而得自由,这也是余秀华的爱情诗在2014年后半年的飞跃,你能感受她的轻松。
在随笔《摇摇晃晃到人间》中,余秀华这样写:“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了诗歌。因为我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
她不能干重活,平常就扫扫院子,农忙时帮忙烧饭洗衣,也摘棉花,更多时间,她孤独,这促使她沉思,写诗。“其实我一直不是一个安静的人,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在给《诗刊》配发的自述中,余秀华写道,诗歌“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对于余秀华被冠之以“中国的狄金森”这样的称号,评论家徐敬亚认为余秀华的抒情诗,情感准确甚至凶猛、感悟精致而微妙,但尚需修剪芜杂,将诗意模式更加完善。因此不仅与狄金森有着巨大差距,连成熟的经典诗的程度也还达不到。这是对余秀华中肯而客观的评价。然而,公众爱读余秀华并没有问题,这也许是中国人真正热爱诗歌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