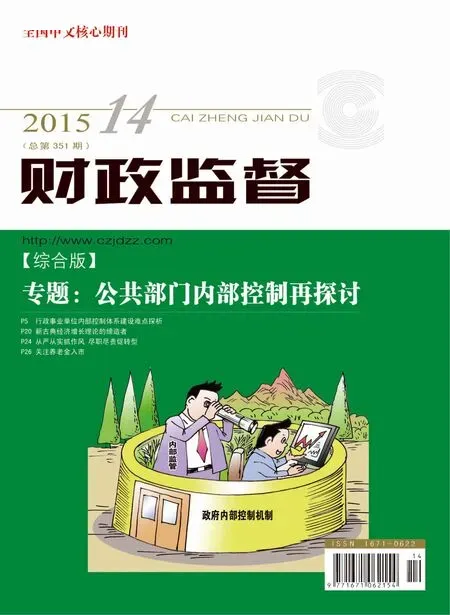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三个问题
●郑春荣/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三个问题
●郑春荣/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低已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4》,2009年-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分别为2.2%、2.0%、2.5%、2.6%、2.4%、2.9%,低于同期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另据2011年审计署公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审计结果,3万亿元的社会保险基金结余中,有96.5%的基金结余存在银行。这说明,基金投资收益低,主要是投资组合偏保守。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6月29日开始,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管理办法拟规定的养老金净资产30%以内可投资股市,最备受社会关注。笔者认为此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新政,总体上来讲是一大进步,但受制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定位不清、基金统筹较低等问题,投资管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完善之处。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性质
养老保险基金的性质决定了其投资风格。
首先,如果养老保险基金是现收现付制,那么资金即收即发,结余量很小,没有保值增值压力,其投资原则追求流动性与安全性,不追求盈利性。如果养老保险基金是完全积累制,那么基金结余将在参保人整个工作期间都不动用,可供投资的期限长达20~30年,其投资盈利性要求就非常重要了,否则基金在几十年里跑不赢通货膨胀率,将严重贬值,影响参保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
其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养老金体系的第一支柱,要解决基本的养老需求,因此更注重基金的安全性;补充养老保险基金(职业年金)属于养老金体系的第二支柱,属于养老金的“锦上添花”,风险容忍性高,可以更好地追求盈利性。
本次入市的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有两种:一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需要引起强烈关注的是,这两种养老保险基金在性质上是有所区别的。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大头,2014年底累计结余3.18万亿元,但其基金性质是含糊不清的: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单位缴费形成统筹基金,职工个人缴费形成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从理论上讲,统筹基金是现收现付制的,不应该也不需要进入股市保值增值,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制的,应该进入股市,追求长期投资收益。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将个人账户资金用于发放当期老年人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实施空账运行,后来个人账户进行了部分做实,但资金管理仍然与统筹基金合并管理。因此,本次养老保险基金入市被一些学者批评是在没有界定基金性质的前提下,匆忙入市。笔者认为,基金性质不清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基金投资股市的比例较低,可以在保证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基金的收益性,可以视为政策的优化。当然,这也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我国应当尽快明确养老保险基金的模式,避免出现制度模式与实际运行情况不相符,影响参保人的参保信心和社会稳定。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是小头,2014年底累计结余3845亿元。目前这部分基金的性质非常明确,是个人私有的、完全积累型养老保险基金。基金投资股市是制度的内在要求。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位农民看到他把养老的钱缴纳到养老保险基金中,却发现每年增值率跑不赢通货膨胀率,他肯定拒绝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自愿参保的)。因此,提高基金收益率是保证参保率的前提条件。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参保人的年龄问题,一般而言,参保人的年龄越小,投资期越长,风险容忍性较高,投资风格较为激进;参保人的年龄越大,投资期越短(离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没有几年了),风险容忍度较低,投资风格较为保守。但本次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办法未能有效考虑这一投资原则的变化。
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目的与责任主体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养老金可以纳入投资运营范围的资金总计约两万多亿元,按照《办法》“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30%”的规定,预计可用于股市投资的资金规模在6000亿元左右。有观点认为,“国家队”的规模又壮大了,在股市出现震荡的当前,养老金入市承载着维稳、救市、托底的功能。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责任主体是谁?不同的责任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
纵观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只有一个目的——在保证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投资收益率的最大化。养老保险基金不应承担所谓维稳、救市的功能,也不负责解决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历史上,曾经有多个国家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结果不难想象:国家经济增长了,但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却低得可怜。举个例子,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在管理上缺乏独立性,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只能投资政府定向发行的国债,而国债利率被人为压低,结果造成中央公积金在1987-1998年之间的实际收益率只有0.07%,与新加坡同期的7.15%实质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差距。在我国也存在类似的例子,以前一些社保大案就是地方领导挪用养老基金给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这可能牺牲养老基金的利益,换取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每个参保人都是养老保险基金的主人,但不可能每个人都亲自管理基金,需要将其管理权委托出去,让专业机构代表参保人的利益来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目标。各发达国家一般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基金理事会,来使养老保险基金能够长期坚持其投资理念(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第102号劳工公约的建议,当政府委派一个机构管理养老保险基金时,受保人员的代表应当参加理事会。理事会由雇员代表、雇主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这三方力量应相对平衡,每方都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在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养老基金理事会的代表性,还引进一些社会保障专家作为“独立理事”加入。
对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我国拟入市的养老保险基金并没有设立理事会,而是将基金交给“受托机构”来全权管理。该办法对“受托机构”的定义是指国家设立、国务院授权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这种管理方式存在两个不足之处:
一是不能保证“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能够充分反映参保人的利益诉求。前文已经谈到,养老基金的投资目标有别于政府的目标,后者主要是为了经济发展、物价稳定和解决就业。如果国家设立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牺牲参保人的利益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那么投资收益就是一句空话,在制度设计上无法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
二是“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有垄断嫌疑。管理办法上并没有提出“受托人”是哪家机构,但目前已有的“国家设立、国务院授权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只有一家,就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那么将三万亿的养老保险基金全部给予其管理,有垄断嫌疑,参保人就没有权利选择、比较和考核“受托机构”了。需要强调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历史良好业绩并不能作为参照物。用于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于允许市场化运营,自2000年成立至2013年底,基金累计投资收益4187.38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8.13%,远超过同期2.46%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但这良好的业绩背后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改制时,引进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作为战略投资者,随着这几大行在内地和香港上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获利丰厚,这种投资机会是不可复制的,也是其他投资主体无法取得的。此外,笔者认为,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管理的1万亿战略储备基金,拟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的养老支出,基本上这二三十年不会动用本金,在资金性质、管理机构设置和投资风格上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宜同时管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保基金。
三、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及其对投资管理的影响
根据现行养老保险管理体制,我国尚未实现真正的省级统筹,基本养老保险完成省级政府统筹的仅有4个直辖市和陕、青、藏等几个省份,养老基金在许多省份仍然沉淀在地级市,省政府只不过拥有调剂金而已。统筹层次低,对投资管理带来了一些困扰:
第一,养老基金入市首先要将各地散落在几百个地级市的养老金结余归集到省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办法》对此也有相关规定。然而养老金结余归集也并非易事,既有相关利益的掣肘也有不同地方收支情况不同造成的归集工作的困难。
第二,养老基金面临持续的申购和赎回问题。由于许多省份和地级市的养老保险基金面临不确定的养老基金收支形势,例如劳动力流入,将增加缴费收入,劳动力返乡,不但缴费收入没有了,已往的缴费收入还要带回老家。因此,一些地区在将养老基金委托投资以后,在面临基金收不抵支时,可能还要赎回投资,这将在操作上形成一定难题,养老基金必须像开放式基金那样,每天公布申购和赎回的净值。■
(本栏目责任编辑: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