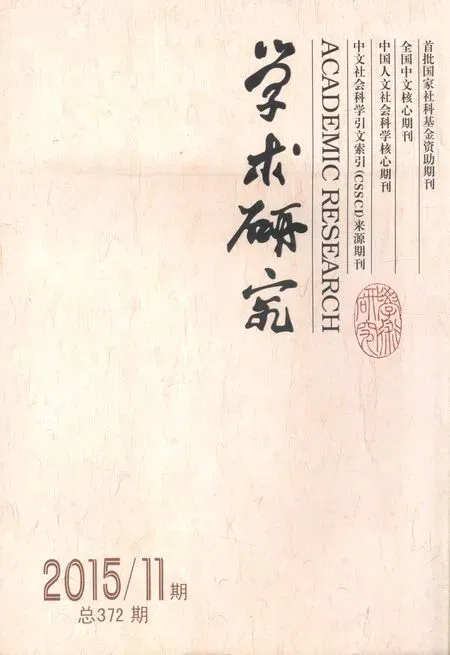西方理性主义终止符:泰德·休斯诗歌综观
张平功
西方理性主义终止符:泰德·休斯诗歌综观
张平功
20世纪英国桂冠诗人泰德·休斯的诗歌作品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他的诗通过自然意象和夸张想象的呈现,不断寻求尊重主观世界、崇敬自然力量的个体存在方式,构建其独有的精神世界的主张,以此拒斥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与正统的人文主义思想。休斯诗歌的主题表征﹑批判精神以及犀利诗风,在当代仍有珍贵的精神价值和美学意义。
泰德·休斯自然主观工具理性人文主义
泰德·休斯(1930—1998)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文学家和桂冠诗人。他的世界观受到多种思想影响,其诗歌特色鲜明,寓意不凡,思辨深刻,有力地批判了工具理性以及现代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其诗歌创作是一个不断远离西方启蒙思想主流话语、不断脱离人类机械生存状态的过程。休斯的创作不受任何既有思想体系或僵化观念限制,敦促人们对现代西方社会中集体无意识及“自然而然”的服从功能进行反复探究,通过重点演绎一系列意象、象征符号及神话典故,以期带动个人、群体抵制20世纪压抑个体生存的西方主流文化,开辟别类生存方式的可能。这从以下六部诗集的综观分析即可看出。
一、反讽现代工具理性:《雨中鹰》、《牧神》和《林神》
休斯反思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诉求一以贯之,尽管在不同时期其诗歌中抵抗现代工具理性的手法有微妙变化。[1]《雨中鹰》(1957年)、《牧神》(1957年)、《林神》(1960年)三部诗集鲜明地表明休斯对现代性、启蒙思想的敌对意识。他强烈质疑启蒙思想主导下的所谓理性与生命形态的实质,看似倒向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实则与后现代感性并无干系,一是他坚信能够在原始与自然状态提供的另一生存模式找到现代工具理性的终止符,二是他几乎所有诗歌都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三是其诗作表露了对真实世界人性压迫的深刻认识和对文化危机的严肃对待。这都说明休斯执意挑战西方现代文明理性的建构,探寻想象中的人类本性,塑造一种新人文主义。这三部诗集一再突出其思想理念,大力拓展创作题材,采用多种新奇复杂的表现形式,抒发对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距离感和反抗情绪。[2]
在休斯的早期诗歌中,存在大量动物意象如雄鹰、美洲虎、熊等。飞禽走兽代表着充满野力与生机的自然,大量援用动物意象来批评人文主义的所谓理性,成为他这一阶段的倾向和最有力的方略。[3]动物界的本能生存模式迥异于现代人精神衰落的状况,它得到了休斯的赞扬。三部诗集对人文主义工具理性的批评主要通过两方面来表现:一是诗中人物(动物)对特定戏剧性情景的过度反应,二是对人类态度或发达工业社会人工制品或明或暗的嘲讽。在诗人笔下,人类残忍迫害其他生物和自然界,而自己却丧失活力,生存状态比多数动物还要低等,如同《雨中鹰》所吟:“我淹没在咚咚作响的耕地,我从/大地的吞咽中拔出一个脚步,/泥土每一次陷绊住我的脚踝……但是鹰//毫不费力高悬着平静的眼睛。/双翼在轻松的恬静中包容宇宙造化,/沉稳得宛如幻景在流逝的风中。”[4]人与动物,常被视为自然界最基本的二元对立。鹰被人类视作低等动物,然而修斯认为,深陷泥潭的人类自身显得颓然不振,毫无生气,丧失了自然赋予的生机活力,与从容翱翔的飞鹰相比人是那么吃力可笑。这三本诗集对人文主义理性的基本特征反复提出质疑,批判大多隐含于各种巧妙复杂的动物意象指涉之中,这颇为大胆地拓展了传统英语自然诗的题材范围和主题呈现。休斯多用反语、讽刺和幻象,抒发其内心的深刻感受,诗风尖锐而狂放,对文明社会的抵制愈加激进,批判愈加犀利。
《马群》、《马群之梦》、《风》、《公牛摩西》和《美洲虎》等诗巧妙地揭露工具理性与人文主义的缺陷,这些诗基于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生存模式的二元结构,表达了诗人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人类与自然之间壑谷鸿沟的担忧;诗歌热情颂扬动物生存所呈现出的无畏精神,并将读者带入这种虚拟现实,使其渐渐熟悉依附于诗中人物自身或周围异我的存在。这些诗维持了休斯批评人文主义理性的一贯态度,回应了压迫人性、丧失人性、无法接纳异我的外在文明现实,并由此澄明了动物被重新赋予的象征意义。诗中渲染了反人文主义倾向,将自然的报复和暴力想象成异我对人类世界的必然回应。因此,现代人与动物的二元关系暗藏预警。如《美洲虎》的动物意象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它既是动物本性的化身,代表着自然野力,也暗喻被理性驱逐的异我本能:“人群围着的一只笼子跟前,如被催眠,/如儿童凝视梦幻,凝神看着一只发怒的美洲虎,/在它的眼睛钻透短短的一段熔丝之后/疾步走过囚笼的黑暗……/它绕栅栏旋转,但对它笼子并不存在/……世界在它有力的大步下转动。/地平线从笼室地上移来。”[5]诗人的描写令人深思。代表自然的美洲虎被人类囚禁,但对它而言,囚笼形同虚设,它依旧昂首阔步追求本性中的自由,将世界踩在脚下,它的狂野暗示着自然对人类暴力的报复。美洲虎暗喻人类异我的本能将最终冲破理性的铁栅。面对这一切,人类似为美洲虎的野性催眠,充满无助与困惑。
《聚会》、《鸫》、《栖息之鹰》等诗中明显带有挑衅意味,通过尖锐的反讽、似是而非的幻想来贬抑整个文明秩序,如鸫般精准有劲的捕杀,如鹰般随心所欲、无须论争地分配死亡。[6]在作者看来,这些均属人类的傲慢天性,是人类存在状态的真实写照。[7]这从某种意义上提出了对抗现行社会秩序的可能,与现代既有思想模式和价值体系相抵触。《鸫》和《栖息之鹰》向读者发出祈求,希望得到积极回应。在前期诗歌创作中,休斯抵制现代社会的情绪和诉求已经显现,同时他对动物的态度处于反思与自省过程,他不断尝试新的自我表达方式,改变对动物界生存状况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认知,大胆地进行了《海獭》、《一只猪的看法》、《六月四日》、《狼嚎》和《第二只眼看美洲豹》等诗歌创作,在揭露人文理性、现代人机械生存状态的缺陷方面大胆探索和尝试。
二、颠覆人文主义的神话:《乌鸦》
《乌鸦》(1972)诗集标志着诗人在抵制现代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启蒙主义思想策略上的转变,体现了其思想和意识导向的变化。[8]他彻底否定人们对发达的现代社会所抱有的希望与憧憬,厉声斥责进步与现代性,并试图说服读者摈除这种观念。然而,休斯精心将现代社会各种脱节错位和弊端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不意味着他是后现代主义者,他抨击现代性之猛烈,恪守既有体系外的价值理念,与后现代轻松愉悦的怀疑和解构论调相比大相径庭。与现代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作抗争是休斯作品的显要主题,这种抗争充分体现于前三部诗集,并在描述乌鸦所面对纷扰现状的《乌鸦》诗集中做了新演绎。《传说二则》和《家世》置于诗集开端,奠定了整部诗集不安的基调。在泰德的象征体系中,“光”代表启蒙运动和当代西方文化,然而,它们所带来的成就和功绩,在这两首诗中却毫无踪迹。在《传说二则》中,主人公乌鸦的心、胆、脾、肺、眼、喉、头发、皮肤都汲取不了一丝光亮,通篇透着让人窒息的阴沉。如此强调黑暗,这不仅是文题修辞的需要,而且表达出诗人对某种无可挽回的危机的强烈感知。组诗描绘了科学技术、工业霸权对原始力量的打压放逐,其中的黑暗意象则暗示着原始力量是完整生物体的必需构成,不可被消灭或镇压。在《黑色四足兽》、《灾难》、《奥斯弗兰塔利斯之战》、《乌鸦在媒体上试音》、《乌鸦行猎》、《不败的乌鸦》、《乌鸦败下阵来》、《乌鸦皱眉》、《乌鸦的虚荣心》等同题材系列中,乌鸦被赋予了高智商和人类特征,它拙劣地模仿人类生存现状,但组诗并没有将乌鸦塑造成始终如一的角色,反而让它在不同背景下呈现出不同面貌,时而是普罗大众,时而突出文化象征,时而被恶魔附身。如果说休斯早期诗作并未充分利用动物世界与人类世界的二元关系质疑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乌鸦》组诗则在这方面发挥了丰富想象,利用主人公乌鸦的所言所行所观所感,深入到了现代西方文化扭曲面,并利用反语和讽刺,与现代社会主流思想针锋相对,对立的口吻从轻蔑戏谑逐渐强化为剑拔弩张的猛烈抨击。《黑色四足兽》和《乌鸦即兴创作》就是对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的直接进攻。《黑色四足兽》中的乌鸦为了找寻四足兽竟到处砍杀,同类相残,连自己的兄弟也要“把他的内脏翻出来看看颜色”,[9]理性压迫已彻底扭曲乌鸦天性,造就了疯魔杀手与极端暴力,这些均成为诗人直接批判和谴责对象。诗人抨击的不单是现代性与启蒙运动的理念架构,由此衍生的行为、思考模式也在批判之列,而且附属于理性体系下的合法暴力与正义战争使两者完全不堪支撑人类社会的和平与持续发展。
在批判西方社会人性的缺失方面,《奥斯弗兰塔利斯之战》、《乌鸦在媒体上试音》、《乌鸦行猎》和《灾难》等篇为典型之作。诗歌以乌鸦为消费文化和大众意识的代表,采用了立体手法,质疑语言、暴力和意识形态三者既有观念,揭露现代社会消费至上文化的弊端。乌鸦在《乌鸦在媒体上试音》中试图对自然高歌却无法发声,怀疑通常使用的语言是否具有表达力;《乌鸦行猎》中的乌鸦与常人无异,有贪婪的占有欲,完全被消费文化所支配。休斯对交流方式的看法与后现代主义者大不相同,他既未抨击人类语言,也未模糊语言跟现实的界线,不过他意识到现代文化对语言以及语言与认知关系的限制是现代人所为,由此,语词背负着极大束缚,如《灾难》诗所说,“它(词)的威力衰退了/它只能吞食人类……它的时代过去了”。[10]《笑声里》和《乌鸦讲述的战争》等诗描述一连串自相残杀的战争与暴力行为,表达了对理性主义的愤怒,突出了诗人对异教时代的满腔热情和重塑人文主义的渴望。《苹果的悲剧》、《蛇的赞歌》、《孩童的恶作剧》、《乌鸦的第一课》、《乌鸦与上帝密谈》、《乌鸦的神学》和《乌鸦的玩伴们》,则对主题的处理有所变化,这一变化旨在颠覆基督教的传统神话和权威。《蛇的赞歌》反对基督教将性看成为人类堕落之源,表达了诗人不满于基督教对性所抱的极端想法,也明确表达了他对现代女性的态度。从一系列关于性的意象可以看出,女性被物化为纯粹的男性渴望或性的激情。在《乌鸦的第一课》、《乌鸦领受圣餐》中,对基督教神话的颠覆愈演愈烈,坚持自然本性的乌鸦不但拒绝接受基督教“主”的教化,还将上帝的尸体当成食物吞入腹中,同时,爱的代言人只能永世目瞪口呆,这是戏剧性表达,也是诗人的态度。《乌鸦的神学》、《乌鸦的玩伴们》明确声言,真正的神灵只存在于原始自然,人类创造的宗教脱离神性,是人为创造的图腾。而《乌鸦的最后据点》、《乌鸦与石头》、《乌鸦将自己画入中国壁画》、《乌鸦唱的大象图腾》、《微笑》、《腐肉之王》、《情歌》等诗,则预示人与自然日益扩大的裂缝即将达到最大化,世界末日的到来正在燃烧一切,却烧不掉厌恶现代文明的乌鸦,它的最后据点是作为天性和本能的象征。这个离弃现代文明的乌鸦最终对着自然高唱情歌,“做着同一个梦,梦里彼此不分离”,宣布对带有深刻局限性的宗教神性的最终判决。贯穿这组诗的暗线是休斯对人文主义的失望——前景狭窄且暗淡的人文主义不能带给人类任何可期的希望与未来,在颠覆人类的宇宙中心地位时,也传递着这样的信息:非人性的力量能够在瞬息间逆转特定社会或文化的发展进程。
三、现代人精神危机的表征:《沉醉》和《穴鸟》
休斯的后期诗歌不仅批判了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还孜孜追求现代人精神危机的终止符。《沉醉》(1977)和《穴鸟》(1978)投映出一种替换性生存方式,它远胜于工具理性主宰下的机械生存模式。诗人在猛烈抨击现代人类世界道德秩序的同时,承认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并非是客观和主观世界和谐统一的进程,因而两诗集建立了一个想象的、自由自在的生存方式,将人类生命的意义、尊严和非理性至上的意识紧密相联起来。这种非理性意识对现代人而言,将个体归入整体,整体永远保持着史前原始时代所具有的勃勃生气,因为后者将自己看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沉醉》神化阳性生殖崇拜,表现了非理性至上的生存方式;《穴鸟》则戏剧性地演绎荣格的“个性化进程”。《沉醉》对女性的刻画显露了休斯的父权意识,他不能理解或接受现代女性主义提倡的女性角色与地位,诗中有的女性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从其他性渠道寻求满足感,另一部分则纯粹沦为男性气概神秘仪式的祭品。[11]丈夫们是缺失人性、单一精神驱动的理性主义者,女人的性格则显得复杂强悍。譬如,她们一开始就肯定了跟拉姆的肉体关系,并且对待耶稣的诞生并不像男性一样态度不一,而是积极维护之,因此女性被描述成男性的对立面,由此让读者误以为诗人对女性心怀某种尊敬之感。但是,诗中的女性仅仅代表肉体,并不具备思考能力。诗人的描写强化了珍妮特、贝蒂、波琳·海根、西湖太太和戴维斯太太的身份意识,但却抹杀了她们的人性和自我认知的客观能力。在叙述转移到拉姆跟费丽茜蒂的关系时,诗人颠覆现代女性角色的手法更为明显,拉姆的无耻行为和伪善阴谋竟透着一股使人感到神秘的敬畏感,他对费丽茜蒂的迫害也被神化。诗人借拉姆对费丽茜蒂的感情发展,说明凡是自然规律都有例外,他并未直接评价两者关系,而是通过结合幻想、暴力与仪式的叙述方式虚构一系列奇妙经历,表露了作者对整个事件发展的看法。作为父权体系的典型产物,费丽茜蒂与拉姆发生特殊关系后拒绝像拉姆生命中的其他女人一样遵从男权社会传统思想,向拉姆提议私奔结婚,却迎来牧师的冷漠无情。《沉醉》最后一章的场景设在女性疗养院,重点描写仪式执行场景,揭开幻想式超越与原始仪式的神秘面纱,诗人视后者为人类存在模式的另一种选择。在最后的章节里,拉姆选择跟费丽茜蒂发生性关系,这在莫德跟其他妇女眼中表明拉姆正在偏离他自己化身的自然力量忠实代言人制定的行为规则。在随后的暴力死亡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已不如其在性别、仪式那样有力地向读者传达出对待女性的态度。从“神圣的物品、神圣的玩偶”这类比喻可以看出,诗人对费丽茜蒂以至所有女性角色的态度都不够端正,诗人试图通过将女性角色抽象化以及中和整体观念的表述,说明她们主体性的缺陷。被动、无知、缺乏自主的特点使她们陷入拉姆的掌控,从而备受侮辱。《沉醉》里仪式的重要还在于整体至上生存方式不能与理性至上的生存方式共处,从中也映出休斯的批评者姿态。
《穴鸟》则体现了诗人情感上的变化,但抵制现代理性主义的思想主旨未变。诗集以轻松的口吻续写《沉醉》,描写手法实现了创新。利用荣格的个性化进程与整合发展模型为当今西方文化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思路,[12]通过内在转化,在炼金术过程中重生。《穴鸟》主人公是苏格拉底式的个体,他为现代主流意识所控制,对现代性霸权思想自信满满,而诗歌明显写出诗人与主人公在意识层面的分离,纠正、补充或是推翻这一个体所包含的意义。自然作为一股再生力量,被各种意象、象征和重复出现的“她”来指代,自然多半不包含暴力,并拯救了向她走近的个体。《尖叫》、《第一次恐惧以后》、《落败时分》、《被告》和《最初,皮肤的可疑图案》等,奠定了《穴鸟》整部诗集的讽刺基调,在揭露工具理性和人文主义之恶时,急切地敦促人类对自然要谦恭崇敬,因为理性思考毫无救赎能力,《尖叫》就开宗明义道:“当我看到小兔子的脑浆迸裂在马路上,/我知道银河系的车轮由我操控。/……/我也张开了口赞美,/但沉默嵌入我的咽喉。/像一把黑曜石匕首,干巴巴的,锯齿的边缘,/无声的肿块如火山口的熔晶,/尖叫/把自己呕吐了出来。[13]
工具理性造成了自然生命的涂炭,而苏格拉底式的主人公“我”已为工具理性剥夺了对人间疾苦的感知能力,仿佛回到休斯早前诗集中无情冷漠的鹰一般。它对一切毁灭视若无睹,只剩一声尖叫,工具理性只得跟《被告》的主人公一起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勒令其经历一趟重生之旅,洗涤罪孽。诗中的个体或谦卑地辩解或高傲地声讨,都构成讽刺,并随着冲突的发展越加尖锐起来。这股原始力量有着自相矛盾的作用,使得死与生、暴力与和平既是手段亦是结果,不可分割亦不可避免,但暴力在此仅代表一种象征性的能指。《绿地之母》和《刽子手》悄然带来神灵威力的广袤无边而无法接近之感,通过隐喻来宣扬神灵力量,这对现代主流意识是非同寻常的。《绿地之母》大力颂扬地球提供给人类丰富多样的生命形式,诗中意象的表现形式、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的内涵将绿色和自然升华为崇高信仰。
理性与文明占主宰地位时,自然存在的完整或本真性不可实现,但《穴鸟》的倒数第二章实现了逆转,主人公的行为表明人类重燃对自然和非人类的神秘崇敬。《穴鸟》似乎解决了主观与客观世界的冲突,这在《骑士》、《某些事正在发生》、《我来的时候看见一个树林》、《在审判庭被严责的乌鸦》、《赤步行走》、《谜语》、《新娘与新郎躲了整三天》组诗中逐渐明朗,从彻底向自然投降的骑士到承认罪孽的乌鸦,直到《新娘与新郎躲了整三天》构架出一种理智与情感、文明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于是,欢喜地喘息,惊奇地呼喊,/如泥造的神明,/卧躺在泥土中,却异常地小心,/让对方尽善尽美。”新娘、新郎重塑对方身体的神话被想象为高级情感意识的载体而保留了神秘的敬畏。同时,代表理性与文明的“他”和暗喻自然与感性的“她”完美地结合,两者的平等共生抚平了彼此的愤怒与对立,对神明般的和谐喜乐“异常地小心”珍惜,孕育出尽善尽美的精神新世界。相比突出仪式感的《沉醉》,《穴鸟》更重视通过一定的转变,人便可以无瑕地融入自然亲密而神秘的关系中,两部诗集都表现了诗人与基督教及其他传统宗教的不休论战,与此同时,诗人满腔热情地崇敬充满生机的自然以及对生命的劳伦斯式的看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诗人所主张替换型生存模式的前提,实现这种模式须依靠现代人意识和实践的根本转变,或如诗歌所示,对现行体系的必然、彻底的颠覆。休斯所秉持的观念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和现代性霸权意识的批判,是高度吻合的。[14]
综上可见,休斯的诗作坚守特定题材及自身的认知导向,独特的诗歌意象、奔放不羁的风格以及深刻的表现力,“为英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5]他通过诗歌传达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文化霸权跟启蒙运动以降的人文主义企图吞并、压制个体,威胁着自然生命体的存在,因此文学创作要揭示这种吞并压制手段的内在特征及形式。虽然休斯的激进姿态与同时期积极抵制主流文化的文学家并无大异,但如果把休斯的诗作与其他同时期批判主流文化的文学作品相比较,前者意义更加深邃,诗风更加犀利。他的诗通过自然意象和夸张想象的呈现,不断寻求一种尊重主观世界、崇敬自然力量的个体存在方式,构建其独有的精神世界的主张,以此拒斥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与正统人文主义思想。
[1]Underhill,Hugh,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Poet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303.
[2]Ousby,Ian,The Cambridge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84-485.
[3]Sanders,Andrew,The Short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2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633.
[4]阮伟、徐文博、曹亚军:《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307-308页。
[5][6]汪剑钊编:《最新外国优秀诗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21页。
[7]Sanders,Andrew,The Short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2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p.634.
[8]Underhill,Hugh,The Problem of Conciousness in Modern Poetry,Cambridge UP,1992,p.634.
[9]刘国清:《论诗集〈乌鸦〉主人公的角色变迁》,《山东外语教学》2004年第5期。
[10]Sagar,Keith,The Artof Ted Hugh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11]Ousby,Ian,The Cambridge Guide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85.
[12]Fordham,Frieda,An Introduction to Jung’s Psychology,New York:Penguin Books,1953,1981,p.77.
[13]Hughes,Ted,Cave Birds:An Alchemical Cave Drama,New York:Viking,1978.
[14]Marcuse,H,“Excerpts from‘One-Dimensional Society’”,One-Dimensional Man,London:Routledge,1964,pp.9-31.
[15]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I106.2
A
1000-7326(2015)11-0154-05
张平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英国斯泰福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广州,51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