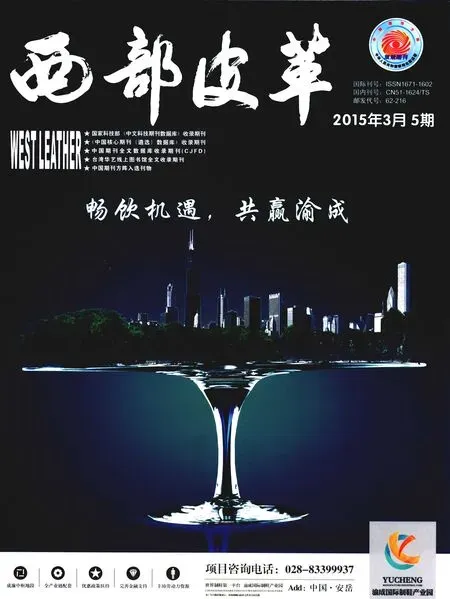古代鞋履改革花如锦(中)
文黑龙江/周祥
古代鞋履改革花如锦(中)
文黑龙江/周祥

【纳底鞋纳出千层底】
中国古代矿山采掘、选矿、冶炼,有文字记载始于战国时管仲的《管子·海玉篇》,书中的“官山海”,就是实行盐铁官营。由此可知中国早在战国时期,铁与盐已有专业经营管理,铁制生活工具已很发达。在坊间及闺秀中,早已有铁针在飞针走线,出现纳底鞋已不足为怪。从考古出土文物亦可得到佐证,如广西出土的两汉铜质跪像,已见有鞋底“纳有线纹”;从山西侯马出土的周代武士跪像背面,明显见有鞋底上有整齐的一行行线迹。秦墓出土的兵马俑中,弓步手所穿方头口履鞋底,都是统一的纳底工艺所成。由此可见,纳底布鞋在军旅群中成为军鞋,已不是简单的鞋底制作工艺,而是一种弃旧图新的制鞋工艺改革,这不啻为一种革命性的嬗变,它标志着纳底鞋的结实耐磨耐用,因此由军旅逐渐普及到民间,并以强大的实用性,广泛在民间流播久经历代而不衰。
纳底鞋历经数千年沿革到清代,并由北京内联升创造出驰名天下的传统产品“千层底”。清朝咸丰三年(1853)由赵廷以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北京创办前点后厂的内联升鞋店,不仅专营朝廷命官的官靴制造,还以小圆口千层底缎子鞋和小圆口千层底礼服呢鞋而闻名遐迩,旧北京曾流传着“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的民谣。当时,穿一件绸子长衫,脚上穿一双内联升的小圆口千层底缎鞋或小圆口千层底礼服呢鞋,为最时兴、最贵雅的上乘人物。内联升的千层底之所以颇受人们喜欢,因以用料质量好,制作精细而取信于人。有一套严格的操作规程,纳底讲究针眼细,麻绳粗,刹手紧,使层层白布结成整体不走形变样。这样的千层布底,
具有冬御寒、夏散热等优点。辛亥革命前,“千层底”主要用作制靴,辛亥革命后,该店又将“千层底”缝绱尖口、圆口布鞋以及大舌棉鞋等延续至今。
千层底布鞋为中国布鞋最有代表性的鞋种。鞋底用料有两种,一种讲究的是以新布,一种是以旧布三五层打成袼褙,用鞋底样剪好,用白布包边,根据厚薄需要,将包好的底片叠好,有专用夹板工具的用夹板夹好;一般民间没有夹板,而是用浆糊将底片粘好,晾干后就可以纳鞋底了,先用锥子锥孔,再用针引麻绳纳实,纳后鞋底正面针脚为整齐的横竖成行,背面横行则为八字形的针脚。千层底正面用料一般均为白布,所以在纳鞋底时为了不因手出汗污染,则用厚布或毛巾将鞋底包着一针一针地纳。年轻的姑娘媳妇往往三五成群结伴,边纳鞋底边聊天说笑或唱歌。在徐州地区有首做军鞋的民歌:“小灯头,亮又亮,妹在灯下做鞋忙。钢针尖,线绳长,纳了一行又一行。不纳龙,不绣凤,妹盼郎哥立战功。双双军鞋送前线。俺和郎哥情意浓。”在山西尧都民间曾流传着一首民歌:“煤油灯,起灯花,新媳妇用针拔了它。灯底下,把鞋纳,千针万线为了他。他在山上搞绿化,连着三月没回家。山高坡陡不好走,不是尖石是碴碴。倘若鞋烂碰伤脚,叫人心疼说句啥?”(《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在战争年代,我军被服厂生产条件有限,只能满足“被”与“服”,而大量的军鞋基本上靠后方广大妇女手工制作。前首民歌是未婚姑娘为参军作战情郎做军鞋,纳鞋帮纳鞋底时所寄予的深情爱意;后着民歌则是刚结婚的新媳妇,为上山搞绿化的丈夫做鞋时,抒发心中对丈夫的疼爱关怀。妇女在飞针走线纳鞋底中,所蕴含的情深深意浓浓,尽在不言中。
余对千层底布鞋太熟悉了,童年时,亲眼所见母亲用旧布打袼褙,白天忙家务,常常在晚间夜伴孤灯,千针万线做一家人所穿的纳底鞋,我就是穿着母亲做的千层底长大的。走向社会我虽告别了母亲所做的纳底鞋,而娶妻生子后,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妻仍然继承祖传做鞋工艺,为一个个呀呀蹒跚走路的孩子们做纳底鞋,直到他们学业有成工作后。在国人眼中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谁没穿过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布鞋呢?如今,昔时曾浪漫了中华大地的千层底,早已成了明日黄花。毋容讳言,千层底先进的制鞋工艺是从古代制鞋编织工艺演变而来,这种划时代制鞋工艺的改革,是文明典雅鞋履发展的推动力,将永垂鞋文化史册而不朽。
【丑陋国粹血泪弓鞋】
南唐后主李煜,虽是一个不通政治、不善治国安邦的皇帝,但却是一位相貌不凡、多才多艺的风流雅士,不仅诗词文章出众,且书法绘画造诣亦颇深。在面对后周强劲的发展形势,李煜所主政的南唐上下只是坐等听从命运安排,已无回天之力挽救败局。这位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皇帝,虽是一个失败的君主,但却是一个成功的词人,一生中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词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千古传诵的佳作,就是出自这位可悲的皇帝笔下。不仅如此,李煜还很有艳福,除了花容月貌、气质高雅的大周小周姐妹,先后为他的娇妻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妃子,叫窅娘。窅娘虽出身于家境贫寒的采莲女,但却轻佻艳丽,能歌善舞,尤善跳金莲舞。十六
岁时被选入宫中,据说她是一名混血儿,眼睛与中原人不太一样,双目深凹,所以李煜赐名“窅娘”。为了欣赏窅娘优美的舞姿取乐,李煜还专为她建了一座六尺高的金莲舞台。为了满足李煜享乐,窅娘跳舞时以帛缠足,使其纤小弯曲如新月,外着素袜,在金制莲花上翩翩起舞,有凌云之态,飘飘然若仙子凌波,十分动人。李煜看了喜不自禁。窅娘于是常常以白绫缠足,以保舞姿优美,因此很受李煜宠爱。缠足女人之脚因此而得名为“金莲”。之后,缠足之风流入民间,宫外女子皆效仿起来。从宋开始,名媛闺秀皆以女子缠足为美、为贵、为娇、为雅,这种陋习渐渐发展到变态的地步。

由于女子缠足脚变形为尖、瘦、小,于是便产生了缠足女子所穿的“弓鞋”。弓鞋其实就是有如春秋时,为被刖刑人定制所穿的“踊”一样,是一种残疾人穿的特型之鞋。一些具有变态审美观的人,穷尽智商赞美变形的小脚与所穿的弓鞋,说缠足形似莲花、莲瓣,美其名曰“金莲”,并爱屋及乌地连所穿的弓鞋也称之为“金莲”。所以,古时金莲泛指女子缠足的小脚或所穿的弓鞋,并以三寸金莲的小脚与弓鞋为最美,“看脚不看脸”已成为那个时代选妻待聘标准。文人骚客通过诗词文章更是把三寸金莲美化到了极致,其泛滥博文屡见不鲜:“凌波步小弓三寸”(徐用理);“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杜牧);“裙边遮定鸳鸯小,只有金莲步步香”(李元膺);“翠裙鸳绣金莲小,红袖弯销玉笋长”(王实甫);“捧心无语步香阶,缓移弓底绣罗鞋”(毛熙震);“帘前三寸弓鞋露,知是腰腰小姐来”(朱有敦)。不仅古代文人骚客以赞美歌颂小脚弓鞋为雅,就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曾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的辜鸿铭,酷爱三寸金莲几近成癖,对其妻淑姑那双小脚爱得近乎痴迷。这个有名的辜疯子曾对其妻小脚妙论为“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委、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为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致。”又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臭豆腐、臭鸡蛋之风味,差可比拟。”据说,他写文章时,淑姑一定要在身边,他一手捏笔,一手捏穿绣睡鞋的小脚,鼻子嗅那味,便文思泉涌,下笔有神。他还有诗赞美他老婆那一双“三寸金莲”:“春云重裹避金灯,自缚如蚕感不胜。只为琼钩郎喜欢,几番缣约小于菱。”
那一双双小脚的女子,哪个不是从五六岁开始缠足,使双足脚趾变形,皮肉溃烂疼痛难忍,“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那双双用血泪绣制精美绚烂锦锦的弓鞋,是一次中国独有的鞋饰变态改革。经千年近似古代刖刑所着踊,对女子的摧残早已被时代抛弃。弓鞋,这朵鞋履“改革”的苦菜花,终以丑陋国粹枯朽在鞋文化的史册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