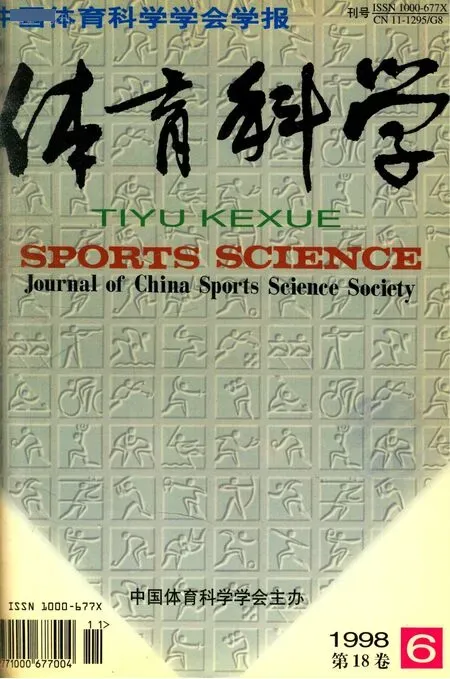从学科交叉与分化管窥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
王颢霖
从学科交叉与分化管窥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
王颢霖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以体育学、体育原理相关著作的内容变迁来解释学科交叉,并将体育学科分化演进历程划分为3个时期:体育学科分化的初现期(20世纪20年代),体育学科分化的扩张期(20世纪30年代),体育学科分化的成熟期(20世纪40年代),以阐释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过程。
学科交叉;学科分化;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
建国以来体育学的发展脉络是十分清晰的,反倒是近代体育学,就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很少有涉及到近代体育学这块领域的研究,尚属未开垦的荒芜之地。无论是近代也好,还是新中国也好,尽管是两段时期,且二者区别显见,但对于体育学来说,它应该是完整的,这关乎到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梁启超曾说:“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14]因此,本研究将分别从学科交叉、学科分化这两个方面入手,梳理史料,以客观地展现并还原出近代体育学及其学科是如何演进发展的,希望能够拾遗补缺。
1 近代中国体育学科之始:体育学
“体育学”首先是作为一门培养体育专业师资人才而设立的课程,体育专业师资人才的培养是起因于《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即“体育”一科被确立为必授科目之后,为解决体育师资教员需求量的增大。晚清政府学部在1906年的“通行各省推广师范生名额电文中,要求府立师范学堂、中学堂另设体操专修科,修习五个月,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授法等课程,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学部,1906)此处并未发现体育专业人才养成教育所需的有关‘体育专业学科’,另查部分体操专业学堂则已出现‘体育学’或‘体育原理’乙科的‘体育专业学科’(表1),(广益丛报,1908;苏竞存,1994,67-75页)且为唯一的‘体育专业学科’,亦是我国体育学原理乙科的雏型。”[9]也就是说,这些培养师资体育机构在专业上主要开设两大类课程,即学科与术科,其中,以“体育学”为单一专业学科。

表1 清末体育专业学校开设体育专业情形汇整表一览表[9]Table 1 Professional Condition of Sports Professional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晚清“体育学”应源于日本,有以下佐证:当时癸卯学制(1904—1911)为仿效日本学制,故而无论是官立,还是私立的体育专业学校所开设的体育专业课程设置上也多为日式,倒也不足为奇。清末时期的体育专业学校创办人多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最有名的就是大森体育学校,清末的这些体育专业学校大部分仿效该校的一些课程设置,如体育学、生理学与解剖学、教育学、体操(包括徒手、器械、兵式3种体操)、音乐等[27]。
经国体更替后,“体育学”逐渐转变,不再是单一的体育专业学科,原有的“体育学”学科为他者所代替,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学制变更”,即从日式的“癸卯学制”(1904—1911)、“壬子学制”(1912—1921),转向美式学制“壬戌学制”(1922—1927),而后者的颁布是受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杜威访华、像蔡元培、胡适等教育家、学者又多为留美人员,无论是从上层建筑——政府层面的倡导,还是教育界学者的推动下,都无疑将中国教育体制,甚至于学术研究体系推向美国化的浪潮中,日式的“体育学”显然不合时宜。二是民国时期留学欧美的体育学生增多。1929年宋君复(留学美国,就学于麻省春田学院)所著的《体育原理》出版后,吴蕴瑞、袁敦礼(二人时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与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的主任)于1933年出版了《体育原理》,这二人皆师从J.F.Williams(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知名学者)。同一时期出版的还有方万邦的《体育原理》(方万邦于1926年赴美,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这些留美学者也将J.F.Williams的著作《The Princip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1927)引进到了中国。由此推之,民国时期“体育原理”源自美国是确信无疑的,这也导致“体育学”课程渐渐为“体育原理”所代替。除了前文所说的3个版本“体育原理”著作外,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与“体育原理”有关的著作还有8个版本(表2)。

表2 1949年以前中国体育学原理相关专书出版情形汇整一览表[9]Table 2 Kinesiology Principles Related Books Published before 1949
从表2所显示的资料可以得知,“体育原理”专著出版的最早时间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但“体育原理”作为一门学科(课程)最早出现在民国时期,且有文献可查的是在1924年北京体育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出现的(伊见思,《北京体育学校之组织》,1924年《体育丛刊》创刊号;图2)。尽管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民国时期的“体育原理”依然受到美国的影响,如金兆均所发表的《体育真义之科学分析》(1941)一文,就是参考了美国学者的研究[爱阿华大学麦克乐教授(Charles Harold McCloy)《体育原理与方法》的笔记和讲义;斯坦福大学赫寿灵登与纳尔逊两位教授的《体育之意义与目的》的笔记与讲义][11]。可见,美国式的“体育原理”已经渐渐为中国体育学者所接纳。
至此,“体育学”为“体育原理”所替代。与此同时,体育学科逐渐扩大:已不再以“体育原理”为单一的理论学科,而“体育学”转而成为体育学科的统一名称。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王庚(1923)就提出“体育学是科学”[28]的观点。到30年代末,阮蔚村在《言论:何谓体育学》(1937)一文中写道:“体育学是适应新时代人类自觉的需要成为一种新的应用科学了。……体育学为新科学。……体育学为树立科学的体育方法之新科学。”[23]文中还涉及到了“体育学之分科及其内容”,体育学的分科包括体育学概论、运动方法学、体育生理卫生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管理学、特殊体育学、体育史学。如此看来,民国时期体育学者已经开始视“体育学”为各门体育学科的总称。“体育原理”内容的扩充与“体育学”的转变,恰好说明了近代体育学科发展的两个显征,即学科交叉与学科分化。
2 近代中国体育学科交叉
“体育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戛然而止,并为“体育原理”所代替,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原理”相比较“体育学”而言,更能说明当时体育在学科发展方面所处于的一个状态——趋向学科交叉,即学科自身内或学科之间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互为借鉴、渗透与移植的一种研究性实践活动。这里以“体育学”、“体育原理”的相关著作为例,对体育学科交叉进行解释与说明。
2.1 “体育学”相关著作
“体育学”相关著作主要有罗一东(1924)与章凌信、杨少庚(1927)所著的两个版本的《体育学》(图1),这两本《体育学》从内容上来看是颇为类似的,都设有“发育论”与“运动论”,这显然是吸收了医学与生理学的理论。不同的是,罗一东在《体育学》“总论”部分的第六章中明确地阐述了体育学与他科学(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之关系,还设有“卫生论”一编,能够将体育与卫生相结合,就已说明当时的学术界还是认同二者的关系,之后的体育理论著作基本上也都加入了与之相关的内容。而章、杨二人合著的《体育学》中则设有“体育在教育上的地位”、“学校体育方法之区分”两个部分的内容,加入了与教育学有关的理论,证明学校体育在当时已经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由此推之,教育学、医学以及生理学应该是最先被纳入到“体育学”当中的3门学科。
2.2 “体育原理”相关著作
“体育原理”相关著作从20世纪20年代起出版发行,直到1948年叶琛的《体育的基本原理》,已发展了20年左右(表3)。

图1 罗一东与章凌信、杨少庚《体育学》比较示意图Figure 1. Comparison on LUO Yi-dong and ZHANG Ling-xin of Kinesiology

表3 民国时期《体育原理》 6种版本内容一览表Table 3 Six Versions of the Princip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1.宋君复的《体育原理》(1929)较为简洁,虽只设了4章内容,但史学、哲学、医学3大学科均包含在内;第三章的第一节“体育与道德”、第六节“体育对于心灵之价值”与心理学相关,但心理学理论不够明确,整体而言,不若吴蕴瑞与袁敦礼、方万邦在章节内容上那样深入。
2.吴蕴瑞与袁敦礼在《体育原理》(1933)中提及到“训练之迁移”,这基本上与现在的提法是相同的,表明了体育学者已对训练内容有所关注,且还结合解剖学、生理学与运动学来阐述体育功能的内涵[5]。从章节安排上显然吸收了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见原书的第三章“社会之背景”,第四章“心身关系与体育”,以及第八章“体育与教育”),这为日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分科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研究。
3.与前两部著作不同,方万邦的《体育原理》(1933)将生理学与心理学融入到第二章“人类的本性和进化”当中,并涉及到了基本肌肉和辅成肌肉、学习的程序、学习律、学习曲线及训练的迁移,这与现在的“运动心理学”内容颇为相似,还设有体育教材、体育测验及测量两章。虽然“教育学”从一开始就为“体育学”、“体育原理”所吸收,但对于“教育学”原理与理论的应用,是从方万邦的著作中才有所体现的。书中还出现了一个比较全新的体育学科身影,就是“体育测量学”(见书中第八章“体育之测验及测量”)。
4.王学政的《体育之基本原理与实际》(1943),相比较其他5个版本的“体育原理”而言,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一是将教育学中的课程理论运用到了第五章“体育课程内容及其教学方针”之中;二是,第七章“训练的规律”、第八章“运动练习之南针”和第九章“基本的技能”具有运动训练学学科的意味。
5.江良规的《体育原理》(1946),从书的目次上来看,要较之以前的“体育原理”书籍有着更清晰的思路,可以看出体育学朝向学科分化的迹象,如体育哲学、体育史、体育生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体育行政、比较体育(参见第三、四、五章“体育之生理学基础”,第六章“体育之社会学基础”,第七章“体育之心理学基础”,第八章“体育之哲学”,第九章“德美两国体育概况”)。
6.叶琛则在《体育的基本原理》(1948)中将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及物理学等学科作为“体育的科学基础”(见该书中的第四章内容),还特地强调了除生理学与解剖学外,“体育程序中社会与心理的因素以及运动技术上物理学的应用,也是同样的重要”[38]。其又论及社会学与体育的关系,“使个人变成团体中的一分子,实际地学习社会行为”,并借助“心理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来说明“体育最能供给自我表现的机会”[38]。此外,其还通过心理学的两个学习理论,即“结的心理学(Band Psychology)”、“盖式塔心理学(或完形心理学,Gestal Psychology)”[38]来讨论它们对于技能学习与获得的认识有何不同,这基本上与当代心理学理论保持一致。可见,学科间互为交叉的这种趋势已成学科发展主流。
以上事实证实了从第一部《体育学》出版发行开始,其理论内容就在不断地扩充与吸纳新的学科知识(表4)。1)在20世纪20年代,史学、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就已经为中国体育学术界所接纳(参见罗一东《体育学》,1924;章凌信、杨少庚《体育学》,1927)。2)进入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以《体育原理》为主的一批体育理论著作,开始将原有史学、教育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知识领域再次扩展到了社会学、人体测量学等新的学科领域。3)至20世纪40年代,则延展至营养学、遗传学、教育心理学以及物理学学科。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些与体育学科密切相关的理论,如运动训练学、运动技能。勿容置疑,“体育学”与“体育原理”的这种学科交叉式的理论研究,为体育学科分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表4 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体育学”、“体育原理”内容发展变迁Table 4 Content Change:Kinesiology and Princip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1920s to 1940s
3 近代中国体育学科分化
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其在原有的“七艺”(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几何、算数、天文学以及音乐学)的基础上,分化出若干个新学科。从原有科学知识体系中脱离而自成一体,又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方法以及相对完整的理论知识体系的一门学科。将这一过程称之为学科分化,学科分化趋势占据近代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使得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得以传播,“中国学术不重分类”[15]的局面被“西学分科”的主张打破。自1903年设立“体操”一科(《奏定学堂章程》)以来,体育经民国时期三十余年的发展,逐渐壮大,从一门“体育学”分化出许多新的体育学科,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体育学科分化的过程。本研究通过考证学科分化时间及其演进历程这两个方面,来具体加以探讨说明。3.1 近代中国体育学发生学科分化的时间考证
从课程设置上来看,晚清时期(20世纪初)的师范学堂及体操学堂受日本的影响较大,只是将体育作为一门课程而已。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始于光绪二十二年(明治二十九年)”[25]。这一年(1896)恰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第一年,而留日极盛期是在“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25](1901—1906)。求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大力宣扬日本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像陈独秀(1901年、1902年、1907年,三赴日本进修)、徐一冰(1905—1907年,于日本大森之体育会体操学校毕业)、秋瑾(1904—1905年,两度赴日本留学)等都是在此间。到1907年,体育学堂办学仿效日本模式创办体育学校更是达到了高峰(图2)。另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以1907年为界,早在1904年推行日式“癸卯学制”过程中,《学务纲要》(张之洞、张百熙所拟)中规定将“兵式体操”练习纳入学堂[40]。很明显,在1907年之前,除了兵操以外,并无专门的体育学科设置。而自1907年之后,“体育学”作为一门课程开始出现在晚清的一些学堂中,直至1911年前后,仍以“体育学”为单一专业课程。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个别学堂(重庆体育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设置课程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学科”一词,但诸如教育学、生理学与伦理学等学科并没有与体育相交叉而产生出新的体育学科。另外,从出版著作来看,晚清所出版的大多是与“体操”有关的著作,且以译著为主。此时并未出现明显的体育学科分化迹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图2)。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体育学科分化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教会学校陆续在全国各地开设学校,西方的一些运动项目以及体育学科通过基督教会学校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期间举办了一些讲习所、训练班,其所教授的课程中,如“在华训练班的课程中,体育专业学科有运动生理学、体育测验、体育史等科目(蔡政杰,1992年,63页)1918年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课程中有‘体育哲理’乙科(蔡政杰,1992年,83页)‘体育哲理’课程正是体育学原理的相关学科。就制度而言,在华的各基督教会学校体育对专业训练课程尚未统一”[9]。若与同时期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2)相比较,不同之处在于教会学校出现了一些“新”的体育科目——运动生理学、体育测验、体育哲理,这为之后的中国体育学向学科分化发展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体育运动推广上,还是在学校体育课程设置上,以及体育学科构建上,教会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近代中国体育学科分化的出现,除了因受到西方的影响外,还源于民国初期涌现出各类单一学科与综合性的科学社团。当时由中国科学社、江苏教育会以及中华医学会等科学社团组建了“科学名词审查会”,在该会的影响下,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核查渐转向分科[8],这意味着学科分化已经成为民国学术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
虽然体育史、运动生理学、体育测验、体育行政、体育教学法、人体机动学等学科已在民国初期的部分学校开设,但是据刘彩霞所编著的《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2003)一书来看,民国初期至20世纪20年代之前,即1912—1919年间,共出版69本图书——其中武术26本、国外拳术2本、体操9本、球类6本、田径2本,仅武术和体操两类著作占到出版总数的50.7%。然而,与以上学科相关的体育学术著作,却是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出版发行的。所以,从时间推断上来讲,将20世纪20年代作为中国体育学科分化的起始时间应该是较为合理而可靠的。
3.2 近代中国体育学科分化的演进历程
20世纪20~40年代是近代中国体育学学科体系架构逐渐形成与完善的时期,本文将近代中国体育学科分化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了3个阶段:1)体育学科分化的初现期(20世纪20年代);2)体育学科分化的扩张期(20世纪30年代);3)体育学科分化的成熟期(20世纪40年代)。
3.2.1 20世纪20年代:学科分化的初现期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体育受到欧、美自然体育理论的影响。麦克乐(Charles Harold McCloy)的两度来华(1913—1919年与1920—1926年)将美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与体育学科引进中国,尤其是其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不仅培养体育人才,还创办了《体育季刊》杂志,编译了多种体育著作与教材,对于推动民国体育学科的确立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中国的体育学者已开始注意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融入进理论研究中,学术研究风气大涨。留学欧、美的体育人才不断增加,不仅推动了近代中国体育学在专业设置上不断完善,更是促进了在20世纪20年代对体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该时期的学科分化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1.就北京体育学校(1924)和北京清华学校暑期学校体育(1928,图2)开设的体育科目来看,已较之民国初期有所变化,即除去体育原理、体育史以外,出现了新的学科科目,如体育组织及行政、运动场行政、人体机动学/身体机动学、运动生理卫生/运动生理、体育建筑与设备、体育教材教法、身体测量学、体育哲学等,学科分化初现。
2.就20世纪20年代所出版的体育学术著作而言(表5),除“体育学”、“体育原理”之外,出现了与人体自然学科有关的著作《运动生理》,说明体育学科已开始转向科学化学术研究。科目设置虽依然超前于专业学术著作的出版,但二者的“聚焦”相对集中在了“体育史”、“体育学”、“体育原理”、“运动生理”这4门学科,初步构成近代中国体育学基本体系框架。

图2 晚清、民国时期体育课程比较图[2,4,7,9,16,22,26,29,41,42]Figure 2. Comparing Sports Discipline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3.学科分化促进了研究领域的细化与学术的职业化。此间催生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代体育学者,且各自都“术有专攻”,如罗一东(研究领域:体育理论,1924)、王怀琪(研究领域:运动学与运动项目,20世纪20年代其共编著20余本书)、程瀚章(研究领域:运动生理,1924;1925;1929),另外,李培藻则主要专注于对国外著作的翻译(3本),比之晚清,体育学者群体固定,学术职业化程度较高,这无疑推动了体育学的学科建设。

表5 民国时期体育主要出版著作一览表(1920s—1940s)Table 5 Sport Book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20s—1940s)
3.2.2 20世纪30年代:学科分化的扩张期
经过“黄金十年”(1927—1937),民国时期体育学科的发展更趋向系统化,也更为成熟。较之第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体育学科,从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1931)、四川体育专科学校(1932)、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33—1937)与北京市立体育专科学校(1936)所开设的体育学科(图2)可以看出,“体育概论”、“国术”、“运动裁判”、“体育统计学”等还是比较新的学科。诸多新学科的涌现,使得20世纪30年代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学科分化的扩张期。
学科分化的扩张,引发了体育理论的蓬勃发展。像罗一东《体育学》(1931;1938)、陈咏声《体育概论》(1933;1934)、宋君复《体育原理》(1933;1934)、方万邦《体育原理》(1933;1936)、吴蕴瑞与袁敦礼《体育原理》(1933;1935)等著作的相继出版,极大丰富了体育理论知识。作为“传统”学科的“体育学”、“体育原理”已经日臻完善,逐渐成长为体育学的主导性学科。
伴随着扩张的深入,使体育学发生两种转向:
一是,学科转向科学化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麦克乐就提出了“体育科学化”[37]。进入30年代后,出现具有标志性的两本体育人体自然科学著作:1)吴蕴瑞的《运动学》(1930),此书参考德、美的运动著作而成,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运动生物力学的基础理论书籍。随即有学者针对此书撰写了《吴著运动学习题之解答》(王锡九,《体育季刊》1933年第1期)一文,可见此书在体育学界还是颇具影响力的。2)蒋湘青的《人体测量学》(1931)参考了美国Sargent(哈佛大学)、梅克洛等人著作,书中介绍了人体测量理论、度量的标准、测量工具与仪器、人体部位及相应的测量方法,还涉及到体格与健康、生理机能(肺活量)测试及其计算公式与方法。这两本书无疑助推了体育学科由“理论式研究”朝向“科学式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历经“洋土体育之争”,国术充分认识到自身“科学化”的缺乏,将一些自然科学理论纳入国术教材与著作之中,像吴图南肯定了力学、心理学与生理卫生的作用(《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1931)[32],吴志青提出将“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原理”作为武术科学化的依据(《科学化的国术》,1931)[33]。
二是,学科转向“本土化”研究。尽管受当时国内科研水平的限制,但我国学者还是能够将相关原理运用于本土研究领域,像吴蕴瑞在《运动学》(1930)中结合本土竞技运动情况,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将力学原理与运动项目(器械体操、游泳项目与田径运动项目)相结合予以技术动作分解与分析(见原书“运动”部分)。“人体测量学”方面,曾仲鲁在《体育测量之研究》(《体育季刊》,1933)中对“欧洲人与日本人及我国民的体高发育统计”,并叙述“体高与体力的关系、与体育发育有关的事项(如遗传、营养)、体高之阶级、体高测量器、体高测量法”[3]。
此外,“国术”作为“本土化”学科在民国时期早已推行,自“1935年之后,‘国家本位’的体育思想升高,体育学界以‘国家本位’和‘适合国情’的立场,表明‘洋土并行’与‘洋土不分’应完全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依归,也是真正落实‘体育本土化’的内涵”[37]。1936年《暂行大学体育课程概要》正式将国术纳入必授科目。受到“体育科学化”的影响,随着学者对于学科理解的深入,接受与消化其他学科,在“国术”一科的原有基础上,学科范围有所延伸,复又纵向衍生出新的分支学科,如国术教学“为初创之学科也(吴图南,1984)”[31]。除“国术教学”外,还出现了“国术理论”、“国术研究”、“国术史”、“国术精义”等学科(见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北京市立体育专科学校)。当然,“体育史”学科也显露出相似特点,除“中国体育史”外,部分学校(重庆大学体育系、科、班)在20世纪30年代开设了“世界体育史”一科,同期还出版了章辑五编著的《世界体育史略》(1931)。这些迹象虽不显著,但是展现出学科分化的又一个趋势,即学科分化转向纵向深入发展。
3.2.3 20世纪40年代:学科分化的成熟期
成熟期的学科分化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学科内涵与理论有所丰富。1)体育史:从1919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出版起始,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王健吾的《体育史》(1922),30年代出版了章辑五的《世界体育史略》(1931)、阮蔚村的《远东运动会历史与成绩》(1933),40年代接连出版了谢似颜《西洋体育史》(1944)、程登科《世界体育史纲要》(1945)、董守义的《国际奥林匹克》(1947),可以看出“体育史”的学科视角与研究主题发生变化,学科理论更加细致化。2)运动生理学: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了由蔡翘所编著的《运动生理学》(1940),书中讨论了肌肉特性、肌肉(横纹肌)收缩、血液循环、呼吸变化、疲劳等内容,这与同时期的西方体育学科研究范围是相吻合的。与程瀚章的《运动生理》(1929)相比,更为接近现代的“运动生理学”。3)体育心理学:1942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体育心理学》(萧忠国、吴文忠编译,1942)论著。书中内容多译自松井三雄(日本国立体育研究所心理学部部长)的《体育心理学》,结合了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如书中第四编“运动的分析”中第二章“智的内容”对人的视野、耳(听觉)身体内部器官的感知觉进行介绍;还有与运动训练相关的内容(参见第四编第一章“运动的内容”),如运动的力量、速度、正确度与确固度以及运动律;除此以外,在第五编“运动的影响”中专设一章讨论疲劳,尤其是涉及到了关于疲劳的测量方法。4)出现“体育概论”与“体育原理”(见前文,不再累述)并存的现象。“体育概论”是自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科,与之相关的书籍在40年代相继出版了3部,表6可以看出,学科理论内容趋渐完善与丰富。“体育概论”与“体育原理”这两门学科较为接近,易为混淆不清,江良规(1946)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体育概论之作用,则极明显,其目的在引导初学者入体育之门,予以体育理论及实际之初步介绍。体育原理则不同,彼乃以种种科学之事实为根据,以理想的态度,讨论各种体育上合理的实施原则,故一,指出实现体育目的所必须依据之原理,原则为理想的;二,所指之原则,并不得为幻想,而是以科学的发见(现)为根据,所以又是科学的。所以体育原理乃‘根据科学的理想’。”[12]此一事实,不仅为我们展示出学科边界与研究对象的确立,还表明了体育学人已经对学科内涵的深度有所理解与把握,这对于体育学及其学科演进发展来说是极具意义的。

表6 民国时期4种《体育概论》版本目次一览表Table 6 Contents of Four Versions’ Physical Education Introduction
2.学科意识与自觉有所提升。期间,体育学者开始反思自身学科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吴蕴瑞在《师范学院体育系之缺点与改进》(《国民体育季刊》创刊号,1941年9月)一文中指出:“共同必修科目太多排挤体育学科。……例如人体机动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史、健康检查、体育建筑与设备,均为体育专业训练之重要科目。”[34]江良规(1946)对体育学内容的层次分类提出“在‘体育学’中,将体育学的内容依据教育学的模式,大分为‘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几个层次”①江良规.体育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转引自“国立”教育资料馆.体育理论基础经典丛书(上)[M].台北:“国立”教育资料馆,2007,4:54.。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46年10月规定了“体育师范科之主要科目为国文、解剖生理、教育概论、体育教材及教学法、体育原理、体育行政、体育测验及统计等七科”[4]。至20世纪40年代,体育学体系构架基本“浮出水面”。
3.学术研究方法有所进展。民国初期的体育研究方法运用较多的就是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法、历史学等。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使用心理学、统计学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体育研究,以体育测量为主,多数研究出现在《健与力》杂志上,如王学政《在文明生活中体育基本问题之分析(Ⅰ)》(1945)[1]中运用了数学图表的形式,虽然文中引用的是美国的例子,但可见中国学者已经受到一些“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当时美国的测验、调查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谌厚博(1945)以1944年四川江津胄才初级中学男生229人的立定跳远成绩为例,计算组距、中两数的百分等级,并画出百分等级曲线图。文中写道:“编制分数的统计方法有用标准差、百分等级,上下四分点及中数等多种,其中以百分等级法比较方便和可靠。”[1]还指出:“体育的推进,有赖于体育测验方法之改进,必须利用科学方法来评定成绩,以及行政效能,教学方法的改进,教材内容的决定等问题。”[1]再有,江良规(1946)提及到要用“科学的研究法:历史、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12]研究体育原理。整体而言,体育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运用虽多以介绍为主,或是引证国外实验、统计数据,但学术研究意识逐步增强。
如果把近代中国体育学放到整个体育学演进发展的历史当中(图3)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中、西方体育学发展轨迹是不同的:1)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是西方体育学率先发展起来的主要学科,并以自然科学为基础。2)中国体育学是从20世纪初的一门专业课“体育学” 逐步发展加以扩大,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其就已经处于学科分化的状态:20年代→体育史、体育学/体育原理、运动生理学;30年代→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学、人体测量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统计学;40年代→体育教育学、人体测量学、运动学、体育概论、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大体而言,中国体育学科在近代时期变化不是很大,主要集中发展在体育史、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学4个学科。3)中国体育学在近代只是停留在对外来知识的“整理”与“消化”阶段,而西方体育学却是在“完善”中不断创建新的学科。

图3 近代中、西方体育学科发展演进比较图①注:图改编自:曹孚.外国教育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7:62.
4 结论
本研究认为,学科交叉与分化是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体育学科的交叉,需要从其他学科那里借鉴一些理论,并以此为根据以扩充体育学的理论知识领域。从“体育学”、“体育原理”内容变迁发展来看:1)在20世纪20年代,内容涉及到史学、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2)进入30年代,则扩展到了社会学、人体测量学等新的学科领域;3)至40年代,则延展至营养学、遗传学、教育心理学以及物理学等学科。由于多学科涉入,使学科交叉趋势日益凸显,促使“体育学”、“体育原理”课程内容不断地充斥与膨胀。当这些学科理论不断地充实着体育理论达到一定的量时,不仅使体育在概念与本质上产生认识的改变,连同学科属性也随着发生动荡。原本在“体育学”、“体育原理”中出现的与自然科学(如生理学、生物力学、医学、物理学)交叉的部分;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心理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部分,这两个部分的理论一旦形成自己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方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新的学科“孵化”出来,“宣告”独立而“自立门户”,由此,体育学科分化进程逐渐显露。1)20世纪20年代是体育学科分化的初现期。体育学科体系初具规模,同时,学科分化促进了研究领域的细化与学术的职业化。2)20世纪30年代是体育学科分化的扩张期。体育理论在此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学科不仅转向科学化研究,还转向本土化研究,且学科分化呈现纵向发展。3)20世纪40年代为体育学科分化的成熟期。期间,学科内涵与理论不断丰富;学科意识与自觉得到增强;学术研究方法有所进步。
近代中国体育学历经晚清、民国时期百余年的风雨飘零,历经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已经堙没有年,与现今体育学相比较而言,可能从研究视角、社会环境、国家意识、研究范畴等方面相去甚远,但它却是学科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拾学科“故纸堆”,不是简简单单地用一些繁琐的文字资料对事实加以描述,而是将其客观辨析,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将一连串的线索,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将其联系,“知其变迁、发展之由”[17],以推导出“前因后果”,使其粲然大明,将近代中国体育学发展脉络予以还原,这无论是对体育学自身构建,还是对学科史的挖掘来说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1]本书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十二)[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5863-5868,5873-5876.
[2]本书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三十)[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14526.
[3]本书编委会.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三十四)[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16618-16633.
[4]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286,296-297,302-303,310-311.
[5]崔乐泉,杨向东.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3-204.
[6]崔卫国,汪建丰.社会科学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0.
[7]邓忠庆.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史略[J].四川体育史料,1984,(2):57.
[8]范铁权.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61-162.
[9]“国立”教育资料馆.体育理论基础经典丛书(上)[M].台北:“国立”教育资料馆,2007,4:5-7.
[10]胡建雄.学科组织创新[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2001:243-244.
[11]金兆均.体育真义之科学分析[J].体育与健康教育(二月刊),1941,(1):3-8,56-60.
[12]江良规.体育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4,6-12.
[13]孔寒冰.高等学校学术结构重建的动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243-244.
[14]林志钧.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32.
[15]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M].北京:中华书局,2012:196.
[16]吕右青.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现状[J].勤奋体育月报,1936,3(8):18-24.
[17]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7.
[18]刘仲林.中国交叉科学(第二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17-119.
[19]刘仲林.现代交叉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0]罗一东.体育学[M].上海:中华书局,1924.
[21]李佳敏.跨界与融合:基于学科交叉的大学人才培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25.
[22]钱泽民.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鼎盛时期[J].上海体育史话,1982,(1):16-17.
[23]阮蔚村.言论:何谓体育学[J].上海体育,1937,1(2):19-21.
[24]四川省核学会·四川省工业卫生研究所《科学学词典》编辑组.科学学词典(讨论稿)[Z],1984:103.
[25]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5,31.
[26]体育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122-125.
[27]王其慧,李宁.中国体育史[M].武汉:武汉体育学院教务处,1984:152.
[28]王庚.体育学与体育教学[J].中华教育界,1923,13(12):1-20.
[29]吴文忠.体育史[M].2版.台北:“国立”编译馆,1961:351.
[30]吴文忠.国际体育文献选集(第一集)[M].再版.台北:国际体育研究社编印,1968:116.
[31]吴图南.国术概论[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144.
[32]吴图南.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7.
[33]吴志青.科学化的国术[M].上海:大东书局,1931:1-4.
[34]吴蕴瑞.师范学院体育系之缺点与改进[J].国民体育季刊(创刊号),1941,(1):36-48.
[35]魏建香.学科交叉知识发现及可视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36]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934.
[37]许义雄,徐元民.中国近代学校体育——思想之演进(下)[M].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9:352,356,402.
[38]叶琛.体育的基本原理[M].上海:大中国图书局,1948:32-34.
[39]杨天平.学科概念的沿演与指谓[J].大学教育科学,2004,(1):13-15.
[40]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2.
[41]周清源.四川体育专科学校概况[J].四川体育史料,1983,(2):39.
[42]浙江体育学会体育史专业委员会,浙江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近代体育史文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229-238.
[4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辩证法原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233.
[44]张春美,郝凤霞,闫宏秀.学科交叉研究的神韵——百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探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18(6):63-67.
[45]BARTLETT R,GRATTON C,ROLF C G.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Studies[M].Routledge,2009:1656-1657,2006-2007.
[46]BEYER E.Dictionary of Sport Science[M].Verlag Karl Hofmann,Germany,1987.
[47]COAKLEY J,DUNNING E.Handbook of Sports Studies[M].SAGE Publications Ltd,2000,8:xxⅱ-xxxⅷ.
[48]KREMER J,MORAN A.Swifter,higher,stronger:The history of sport psychology[J].Psychol,2008,21(8):740-742.
[49]LAVALLE D,KREMER J,MORAN A P,etal.Sport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Theme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5-6.
[50]JAN BORMS.Directory of Sport Studies[M].5thed.Human Kinetics,2008:81.
[51]MASSENGALE J D,SWANSON R A.The History of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M].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1996.
[52]MECHIKOFF R A.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s to the Modern World(Sixth Edition)[M].McGraw-Hill,2014:271-272.
[53]NAUL R,HARDMAN N.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Germany[M].Routledge,2002:28-36,138.
[54]ZACHAZEWSKI J E,MAGEE D J.Handbook of Sports Medicine and Science Sports Therapy Services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s[M].John Wiley & Sons,Ltd,2012:14-15.
[55]TOMLINSON A.A Dictionary of Sport Studi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431-432.
A Restricted View o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inesiology in Modern China from Discipline-crossing and Discipline Differentiation
WANG Hao-lin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nsultation,and logical analysis,this paper illustrates cross-discipline through discussing the changes of kinesiology and princip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divides sports discipline differentiation evolution process into three periods:the early period of sports discipline differentiation (1920s);the expansion period of sports discipline differentiation (1930s);the mature period of sports discipline differentiation (1940s).The main purpose is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sports science.
discipline-crossing;disciplinedifferentiation;kinesiologyinmodernChina;evolution;development
1000-677X(2015)06-0003-10
10.16469/j.css.201506001
2014-12-17;
2015-04-25
王颢霖(1978-),女,吉林镇赉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与体育教育训练学,Tel:(0373)3326352,E-mail:haohaowhl8022@163.com。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