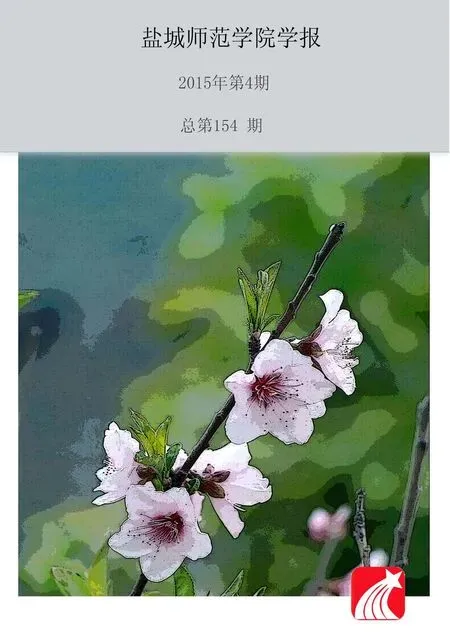论并协与互补思想的元理论意义
——从外语研究的价值说起
杨雪芹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论并协与互补思想的元理论意义
——从外语研究的价值说起
杨雪芹
(盐城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在外语研究价值的思考中,常见的悖论有:外语研究的主观性与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客观性;理论研究的系统有序性与现实的复杂无序性。韩礼德的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思想包含的启示是多重的,主要有三点:整体主义语言研究观、语言的经验识解作用和科学真理相对论。
韩礼德;并协与互补;外语研究;主观与客观;语言系统;整体主义;真理相对论
人类活动往往具有目的性,外语研究也不例外。人们从事外语研究大多是相信其具有价值,当然也不排除完全出于兴趣和好奇的研究行为,但外语研究是有价值的行为活动,这一观点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那么,外语研究有何价值?对于这个议题的探讨,回答可以是多元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对某个事物或行为进行价值判断时,往往人的功利性会使我们的判断产生偏差和失误,从而影响我们的思考。本文首先关注外语研究的价值思考中我们面对的悖论:外语研究的主观性与科学研究追求的客观性;理论研究的系统有序性与现实的复杂无序性。然后,我们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的思想来寻找解决悖论的思路,从而对外语研究的价值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也是外语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体现。
一、外语研究的主观性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在对外语研究的价值作思考时,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理想。因为追求价值中立、追求外语研究的客观性才是外语研究具有价值的前提。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像许多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一样,外语研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其根源主要来自于外语研究所研究的对象——各种人类自然语言、错综复杂的语言使用和交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学、还有使用语言的人。研究涉及到人,人具有思想、复杂的心理活动和主观价值判断。这种研究对象上的多样性、动态性和异质性决定了外语研究的复杂性,也削弱了其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很难进行总体判断)和客观性(认识的片面性、局部性)。
外语研究对象上的这种主观性根源也影响到外语研究的课题特征、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的选用上。外语研究的课题往往是关涉人们外语使用实践活动的研究:如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某个外国作家的研究;某个翻译实例的研究等;即使对某门外语的研究,也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或理论框架。可见,人的主观因素及其影响存在于每一个外语研究课题。而且,这些课题研究对象要么是个别的,要么是局部的,要么是特殊的,很少具有代表性,相应地,外语研究领域不存在着绝对适用的研究方法,只有相对适用的研究途径。因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具有情境性,外语研究很难做出必然性的结论。
但是,科学研究中,客观性是人们公认的基本要求。只有客观的东西,才是相对稳定的,才是比较可靠的,这也是人们对知识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对客观性的追求源于自然科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常常是可以控制的,多采用实验室试验研究方法,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认识事物规律。即对事物进行推断,然后进行实验,保留被证实的东西,排除不被证实的东西。但是对于外语研究而言,这种试验试错的方法是不允许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人或者社会是不能拿来做试验的,更不可拿来试错。
客观性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外语研究也不例外。虽然外语研究具有内在的主观性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语研究要丢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追求。失去了客观性,外语研究的价值会变成无源之水。那么,如何理解外语研究的客观性?外语研究的客观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认为:外语研究的客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追求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实践以及客观地对待外语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追求相对的客观性。外语研究者对客观材料或文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或成见,更不能任意歪曲或虚构事实,以客观材料为依据,让资料和数据“说话”,在解读、分析和判断资料和数据时,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价值中立。不可夸大外语研究结果的作用,承认其局部性和或然性。
二、外语研究的系统有序性与现实的复杂无序性
这个悖论指向的是外语研究的可实践性问题。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外语研究远离教学现实;很少有外语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实践。这是不可回避的实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外语研究的价值要打折扣。相反,这些抱怨体现了人们对外语研究的价值抱有不切实际的功利性期望。许多人认为研究就是服务实践,研究结果的价值就在于可以直接转化使用,落实到外语研究领域,语言学理论要能够应用于外语教学,翻译理论要能够指导翻译实践,至于外国文学研究,甚至出现了“文学无用论”的价值判断。这些对外语研究价值的不合理的武断,忽略了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过度简单化了现实的复杂性。这就是外语研究的价值思考中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悖论:研究的系统有序化与现实的复杂无序性。
外语研究是一种追求知识的过程。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Truth),只能把握相对真理(truths)。外语研究更是如此,因为外语研究的个体化特征,即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个体化:研究者独立地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一个作家、某门语言、语言的某个方面、语言学的某个流派、某部翻译著作等,所揭示往往都是偶然的现象,这种单个性或局部性使得外语研究结论的推广性和应用性受到限制。而且,任何理论研究具有系统化、规律性和有序性,而现实却是动态的、变化莫测的、杂乱无章的。外语研究所发现的理论或成果是我们基于某种视角从外语实践抽象或提炼而成的,凸现了某些特征,弱化甚至隐去了其他一些特征,并不是外语实践的忠实的镜像,更不具有预测性和可复制性,因为研究实质上是选择、聚焦、分类、凸现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可过高地企求外语研究的直接实践价值。笔者认为:外语研究的价值主要不在于指导实践的能力,而是在于理解世界、解释世界、反思自身、改变观念,影响人的精神等方面,其真正作用在于化人。这种作用是无形的,但却是重要的,远比物的作用要大。不可否认,其他科学研究也会具有这种作用,但是,外语研究所提供的跨语言、跨文化的视角能帮助我们更深刻体会人类对世界多元化的理解和解释以及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作用。
三、并协与互补思想的内涵与元理论意义
上面讨论的问题不但在思考外语研究价值时会出现,也困扰着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的价值判断。但是悖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关于外语研究的价值的主题的无解或无意义,相反,对悖论的思考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外语研究的价值。下面,我们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关于语言的并协与互补的思想作例来理解如何化解以上的悖论。
“并协和互补”这个术语来自于韩礼德的一部书名:《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此书首次于2008年在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韩礼德本人的翻译,原书名是英文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他译为“并协和互补”有其独到的用意:语言系统中所涉及的选择都以其他选择的存在为前提,各自对整体的意义做出贡献。其中“Complementarities”是复数名词,原形为“Complementarity”,他使用复数与“并协”的概念在于强调:语言系统中的互补存在于多系统、多层次,而且是同时存在着。本书主要分析并阐释了存在于词汇与语法、作为系统的语言与作为语篇的语言、书写与说话等三个方面的互补性。笔者认为:韩礼德的并协与互补的思想不仅仅是对语言现象的分析,更具意义的是它也反映了韩礼德的世界认识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外语研究的本质与价值。
首先,韩礼德认为在语法与词汇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中,语法与词汇被合二为一,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称为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经常被简称为语法,淘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把单词看作砖瓦通过语法泥灰粘在一起的区分性做法[1]31。他认为词汇语法构成一个连续统(lexicogrammatical continuum),之间的分界模糊,互补性是说明他们整体性的特征之一。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词汇语法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部分,是一个纯粹抽象的、不直接与物质世界发生联系但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组织意义的空间,为语言实际运作的部分,也是语言力量的源泉。
根据韩礼德的观点,词汇与语法是互为补充的,即人类经验中的现象要么是以词汇的方式(具体的、开放式的、灵活的、低信息量的)得到识解,要么是以语法的方式(广义的、系统的、封闭式的、高信息量的)得到识解;复杂的现象则会既有词汇的又有语法形式的识解[1]9;48-49。以英语中的PAIN(疼痛)作例,从现代英语语料库(COBUILD)中找出许多关于“疼痛”的表达式,有词汇的;如:hurt, pain, ache, sore, painful, burning, throbbing, stabbing, headache, toothache, stomachache 等;也有语法形式的,被识解成事物、过程、特质等,如:It hurts/It’s hurting; I hurt/ It hurt me/I hurt myself; My leg hurts/ I hurt my leg等等。因为疼痛是私人化的、复杂的感受,语言中的表义资源——词汇与语法——均被用上,所以,英语中用了如此多的关于“疼痛”的表达式(这里列出的仅为部分)[2]。日本学者Motoko Hori揭示日本语中也有许多表达“疼痛”的方式,有词汇也有语法形式的。这个例子说明:“人们可以这样识解疼痛,也可以那样识解疼痛,而且,即使这些识解中有些相左(例如关于疼痛的语法识解中,斜线符号链接的成对的例子),但是唯有通过多种方式的同时识解,我们才能得以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全景图”[1]9。
第二,并协与互补也存在于作为系统的语言(language as system)与作为语篇的语言(language as text)之间。这里的“语篇”和“系统”为同一“语言”现象的两个方面,作为系统的语言的含义是:应该把语言看作是产生意义的、有系统性的资源,即系统为“意义潜势”,语篇为“现实化了的意义潜势”[3]。其实任何语言理论和研究都会面临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韩礼德[4]认为索绪尔只是提出了问题:区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但未能解决这个问题(言语的本质及其与语言的联系),因为索绪尔的结论是:语言学只研究语言,让人们觉得语言和言语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现象类别。韩礼德则借鉴了哥本哈根学派叶姆斯列夫的观点,认为语言学家描述语言而不解释语篇是没有结果的,反之,描述语篇而不涉及语言也是空洞无物的。他提出要把语篇作为过程来解释,把系统作为进化来解释。也就是,要用动态方式再现系统及其具化(即语篇)。所以,语言系统和语篇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现象,而是同一个现象,它们的不同,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即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是系统,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语篇。这正是两者互补的理据所在。系统往往是抽象的、隐藏的,语篇则是实例、语言的使用。两者是通过“例示化”(instantiation)连接起来的,即语篇是对系统的例示化,而系统是语篇的潜能,每个语篇(语言使用实例)都通过对意义潜势的参照获得意义,例示化问题指向的其实是可观察到的现象与背后系统之间的关系。所以,研究语言要结合系统与语篇这两种视角,不可厚此薄彼。
第三,说话与书写(又称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并协与互补,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与联系。说话与书写是两种不同的意义形态、不同的意义介质。直观上看,说话是即兴的、无自我监控的、稍纵即逝的、似流水;书写却是抽象的、可以反复修改的、将意义固化为静态。韩礼德用流水与冰川、舞蹈与雕塑等多对比喻来形容它们的差异[1]165。它们都具有语言复杂性,但表现形式却不同:书写通过词汇密度的增大变得复杂,用数量少的小句来容纳大量的词项;而说话则通过语法上的复杂性变得复杂,利用语义扩展和投射等手段构建小句复合体。虽然,书写最初是寄生于口语,但是,书写并不是写下来的口语。
书写与说话的联系在于它们在语法上的延续进化。受到英国爱丁堡大学20世纪中叶语言学家戴维·阿伯克龙比(David Abercrombie)将口语与书面语的联系置于相应的历史视角研究的启发,韩礼德没有停留在静态地直观地比较说话与书写的异同,而是把两者在语法上的进化与联系放在人类经验识解和认识能力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并得出独特的研究发现。他一直感兴趣于科学话语的形式的进化以及它们与日常语言,特别是与口语的联系,还有它们与其他形式的成人书面语的关系,特别是与现代国家的标准语言的联系。这里的“口语”指说话;“标准语书面语”和“科学语言”则是书写。韩礼德认为这三者是人类经验识解和重构中三种典型的意义表达方式,它们也构成了人类意义能力进化的三个关键阶段:书写一开始寄生于说话,与人类定居文化紧密相连;科学语言则是与人类现代文明时期的科学发展分不开[5]108-110。
韩礼德认为以上三种并协与互补各有侧重。语法与词汇基于精密阶在意义的聚焦上形成互补:广义的意义还是特定的意义;系统与文本基于例示化在观察语言的角度上形成互补:意义潜势还是意义实例;说话与书写则在体现化上形成互补:意义表征为动态的过程还是静态的事物。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拓展语言创造意义的策略[1]184。
韩礼德的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思想包含的启示是多重的。在此,我们主要讨论三点:整体主义语言研究观;语言的经验识解作用;科学真理相对论。
韩礼德采用的整体主义语言学研究方法,将词汇与语法合二为一,兼顾语言的系统与语篇,从历史的视角建立说话与书写的联系,其依据是它们之间的并协与互补关系。从并协与互补的思想内涵来看,最明显的特点是强调语言系统在许多层面的互补与融合。以往研究过多注重词汇与语法、系统与语篇、说话与书写之间的不同与区别,将语言分解成语法、词汇、语音、句法等组成部分,采用由部分到整体的成分分析方法去研究语言,这种语言学范畴的切分一方面帮助我们将语言这一复杂无比的现象化整为零、化繁为简,从某种程度上,便于研究的展开,但同时也肢解了语言,忽视了语言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的事实,对语言进行人为的割裂与区分,其结果是:研究仅聚焦于语言的构成成分,话语的意义被挤出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而韩礼德这种对待语言研究的整体性思维纠正了以往语言学范畴对语言的人为切分,尊重语言的整体性,关注语言的功能意义。
其次,并协与互补理论揭示了语言在人类经验识解中的作用。无论是语法与词汇还是说话与书写,在韩礼德的并协与互补思想中,都被看作是人类识解经验的意义资源。正如“疼痛”经验可以有语法识解的途径(英语等语言中有许多表达疼痛的词汇),也有语法识解的途径(多种表达疼痛的语法形式),经验世界不等于客观世界,因为前者有了语言作为中介,语言中词汇语法的范畴化作用将混沌一片的客观世界“格式化”。韩礼德关于说话与书写的联系告诉我们,口语与书写均是识解经验的方式,这两者的联系还告诉我们:人类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被识解与重构:定居文化之前口语语法识解的是游牧文化的存在现实;书写识解了一个定居农耕文化的人类存在现实;科学书写则是人类科学文明时代的经验认识与表达意义方式[5]121-122。这些让我们知道语言不是工具,语言参与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人类认识的发展,语言的作用不可小觑。
与语言经验识解作用相关联的另一意义是科学真理的相对性。并协与互补理论,尤其是关于科学语言本质的研究,在知识本质方面,揭示了任何理论都是语言建构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也不例外。事实上,正如韩礼德所言:“科学无开端,它只不过是语法构建关于我们内心和周围世界的理论的继续。”[5]128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现实的两个向度:客观现实和认知现实。客观现实是指自然环境,有些已被人类以某种方式认识了的,也有未被人类认识的;认知现实是指人类的知觉和创造,科学理论属于此类现实。认知现实与语言密切相关,韩礼德的语言建构论思想揭示了人类认知的创造可以修改客观的现实。所以,科学研究作为认知现实的活动,并不是客观现实的镜像反映,它离不开语言的建构作用,科学研究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这就是科学真理的相对性。
四、结语
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理论在语言学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秉承了英国语言学研究的传统精神,凝聚了韩礼德多年来语言学研究的思考,揭示了语言的经验识解作用以及人类认识的进化性。在语言学研究层面,它反思了范畴切分所带来的弊端,批判了以往研究对语言的整体性的忽略,它提醒我们“语言发挥功能的方式不是各个部分分别运作,而是整体的”[1]169。
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理论的深远意义超越了语言学界,尤其是在认识论层面,它包含更多的启发。并协与互补的视角指出“我们只能做到对部分事物研究透彻,”[1]35无法做到对事事无所不知,因此,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协同合作,兼收并蓄。回到本文开始的话题:外语研究的价值。语言的并协与互补的思想契合了外语研究的特质:众多研究者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得到不同的解读,其中无单一研究可以揭示绝对的真谛,大家们的研究也构成互补和并协的关系:互为语境,互为前提,互为观照;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因此,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要做到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这一点也契合了我们所讨论的外语研究价值判断中的悖论中的真理相对论,即科学研究很难做到绝对的客观。
[1] 韩礼德.语言系统的并协与互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韩礼德.韩礼德文集·英语语言研究:第七卷[M].英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311-335.
[3] 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M].伦敦:爱德华阿若德出版社,1978:40.
[4] 韩礼德.韩礼德文集·论语言与语言学:第三卷[M].英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96.
[5] 韩礼德.韩礼德文集·科学语言:第五卷[M].英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朱莉莉〕
The Meta-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Halliday’s Notion of 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YANG Xue-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China)
In considering the valu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we are often confronted with two paradoxes: the subjectivity of research on foreign languages versus the objectivity as a standard pursued by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tidy scientific models and theories versus the vast, turbulent and untidy reality. This paper aims at interpreting Halliday’s notion of 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as a resolution of these two paradoxes. It is argued that this notion, by tak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language study, reveals the categorization of human language and questions such common views as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absolute Truth.
Halliday; 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subjectivity versus objectivity;language systems; holistic approaches; relative truths
H08
A
1003-6873(2015)04-0073-05
2015-05-25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韩礼德生态语言学思想研究”(14jsyw-34)。
杨雪芹(1966-- ),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