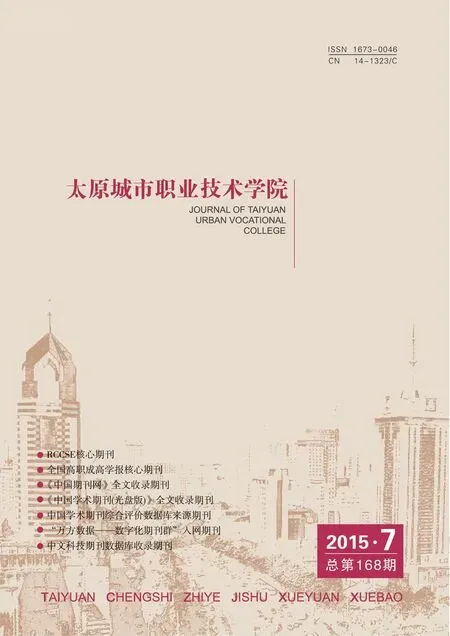宋词词牌名的英译方法浅探
江晨阳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宋词词牌名的英译方法浅探
江晨阳
(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宋词是一种脍炙人口的文学表达形式,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奇葩,其优美精致的句子大多成为千古绝唱。要促进这一文化精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对词牌名的准确翻译至关重要。本文着眼于对常见翻译方法的分析和对比,提出了对词牌名翻译标准化和统一化的看法。
词牌名;英译方法;标准化;统一化
宋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学表现形式,它有着丰富的文化意境。词始于南朝时期,形成于唐代,兴盛于五代,至宋代达到巅峰。不少专家学者致力于将这一文化精华译介到国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者们做了很多开拓性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其中不乏洞见与精湛之作。但是不得不指出,目前国内对于宋词的翻译,尤其是对词牌名的翻译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不同于散文、小说等文体,词的翻译更具难度。每首词都有它特定的词调,每个词调都有它特定的名称,即词牌名。词牌名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词的题目,仅仅只是代表这首词所遵循的格律,包括字数、句法、韵脚、平仄等,但词牌名本身通常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然而,词牌名翻译的标准化与统一化始终难以实现。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势必会对经典文化的对外传播形成阻力。
一、词牌名英译现状分析
总结学者们的观点,词牌名可分为两大类:有历史典故的词牌名和一般性的词牌名。一般性的词牌名包括没有历史典故的词牌名和取自前人某个词句的词牌名,以及仅为风雅而取的词牌名等等。没有历史典故的词牌名包括本该有历史典故、但却已经无从考证的词牌名。现阶段,对词牌名的翻译,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译法。有的译者直接采取音译,例如赵恒元先生所译的《沁园春》即为OnthePatternofQinyuanchun;也有学者认为音译未能更好地传情达意,主张译意才是词牌名翻译的最好方式;也有学者采用不译的方式,将和词的内容关系不大的词牌名省略。
综合考察目前已有的词牌名翻译,各种译文的不标准和不统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词语搭配不一致,如《子夜歌》的译文就有SongofMidnight,Midnight Song,SongatMidnight三种,其中所搭配的介词各不相同。二是措辞的不严谨性,如《踏莎行》的一种翻译是TreadingonGrass。这里的“莎”指莎草,而非泛指草(grass),《踏莎行》的准确译文应为TreadingonNut Grass。三是由于译者对文化典故的了解不足而造成的,如《念奴娇》就有以下几种译文:DreamingofherCharm,CharmofaMaidenSinger,CharmofaSinger。念奴是唐玄宗天宝年间一位著名的歌妓,玄宗时常召见命歌,将她的歌取名为《念奴娇》。若了解其文化背景,第一种译法就不免让人捧腹了。
二、词牌名常见翻译方法
要解决词牌名翻译的不标准和不统一,似应从翻译方法着手探究。现阶段对词牌名的翻译,尚未出现统一的翻译准则,所以翻译的灵活性较大,译文多种多样。不同的译者,站在不同的角度,遵循不同的翻译理念,就会翻译出不同的风格。为探讨词牌名规范翻译的可行性和实现的具体途径,现结合已有译文对几种常见的翻译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和探讨。
1.零翻译法
所谓零翻译法,就是对原文中的事物或概念不做翻译。美国学者兼诗人巴恩斯通,美籍华人聂华苓和我国学者赵甄陶都在翻译时采用零翻译法。例如聂华苓在翻译《沁园春·雪》的时候,省略词牌名,只翻译了“雪”:Snow。
词牌名通常情况下与词作的内容没有联系,只是表示该词作遵循的是哪一种格律,包括对仗和平仄。而当词作内容译成英文之后,也就没有对仗和平仄可言了。这体现了文化的一种不可译性。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考虑到译语读者的理解能力,省掉他们难以理解的部分,将之忽略不译也是一种可行的翻译途径。
但是,零翻译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它破坏了词作的完整性,使得中华文化的精华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流失,也使得对词文化有深厚兴趣的外国读者,丧失了品味不同的词牌名所代表的格律美。虽然在西方文化里找不到与词牌名相对应的东西,但作为词的一部分,词牌名具有表达词的调和节律的作用,不能随意删除。诚然,一般的西方读者很难领会词牌名的意义,但是词牌名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长期沉淀,深化了词的内涵,增添了词的韵味,拓展了词的联想空间,是值得保留的文化瑰宝。并且,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相信国外读者也能慢慢理解词牌名的内涵。省略词牌名不译,相当于对词牌名的对外传播判了死刑。所以,笔者认为,零翻译法不是最好的选择。
2.直译法与意译法
直译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词牌名的意义上,即按照原文的表达方式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意译法则是离开原文的表达形式,将原文内容化隐为显、化曲为直、化深为浅的翻译。两者都是对词牌名的译意,但侧重点不同。例如《苏幕遮》,直译则为Screenedby SouthernCurtain,意译则为Water-bagDance。
不难看出,直译出的译文只是简单地体现了词牌名的字面意思,而其相关典故却无从体现。有时,直译出来的词牌名还会出现与词本身的感情基调不一致的现象,从而引起国外读者的困惑。例如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直译为RecallaQinBeauty,很容易让国外读者“顾名思义”感受到一种充满温柔缠绵的儿女情长,而事实上,词作本身传达的是一种沉郁的感情基调。意译有时也会使不熟悉源语文化背景的读者感到困惑。就《苏幕遮》的意译译文Water-bagDance而言,如不另外加注解释此曲的典故,恐怕读者会云里雾里,全然不知所云。此词牌名典出古龟兹国,是为了配合浑脱舞(Water-bag Dance)而作,“苏幕遮”是一种涂了油的帽子,“浑脱”则是油囊,舞者用“浑脱”装水互相泼洒,“苏幕遮”的使用即是为了不使冷水泼到头面。
但是,直译法和意译法能够较好地忠实于词牌名本身的意义,且能较好地保留词牌名的意境美。
3.音译法
音译法就是直接用汉语拼音来转写汉语词牌名的读音。例如,学者黄龙和赵恒元将《蝶恋花》分别译作To theTuneofDieLianHua和OnthePatternofDielianhua。
音译法避免了零翻译法、直译法和意译法所带来的问题,既不会出现直译译文感情基调的不一致,又不会丧失词作的完整性,而且对于刚刚接触中国词作的外国读者而言充满了异域风情。但应指出的是,音译法仍然存在许多缺陷。首先,音译法很难实现翻译的“信达雅”;其次,采用音译翻译过来的词牌名形同虚设,译语读者获取的信息度为零;第三,由于汉语拼音的发音规则与英文大不相同,译语读者可能连准确的发音都做不到。虽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音译过来的词牌名也许会像“龙”的新译法“loong”一样,逐渐被外国人所接受,但是由于词牌名的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且隐含意义丰富,要让外国读者接受这种译法绝非易事。
4.加注法
基于以上讨论不难发现,任何只侧重于一个方面、只翻译其中一部分的译文都是不完整的。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加注法,即通过加注来补充在词牌名意译或者音译过程中遗漏的重要信息。
(1)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
顾名思义,“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就是在翻译词牌字面意思或深层含义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注解,尽量将原文中的典故传播出去。例如,《雨霖铃》的词牌名称来源于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仅仅只是将其直译为BellsRingingintheRain无法传递其文化背景信息。但加注法(包括夹注、脚注和尾注)可实现此目的。例如可在文尾添加如下注解:“Note:Itisrelatedtothelegendof EmperorXuanzongandhisimperialconcubineYang Yuhuan.WhenEmperorvisitedSichuan,itrainedfordozens ofdaysonhiswaytoLuoValley.Therainsplashedthebells onthecarts,makingaseriesofringing.Hearingthis,XuanzongbegantomemorizehispastloverYangYuhuang,sohe madeanoperasingercomposeasongwiththenameof‘Bells RingingintheRain’”.
(2)音译法+加注法
“音译法+加注法”与“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实质相同,都是通过加注来向译语读者展现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二者不同之处仅在翻译词牌名的方法不同。同样是《雨霖铃》,“音译法+加注法”的加注内容与上文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其词牌名音译为TotheTuneof Yulinling。
(3)“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与“音译法+加注法”比较
两种译法虽然是异曲同工,但是在传达文化内涵的时候两者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大有不同的。有学者认为,“音译法+加注法”要优于“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在音译的基础上加注解释词牌名在词这种文体中的作用及其所蕴含的历史典故、感情基调,这种译法会收到以下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译语读者通过注释对词牌名的了解不断加深,加上英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音译的词牌名可以完全融入英语词汇当中,这些注解慢慢地也就可以省略了。
笔者认为,学者们所提出的“音译法+加注法”的优点以及“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皆可秉承。但是,“音译法+加注法”的缺点是,在传递典故的同时,无法将汉语词作中常用的意象与意境相结合。例如汉语的“柳”字,因其与“留”谐音,所以在中国诗词中是离别时不舍之情的象征,这对于对中国古典文化了解不深的国外读者来说很难理解,但是如果采取“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就可以在传达典故的同时将这种文化内涵传播出去,这不仅对诠释词牌名本身的内涵有重要的作用,在帮助国外读者了解中华文化方面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翻译词牌名时,我们很难用一句简短的英文同时实现“信达雅”,其中“信”、“达”是难点所在,症结在于词牌名的典故内含丰富。而“雅”是可以实现的。例如上文所提到的《蝶恋花》,直译译文ButterflyinLovewithFlower遵循了原文本身的古雅风格,译文也简明优雅。就词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文学艺术,传达美感是其特征之一,因此我们在翻译时追求译本的“雅”也是对其本质的实现,是对“信”与“达”的一种回归。
三、对宋词词牌名翻译统一化和标准化的思考
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对中华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和概念的统一化、标准化的翻译将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对外交流。宋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推动其向外传播,统一而标准的翻译至关重要。
诚如许渊冲先生所言,“译诗不是科学,而是一种艺术,是译语与源语间的竞赛”。而词作为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学形式,在英语文化体系中,确实难以找到一种能与相对应的文学形式。特别是词牌名这种看似不重要却又极为特殊的形式,词虽短,但意韵丰富,且大多数词牌名都涉及一定的历史典故,隐含的深意更是耐人寻味,翻译起来,着实让人踌躇。零翻译法看似行得通,但它不仅破坏了词作的完整性,同时也会造成经典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丢失。音译法虽能保留词作的完整性,保留异域风情,但过多采用音译,听起来难免音调节奏怪异不和谐,也丧失了传递音韵美的能力。直译法和意译法能较好地体现词牌名的本意,并保留一定的音韵美,但在传递文化典故方面似有缺欠,且因词作常用的意象不为外国读者所熟知,有时也会引起读者的困惑。“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相对而言能较好地实现“信达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西方文化的包容性,词牌名所携带的文化内涵能逐渐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
文学作品的美感来自许多方面。翻译不但是审人之美,而且要传人以美。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其《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词牌名的翻译也应如此,既要表达出原作的意美,又要不失其音美与形美。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熟练的双语转换能力,还应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以及求真务实的学术风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一般性的词牌名,可以直接采用直译或意译法。而对于那些用到典故的词牌名,译者要找到典故,在直译或意译词牌名的基础上,通过加注将其文化内涵解释清楚,即上文所提及的“直译法/意译法+加注法”。当然,笔者认同在遇到中国某些特有的物件、特有的概念以及人名、地名等时采用音译,如朝代名“秦”,可音译为Qin。
[1]NieHualing,EnglePaul.ThePoetryofMaoTse-tung[M]. London:WildwoodHouse,1973.
[2]顾森,李崇月.浅谈词牌名的翻译——以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为例[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 86-88.
[3]欧秋耘,刘莹.词牌名汉英翻译统一性的研究[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3):21-14.
[4]武咏梅,吴祥云,朱娥.唐宋诗词词牌名的英译探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刊,2011(5):67-70.
[5]陈明源.常用词牌详介[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6]辜正坤.毛泽东诗词(POEMSOFMAOZEDONG)(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郑静.形似与神似——小议唐宋词词牌名的英译[J].云南财经大学大学学报,2003(3):117-119.
H315.9
A
1673-0046(2015)7-01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