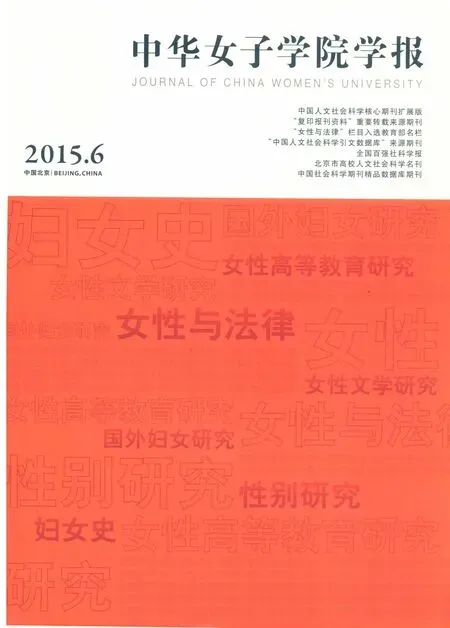《远离尘嚣》中芭斯希芭反传统形象的瓦解
毕素珍
《远离尘嚣》中芭斯希芭反传统形象的瓦解
毕素珍
《远离尘嚣》中的芭斯希芭以其性格、经济和情感上的独立对抗着父权制,展示了一个反传统的独立女性形象。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与人和命运的抗争之后,她最终放弃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自我意识,向传统的婚姻、观念和社会环境妥协屈服。这一反传统形象的瓦解主要来源于作者创作中的男权主义视角、内在精神冲突以及莎翁戏剧中性格悲剧的影响。
芭斯希芭;反传统;瓦解;男权主义
《远离尘嚣》是托马斯·哈代以威塞克斯乡村为背景的系列小说的重要开端,也是哈代第一部大获成功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子同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作为奠基之作,它在哈代的作品中占据着独特位置。芭斯希芭是哈代创作的第一个比较鲜明的独立女性形象,她聪慧勇敢、自信果断、知识丰富、思想活跃,追求自由独立,反对传统束缚,具有叛逆精神,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颇具独立性和现代性。
一、反传统独立女性形象的树立
1.强烈的女性意识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男性处于主体地位,拥有对女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女性则从属于男性,出嫁前是父亲的财产,出嫁后又成了丈夫的财产,被迫生活在男权社会制定的束缚和压制女性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中,呈现出波伏娃所谓的“第二性”特征。小说中的芭斯希芭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乡村姑娘,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农场主,性格不羁,讨厌束缚,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自豪,不断挑战传统道德约束,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表现为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肯定,并意识到作为人的独立存在。”[1]芭斯希芭在小说中的第一次露面,便生动地表明了她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欣赏和认同。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当众照镜子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行为,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坐在马车上的芭斯希芭却拿出镜子,认真端详起自己来。她毫无顾忌地欣赏着镜子中的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件大自然塑成的美丽作品,她那富有美感的女性特质、青春活力与勃勃生机,使她不禁绽开双唇,露出微笑。芭斯希芭这一“不得体”的出场行为表明了她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并为有这种身份而感到骄傲,传达出作为女性的自豪感和尊严感。
同时,芭斯希芭也清晰地认识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只是男性的财产,并以此为理由拒绝了奥克的求婚。罗斯玛丽·摩根从女性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芭斯希芭体现出的性别建构和权力关系加以探究,认为芭斯希芭以自己所具有的性别力量和骄傲逾越了当时社会规定的女性性别角色,对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男性,包括奥克在内都提出了挑战。[2] 16-17芭斯希芭不断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坚信自己就是“女性中的佼佼者”,告诫人们不要认为她是女性就无法妥善管理农场,并以实际行动努力证明女性并非社会所认同的“弱者”。接管庄园之后,她特意向雇工们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你们现在有了一位女主人,而不是男主人。”[3] 86她敢于正视男性员工的怀疑与不满,严厉斥责管家对女性的轻视与辱骂;她在农场管理上的作为,也证明了她试图超越父权制社会的限制,追求独立自主,并且在由男性统治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决心。
2.施展才能,经济独立
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离不开必要的经济条件。“女性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就必然成为衡量和评价女性地位的物质基础,并在社会诸因素中处于核心地位。”[4] 110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能否解放自身,也主要取决于他们在经济上能否摆脱自己的依附地位。乔治·艾略特曾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完美女性是彻头彻尾的绣花枕头,她们不能自立,除了生儿育女和供人观赏外别无用途。[5] 85芭斯希芭无疑是维多利亚时代完美女性中的另类。作为一名农场主,芭斯希芭获得了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经济地位。她雷厉风行且富有魄力,显示出丝毫不逊于男性的独立和能力,对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发起了挑战。
管家因偷窃被解雇后,芭斯希芭自己管理农场事务,回应人们对于她能否管理好农场的质疑。作为农场经营者,她勇敢坚定,亲力亲为,全力以赴:为确保一切平安,她会在每晚巡视农场房舍;她大胆走进谷物交易市场,与人讨价还价,表现得成熟自信;她知人善任,指挥若定,将农场的事务安排得妥妥当当,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实现了经济独立,赢得了他人的尊重与信任。
3.自由平等的爱情婚姻观
经济上的独立使芭斯希芭获得了思想上的独立和人格的自由,敢于对传统的宗教伦理和封建道德提出质疑反抗,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爱情和婚姻生活。在爱情上,她遵从内心感受;在婚姻中,她追求自由与平等,彰显了她对待感情独立自主的态度。对于不爱的男人,她懂得拒绝,对于倾心的男人,她又敢于表露。她曾表示:“虽然也许哪一天,有人会把我娶走,可我就是不愿意让人这样想,好像我是男人的财产似的。”[3] 30
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观念通常把婚姻视为女性获取幸福的唯一途径,相夫教子是她们婚后的天职,她们唯一的活动空间便是家庭。然而,芭斯希芭在感情上决不任人摆布,不甘处于卑微、被动的地位,而是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显示了与传统相悖的特性。她没有因为在奥克第一次求婚时财产上富于自己而动心,也没有因为波德伍德家资可观、声望较高而接受,而是遵从内心的感受,在三个追求者中选择了对自己有吸引力的特洛伊。芭斯希芭否定奥克和波德伍德的原因还在于抗拒他们与传统的威塞克斯社会一致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以及希望她成为一位贤妻良母的要求,这不符合她对自由平等婚姻关系的期望。她注重的是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与相互尊重,“我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公正——就这些!”[3] 292
二、反传统新女性形象的瓦解
1.向传统婚姻屈服
哈代塑造的许多女性人物都在传统操守与自然本能之间犹豫和挣扎,最终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与摧残,芭斯希芭也不例外。她聪明独立,敢于挑战传统价值取向和世俗道德标准,表现出一种超越所处时代的形象特征,然而小说貌似大团圆的结局实则是对这一反传统女性形象的瓦解。芭斯希芭在经历了婚姻破碎,丈夫背叛、失踪及死亡,波德伍德被捕入狱,农场危机等种种不幸之后,心力交瘁,束手无策,发现了自己的柔弱与无助。曾经独立、勇敢、坚强、自信的她开始绝望,脆弱得不堪一击,不得不向她曾经毫不犹豫就拒绝其求婚的奥克求助。基于与奥克之间目标一致的伙伴关系和同志关系,她嫁给了奥克,并将自己与农场一起交给他打理。虽然芭斯希芭与特洛伊的婚姻颇为失败,但她的自由选择是对男性权利的极大挑战,她的自主意志在此走到了顶峰,而她在小说最后的归宿则意味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屈服,她对奥克的选择似乎不是出于感情的强烈驱动,而是一种被迫的妥协与接受。
小说结尾处提出要走的是奥克,求婚的却是芭斯希芭,奥克和芭斯希芭角色位置的颠倒,似乎正是一种“复位”。奥克回到了他本身应处的农场和家庭主人的位置,芭斯希芭也回到了做一个顺从的漂亮妻子的本分。父权社会不仅用强大的男性话语潜移默化影响着被压迫的妇女,而且对所谓的叛逆者进行持续驯服和无情惩罚,使她们最终放弃自我,由反抗变为妥协到认同世俗社会规范和要求。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精神和拒绝男性束缚压制的新女性,就这样在经过了一系列与人和命运的抗争之后,最终“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全然交付给她曾经拒绝过的男人。正如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一书中提出,“两性实际上是权力关系,是一个群体与另外的群体的权力结构和安排。”[6] 36从本质上看,父权制的建立就是一个统治阶级的建立,以保证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远离尘嚣》向读者所展示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奥克“驯悍”的历程,是奥克实现对芭斯希芭统治的历程,在这一历程的终点,芭斯希芭心甘情愿地让奥克“驯服”了,成为几乎彻底意义上的失败者。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和自由平等艰难探索,苦苦抗争,不懈努力,然而事实证明她根本无法以自身的薄弱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社会现实,反而不断遭到沉重打击,她身上曾经闪耀的新女性光辉一闪而过,最终还是回归传统女性形象。
2.丧失经济基础,放弃独立自我
嫁给奥克意味着芭斯希芭放弃了独立的自我,她对农场的放弃同时意味着独立经济基础的丧失。经济基础是女性脱离男性控制、奴役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经济权力的丧失就意味独立生存机会的丧失。丧失经济基础的芭斯希芭从此以后只能依靠奥克生存,只能是他者,这也是她精神上依附男性的开端。
奥克娶芭斯希芭,是要使她放弃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以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生活原则来改造她。在婚礼上,芭斯希芭依顺了奥克的要求,按照奥克的喜好把头发按几年前在诺康比山坡上时那样梳理起来。她的笑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轻易快活的大笑变成了现在的浅浅微笑。芭斯希芭所有的梦想与激情在她身心疲惫之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向生活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心甘情愿地被奥克改造,被社会改造。那个曾经勇敢、独立、果断的新女性消失不见了,她的思想态度、精神状态完全被奥克的思想和原则所取代,被社会所驯服,在男权主义的洪流中被磨去了棱角,她变成了父权制社会下的一名普通女性,放弃了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高兴地过起了从前最厌恶的平庸的农妇生活。可以说,芭斯希芭与奥克终成眷属的结局,包含着一个女性的悲剧,一个本性被泯灭的悲剧,一个反传统形象瓦解的悲剧。
三、反传统女性形象瓦解的主要因素
1.男权主义视角
哈代对女性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深深关切,对女性内心痛苦和不幸遭遇的无限同情,对女性反叛与抗争精神的热情赞颂,使他在这一方面几乎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男性作家。但是,他的男性身份和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又使他无法跳出男权主义视角和思想框架,其创作的女性形象依然渗透着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无不拥有美丽的面庞和优美的身段即源于此,芭斯希芭就是一位“一张具有古典美的脸蛋能配有同样的身段”的“林中仙子”。[3]19体现着男权社会传统的审美标准对女性的期待和再现。女性的外表不仅是男性目光的审美对象,也是男权话语主导下的道德诉求的产物。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男性通常会按照自己理想的标准去塑造和规范女性。芭斯希芭是作为男人的一面镜子而存在的,并未摆脱证明男性存在和男性价值的他者的地位。不难看出,哈代对女性美的赞美、对女性美好品行的期待,仍然未能摆脱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小说中不时可见的发自“隐身叙述者”的评论,奥克、特洛伊和波德伍德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凝视”,无一不是最好的说明,这是由于“在最纯粹的男人的角度里,既是最独特的见解,也往往笼罩着社会规定的意识和影子”。[7]5
哈代视女性为天生的弱者,因而他笔下的女性都带有柔弱性。哈代给予她们赞美与同情,“我的作品只不过是呼吁人们不要对人——或对妇女,对低等动物——残忍”[8] 70,但他把新女性表现出来的矛盾性与分裂性归因于女性脆弱的本质,便是他狭隘男权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也是他笔下新女性形象瓦解的原因。芭斯希芭独立高傲,曾经坚强地经营农场,但在强大的奥克面前她依然只是一个弱女子,她离不开奥克,必须依靠奥克来挽救农场的危机。正如卡萨格兰德指出,作者哈代在小说中反映出芭斯希芭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是因为她具有“女性固有的弱点”。[9]452在菲勒斯中心的社会里,再强大的女性都无法敌过再软弱的男性。“芭斯希芭就是芭斯希芭,但她是个女人……不管芭斯希芭多么可爱迷人,她仍然是个弱者;……这就是哈代想象力的基础部分,也是他许多作品中的主要成分。”[10] 214哈代对女性的同情,是出于认同妇女本身就是弱者的观念上给予的同情,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同情,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地位上的同情。哈代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男性身份,注定了他不可能大大超越当时社会的观念和信条,因此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也难免带有男权意识的影子。
2.哈代本人的精神冲突
芭斯希芭这一反传统形象的瓦解,也是作家哈代本人精神冲突的表现。哈代在青少年时期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后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识到了宗教的僵化与愚昧,逐步发展到摒弃和抨击基督教。此外,哈代还接受了穆勒、斯宾塞、赫胥黎等人著作中的民主思想与进步观点,在文学创作中反对摧残人性、压抑爱情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热情颂扬积极、进取、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一个旧教条同新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唯心论和唯物论激烈搏斗的时代,哈代发现尽管当时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受到挑战与冲击,人文精神却依然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现实状况使他的思想陷入了极度的彷徨与悲哀之中。芭斯希芭变化动荡的思想状态反映了作家矛盾的、双重的心理。芭斯希芭拒绝奥克的求婚是她不愿受男人控制与摆布的体现,彰显了人文主义的自由个性,而她在历经挫折之后最终嫁给奥克的结局,则是她回归基督教顺从忍让的牺牲精神的过程。小说中芭斯希芭反传统形象树立与瓦解的过程,充分反映了哈代虽赞同人文精神,但又认同于基督精神的矛盾心态。
哈代徘徊于激进与传统之间的婚姻观,也是造成其作品中芭斯希芭反传统形象瓦解的原因之一。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文明,也对当时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社会的重大发展与变革,在哈代的文学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哈代笔下的新女性对传统道德约束的反抗,对完整独立人格的追求,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折射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历史进程。1856年英国第一次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运动虽然迫使社会重新看待与判断妇女的地位和行为,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真实处境以及人们脑中传统的女性观和婚姻观。社会变革与传统观念的矛盾,女性关怀和男权意识的激荡,造就了哈代独特的婚恋观。弗吉尼亚·伍尔芙透彻地分析了哈代的婚恋观,认为在哈代小说中,激情往往会带来负面影响。[10]215哈代显然并不认同波德伍德式的激情,而更倾向于将爱情诠释为一种以双双投身于一项共同事业为基础的情感。奥克最终能与芭斯希芭结合,就是因为这种感情比激情对于婚姻更为重要。芭斯希芭最终遗憾地回归传统,表现了她作为独立意识个体反抗的不彻底性,也充分反映了哈代的内在精神的冲突在婚恋观上的体现。
3.受莎翁戏剧中性格悲剧的影响
哈代热爱戏剧研究,在小说创作中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特别是莎氏悲剧的典型特点——主人公的悲剧往往源于自身的性格缺陷。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的忧郁、奥赛罗的轻信、李尔王的刚愎、麦克白的野心无不是酿成其悲剧的重要原因。这种性格的缺陷,反映了人的局限性和真实性。受其影响,哈代的小说绝不以道德说教为指向,他承认人是不完美的,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缺点,正是这些性格上的缺点,使人物的人生在社会大环境的催化作用下发生悲剧反应,导致不可逆转的悲惨命运。哈代主要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大多是有性格缺陷的悲剧人物,她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不高,没有钱财,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过分的奢望或追求,她们不安于环境或命运对她们做出的安排,追求爱的自由和权利,然而这个起码的要求却不能得到满足,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以悲剧结尾。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她们都继承了莎氏悲剧中人物性格悲剧的特点,在追求自由意志和自我价值、与环境和命运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其性格中的弱点在特殊环境的映衬之下愈益突显,形成独具特色的哈氏“性格与环境”的悲剧小说。
《远离尘嚣》是哈代反思性格与悲剧之间复杂互动的肇始。芭斯希芭对自己的生活具有明确的方向和沉着的把握,但她同样具有致命的缺点:傲慢和虚荣。正是这一点让她一直在奥克、波德伍德和特洛伊之间犹疑;使她对奥克的求婚不屑一顾;令她由于气恼波德伍德对她的淡漠而寄出情人节匿名卡惹来麻烦;也是这一弱点使她为特洛伊的英俊外表和甜言蜜语所吸引,不顾他人的议论和反对盲目陷入爱河,又对特洛伊谎称要娶别的姑娘信以为真,一时冲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不假思索地嫁给了他,从而酿就一场悲剧,导致了一系列悲惨事件,把别人也把自己推入了可悲的境地。然而,从根本上支配着她的所作所为的,似乎应该是她性格中表层的冲动和深层的传统之间的矛盾。她的冲动似乎表明她有意要同形形色色的束缚抗争,她性格深处的传统观念和善良却从根本上抽去了她赖以面对冲动的精神力量。因此,芭斯希芭虽然经常显得自信果断,敢说敢做,可事实上,她仍然不得不按社会定下的规矩行事。她可以出于冲动给人寄一张情人节匿名卡,也可以出于冲动把人给辞了,她可以不顾体统夜会情人,也可以一意孤行同特洛伊结婚,但是她却出于“内疚”而无法一口拒绝波德伍德那显然不切实际的求婚,更出于“名声”的考虑而在同特洛伊吵翻、在荒野里待了一个晚上之后,又回到那个可怕的家中。哈代通过芭斯希芭的坎坷遭遇揭示出人性的弱点以及可能引发的悲剧。
四、结语
哈代在《远离尘嚣》中创造了芭斯希芭这一有别于英国文学传统的乡村女性形象,体现出对女性社会角色乃至人类道德问题和生存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体现出了一个人文学者的至情关怀。但是,作者的男权视角、内在精神冲突以及对性格与悲剧关系的认识使得他塑造的这一新女性形象并未彻底摆脱传统社会对女性的传统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没能脱离传统女性忍让、屈从、牺牲的本质,芭斯希芭表现出来的压抑的自我反映出她思想、个性的矛盾性和双重性,她最终的妥协和屈服使得自身的反传统形象被瓦解,她最终又回到原点。芭斯希芭的命运轨迹揭示了女性被男权遮蔽、压抑进而毁灭的普遍意义,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伦理制度的思考,对女性性别符号的重新审视以及对女性命运的现实关注。
[1]蒋橹、何青.维多利亚时代男权统治与作品隐含的女性意识[J].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6,(4).
[2] Morgan, Rosemarie. Cancelled Words: Rediscovering Thomas Hardy[M]. London: Routledge, 1992.
[3](英)托马斯·哈代.远离尘嚣[M].张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7.
[4]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6](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7]罗婷.女性主义文学和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8] Gibson, James ed.. Thomas Hardy: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9] Casagrande, Peter J.. A New View of Bathsheba Everdene[A]. Robert C. Schweik ed..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C]. New York: Norton, 1986.
[10]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A].陈焘宇.哈代创作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责任编辑:贾春
TheCollapseofBathsheba’sUnconventionalImagein FarfromtheMaddingCrowd
BI Suzhen
In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Bathsheba confronts patriarchy with her independence in character, economyand emotion and displays an unconventional independent female image. However, after experiencing a series of protests from people and from fate, she eventually gives up her independent economic base and self- awareness and yields toconventional marriage, idea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e collapse ofthis image is mainlydue to the author’s patriarchal perspective, inner conflict and the influence of Shakespearean character tragedies.
Bathsheba; unconventional; collapse; patriarchy
10.13277/j.cnki.jcwu.2015.06.018
2015-08-08
I206
A
1007-3698(2015)06-0116-05
毕素珍,女,中华女子学院外语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理论。100101
本文系中华女子学院2014年度科研规划课题“哈代‘威塞克斯小说’女性形象系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G2014-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