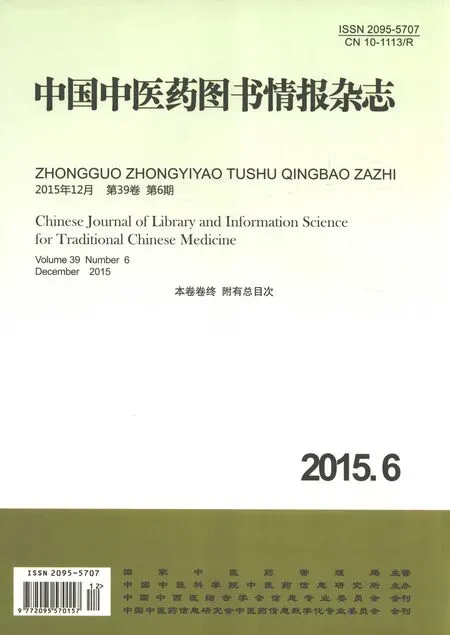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新进展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评介
李伟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新进展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评介
李伟霞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韩毅著《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依据中医传染病学和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重点研究了宋代瘟疫的流行概况、地理分布、社会影响、病因病机,以及宋代政府、医学家和社会民众等对瘟疫的认识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该书史料丰富,采用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次系统研究、科学揭示了宋代瘟疫的流行和防治情况及其规律,解决了宋代瘟疫防治的许多重大医学问题和技术难关,具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借鉴意义。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韩毅;评介
任何时代,瘟疫的流行都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影响。发年在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06年的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让人们感受到了全球大流行疾病带来的恐慌。瘟疫最大的特点是发病迅速,传染性强,病情危重凶险且经常大范围的爆发流行。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韩毅著《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就是围绕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而展开的专题性研究。该书首次系统研究、科学地揭示了宋代瘟疫的流行和防治情况及其规律,不仅解决了宋代瘟疫防治的许多重大医学问题和技术难关,而且也拓展了中国古代瘟疫史研究的内涵,具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4),共9章,106.4万字,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学家王曾瑜研究员作序。该书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 4个基本观点:⑴宋代形成了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从而将皇帝、政府、医学家、宗教人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紧密联系起来。⑵宋代不同社会阶级在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各级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力量的作用。⑶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官私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说明中医提倡的病证在防疫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⑷疫病流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革新,对于营造整个社会重视医学起了政策性的导向作用[1]。
1 史料丰富,来源广泛,统计全面
两宋时期,瘟疫发生比较频繁,近代有些学者对于这段时期疫病流行的次数、地理环境与疫病流行的关系以及应对疫病的政策等都做过一定的研究,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史料统计不够全面,难以准确反映宋代瘟疫流行的概况与防治措施。作者经过广泛查阅各种文献,将资料分为以下 4种。⑴历史文献,如《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太宗皇帝实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庆元条法事类》《宋朝诸臣奏议》《名公书判清明集》,以及宋人撰写的史书、文集、笔记、奏议、诗词、墓志铭等。⑵医学史文献,包括宋代医学家撰写的医学方书、医案病案、疾病分类、病因病理、临床诊断、处方用药,以及宋本医书的序言、跋、敕文和牒文等。⑶宋元明清地方志中《祥异》《灾异》《物异》等记载的疫病史资料,以及《城府》《抚恤》中记载的医疗机构设置情况等。⑷近现代学者关于宋代医学史研究的相关论著和论文。
在以上史料的基础上,作者完成了10万余字的《宋代重大疫情年表与史料》,统计出北宋境内约发生149次重大疫情,南宋境内约发生144次重大疫情,合计约 293次。此外,辽、夏、金、蒙古、吐蕃地区约发生18次疫情,部分疫病在宋辽、宋金、宋蒙等边境地区流行,对双方边民造成很大影响。作者统计的疫病流行次数和史料,较前人研究更加全面细致,成为本书研究的学术基础。
2 重视不同阶层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
该书在研究宋代社会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上,不仅重视皇帝和政府观念,也着重探讨了宋代医学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反应。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繁盛时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皇帝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政府防治疫病的各项措施的有效实施[2]。然而宋代皇帝和政府对疫病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变化,经历了“上天垂佑”“自然灾害”和“疾疫过后,盗贼必起”的过程后,将疫灾视为“四大灾害”之首。宋代名臣邢昺(932-1010年)指出,“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3-4]。
宋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力量的作用,宋徽宗赵佶认为“治病良法,仁政先务”[5]。其采取的医学、经济和政治措施,不仅有利于控制疫病传播,而且也将封建社会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疫病防治中,国家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了政策依据、法律保障和实际指导。宋政府不仅重视疫情信息的收集与上报,医学机构的建立与参与,病因病机的解释与应用,新方书的整理与刊行,防疫药物的研发与制造,患者的隔离与治疗,病尸的掩埋与火化,而且对民间救治采取了支持、引导和管控的政策。
宋代的社会民众也积极参与了疫病的预防和救治工作,许多医学家不仅亲自到疫区治疗患者,而且还撰写方书,将疾病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法则一一说明。一些宗教人士则参与了施舍粥药、收留病患和掩埋病尸等工作。至于普通民众,他们对于疫病的认识和态度,大多数采取逃避措施。宋代采取的官民联合应对疫病的措施,顺应了宋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中医传染病防治史上具有积极作用。
3 多方面探讨应对疫病的防治措施
疫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不仅会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还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事战争和国家统治秩序带来严重影响,在制定应对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医学、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多方面措施。
本书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宋代防治疫病时在医学方面采用了编撰方书、依方制药,派医诊治、施散药物,隔离病患、防止传染,施送棺木、掩埋尸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等措施。尤其是宋代将官修医书《太平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熙宁太医局方》《校正和剂局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及医学家所撰医书如苏轼《圣散子方》、朱肱《南阳活人书》、史湛《史载之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董汲《旅舍备要方》、王貺《济世全生指迷方》、张锐《鸡蜂普济方》、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洪遵《洪氏集验方》、王硕《易简方》、严用和《严氏济生方》、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等应用于疫病救治中,严令按方书配药,极大地促进了成药在疫病防治中的应用。在经济措施方面,划拨资金,赈济粮食,减免赋役,发放度牒。在政治措施方面,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要求上任官员严格按照时令来确定上任时间、以避炎瘴,下罪已诏、封神祭祀,政绩考核、奖惩官吏。在军队系统,宋代还采用了一些特殊的防治措施,如改革屯戍制度,选择“善地”作为军营地,确立“二年一代”的戍守制度,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遣发”,起用“峒丁”或“土人”戍守,以便尽可能地减少瘟疫流行对官兵造成的危害。
本书作者在研究中列举的有关宋代官府和医学家对疫病病因病症的探索,丰富的医案病案,以及医学家开具的上千副中医药方剂,再现了宋代应用医学防疫的全景。
4 关注人疫和畜疫的研究
两宋时期,农业在我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农业生产生活主要动力和运输工具的耕牛和马匹,在宋代社会也受到高度重视。然而,由于官营畜牧业场地的南移和牲畜饲养方式等的变化,畜牧中频频出现疫病的流行,迫使宋代政府不得不去考虑牲畜疫病的防治工作[6]。
本书作者在研究宋代瘟疫的流行和防治时,不仅考虑人疫相关的医学知识,更是用一整章来探讨有关畜牧疫病的内容,包括牲畜疫病的流行、社会影响及其特点,以及宋代对畜牧疫病的认识和态度,重点关注牛疫和马疫的防治措施。其内容包括:⑴建立完善的兽医检验检疫制度;⑵建立畜牧兽医机构和医马院,修缮马厩和驿路养马处所,重视兽医的选拔和临床实践;⑶颁布医牛、医马方书,规范牧养法,研制和发放药品;⑷积极治疗病牛、病马,并采取隔离、出卖等措施,防止疫病扩散;⑸严司其职,制定赏罚条例等。这些研究是以往的瘟疫史论著中从来没有出现的内容,不仅拓展了医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经济史、畜牧兽医史研究也有较大的帮助。
5 研究方法新颖,重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疫病虽然是一个医学问题,但仅用医学史和中医传染病学的研究方法,只能解决宋代疫病的概念、发展源流、病因病理、流行过程、临床症状、临床诊断等,无法解释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如何影响疫病的流行和发展,这就需要借助医学社会史的方法。本书作者一改此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模式,从疾病史与社会史的角度,揭示宋代皇帝、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态度和防治措施。同时,作者还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解析了宋代社会疫病防治中出现的复杂的阶级性、等级性以及社会各阶级在疫病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和局限等。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宋代疫病防治措施,作者在《第四章 宋代政府防治诸路州县瘟疫的措施》《第五章 宋代政府防治军中瘟疫的措施》《第六章 宋代政府防治牲畜疫病的措施》《第七章 宋代地方官吏对瘟疫的认识与防治措施》,以及《第八章宋代医学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对瘟疫的认识与防治》中,不仅整体地介绍了宋代在政治、经济、医学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更在每个章节之后附 1则个案研究,用具体事件向读者展示宋代的每项防治措施的实施方法,有利于读者去思考各项措施的利与弊,从而为现代疫病防治提供经验和教训[7]。
总之,该书在研究宋代瘟疫流行与防治方面,史料丰富,分析全面,结论有理有据,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有较大的突破与创新。该研究不仅有利于拓宽中国疫病史学术视野,把疫病史的研究拓展到整个社会史与文化史的领域,而且有利于今天重新审视国家与医学、传统与现代等问题,还能为今天如何认识、面对以及处理现代疫病等提供有益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同时,对宋代瘟疫的积极探索,有益于全面了解在中国古代瘟疫防治体系中,国家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认识历史上国家和社会的疫病救疗事业的发展轨迹,探明宋代社会的反应机制、防治措施的发展脉络、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等[8]。
[1] 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10.
[2] 韩毅.政府治理与医学发展:宋代医事诏令研究[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398-406.
[3] 脱脱,阿鲁图.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799.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1507.
[5] 赵佶.圣济总录[M].郑金生,汪惟刚,犬卷太一,校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2240.
[6] 韩毅.宋代的牲畜疫病及政府应对——以宋代政府诏令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28(2):132-146.
[7] 韩毅.将政府、医家和民间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J].人民论坛,2013(13):78-80.
[8] 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概要[M]//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概要(20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94-304.
Research Progress in Chinese Ancient Plague History - A Review of Prevalence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Plagues in the Song Dynasty
LI Wei-xia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Han Yi’s book, Prevalence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Plagues in the Song Dynas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prevalent overview,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ocial influence, etiology and pathology of plague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recognition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Song government, medical scientists and ordinary people about plagu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TCM lemology and medical social history. The book had abund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bined integrated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ogether, firstly systemically researched and scientifically revealed the prevalence, preventive conditions and law of plagues in the Song Dynasty, solved many important medical problems and tackled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had certain references for academy and reality.
Prevalence and Preventive Treatment o f Plagues in the Song Dynasty; Han Yi; review
10.3969/j.issn.2095-5707.2015.06.012
2015-09-15)
(
2015-09-30;编辑:魏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S105)
李伟霞,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医学史研究。E-mail: elisebet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