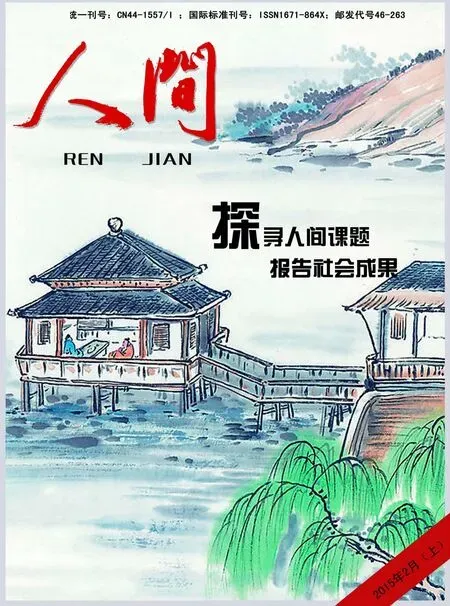试析毛泽东主观素质的时代契合性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 石翼飞
试析毛泽东主观素质的时代契合性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 石翼飞

坚持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认识领袖人物,一方面要看其所处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要其自身所具备的主观因素,两方面互动结合是领袖人物成就伟业的原因。以毛主席为例,他集以下四个特点于一身:一是怀揣挽救民族危亡、恢复中华独立的远大志向;二是具备博古通今、运筹帷幄的深邃智识;三是恪守热爱人民、服务人民崇高道德;四是具有吞吐天地、舍我其谁的领袖气质,而这些品质素质与其所处时代达成了较高层次的契合。
毛泽东;主观因素;契合;时代
杰出人物的成长与成功,一方面是时势造就英雄,个人受历史必然性的陶铸和催发;另一方面是英雄顺应时势,个人以其特有的思想意识、气质胸襟、心性品格顺应时势的召唤。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从个人素质来说,是由于他在其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培养和形成了远大的志向、深邃的智识、高尚的道德、领袖的气质等优秀的个人主观素质品质,而且这些主观素质与时代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
一、毛泽东之志——救亡图存、独立自主的远大志向
志向是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形式,是一种积极的主观意识,代表一个人的理想、胸怀、奋斗目标,彰显个人的斗志、毅力、心性品格,是人生境界的体现,确保人生进行过程的积极态势以及人生完结形态的审美价值。
1.毛泽东时代的志向崇尚。
清末民初的中国深陷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时代以其悲怆声音呼唤有志之士:国土被瓜分豆剖、主权被肆意践踏,需仁人志士以爱国救亡为己任,带领华夏民族驱逐列强,恢复独立自主;封建统治腐朽颓废、百姓惨遭盘剥压榨,需仁人志士以民主爱国为己任,带领人民群众推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等民族先觉顺应时代呼唤,以其澎湃的激情和执着的志向指导社会活动,形成了近代以来革命热情最为高涨、思想碰撞最为激烈的局面。毛泽东继承和发扬先辈志向,并以理想志向激励自己的精神生活,形成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少年时作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志向对于他人生道路的指引;中年时作诗:“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体现了他执着革命理想而不叹年华易逝的旷达气概。
2.毛泽东志向的时代契合性。传统文化要求志存高远,注重向内修养来通达志向。毛泽东志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却与此相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志愿是当一名教师,其次是记者”[1];且其志向的形成和发展最开始是受外界的刺激,而非通过向内的修养,他曾说:“我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支部队去战斗。我是被迫这样做的。反动派杀人太多。”[2]当然,随着毛泽东人生际遇的不断变幻、知识积累的不断丰富、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生感悟不的断深刻,其人生志向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升华:由看到政府镇压饥民而产生同情农民、向往平等的心理,到阅读《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而产生振兴国家、抵御外辱的意念,到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感动而渴望建立理想社会,再到被十月革命胜利消息振奋而发起征召有志救国救民者,最后在《湘江评论》报刊上指出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阶级压迫,其志向实现了由朴素的惜民心理向爱国主义理想的萌动,由民主爱国主义向民主革命思想的转变,由革命的爱国理想向马克思共产主义信念的升华。
毛泽东能够深入社会实践,接触底层百姓,了解普通大众饱受封建压抑和外族侵略的苦楚,其志向的具体内容具备更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其志向的丰富和升华,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有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个过程比闭关自省更为实在和深刻,志向的秉持更加坚定和执著。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在风云际会的近代中国,封建王朝式微,民族危机加剧,其个人志向的确定与调整都顺应了历史潮流,达成了与时势的高度契合,其伟大抱负也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得以实现。
二、毛泽东之识——博古通今、运筹帷幄的深邃智识
智识是客观世界的在人脑的主观印象,是使人区别于动物,向更为高级的形态发展内在原因,对于个人而言,智识积累越多、智识水平越高、智识结构越优化,则越能表现出对于社会的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越能展现出对于社会的适应和改造能力。
1.毛泽东时代的智识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行进到清末民初已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传统文化的自我反省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构成崇尚新文化、新知识的内外原因。首先,崇尚伦理的传统畸形发展,将人置于伦理框架的前提下,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消融个人的自身价值和应有权利,人民的主体地位、自我意识和主体价值观念淡化,致使群众智识淤塞、思维水平下降。其次,热中政治倾向极端发展,致使官方的需要成为评判是非曲直与轻重缓急的唯一标准,遮蔽了经济的作用,抑制了人民解决经济问题的创造力。再次,伴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带来的沉痛巨创,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中国人民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比较中,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与落后。最先从天朝大国迷梦中醒来的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世界的客观审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注重。毛泽东也在这种文化激荡的时代,广泛涉猎、博采众长,打下了深厚的智识基础。
2.毛泽东智识的时代契合性。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知识的更新满足了社会发展的最新需要。少年时代的毛泽东饱读诗书古经、博览历史典籍,了解风土人情,深谙民族心理,有利于其用国人习惯方式处理现实问题。青年时期的毛泽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并经过各种思想的冲撞比较,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迎合了时代对于革命人才的崇尚。大革命失败,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出政权”,由此中国革命的道路由民众运动转向武装斗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使全国革命斗争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面对敌强我弱的革命形势,毛泽东提出了诸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革命思想。面对抗日战争时期“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科学地预测了抗战由战略防守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为全国军民厘清了思想。解放战争时期,为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毛泽东带领人民解放军运用“人民战争”的思想,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以及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其信仰从笃信孔夫子到崇拜“康梁”再到执着马克思不断跃进,其世界观由唯心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不断蜕变,形成了一套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学识体系。这一体系被中国近现代史所证明是一个结构优化、具有很高实践指导价值、与时势高度契合的知识体系。
三、毛泽东之德——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崇高道德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善恶标准的内化作用使社会成员自觉地克制欲望,避免与社会公德的矛盾,实现个体与外在社会及内在自身的安定和谐。个人越是具有高尚的道德,则越能展现其人格魅力、亲和力和感染力。
1.毛泽东时代的道德崇尚。社会转型期的清末民初,以儒学为核心的旧道德崩溃,价值取向紊乱、非道德主义泛滥、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道德教育扭曲变形,与此同时,树立新的道德规范,强化新道德的控制机制成为发展趋势。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传统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于此相应,道德救世思潮则日趋高涨,此思潮以人为主体,围绕道德思维、道德理想、道德精神、道德责任、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等方面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近代志士仁人经邦济国的重要精神武器。毛泽东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并不偏执顽固,他积极关注社会形势、参与社会实践,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传统道德有所损益,避免迂腐落后;他既能保持清醒,深究传统道德之积弊,又能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并结合时代需要博采众长,运用实践,避免虚妄激进。
2.毛泽东德行的时代契合性。秉承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又根据时代的特征赋予传统道德新的内容、新的作用,是毛泽东的道德崇尚与时代契合的主要体现。他赋予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以新的时代内容,创造性地融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应用其中,从根本上颠覆传统民本主义中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主奴关系,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念;他赋予传统道德范畴以新的时代内容,将“智仁勇”的封建道德范畴进行历史唯物论的改造,提出:“智”是指导革命的科学理论,“仁”是亲爱团结的阶级情意,“勇”是克服困难的英雄气概,使其获得革命的含义;他赋予传统修德行为以新的途径,一改通过精神体悟达到提升道德境界的向内修炼方式为强调社会实践、投身革命斗争的外向修为方式,提倡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造自我,不断净化思想,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无私的、忘我的“纯粹的人”;他赋予道德新的作用,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在逻辑层面为人民群众推翻腐朽政府正名,使新道德成为革命的有力精神支持。
毛泽东在内容和作用上对于传统道德的颠覆和超越,使其道德理想越来越科学,道德境界越来越高尚,道德实践越来越契合时势。其完善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境界使他在党内形成了较高的威望和较强的魅力。威望以强力聚集人,魅力以柔力吸引人,这使他自然地站在了“人和”的道德高地。
四、毛泽东之气——吞吐天地、舍我其谁的领袖气质
气质是人的一种神之于内而形之于外的感觉,它在身心素质的基础上,体现在外在的神态眉宇、动作步调、谈吐着装等方面的独特风采。对于个人而言,气质可以扩大个人思想影响和实践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是其走向成功不可忽视的主观因素。
1.毛泽东时代的气质崇尚。传统的气质评判标准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受到极大冲击,封建社会推崇的谦谦君子,往往被视为迂腐之辈,在革命年代难有大作为;揭竿而起、带有江湖义气的农民起义首领,思想先进、带有很浓的学究气质的读书人,也被实践证明不能担当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什么样的气质才符合革命时代的需要?中国近现代抵御外强侵略的斗争节节败退,人民的士气大受打击,民族自信受到挫折,时代需要国人保持气质,保全气节,因为只要气质在,则民族的斗志还在、信心犹存,民族就不会败亡,革命仍将继续。乐观豁达、坚忍不拔的革命气质,对内可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可增强对敌的威慑力,革命志士的英勇无畏的气节感召人民大众,推动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生于农村的毛泽东,既与农民有着共同的语言,又能深入工人生活,与工人打成一片;同时,他专于革命理论研究,还能和先进知识分子畅通交流。应该说,时势的催发和实践的锤炼,塑就他的能被中国各个阶层人民接受领袖的气质。
2.毛泽东气质的时代契合性。学生年代,毛泽东致力于学习和消化革命理论,虽积极关心时势、热衷革命运动,但主要以参与者身份投身革命;虽然他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其“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时有显现。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几经革命战争的高潮与低谷,由一个革命的参与者变为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他对于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的卓越才能,使其领袖气质逐步彰显。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具有雄才大略,又是一位军事家,能够运筹帷幄;既是一位知识分子,具有远见卓识,又是一位农民,能够肝胆相照;既是一位革命家,具有革命气节,又是一位诗人,天生豪迈奔放。同时,毛泽东性格既有“虎气”又有“猴气”,“虎气”表现在吞吐天地、气壮山河的豪气,不怕鬼、不信邪、敢作敢为的勇气,表现为倔强刚毅、百折不挠的犟气;“猴气”表现在机警过人、见微知著的洞察力,表现为能屈能伸、进退自如的灵活性,表现为洒脱机智、诙谐乐观的幽默感。“虎气”与“猴气”的互补,能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再有,毛泽东继承了湖湘文化的“霸气”和“蛮气”,“霸气”使他具备舍我其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蛮气”使其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革命意志。毛泽东个人气质的动态发展与多样形态,契合了客观时势的需要,成为其成就伟业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
关于杰出人物较于常人更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并没有落入英雄史观的窠臼,因为我们承认杰出人物必须以其存在的社会条件为前提,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且少数杰出人物只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我们所要正视的是构成群众的众多个体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可简单地等量齐观,杰出人物所承担的责任与和做出的贡献更大,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在于杰出人物具有超出常人的个人品质与素养,当这些素养又恰恰与时势契合,英雄则顺乎自然地被时势造就。
[1]参见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4页。
[2]参见胡哲峰、孙彦编著:《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5页。
A75
:A
:1671-864X(2015)02-0032-03
石翼飞,男,1979年9月,讲师,中共杭州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