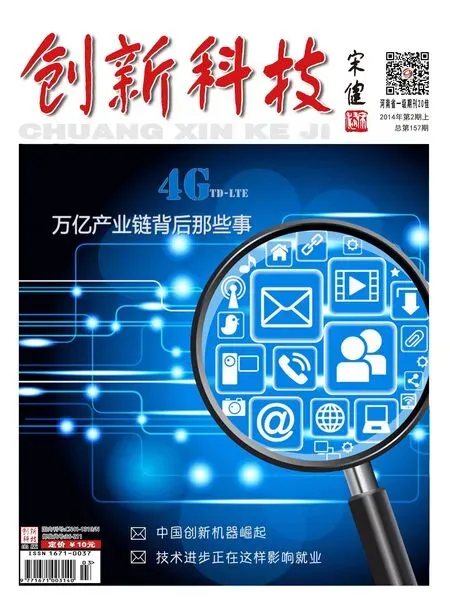科学是怎么误入歧途的
文/译 科
现代科学家们相信有余,验证不足——有损整个科学界和人类。学术界有太多的发现不过是伪劣实验或低劣分析的结果。
生物技术风险投资家们的一般经验是,乐观估计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有一半无法证实。2012年,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安进公司(Amgen)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癌症研究方面的53项“标志性”成果中,他们仅能证实6个。此前,医药公司拜耳(Bayer)的一个研究小组重复做了67项与标志性成果同等重要的论文研究,仅有1/4得到证实。一位计算机领域的著名科学家颇为苦恼,因为在他的研究子领域中,3/4 的论文都是骗人的鬼话。2000~2010年间,大约有80000名患者参加临床试验,但相应的基础研究却由于错误或不当后来被撤销。
垃圾成堆
就算有缺陷的研究不至于危及人的生命——大部分这类研究离进入市场还很远——但浪费了财力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智力。阻碍进步的机会成本虽然难以量化,但可能十分巨大,还会越来越大。
原因之一就在于科学界的竞争激烈。1950年代,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绩斐然的现代学术研究初具规模,但它仍然是少数人的游戏。整个科学家的队伍人数不过二三十万。随后人数暴增,据最新估计,活跃的研究人员数量在六到七百万之间,科学家们已经丧失了自我监督和质量控制的作风。学术生涯受制于“不发文章就丢职称”的束缚。职位竞争是你死我活。2012年美国的全职教授平均收入是135000 美元——超过法官。一个学术职位每年都有6 名新毕业的博士争夺。如今,验证研究(重复他人的研究)对于研究者的职业生涯毫无帮助。没有验证,靠不住的发现就推翻不了,会继续误导我们。
追名逐利的思想也在鼓励夸大事实,对研究结果挑肥拣瘦。为了维护自身的独家地位,主要的期刊都硬性规定很高的退稿率:超过90%。最能抓眼球的发现才最有机会发表。难怪1/3的研究人员都知道有同事粉饰文章,比如说“根据直觉”得出结果,剔除其中不合适的数据。而且,由于世界各地攻关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小组越来越多,原本在真正的发现和捏造的数据怪胎之间的混战中总是有一个研究小组倒下,现在倒下的可不止一个了。如此这般似是而非的相关性常现于渴望惊人论文的期刊。就算这些相关性研究是葡萄酒饮用、老龄化或放纵儿童玩电子游戏的文章,也很可能占据报纸头版。
相反,没能证明某个假设的论文鲜有期刊愿意出版,更不用说得到认可。“否定性结果”的论文现在只占发表论文的14%,而1990年是30%。然而,对于科学,证伪和证实同等重要。不发表证伪文章意味着研究人员要浪费金钱和精力去探索其他科学家业已证明的死胡同。
神圣的同行评议也不尽如人意。一本著名的医学期刊做了个同行专家评议研究,发现大部分评议人即便已经被告知这是一次测试,也没能发现故意插入论文中的错误。
亡羊补牢
这一切使得致力于发现世界真理的这一行业的根基摇摇欲坠。怎样才能重整旗鼓呢?首先,所有学科都应效仿那些竭尽全力严格标准的榜样。认真处理统计数据不失为一个好的起点,特别是在通过大量数据筛选来找寻模式的领域里,这类领域越来越多。遗传学家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把基因组测序早期海量的似是而非的结果转化成了一系列真正重大的发现。
在理想的情况下,研究方案应事先记录下来,用电脑监控过程。这可以遏制在实验期间篡改设计、夸大实验结果的诱惑。(药物临床试验已经有了这一套制度,但执行情况参差不齐。)在可能的情况下,试验数据也应该是开放的,供其他研究人员检查和测试。
最开明的期刊已经不那么反感缺乏轰动效应的论文。一些政府资助的机构,包括每年支出300 亿美元研究经费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研究鼓励验证研究的最好办法。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深谙统计知识。但这些趋势需要走得更深入。期刊应分配空间给“索然无味”的研究,资助者也应为此预留资助。同行评议应该更加严格——或者完全废除,转而采用追加评议这种出版后评价形式。在物理学界和数学界,这一制度近年来一直行之有效。最后,政策制定者应确保使用公共资金的机构也尊重这些规则。
科学依然大受尊重——即便有时候令人莫名其妙。但其特殊地位的基础是,大多数时候正确、错误的时候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宇宙真的不缺真正的奥秘,需要科学家们世世代代努力探索。弄虚作假的研究铺就错误的道路,是通往认识真理的道路上不可饶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