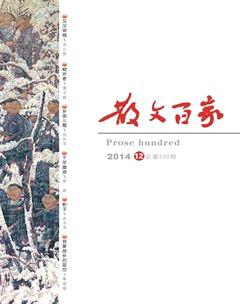乡里旧事(三题)
乔林晓
纺车与织布机
父亲说,祖上穿衣盖被离不开纺车织布机。他是1930年代生人,那年月的村子里,纺车织布机可是司空见惯。年年月月,男人们在地里忙活,女人在家里纺线织布,那都是为着吃饭穿衣这个最微薄的需求。
我们那地方管织机上织出的布叫老布,管从县城花钱买回的布叫洋布。老布洋布叫法不同,情感取向也不同。我老奶奶就蛮喜欢老布,她说,老布结实耐磨,弄身衣服,三年五载也不会破。可洋布,看上去好看,单薄得像张纸,一年下不来就破开洞了。
我记事时,我老奶奶已是一位苍苍老人了。她手拄拐杖,进进出出,一身中式服装,——不用说,那都是老布缝做的。可她不动手做,她人老眼花,力不从心了。包括我老爷爷的一身中式服装,都出自母亲之手。母亲还纺线织布,织出的布匹除了做衣服,还做被子。我家里有几床被子,那被里被面就全是老布。当然,也有洋布缝做的被子。白天里,老布被子与洋布被子叠放一起;到晚上,就各有归属了。老布被子父母盖,洋布被子孩子们盖,这都成习惯了。父母说,老布被里粗糙,怕孩子们不喜欢。这话语里还隐约蕴含另一层含义:父母是蛮喜欢这老布被子。只不过没有明白说出罢了。
我老奶奶家里,从被褥到衣服,乃至围裙这样的小玩意儿,都是老布做的。若是有人建议弄成洋布的,她定会断然反对,她是从骨子里喜欢老布的。若是再规劝几句,她或许还会动怒,她会说出老布的一大堆好处来。
我老奶奶家里,搁着一架纺车和一台织布机。它们并排一处,一高一矮,一大一小,倒像一对好兄弟。每隔一些时日,她就拿鸡毛掸子掸掸上头的灰尘,她真是挚爱它们的。这纺车织布机倒也不总是闲着,有时就会搬到我家,——母亲要用来纺线织布的。可纺线织布一结束,纺车织布机重又搬了回去。我老奶奶把它们看得紧紧的,好像一不留心就损坏或丢失了。
母亲纺线织布的情形,我印象颇深。一年里,会花费那么三四个月去操弄。在我六七岁前后的几个年头里,年年如此。纺线是纺线,织布是织布。有的时候,先纺线再织布,各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有的时候,则放在一天里头,白天织布,晚上纺线。
纺车转动时,发出“呼呼”的响声。这声音悠长绵延,时断时续,倒像一首曲子。母亲这头转动把儿,那头的棉线就一长条一长条伸出来了。时候不长,就是一纺锭的棉线儿。母亲把它轻轻地卸下来。完后会弄成一个个大线团的。夜深人静时,纺线的声音尤其清晰。我们家养只小花猫,它晚上也打鼾。两种声音此起彼伏,相互应和。母亲怕纺线影响我们,就索性把纺车搁到灶台下的一角。她这担心其实多余。我们都习惯了,那就跟催眠曲差不多。每晚,小花猫就鼾声不止,我们也爱听,从不会把它轰出门外的。
织布机却是搁在炕头的,就紧靠着窗户。它那样子大大的,把大半个炕窗户都给占去了。可母亲说,就得这样,来回穿梭,没亮光不行。窑洞里头原本就不甚亮堂,有织机挡着,就愈发不亮堂了。母亲操弄织布机的那两三个月,屋子里满是梭子的声音。她一坐上去就是好一阵子。早上的日头斜着进了屋子,她就忙开了,到午后,日头又斜着走出去,才伸展伸展发麻发酸的身子,走了下来。
老布是随着日子,一丝一丝往长伸展的,三五天下来,才窄窄一条,三五十天下来,就卷成圆桶形状了。一个年头里,究竟要弄几匹老布,母亲心里自然有数。我老奶奶那头,衣服被子要划算在内;我们家这头,父母的衣服,还有他们的被子,也要划算在内。除此之外,多出一些也不显多余。搁在箱底里,总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几棵桑树
我家院子底下有几棵桑树。具体数目记不清了,三棵,或许四棵。散布在几丈见方的小土堆上。每天一出门,跑下土坡,三两下就坐到树杈上了。出来玩耍时,这里也是我最先流连的地方。我一来,近处几家的孩子也很快赶过来了。我们摇晃着树枝,我们俯瞰着树底下的草儿虫儿。玩到性子上,就忘乎所以。我们开始追逐起来,那树杈离地面不过几尺,就是不留神,跌坐下去,也无关紧要。至多会把屁股给弄疼。揉揉弄疼的地方,扑扑尘土,便跳上去,重又开始玩儿了。
可一旦叫大人看见了,就不能再无所顾忌地折腾下去——最起码得跳下来,等大人走远了,再做打算。大人是害怕我们把桑叶给弄掉,甚至把树枝给折断。这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猛烈摇晃树枝,都给他们看到了,而且不止一回。而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玩兴也正浓。无端地中断我们的玩兴,自然心有不甘。所以,我们阳奉阴违,会伺机重来的。
我们的心思大人倒也清楚。他们感觉恫吓不灵验,就转而安抚起来。他们说,瞧瞧看,树上的桑葚多稠,等红透了,味道可甜美了,好生对待桑树吧!
我们爱吃桑葚。可每年每年,桑葚还未红透,就所剩无几了。其缘由也说不分明。或许是叫大风给吹落地了,或许是村那头的孩子给弄跑了,或许又是养蚕人弄桑叶无意中损坏了。
那桑树是我们家祖上栽种下来的,本家的叔伯们喜欢养蚕,我家也喜欢养蚕。天气一转暖就忙活开了,凌晨,日头还没出山,就有人前来采摘。这带露水的桑叶鲜活柔嫩,立刻拿来喂蚕并不合适。不过没事,拿棉布一片一片给擦拭一番就好了。
桑叶上来的时候,树荫浓密浓密的,坐在底下乘凉,可是个美不胜收的事儿。初夏时节,天气明显溽热了。早饭过后不久,我们就聚到树底下了,或玩军棋,或打扑克,或摆弄几回过家家的游戏。不知不觉地,日头就到中天了。
我们在树底下玩的时候,母亲在家里忙着喂蚕。桑叶吃光了,她得赶快加上新的;蚕屎多了,她得清理清理。夜里,我们睡觉,她还记挂着,她要起来两三次照顾照顾蚕宝宝。
母亲不停地忙活,我全然不觉。直到洁白的蚕茧收获了,我才恍然明白,今年的养蚕又结束了。几个箩筐里,蚕茧堆得满满当当。母亲与父亲却在商量着卖蚕茧和来年养蚕的事儿。
收获的蚕茧大都卖了,丢下来一小部分弄成把状的丝线,母亲做棉被衣服要用。抽丝那阵,满屋子弥漫着蚕蛹的香味儿。木式的蚕车架在锅台上,散在热水里的蚕茧来回翻动。母亲拿手一拉,许多蚕茧凝成一股蚕丝就出来了。母亲拨弄蚕丝,跟前还有一位大婶手把枴子,缠绕丝线。我在一旁却早已等不及了,我想快些吃到蚕蛹。忙活抽丝的这几日,会有许多蚕蛹出来,可以尽情享受。
养蚕的事儿忙碌停当,桑树的树叶依旧浓密。那要等到立冬前后,霜期来到,才片片飘落。霜期一来,最先飘落的就是桑叶。头天还密密一树,到第二天就全没了。地上桑叶多了,鸡儿猪儿就肯前来。这个时候,它们尽可以多呆一阵子,这跟热天时不一样了。那时,我们常常前来。有我们在,它们就望而却步了。
一间瓦房
我家院子东面有一座瓦房,母亲管它叫房子。其实,它算不上房子,因为里面从未住过人。它其实是一处牛圈栏。
这瓦房搭建的初衷正是要养牛,倒也的确养过一两个年头。母亲说,她年轻时的那些个年月,日子极度清苦。把公家的黄牛拉回来喂养,可以多挣些工分。工分多了,分到手的粮食就多些。可不知为啥,仅仅一两个年头,养牛的事儿就结束了。
这瓦房就此空置下来。
从我记事时起,瓦房里头就堆积着麦秸秆和杂物。麦秸秆是引火做饭的好东西,炉子里塞进一小把,就可把木柴给燃着的。不止一回,我看到父亲把大捆的麦秸秆往里头放。所以,这麦秸秆总是那么多,似乎就从未下去过。杂物则是母亲放进去的,穿旧的鞋子,少一条腿的桌子,破开口子的坛子,没有把儿的锄头,总之,大凡派不上用场、又舍不得丢弃的玩意儿,母亲就一股脑地放进去。这些杂物被麦秸秆掩埋得不见踪影,可也没事,只要用手翻动几下,就又露出来了。
多数时候,杂物是受冷落的。都是些用旧用破的玩意儿,哪能受到青睐?可院子里一有孩子前来,就又是一回事儿了。我们要过家家,却没合适的物件。我眉头一皱,立刻就想到了它们。想到了就开始动手,三下五除二,很快,我们就翻弄到院子里来。玩到兴头上时,我们就忘乎所以了。杂物在院子里四处散落,成了大人走路的障碍。每每这时,母亲就不悦了。
有的时候,我们还进到瓦房里玩。厚厚的麦秸秆,软绵软绵的,坐在上头舒服极了。我们在上头打滚、摔跤,我们还打扑克、玩军棋。我们一样也有兴致高涨的时候。高涨起来了,我们就撕破嗓门喊叫。母亲在屋子里听到了,就会出来。她说,这些干燥的柴火底下,最肯隐藏蝎子的,叫那东西扎一下,可吃不消,要难受几天几夜的!
盛夏里,我家习惯在瓦房顶上晾晒东西。这地方高出地面丈许,干燥又干净,鸡儿猪儿想搞破坏,也没那么大能耐。粮囤里搁久的陈粮,坛子里腌制的酸菜,采挖回来的药材,都可以拿上去晾晒的。房顶上时常丢一块苇子席,晾晒的东西就是搁在它上头的。日久天长,日晒雨淋,席子破旧了,父亲便换一块新的上去。村人前来串门,瞅到那席子,就说,瞧你家的席子多好,时常是新新的。他们或许不清楚,这苇子席其实是暗暗地变换着的。
我在村子里念小学时,也时常在这瓦房里进进出出,不过,已经不是玩儿了,是帮着大人忙活家务的。我也时常借着土墙,飞身跃到瓦房顶上,那同样不是玩儿,那是帮着大人晾晒东西。小学毕业后,我离开村子求学,和瓦房“打交道”的机会便少了许多。再以后,我家搬了家,这瓦房连同整个院子变卖给了别人家。于是,就没机会与瓦房“见面”了。
前几年,我回家偶尔路过,发现瓦房早就没了影儿。村人说,那主人家为了多弄出一些土地,便用推土机把瓦房给铲除了。听着这话,我不由生出几分惋惜来,心里好像丢失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一回头,发现四处是一排排齐整的砖窑平房,与瓦房同处一个年代的土窑洞看不到了。
而这,也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