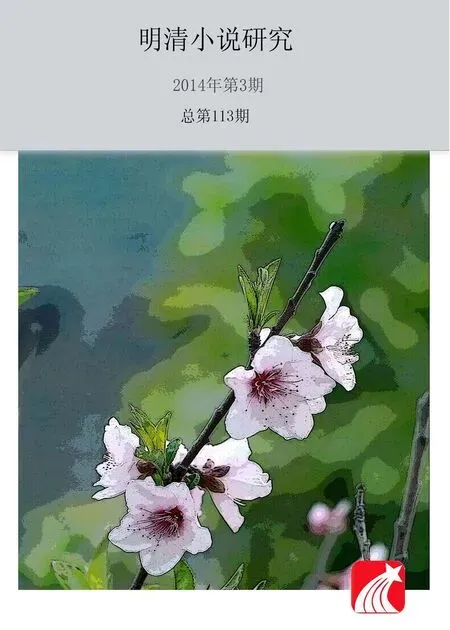道教的承负说与袁枚的《子不语》
· ·
道教的承负说与袁枚的《子不语》
·王云·
尽管袁枚不信奉道教,但道教的承负说不失为观察《子不语》的一个有效视角。《子不语》中既有着与承负观念相一致的描述“父债子偿”式超自然恶报情节的小说,又有着与承负观念不一致的对“父债子偿”式超自然恶报情节进行反拨的小说。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是由超自然力量而造成的善福恶殃情节彰显出来的,是借助宗教正义而实现的艺术正义,然并非所有这类情节都能彰显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因为并非所有这类情节都体现了“得所当得”和“一视同仁”这正义的两大要素。以此观之,也只有上述后一类小说才真正地彰显了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在清朝这样一个正义观念比较缺乏的年代里,它们在思想上有着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本文不仅以艺术正义的标准评价了上述两类小说,而且还评价了可能成为其观念基础的各种思想资源。
袁枚 《子不语》 道教 承负说 艺术正义
一、《子不语》中的“父债子偿”式小说
《子不语》(《新齐谐》)续卷八中有《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此则笔记小说以曾经是山阴活无常的冥役韩六为贯穿人物,连缀起发生在山阴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如下:
戴七亦山阴役,好嫖赌,辄月余不归。其妻某氏托其邻王三寄口信,云要钱米度日。王三寻见戴七狭邪,则戏云:“尔在此贪花,尔妇有信,尔无钱寄归,尔妇亦要养汉矣。”戴七信以为真,曰:“伊妇人,乃与王三作此言,伊必有故。”是夜二更归,急叩门,妇披衣起开门,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语而入室卧。戴以为有所私在室也,提灯遍烛之不得,坐而疑之。适有吴某者,亦同役,过其巷,偶磕烟灰于其壁者三声,其夫方疑,谓是必有所约而至也,开门逐之。吴怪之,急走。戴逐里余,及吴,各相视而散。戴归,谓妇与吴私,殴之,妇方妊月余,毙。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吴晚饭罢,口噤,遂绝音。昏睡去。诘朝起,则曰:“我当往谢韩六,我当往告戴七。”盖噤时见两冥差,其一为韩六也。摄至冥司,见主者暖帽如显官服,谳王某以口舌戏嘲,酿人命,寿既尽,当杖四十,枷三年,另案再结。吴以非法饮食之灰,不应夜深磕人门壁;戴既开门出,尤不应急走;戴既逐里余相见,亦当说明其故以释疑。吴当夺筭半纪,掌责百二十。戴游荡不归,以疑杀妻,当得绝嗣穷饿。检冥籍,戴已有子七岁,命五鬼摄取其魂。且云:“韩六读谳词与伊听,需费八百,乃诣韩家焚楮谢。”戴闻之骇,挈子叩祷于神,第三日,子无病猝死。吴面上掌痕四阅月而青褪。
作为父亲的戴七作孽,戴七之子七龄童却代其父受冥司严惩,以致丢了性命。以今人的眼光观之,这个故事实在是荒唐之甚。然而,类似的故事在《子不语》中并非孤例①。譬如《子不语》续卷七中的《杀一姑而四人偿命》:周某兄弟二人娶妻后各有一子。周某父母殁后,遗一小妹。两个哥哥都不喜欢她,两个嫂子尤其虐待她。小妹已许配给一教书先生的儿子,只因教书先生家境贫寒,无力迎娶。于是,教书先生的儿子只得到周家做招女婿。两个嫂子常暗中商量:养活一个小姑已经够累人了,现又多了一个吃白食的,总要设法赶他们走才好。不久,周某兄弟去城外佛寺读书,妹夫也恰好回家探望双亲。见此情景,两个嫂子也借故回了娘家,临走前把柴米食物都锁了起来。次日,小姑入厨房,无以为饮,忍饿两日,实在没脸向邻居求援,左思右想,苦无良策,最终只能以自缢了事。听说小姑已死,两个嫂子皆从娘家归,并召回了她们的丈夫。她们对丈夫谎称小姑得病而死,于是周家将其草草殡殓,并寄书至其夫家,让他们派人来将棺柩拿回去。正当这两个恶嫂自以为得逞之时,周家开始频繁地出现冤鬼啾啾的哭声。数月后,大嫂母子俱暴病而亡。不久,二嫂母子亦病。二嫂恐惧极了,嘱丈夫日夜守之。尽管如此,某晚二更天时,一赤发蓝面、手持钢叉的鬼卒还是当着二哥的面攫取了其子的性命。次日黎明,二嫂亦殁②。
这两则笔记小说的共同特征是“父债子偿”,即父辈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了他人的生命,父辈与儿辈或仅仅儿辈反被超自然力量剥夺了生命。夺人财物,还人财物;害人性命,偿人性命。这在信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之原始复仇观念和朴素正义观念的中国古代社会往往被视为天理或天道,我们无法对此苛责。但施害者与受罚者,也即恶行的主体与恶报的客体总该相吻合才对呀。不然,先人作孽,后代又何罪之有呢?在道教看来,先人作孽,后代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罪过,但后代会因此而遭受无罪之殃。后代何以会无辜遭殃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引入道教的承负说。
二、承负说观念与父债子偿式小说
道教的承负说肇始于《太平经》,而《太平经》则问世于东汉后期,是现存最早的道教经典,因此承负说可谓道教关于善恶报应的最古老的理论之一。《太平经》卷三十九《解师策书诀》云: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令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③
《太平经》卷十八至卷三十四《解承负诀》云:
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④
《太平经》认为,先人的善恶行为会给其后代(后生人)带来相应的祸福报应;任何一个人都要承受五代先人的善恶行为所带来的祸福报应,此为“承”,任何一个人的善恶行为都将福及或祸及五代子孙,此为“负”⑤。“承”与“负”一体两面:“承”是着眼于后代与先人的关系而言的,而“负”则是着眼于先人与后代的关系而言的。正因为有“承”与“负”,所以才会有“行善反得恶(报)”和“行恶反得善(报)”这种反常现象的发生。当然,《太平经》并未否定“后生人”行善去恶的价值。“后生人”亦有其“后生人”,他的善恶行为同样会给其后代带来相应的祸福报应。不仅如此,“后生人”的善恶行为也会给自己带来相应的祸福报应,从而抵消其先人的余殃和余福。若“后生人”有极大的善行,那么即使其先人有恶行,也不能殃及他;反之,若他有极大的恶行,那么即使其先人有善行,也不能福及他。
《太平经》所建构起来的承负说在道教思想发展史上造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后世很多道教经典皆表达了承负观念。汉(或魏晋)《赤松子中诫经》记赤松子言曰:“此乃祖宗之罪,遗殃及后。自古英贤设教,留在《仙经》,皆劝人为善,知其诸恶,始乃万古传芳,子孙有福。”“积恶之殃满盈,祸及数世矣。此为司命夺筭,星落身亡,鬼拷丰都,殃流后世。”⑥宋《太上感应篇》记太上老君言曰:“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⑦宋(或明)《文昌帝君阴骘文》记文昌帝君言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⑧清《关圣帝君觉世宝训》记关圣帝君言曰:“近报在身,远报子孙,神明鉴察,毫发不紊,善恶两途,福祸攸分,行善福报,作恶祸临。”⑨在从东汉末至清这一千五百多年时间里,道教一直大力宣称,先人作恶,后代就会遭受无罪之殃。从此观之,《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中的戴七之子和《杀一姑而四人偿命》中的周氏兄弟之子被鬼神剥夺生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道教的承负观念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小说创作,从而使“父债子偿”式的超自然情节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屡见不鲜。如清褚人获(1635-?)《坚瓠集》中的《金锭》:洞庭东山有金驼子,他背曲如弓,人称金锭。因相信其能给他人带来好运,所以每逢他人家里有喜事,必邀请之。金锭每至他人家里,主人必奉上金钱,馈赠酒食。一来二去,金锭渐渐富足起来,有良田二十余亩。金锭某同乡欲谋其良田,便暗中陷害金锭,使他倾其囊,卖其田。金锭遂贫,也无人再邀请他,而某同乡竟如愿得其良田。事后金锭获知真相,某晚怀利刃于道旁侍某同乡夜饮归,忽转念一想,他昧心,我又何必作恶,于是掷刀于河。返家途中金锭不小心触桥柱而跌倒在地,这一跌竟使金锭从此挺直腰背。也就在金锭掷刀之时,某同乡七龄之子为家中屏风绊倒,遂成背曲难伸的驼子,翌年竟不治而亡。作者褚人获以短短六字作结:“报施不爽如此。”如果借用《太平经》中的话来说,那便是“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过于邻里,后生其子孙反为邻里所害,是即明承负之责也”⑩。有着类似超自然恶报情节的还有南北朝颜之推《冤魂志》中的《徐铁臼》、宋郭彖《睽车志》中的《章思文》、明《轮回醒世》中的《孽子历四难而奋迹》、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夙世冤愆》和清潘纶恩《道听途说》中的《李二妈》,等等。
三、袁枚对道教等中国制度性宗教的态度
拙文《论艺术正义——以社会正义、宗教正义和艺术正义为语境的研究》指出,艺术正义和宗教正义对社会正义之不足的补偿是有选择的补偿。这种选择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在善有善报与恶有恶报之间倾向于选择恶有恶报。当艺术正义不得不借助宗教正义而彰显时,这种倾向性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以为,这同样可以从安全需要这一人的类本能中去寻找原因。在社会生活中,比较容易破坏人们安全感的是有人行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对社会正义不足之补偿的这两种正义必然会把重点置于恶有恶报之上。惟其如此,才能在较大程度上给人以安全感”。宗教典籍或艺术作品中形而下的“父债子偿”式的超自然恶报情节能否彰显形而上的宗教正义或极端形式艺术正义(借助宗教正义而实现的艺术正义),这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我们暂且搁置不论。就形而下这一层面而言,《太平经》关于承负思想的话语显然在善有善报与恶有恶报之间选择了恶有恶报。《太平经》在阐述承负说时既认为先人作恶后代遭殃,又认为先人行善后代获福。然而,前者无疑是它着力强调的重中之重,它阐述前者的篇幅远甚于阐述后者的篇幅。同样,《子不语》显然也在善有善报与恶有恶报之间选择了恶有恶报。这一笔记小说集中与道教承负观念相一致的超自然情节几乎都是先人作恶后代遭殃。
如前所述,在道教看来,先人作孽,后代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罪过。上引“令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一语充分表达了这一观念。尽管后代无罪,但后代会因与先人的血缘关系而遭受无罪之殃。仅仅因为与先人的血缘关系就应该遭受无罪之殃,道教的这种观念显然有其荒谬之处。上引《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和《杀一姑而四人偿命》等小说是否可以表明袁枚受到过道教颇为荒谬的承负说的影响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笔者之所以给出如是答案,是因为以下两点。
第一,袁枚编撰这些小说,未必意味着他认同先人作恶后代遭殃这样的宗教观念。袁枚《子不语》序云:
余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餍八珍矣,而不广尝夫蚳醢、葵菹则脾困;嗜音者备《咸》、《韶》矣,而不旁及于《侏》、《僸佅》则耳狭。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
而袁枚《答杨笠湖》则云:
《子不语》一书,皆莫须有之事,游戏谰言,何足为典要;故不录作者姓名。
王英志《袁枚评传》在援引以上两段时解读道:“袁枚认为在寡欢乏味的生活中,怪、力、乱、神之事可以广博见闻,驱庸起惰,增添刺激的乐趣。……此外,袁枚又于原刻本上自题‘随园戏编’四字。综上所述,也可见《子不语》的编著:一是于写作‘文史’正业之外的‘自娱’‘游戏’笔墨,并不当作‘正经正史’来看待;二是所记内容很多是采集而来的,并非是凭空结撰的,当然它们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的,这也是清代文言笔记小说的共性;三是所记之事特别是鬼神之事,多为‘莫须有之事’,作者并不全信,所以说不为之‘所惑’,只是‘记而存之’。当然其间时或有作者的某种意旨。”王英志先生的这番解读深中肯綮,笔者尤其赞赏“其间时或有作者的某种意旨”这一判断。仅仅读《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和《杀一姑而四人偿命》等,我们可以说,袁枚有可能认同先人作恶后代必然遭殃这样的宗教观念。然而,如果把这两则小说与《子不语》卷七中的《李倬》等联系起来看,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第二,退一万步说,即使袁枚认同先人作恶后代遭殃这样的宗教观念,也未必是受道教的承负说影响所致。袁枚的思想基础——如他自己所言——是“三分周(公)孔(子)二分庄(子)”。他并不信服佛教和道教这中国两大制度性宗教的学说,他于《答项金门》中说:
仆生性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学。自觉穷年累月,无一日敢废书不观,尚且正经、正史不能参究,何暇攻乎异端,以费精神縻岁月哉?既不暇观,亦不暇辟,庄子所谓虚而与之委蛇足矣。
这段话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袁枚对释道的基本态度:佛教学说、道教学说和理学皆异端也,因此既没空(即没必要)去学习这些学说,也没空(即没必要)去驳斥这些学说,只要“虚而与之委蛇”就足够了。袁枚对释道的基本态度还可见于他另一些文字作品,如《二月八日记梦》一诗的小序:
夜梦老僧入门长揖,贺余二十二将还仙位。问是何年月日,曰本月也。少顷又一道士如僧所云。余生平不喜二氏之说,而妖梦忽至,验固佳,不验亦得。
王英志《袁枚评传》说:袁枚“对道士甚憎恶,视之为‘妖道’。《子不语》记载不少揭露道士以妖术害人的把戏”,“袁枚笔下的道士大多是害人、骗人、贪财贪色的恶棍”,“袁枚对僧侣、道士的抨击,其实就是佛教、道教的否定”。以其对释道的态度来推断,我们可以说,袁枚可能都没有看过《太平经》等,更遑论受其影响。
如果假定袁枚认同先人作恶后代遭殃这样的宗教观念,而又不是受道教的承负说影响所致,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有可能因受到当时中国社会法律领域中株连观念的影响而生发了相应的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观念。袁枚是一个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的观念极其淡薄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没有分散性宗教的观念。民间信仰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分散性宗教。“道教最与民间信仰接近……”。道教的承负说集中地表达了先人作恶后代遭殃的宗教观念,然民间信仰却没有一种成熟的学说来表达如是观念(这也正是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本质区别之一)。没有一种成熟的学说,并不意味着这种观念不存在。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也偶尔能听到“断子绝孙”之类的咒语。这类咒语告诉我们,民间信仰关于先人作恶后代遭殃的观念至今余音不绝。实际上,道教和民间信仰关于先人作恶后代遭殃的观念都是从株连观念中衍生而来的。一个人只要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株连观念,且非彻底的无神论者,就有可能萌发先人作恶后代遭殃的宗教观念,无数人具有这样的宗教观念,就会汇聚成民间信仰的观念。
四、承负说观念与法律领域中的株连观念
先人作恶后代遭殃,其实质也就是株连无辜。宗教的某一种观念往往与产生这一宗教的社会之正相关观念有着源流关系。道教的承负观念无非是当时中国社会法律领域中株连观念在宗教领域中的变种,是株连观念神圣化的产物。何谓株连?《释名·释丧制》曰:“罪及余人曰诛。诛,株也,如株木根,枝叶尽落。”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株连早在商朝末年就出现了。据《尚书·泰誓》,周武王就曾指责商纣王“敢行暴虐,罪人以族”。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族刑及其他形式的连坐肇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时期。《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的成文法典,制定者为战国时期魏国的改革家李悝(公元前455-公元前395)。《法经》云:“越城者,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则夷其乡及族。”“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新唐书·吉温传》曰:“于是慎矜兄弟皆赐死,株连数十族。”类似这样的记载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可谓屡见不鲜。族刑等连坐制度一直持续至清末因沈家本(1840-1913)等奏请废除“缘坐”(即连坐)等酷刑而寿终正寝。
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记小说也是史书,不过是“稗官野史”或“正史之余”而已。笔记小说中不乏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株连案的记载。《子不语》续卷六中有《赵友谅宫刑一案》。该小说讲述的便是一桩株连案的本末:
赵成者,陕西山阳城中人。素无赖,老而益恶,奸其子妇,妇不从,持刀相逼,妇不得已从之,而心终不愿,私与其子友谅谋迁远处以避之。其戚牛廷辉住某村,离城三十里,遂往其村,对山筑舍而居,彼此便相叫应。居月余,赵成得信追踪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辉。牛设馔款待,乡邻毕集,席间,客严七与牛至好,问牛近况,牛告以生意不好,卖两驴得银三十两,以十金买米修屋,家中仅存二十金等语。赵成欲通其媳,厌友谅在傍,碍难下手,知邻人有孙四者,凶恶异常,且有膂力,一村人所畏也。乃往与谋杀牛廷辉,分其所剩金。孙四初不允,赵成曰:“我媳妇甚美,汝能助我杀牛廷辉,嫁祸于友谅,友谅抵罪则我即以媳妇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孙四心动,竟慨然以杀牛为己任。是夜与赵成持刀直入牛家,友谅见局势不好,逃入山洞中。孙、赵两人竟将牛氏一家夫妇子女,全行杀尽,而往报官,云是友谅所杀。县官路学宏急遣役往拿,见友谅匿山洞中,形迹可疑,遂加刑讯。友谅不忍证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痛哭诬服。然杀牛家之刀,原是孙四家物,赵家所无也。屡供藏刀之处,屡搜不得。路公以凶器未得,终非信谳,遂叠审拖延,连累席间饮酒乡邻十余人,家产为空。一日捕役方带赵成覆讯,成自喜案结矣,策蹇高歌。其媳见而骂曰:“俗云虎毒不食儿,翁自己杀人,嫁祸于儿子,拖累乡邻,犹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当,天地鬼神肯饶翁否?”赵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闻于官。官始穷问。赵成初犹不服,烧毒烟熏其鼻方输实情。按律,杀死一家五人者,亦须一家五人抵偿。按察使秦公与抚台某伤其子之孝,狱奏时为加夹片,序其情节,奉上谕:赵友谅情似可悯,然赵成凶恶已极,此等人岂可使之有后?赵成着凌迟处死,其子友谅可加宫刑,百日满后,充发黑龙江。
自己的老婆为恶父奸污,自己为恶父诬陷,而赵友谅始终恪守亲亲相隐的原则,但最终却遭受了皇上所钦定的“宫刑”和“充发黑龙江”这两项刑罚。这样的判决要说多荒唐就有多荒唐,然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
西方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株连,譬如古罗马时期。这说明株连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性。大凡低级形态的社会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这主要因为低级形态的社会治理能力弱,因而不得不通过要挟来威摄潜在的犯罪者和违法者。株连的实质也就是要挟,它把潜在的犯罪违法者的亲属作为“人质”,把人类原始的亲属之爱作为压制潜在的犯罪违法者的筹码,从而最大程度地增加犯罪违法成本,塑造国家机器的威严形象,最后力图达到减少犯罪违法现象的目的。战国时期商鞅的一段话颇能显示这样的治理思路:“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然而,诡异的是,中国的株连现象有着非西方社会可比的三大特征:第一,充分制度化。自《法经》问世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刑律中大多有“族诛”、“缘坐”(即“连坐”)和“禁锢”(即“籍门”)等内容。第二,持续时间长。如前所述,株连现象一直从商代延续至清末。第三,波及区域大。秦朝以降,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央集权国家,一旦国家刑律允许株连,那便是全国一体推行。反观西方,我们可以发现,株连现象基本上随着古罗马帝国的陨落而消失,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制度支持,西方后世的株连总体上呈现出偶发性特征。面对中西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水平,可能还无法解释它们的成因。要合理地解释如此差异,尤其要合理地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中株连“充分制度化”和“持续时间长”这两大特征,我们还需要考察古代中国独特的地缘文化、古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古代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独特社会制度“理性化”的儒家伦理,以及由上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儒家伦理合力而成的古代中国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等。
五、《子不语》中的反父债子偿式小说
袁枚在《子不语》中一再地描述了先人作孽后代遭殃的情节,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说,袁枚是有可能认同承负观念的。如果真这样认为,我们实在是误解了他。如前所引,在《赵友谅宫刑一案》中,赵友谅的老婆骂其公公曰:“俗云虎毒不食儿,翁自己杀人,嫁祸于儿子,拖累乡邻,犹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当,天地鬼神肯饶翁否?”“一人作事一人当”的实质也就是“罪责自负”。而“罪责自负”既与中国古代社会领域(或法律领域)中的“株连”针锋相对,也与中国古代宗教领域中的“承负”针锋相对。“株连”和“承负”的要害恰恰是分摊或淡化了犯罪违法主体的责任,恰恰是一人作事非一人当或者一人作事由别人当。
《子不语》卷七中有《李倬》。福建书生李倬于赴京赶考途中遇上了河南书生王经。王经自称资费不足,请求李倬带他同船进京。尽管在赴京途中王经的行为有些怪异,但总体上李倬还是与他很谈得来。已至京城外,王经长跪请求:“公毋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阳生员,有才学,当拔贡,为督学某受赃黜落,愤激而亡。今将报仇于京师,非公不能带往。入京城时,恐城门神阻我,需公低声三呼我名,方能入。”王经所说的督学,正是李倬的座师,因而李倬拒绝了其请求。王经说,你偏袒你的老师,拒绝了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要设法复仇的,而且连你也一起收拾。李倬无计可施,只能照他的话去做了。安排了住处等之后,李倬即去拜访其座师。进了座师的家门,座师一家正哭成一团,座师对李倬说,“老夫有爱子,生十九年矣,聪明美貌,为吾宗之秀。前夜忽得疯疾,疾尤奇,持刀不杀他人,专杀老夫。医者莫名其病,奈何?”李倬非常清楚其中的缘由,便主动请求说,“待门生入视郎君。”话还没说完,只听“公子”在内室笑着说,“吾恩人至矣,吾当谢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倬进了内室,握着“公子”的手,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座师一家十分不解,也更加害怕,于是把李倬叫出了内室,李倬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于是全家人都跪在李倬面前,求他说情。李倬重入内室,再次劝说“公子”。最终“公子”同意以毁坏一只玉瓶和几件貂裘了事。摔碎了玉瓶和焚烧了貂裘之后,“公子”大笑着说,“吾无恨矣!为汝赦老奴。”言毕,拱手作揖,作辞行状。而公子的病也立即就好了。
李倬究竟说了怎样的一番话才让“公子”(即王经鬼魂)放弃了索取李倬座师父子两人生命的念头呢?李倬是这样说的:“君过矣!君以被黜之故,气忿身死。毕竟非吾师杀君也。今若杀其郎君,绝其血食,殊非以直报怨之道。”这番话有着两层涵义,它们都无意间涉及了现代法律正义的两大原则。前一层涵义讲的是“罪罚相当”(罪刑相适应),李倬的言下之意是,我的座师固然有罪,然罪不至于受如此惩罚,量刑过重是不正当的。后一层涵义讲的是“罪责自负”,李倬的言下之意是,我的座师固然有罪,然其儿子却是无辜的,报复其儿子是不正当的。值得注意的是“公子”(即王经鬼魂)听了这番话后的反应:“其子语塞,瞋目曰:‘公语诚是,然汝师当日得赃三千,岂能安享?吾败之而去足矣。’”“公语诚是”这四个字说明“公子”(即王经鬼魂)是信服李倬的说法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经鬼魂以后的遭遇。“李(倬)是年登第,行至德州,见王君复至,则前驱巍峨,冠带尊严,曰:‘上帝以我报仇甚直,命我为德州城隍。尚有求于吾子者,德州城隍为妖所凭,篡位血食垂二十年。我到任时,彼必抗拒,吾已选神兵三千,与妖决战。公今夜闻刀剑声,切勿谛视,恐有所伤。邪不胜正,彼自败去。但非公作一碑记晓谕居民,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公将来爵禄,亦自非凡,与公诀矣。’言毕拜谢,垂泪而去。”上帝因为王经鬼魂能够公正地复仇,故任命他为德州城隍。如果按照袁枚的这一说法,那么,承负观念未必出自道教所谓上帝的旨意。
如同《李倬》,《子不语》中的不少小说皆表达了“罪责自负”的思想。如卷十中的《猴怪》和卷二中的《算命先生鬼》等。《猴怪》:“(温)元帅怒曰:‘……汝又不仇吴而仇其妻,甚为悖乱。’”《算命先生鬼》:“神曰:‘其兄触汝,而责之于妹,何畏强欺弱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则小说中的“温元帅”和“神”也都是道教的神。
六、佛教不代受观念与反父债子偿式小说
反承负的观点与印度佛教的“不代受”观念最为接近。《无量寿经》、《法句经》、《般泥洹经》、《出曜经》和《起世经》都充分表达了这种观念,如《无量寿经》曰:
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之,无谁代者。
又如《般泥洹经》曰:
相须所作好、恶,身自当之;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
另《法句经》:“行恶得恶,如种苦种。恶自受罪,善自受福。习善得善,亦如种甜,自利利人,益而不费。”《出曜经》:“作恶自受其殃,无能代者。”《涅盘经》:“无有自作,他人受累。”《起世经》:“此之苦报恶业果者,非汝母作、非汝父作、非汝兄弟作、非汝姐妹作、非国王作、非诸天作,亦非往昔先人所作,是汝自身作此恶业,今还聚集受此报也。”这些佛经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印度佛教奉行的是报应止及行恶者一身的原则。
中国宗教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于信仰体系多元,更表现于三教合流。正因为三教合流,儒释道甚至民间信仰的某些元素难免会在中国古代小说等故事性艺术作品中搅在一起。譬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其地狱的概念很快与道教或民间信仰的冥府(地府、阴府)相混同。明《轮回醒世》中有《假他子还魂》,这则小说开篇即写道:“登州常志毅,每造罪孽,不由仁义,妻许氏劝之不从。生儿四岁,志毅一旦暴卒,阴司摄其魂,历数其罪,痛加楚挞,且谕曰:‘追汝命,不足尽汝罪,还当断汝后。’志毅泪诉曰:‘自作自受,罪亦何辞,惟不累及妻孥,使寡妻孤子得保令终可也。’阎罗曰:‘若使恶人有后,何以见阴司报应?’遂不容分辩,竟驱入虎头门。”这里的“阎罗”即“阎罗王”、“阎魔王”或“阎王”。众所周知,他是佛教传说中管理地狱的魔王。然他表达的观念却是地道的道教承负观念或者某些中国化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而非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这既要拜佛教中国化所赐,更要拜三教合流所赐。
在善恶报应观念方面的三教合流早在东晋已初露端倪,厥功至伟的是东晋高僧慧远(334-416)及其《三报论》。黄启江在《佛教因果论的中国化》中指出:“慧远在庐山传净土教远在法藏倡法界缘起说之前,不知四种缘起之观念,所以他虽然谈三报,却只环绕着‘积善之家’和‘积不善之家’的解释,欲用三报说将余庆或余殃观念合理化。可是他没有厘清佛教业报的特性是‘自业自得’或‘自作自受’而不会发生转嫁到家人身上,而使其获祥或获殃之现象。他虽然解释了‘积善之无庆,积恶之无殃’的原因,但却根据一个非佛教的命题来说明报应之不爽,等于是在法藏的佛教因果论之外,又开辟了一个不同的中国化因果论。”“值得注意的是,环绕在‘积善之家’一议题的因果论与慧远所说的因果论相结合,而形成了中国民间所流行的因果论。这个因果论一方面着重当下即验的‘现报’或‘速报’,一方面又强调报应来自于天,而垂及家庭、后世。它以传统中国的天道观与家庭观为基础,而谈‘生报’或‘后报’;奉不可知的天为赏善罚恶的主宰,推造业者应受之业报至其家庭之成员,而忽略了个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而受报的‘自业自得’的道理。这种中国化的佛教因果观,与法藏一支的佛教因果论既不相符合也不相统属,但它却广为民间所接受,而变成民间长期所信仰的佛教因果论。”
然而,慧远的同时代人、东晋居士郗超(336-377)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失时机地捍卫了原教旨意义上的因果报应论的纯洁性。他在《奉法要》中不仅对社会领域(法律领域)中的“株连”现象进行了批判,而且还不点名地对儒道那种传统的报应观念进行了批判,从而重申了印度佛教的“不代受”命题。他认为,先人行恶后代遭殃,先人行善后代获福之类的观念一不符合历史事实,二不符合佛教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然齐、楚享遗嗣于累叶,颜、冉靡显报于后昆,既已著之于事验,不俟推理而后明也”。“哲王御世,犹无淫滥,况乎自然玄应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错受,善恶无彰,其诬理也,固亦深矣。……是以《泥洹经》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应理。”
不过,如同不信奉道教,袁枚同样不信奉佛教,前面不少引文皆已表明了这一点。此外,袁枚还说过,“仆平生不喜佛法”,“逢僧我必揖,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揖僧僧现在”,“见佛吾无佞”,“然余性不饮,又不佞佛,二事与太傅异矣”,“诵经,念忏,做七,营斋,我生平所最厌者,汝可告诸姊妹:来祭我一场,我必享受,哭我一场,我必悲感。倘和尚到门,木鱼一响,我之魂灵必掩耳而逃矣,于汝安乎”?因此,《李倬》所折射出的观念只是与佛教的“不代受”观念有暗合之处罢了,如果仅仅因为《李倬》而判定袁枚受到过佛教“不代受”观念的影响,那无疑是过度阐释了。
七、艺术正义视域中的(反)父债子偿式小说
拙文《论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以中国古代戏曲为主要样本的研究》指出,艺术正义和宗教正义是“道”,而善福恶殃情节是“器”。艺术正义和宗教正义正是由善福恶殃情节彰显出来的。艺术正义又可分为一般形式的艺术正义和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如果说前者是由自然力量(人的力量等)而造成的善福恶殃情节彰显出来的,那么后者则是由超自然力量(鬼和神的力量等)而造成的善福恶殃情节彰显出来的,是借助宗教正义而实现的艺术正义。必须补充的是,并非所有的善福恶殃情节都能彰显艺术正义和宗教正义,因为并非所有这类情节都体现了正义的要素。落实在本文的话题上,我们应该说,并非所有的由超自然力量而造成的善福恶殃情节都能彰显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因为并非所有这类情节都体现了正义的要素。
如前所述,在《子不语》中,《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和《杀一姑而四人偿命》等有着与道教承负观念相一致的“父债子偿”式的超自然恶报情节,而《李倬》等则有着与佛教不代受观念相一致的对“父债子偿”式超自然恶报情节的反拨。也只有后者才能真正地彰显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父债子偿”式的超自然恶报情节之所以不能彰显极端形式的艺术正义,是因为它同时违背了“得所当得”和“一视同仁”这两大原则。
“得所当得”也就意味着合理分配权利和义务(责任)。《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按照现代正义观念,人的重要权利尤其是其中的生命权是天赋的,不可让与的。这里的“不可让与的”原文为unalienable,unalienable意即“不可分割的”、“不可让与的”和“不可剥夺的”。借助这个词强烈的决绝意味,《独立宣言》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正当而又充分的理由,人包括生命权在内的重要权利是绝对不可剥夺的。《独立宣言》是美国的,但这句话表明的却是天下之公理。构成“正当而又充分的理由”之最起码的条件是依善法判定被剥夺权利之人已经严重或不严重地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由此可见,仅仅因为与父亲(或父辈)有着血缘关系,就剥夺儿子(或儿辈)的生命权,这理由既不正当,也不充分。根据“一视同仁”的原则,如果仅仅因为血缘关系而认可“父债子偿”,那我们也应该认可“子债父偿”、“兄债弟(妹)偿”、“弟债兄(姐)偿”,甚至也应该认可某人犯了罪而由血缘关系更远的亲属来赎罪。仅有“父债子偿”,而无“子债父偿”等,岂不有违“一视同仁”的原则。反过来说,若真认可了“子债父偿”等,天下哪里还有犯罪主体的责任,天下哪里还有该受恶报的客体与不该受恶报的客体之间的界限,这岂不更有违“得所当得”的原则。
从根本上说,“一人作事一人当”是自然法的准则,即镌刻在大多数人心中的神圣的法律条文,更是社会正义和宗教正义的准则。而道教的承负说则全然违背了这样的准则。笔者借助承负说的视角来研读《子不语》中的小说,看到的是清代民间社会中艺术思想、宗教思想乃至法律思想的复杂性。摒弃其中落后的思想,发扬其中先进的思想,这对于今天正致力于建设一个正义社会的人们不无裨益。
注:
① 疑似有“父债子偿”情节的另有《子不语》卷十中的《卖浆者儿》。除“父债子偿”外,还有“夫债妻偿”,如《子不语》卷十三中的《鬼势利》。
② 清金捧阊《客窗偶笔》(《客窗笔记》)中有《一命四偿》,其故事和文字均与此则小说大同小异。《子不语》今存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随园刻本,《续子不语》最早版本为嘉庆初年(1796)随园刻本。《客窗偶笔》初次刊印于嘉庆二年(1797),那一年也即袁枚卒年。据此推算,金捧阊做“文抄公”的可能性远大于袁枚。
③④⑩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0、22、54页。
⑤ 《太平经》:“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此话意即,前“承”五代,后“负”五代;前后十代,才算完成了一个承负周期。
⑥⑦⑧⑨ 唐大潮等注释《劝善书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15、55、66、151页。
责任编辑:倪惠颖
上海戏剧学院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