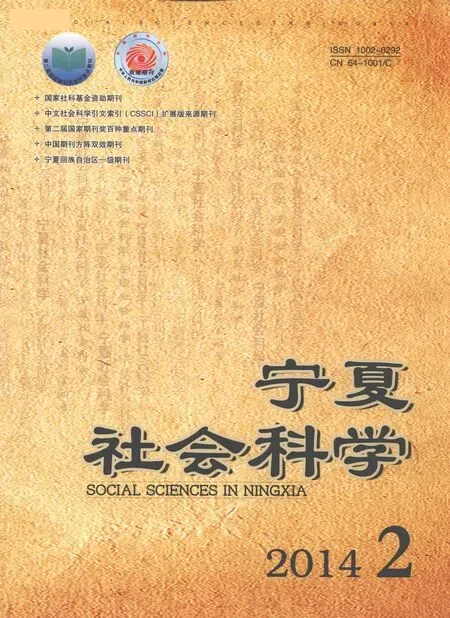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
刘 波,王义汉,谢镇荣,尉建文
(1.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081;2.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一、引 言
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其间不仅需要大量物质资本的投入,还需要人们动员各种类型的资本。在灾后恢复的过程中,人们大致可以依赖三种资本,即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经济资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和灾前的经济实力对灾后恢复的影响;人力资本主要强调教育和社会技能对灾后经济状况的改善作用;社会资本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灾后重建的意义。在不同的灾情、不同的社会特征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三种资本在灾后恢复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面对汶川灾后恢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我们有必要研究中国社会在面对大灾难时,人们是如何利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恢复重建的。这对我们深入了解灾后恢复过程,积累灾难应对和恢复的经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经济资本与灾后恢复
灾害过后,社会经济遭受到了重创,经济生活的恢复是灾后重建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关系到灾民们的生存问题。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地位同时有“存量”和“流量”两个层面的含义,但在灾后恢复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更多的“流量”含义。[1]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对不同经济状况的家庭都会带来破坏,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在地震中或许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但研究发现,以前经济状况越好的家庭,越有条件和资源来消除地震影响,能够更快地从地震的损害中恢复过来。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更可能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到灾前水平。[2]同时,震前社会经济地位越好的家庭,越能够为住房重建得到更多资金,兴建更好的住房。而那些震前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家庭,越需要依靠政府补贴和借贷来完成住房重建。[3]
(二)人力资本与灾后恢复
人力资本是对物质资本而言的一种资本形式,主要是指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4],学界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对个体经济地位和生活的影响方面。我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在灾后恢复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越丰富,地震影响则会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在地震应急方面越可能采取正确的措施,在地震后越有可能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地震的损失。[2]另一方面,更好的人力资本特征能更有效地发出“偿还能力”信号,更可能从金融市场上获得灾后恢复所需的金融资源。[1]学者赵延东发现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对灾后经济状况的改善具有显著影响。[5]与之相对照,贫困家庭(个体)可能由于缺乏技能、身体残疾、年龄偏大等原因,在整个灾后恢复过程中困难重重。[1]
(三)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
近年来,社会资本的概念被引入到灾害学的研究领域,为灾害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地震后,社会资本对于传递信息、提供救援、获取资金和灾后恢复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受灾者灾前社会网络的嵌入密度较高且其男性成员较多、年轻人占比例较高的,则在灾后恢复期间获得非正式社会支持也越多。[6]研究表明,其中社会网络关系在灾后搜救行动中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资本,勒恰特在研究1980年的意大利地震时发现,97%的被困受伤者是靠周边其他受灾者徒手或用简单工具营救出来的。[7]社会网络对家庭重建资金的获得主要表现在网络资源量越丰富的家庭越可能为住房重建筹集到更多的资金。[8]学者们指出,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社会资本在灾害中受到损失更小,因而是受灾群众灾后重建中最可依赖的资本。[9]
综上所述,三种不同的资本在灾后恢复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但究竟哪种资本意义更为显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政府更合理地分配救灾和重建物资,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的研究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基于2009年对灾区17个村落的问卷调查,通过对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灾后恢复中作用的对比分析,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和西南交大等高校合作展开的灾后重建研究项目。2009年,研究组集中调查了四川省的极重灾区,包括绵阳市和德阳市等地区的17个村镇,以家庭户为单位,抽取558个家庭户样本,采用入户调查的形式,问卷与访谈相结合,调查内容主要是家庭的基本信息、家庭的经济状况、住房信息、社会支持情况和社会态度五个方面等。
(二)主要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灾后生活恢复情况,设计的问题是“你家的生活水平什么时候能恢复到震前的水平?”选项是“现在就是震前水平=1”、“半年之内=2”、“三年之内=3”、“五年之内=4”、“更长时间=5”,被访者根据自己家庭的重建情况作出回答。
自变量是分为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类。测量经济资本的变量有“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家庭是否领取贫困救济金”、“是否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测量人力资本的变量有“家庭成员在外务工的人数”、“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家庭获得职业证书的人数”。社会资本的测量是从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结构入手,两个变量分别是“春节拜年网的人数”、“网络成员中非农职业所占的比例”。另外,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了两个控制变量,即“家庭的规模”和“家庭中党员的数量”。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中,因变量生活恢复情况是定序变量,因而我们采用Ologit模型,方程表达式为:

其中,Yi表示生活恢复情况,Xi表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控制变量,εi表示误差项。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将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其次纳入测量经济资本的变量,再次是测量人力资本的变量,最后纳入测量社会资本的变量,这样更直观地比较三种类型的资本对生活恢复情况的影响。
四、分析结果

表1 生活恢复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我们检验了三种类型的资本对灾后生活恢复情况的影响 (见表1)。模型1是基准模型,我们将控制变量纳入其中,检验其对生活恢复的影响。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经济资本变量纳入其中,结果显示经济资本对生活恢复情况没有显著影响。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把人力资本变量纳入其中,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的变量对于生活恢复情况的影响依然不显著,但与前者相比,模型3的伪R2增加了0.01且F值显著,说明模型3的解释力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善,人力资本对生活恢复有一定影响。在模型4中,我们进一步纳入社会资本的变量,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对灾后生活恢复情况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对灾后生活恢复情况有显著的正影响,其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灾后生活的恢复,但是非农职业占比却不显著,这可能与我们测量网络结构时选择的职业有关。在农村地区,家户社会网络中非农职业的比例大多偏低,从而影响分析结果,但模型的伪R2相比于模型3增加了0.003,且F值显著。这说明纳入社会资本的变量对于模型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善,社会资本的变量对灾后生活恢复效果是明显的。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虽然对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善,但由于其变量不显著,总体而言二者对生活恢复情况影响不是很大。相反,社会资本的变量对生活恢复情况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灾区群众生活恢复的速度越快。由此可见,相比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家庭灾后重建的作用更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在灾害发生后,家庭可以利用三种类型的资本摆脱灾害的影响,为恢复正常的生活提供条件,但三种类型资本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灾后重建的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的影响显著,从而论证了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灾后正式援助制度处于转型期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正式制度不足的作用。
虽然本研究看到了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有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灾后重建的研究还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汶川地震震级高、破坏性强,再加上本研究调查的都是极重灾区,在如此特殊的情况之下,社会资本对于灾后恢复的作用,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持谨慎的态度。第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微观的社会资本,它作为一种非制度因素,本身的局限性——虽然家庭认识的人的职业与农业相关的占比越大,可能获得的援助越多,但这些援助更多的是非正式的、暂时的、薄弱的支持,这决定了其对灾后恢复的影响不大且作用不稳定。第三,本研究未考虑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灾后恢复重建的影响,显然宏观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对灾后重建的影响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1]卢阳旭.突生与连续:西方灾后恢复的社会学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1(2):38-42.
[2]陈升,孟庆国.汶川地震对受灾居民的影响研究——来自四川省5个地震重灾区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09(4):91-99.
[3]卢阳旭,赵延东.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资金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2(6):93-101.
[4]江涛.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其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6):84-87.
[5]赵延东.自然灾害中的社会资本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07(4):53-60.
[6]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J].社会学研究,2007(5):164-187.
[7]李智超,罗家德.透过社会网观点看本土管理理论[J].管理学报,2011,8(12).
[8]Lechat M.Corporal Damage as Related to Building Structure and Design[M].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Catholic University.Belgium:Lovain.1989.
[9]Dynes,R.,2005,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s the Primary Basis for Resilience ,University of Delaware[J],Disaster Research Center,Preliminary Paper No.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