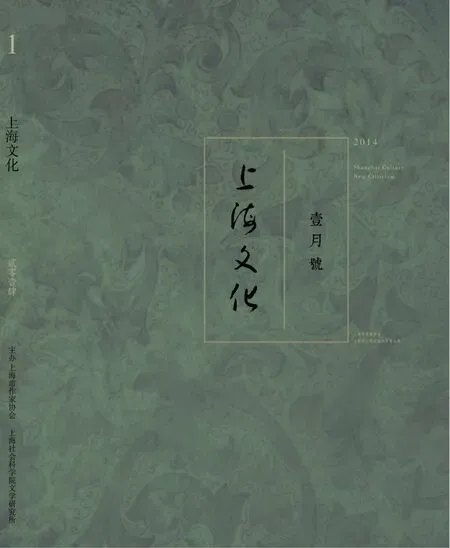艺术品*
珍妮特·温特森洪颐译
艺术品
珍妮特·温特森洪颐译
它的含义游离于任何已有的理论,它独自述说着自我
阿姆斯特丹。这里适逢雪花纷飞的圣诞,河水也因严寒静止流淌。
我像一个浪荡子,在雪地中恣意孤独地漫游。然后,我看见了一幅画,被放在一间小小的美术馆。我被召唤着为它驻足。
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吗?看看那绘画的质感还有稀薄颜料的笔触!可为什么我还在画面里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恐怖?是现代感……它的含义游离于任何已有的理论,它独自述说着自我:
一个身着蓝袍,面露愁容的女人在下水道里奋力拖拽一个巨大的月亮人面。
在这幅画前踟蹰,我该如何是好呢?就一直这样放任心潮四溢澎湃?
我最终逃也似的穿过了马路,钻进一家书店。只有被包围在这无尽而亲切的书籍里,我才能感觉自己安全了,因为在这里面有我所熟知的,认同的一切。书籍对我的影响深远,我也了解它们。我承认自己之前对视觉艺术无有兴趣,这是由于我向来完全忽视文本外其他事物所造成的。于是,我对绘画一无所知,故而也一无所得。我甚至从未对某一幅画全神贯注地看上哪怕一小时。
我又该如何是好呢?
原本我打算第二天就离开阿姆斯特丹,却最终改变了行程。我惴惴不安地入睡,又再早早起了床,为了能够排队进入国家博物馆,还有梵高博物馆参观;之后我又花费每一下午去私人画廊学习考察;到了晚上,则是阅读时间,我一本接着一本阅读,不停地阅读。我慌乱如此,只有靠掌控目前问题的大小企图得到某种平静。这种痛苦与绘画无关,后者总是让人维持着平静的状态。毫无疑问,我爱上了绘画,这种情感无法言语。我成了彻彻底底的哑巴。曾经那“这幅画什么也没对我说”变成了“我对这幅画不知该说什么”。即便如此,我表达的欲望却愈发迫切。
长时间地欣赏绘画使人犹如身临异国,远离了欲望和悲伤,而依靠零星的关键词,再加上点语言组织,就渐渐地在这片寂静中圈出一块空地。艺术,我指个别及其所有的艺术,而不仅仅指绘画,它是异国他乡,是我们自欺欺人的那个自以为熟悉的地方。只有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才会笨到同时忽略它其中奇异的风俗和它独一无二的语言。可惜,事实上无人曾惊讶于这些奇异之处,反而对其做出的不当评断颇多。每天,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都在遭受着曲解。
我们无法否认,且绝无例外,有道语言的鸿沟正架设在我们与艺术之间。我们难以理解艺术的自白。
我读过拉斯金的《现代画家》,读过佩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研究》,乔舒亚·雷诺尔德的《争论》,本纳德·比瑞森,肯尼斯·克拉克……对了!还有斯科特的《一间自由的房子!》,韦斯特尔的《十点钟的演讲》,凡赛瑞,迈克尔-莱维,威廉-莫里斯。我了解我的但丁,但我还需要一位精明而博学的向导,他应当和我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对,我需要这样能沟通的人,需要无论他是故去的先哲或仍是身处现世。我需要这样值得信任的人来一同商讨从古至今的善恶好坏。我需要这样一个在艺术的异世中游历多年的人,他会流利地使用里面奇怪的语言和方言,他能够为我介绍里面的风土人情。艺术是古怪的,惯用的那些驯服或是激化它的方法都无法成功地将其加上常识的条框。试问会有谁能在动物园见到真正的狮子?
直到最终,回到家,翻遍二手书店的书架,我找到了罗杰-弗莱。
也许绕回到布鲁姆斯布瑞集团看起来实在太过时了,但我不在乎时髦,只看重那些能够超越时间的,像是书籍,音乐和图画的永恒经典。
弗莱即是我所需要的。至少对我来说是个完美的向导。他的理论与沃尔特·佩特很接近,但更强硬。我现在总算明白过来其实我不赞同艺术(个别及其所有的艺术)与美是可以分离的,也不主张在同一社会里艺术与美或取其一。这样我就站在了哈罗德·布鲁姆观点的同一边。他提出过欣赏艺术能让人“沉迷于一种优越的时光”。艺术,个别及其所有的艺术,是自省,是欣喜,也是转变和愉悦。与哈罗德·布鲁姆观点不同的是,我相信人们可以被教会去爱他们以前不爱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让艺术发挥作用,优越的时刻是可以为所有人存在的。让艺术继续成为那些懦夫口中的谬论吧。只要我努力了解艺术,艺术也会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在我身上起到神奇的作用。
艺术,个别及其所有的艺术,是自省,是欣喜,也是转变和愉悦
我所能做的最有用的改变是我观看的方式,去学习如何欣赏一幅画。我发现自己感知的量度在逐渐扩大。艺术让人敞开心扉
我最早了解罗杰·弗莱是通过弗吉妮亚·伍尔夫撰写的《弗莱传》。同样也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频率如此频繁,但凡关于现代主义的文献都会提到他。是弗莱首先向我们引进了“后印象主义”这个词汇,连他自己也完全未预料这一举动将会在20世纪后期的英国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教友派信徒,又同时被培养成为一个科学家,而且还对绘画充满激情。20世纪的前三十年,在英国没有人能比弗莱更积极地提倡和保护新作品了。弗莱写作的核心就是激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聊的。而我呢,则需要令生活和艺术都变的愉快的方法,既不羞于表露情感,也不在意展示美丽。
我给我自己主动学习的成绩打一个八分。当我集中注意力于现代画家时,我也同样会将阅读的重点放在过去的神甫和先知上。这将拯救我于“老大师综合征”,所以我不会至于对某幅画抱有未曾觉察的尊敬或是十分失礼的自满。同时也让我能验证我的那些艺术作家朋友提出的理论与设想。我觉得这样“瞻前顾后”地查阅学习艺术史或许是最好的办法。我对绘画的了解比对文本的了解相对较少,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所能做的最有用的改变是我观看的方式,去学习如何欣赏一幅画。我发现自己感知的量度在逐渐扩大。艺术让人敞开心扉。
艺术也耗费时间。单独花上一小时观看一幅画是痛苦的。参观美术馆的过程就是鼓励以匆忙的态度对待艺术。展厅里除了画,还有精彩的演讲,诸如此类的事,都是确切的,独立的,每一个都是不容忽视的自我。最后这一切反而不能让我们好好看一下真正需要被关注的展品。我并不是指拥挤的人群,保安、射灯和绳索让我联想到神经般的表演,我指那些无关紧要的厚窗帘遮挡了众人观看作品的视线。渐渐的,美术馆也都开始习惯对外宣称他们什么时候,又花了多少钱才得到的这件作品……
价值连城!观赏者看不见帆布上的颜色,他们只能看见帆布上的钱。
这些画有名吗?当然!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花费生命里的一分钟站在它们面前。
这些画有权威性吗?旅游手册上写到它是藏品的一部分吗?如果是的,那么就会有一半的游客因为它的定义而停下观赏,而另一半因为它的定义而弃之如敝履。
作画者是谁?我们知晓他或她的私生活吗?上过电视吗?如果没有,博物馆肯定又会播放大段关于画家各种少年经历或是辛辣大胆的绯闻。
哪里是茶室/洗手间/商品店?
这些画儿都摆在哪里?
就这样走马观花地参观,无尽的从旁讲解,过度的拥挤,一个卡着另一个,堆满一个又一个的展厅,实在让人难以对作品心生喜爱。因为爱是需要时间的。你或许和我一样不能好好参观博物馆,而无法一次次不停去看,甚至花费巨额资金去购买(当你喜欢这些绘画时,你不可避免也会掏腰包去买下它们),直到自己走进图画的奇怪世界,在这些当代艺术中返璞归真,并发现到一些任何不同寻常的感悟。时间花费的值得与不值得也是可以被整体地衡量的,与其花时间坐在电视机前或是DIY商店里,还不如去看看画;与其计算到底花钱买最新卫星设备还是新电脑,不如收购珍藏一些作品呢。
我热衷于绘画作品,美术馆的糟糕环境也不像以前那样让人提不起劲了。我学会忽略周遭的一切,只把下午花费在其中一到两件的作品中去。
设想我们达成了协议,愿意坐下来,自己认认真真地花一小时欣赏一幅画。而这幅画也同样是最初的样子,没有经过包装炒作,让人不会携带哪怕一丁点的成见来看待。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什么呢?
不断增加的不适感。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只是因为事物本身而单独地,全神贯注地观察一样东西吗?日常总消逝在一片混沌中。倘若我们来到戏院或是影院,眼前的图片不停变换,台词也会同时分散注意力,故而我们不会细细看它们。对于我们熟悉的爱人,又有必要去多看他们一眼吗?这免不了成了人们婚后状态的可笑之处。所以我们也不会仔细去看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亲人。同样的,我们看待画作也是如此,不过这里我们已经同意单独花一小时来看它了。说到底,我们并不善于观察。
不断增加的分散。我是否在神游万里?想着当天的工作,想着球赛,想着晚餐吃些什么,想着性,想着一切只要不看着绘画能做的其他事。
不断增加的编造。在一段时间的白日梦后,愧疚以及责任感会强行将人的注意力转回画面上。
这是描写什么的?是风景画吗?是肖像画吗?最好的是,它是裸体吗?如果画面能够提供逃离的蛛丝马迹,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始天马行空。我会像艺术史学家们鉴定伦勃朗《夜巡》中的人物那样编造画面上主人公的故事。随着逐渐融入画作,我现在觉得更加自信了。一幅画就是自身的题材,不是吗?我的题材是抽象画。不要紧,那个粉红色会不会适合我?
不断增加的愤怒。为什么这幅画不能做点什么?为什么它总是挂在那里看着我?这幅画有什么用?画不是应该让人心情愉悦吗,可它让我很恼火啊。我为什么要尊敬它?很明显它一点也不尊敬我……
尊重我只是算得上要求艺术符合我们所见所闻的潜台词;我们对于艺术的需求就是要求它反映观众了解的现实。真正的绘画往往只是偶然才能做到这点,大多数时候,它们总是固执己见。艺术是想象,艺术却不是世俗。
当保护作用的厚窗帘被挪开时;把以前被保护着的嫉妒,权威,细枝末节都被放一边时,即使最熟悉的绘画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力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与蒙娜丽莎单独呆上一小时。
可我们可怜的艺术爱好者在他美学实验室中却不能从对艺术品臆想的层层保护中成功感知自己,他只能发现自己总对着艺术品分散精力;因无法集中注意力,他总是失败。他还没在绘画中发现任何东西,可绘画却已发现了他许多。绘画告诫他,他还需磨练。
一切并不如看起来那样无可救药。如果我能被劝说着重新做次实验(一次一次不停试下去),那么在起初发觉自己不知如何看一幅画的震惊之后,就会发现那些逐渐浮现的与众不同的事物,那时,想法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思考如何去喜爱艺术品这个层面上了。
尊重我只是算得上要求艺术符合我们所见所闻的潜台词;我们对于艺术的需求就是要求它反映观众了解的现实
真正的艺术家追随着矛盾;假艺术家却总希望(其他人)能够解决矛盾
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一个美国人。他是驯兽师,还是耶鲁的哲学家,维基·希姆。维基写过那些与美丽动物共事的人共同的经历,他们都曾面对动物深邃复杂眼睛产生过一瞬的晃神,这是种尖锐且尴尬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那些动物算计着。艺术也有深邃复杂的眼眸,而且大多是都是气势逼人的。或许,我们该让艺术装聋作哑,这样它就不再会表达我们总觉得匪夷所思的事了。如果艺术,个别及其所有的艺术,与真理相关,那么一个持否定观点的社会也一定会觉得艺术没有任何用处。
在西方,我们靠弱化或是熟悉艺术来避免它带来的痛苦。我们对过去的沉迷加重了新作品较之于精致传统艺术而展露出的原始和粗糙,同时,对过去的过分迷恋也等同于拒绝了传统与当下的密切联系。通过分裂人类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我们做出了错误的比较,错误的预期;在哀叹当今的音乐,诗歌,绘画,散文,表演艺术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创造出当下预期作品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誓旦旦说我们没有受到艺术影响的原因。事实上,相对于忙着像过去那样创造,我们似乎更倾向于不断否定当下。现今的艺术界就是这般蹒跚前行。其实,如果你喜欢塞尚,你也可以喜欢霍克尼呀,可以喜欢博伊德,或喜欢拉奥,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喜欢塞尚,就应该不只做空口承诺,拿出自己的真才实干!
我们是一群奇怪的人:我们迫使艺术家在他们活着时过得很艰苦;我们要么不给他们钱,要么就用钱毁掉他们;我们要么使用无用的赞美奉承他们,要么采用无用的诽谤伤害他们,而当他们很老了,或是走了很久,或是争议过大而无法被雪藏时,我们又开始膜拜他们,故而原本的那些狂野被驯化,原本的那些反抗变成了权威。去膜拜绘画等同于去摧毁它们。当那种熟悉感变得过于强大,历史,流行,协会,都会满满挤在参观者与绘画之间,阻塞一切。不单单绘画遭遇此种折磨,艺术家们也无一例外。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呼吁艺术家们尝试使用各种媒介去创造新的艺术。我不是指新作品就是抹杀过去;正相反,过去会被重提。它没有失去权威,只是那些被吸收的元素并不为人所熟知罢了。这是在它原有活力基础上建立的新起点新使命。正如塞尚重新演绎了莱昂纳多·达芬奇,毕加索及之后的霍克尼的作品中都能发现米开朗基罗的影子。这并不是缅怀古人,这是艺术血脉的传承。其中互相的影响并不比这之间的联系少多少。
我不想对所谓的大师做过多讨论,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或是大多数或是少部分,能与过去相连且能用自身创造出通往未来的媒介的那群人。真正的艺术家会学习过去,而非仅仅作为一名单纯的复制者或是模仿艺术家那样只满足于把最终完成的作品,即艺术品,签字封箱送往沉迷复制品的大众那样才算学习过去。真正的艺术家只单纯地把艺术品看作一种艺术的过程而喜欢艺术品。这是事物自身存在,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它诠释着它独一的挣扎,兴奋与能量。真正的艺术家追随着矛盾;假艺术家却总希望(其他人)能够解决矛盾。
如果真正的艺术家是被各个时空接连的,那么他或她能给予那种我们所苦苦追寻的联系。连接过去,一个又一个时间的片段,连接客观世界。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且无视科技的破坏。一幅画,一本书,一曲歌都能够让我联想起各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已经忘记的感触和思考。无论艺术在潜意识里穿行,还是它糅合了我们的记忆而具象化,我都无法弄清楚。我只知道艺术的过程是一连串的刺激,它可能像是一种电压,因为艺术就是种超乎寻常的传输器,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的接收设备能够良好运行。
那该如何办到呢?
喜好无法被标准化,否则将令人十分厌恶。艺术中没有戒律,艺术鉴赏也没有简单的原理可循。“我喜欢这个吗?”是每一个人面对一幅画时所应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结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会喜欢呢?如果不喜欢,那么不喜欢的理由又是什么?明显而直观的情感反应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我们的评断与作品本身无关。
“我不能理解这首诗。”
“我从不听古典音乐。”
“我不喜欢这幅画。”
都是相当常见的评论,然而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书籍,绘画或是音乐的想法。它们表现的重点是说话者本人。可是在现实中,类似的言语却可以成为艺术评论,这些源于我们不大愿意承认的诸如忽视,懒惰,及完全的误导的过失。我听过了许多指责艺术家傲慢的言论,却从没有关于观众傲慢的批评。那些观众,既没有作过画,也不必冒任何风险,他们的人生和生活与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没有丝毫联系,他们的话也无法给媒体任何观点或是方法,他们只是随意扫一眼,匆匆浏览,发表些高谈阔论,然后动动手指拍几张照,再像罗马暴君那样气势汹汹地离开。哦,这不算傲慢;他们当然能毫不费力地花费几秒钟就吸收下艺术家和艺术一切的总和。
如果直白的情绪反应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我喜欢这个吗?”这样的开放式问题将根本得不到最终定论。我们情感的检验总是应该要让步于对作品的检验。这既是对作品的公平,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弄清自己的感受;去展现出嫉妒、观点、焦虑,甚至是一天的心情。虽然相信我们的直觉是对的,验证这些想法却也同样重要。如果它们就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那么我们的直觉是经得起考验的,反之,我们以后也不该继续那么敷衍了。事实上艺术面临的最大最先的阻碍就是它能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的全部暴露出来。
当你说“这件作品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当你说“这件作品很无聊/毫无意义/愚蠢/朦胧/杰出等等”时,你也许是对的,因为你所见的本来就是创作者一时的怪念头,你也可能是错的,因为它已超出了你个人经历所认知的完整世界,所以你要否定绘画所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对幻想世界的否定总是比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更强烈。每一天,我们可以用无数种方法验证自我。我们面对真正的艺术却会产生对“我”的质疑。
我听过了许多指责艺术家傲慢的言论,却从没有关于观众傲慢的批评
一个平行的爱将会是公正的;与艺术坠入爱河挑战着我们依附的现实,我们要同时承受爱产生的压力和颠覆世界时的恐惧。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想要的,最前沿的,令人沮丧的,新颖的观点。我们总是努力像驯化我们自己情感环境那样去驯化我们美学环境。我们已经驯化了我们的客观世界,我们也要满足于其余所有的驯服,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可以去喜欢一样你一无所知的东西,甚至说,永不消逝的质朴和纯真才是上天赐予的宝贵财富
艺术不能被驯服,即便我们反可能被艺术驯服,我们对于艺术珍藏品的认知在步入学堂就已定型。那些媒体所鼓励的,每天普通大众所引以为傲的新鲜事物和没有教条的“我知道我喜欢什么”的方法,其实一点也不新鲜,且一点也没有摆脱教条。然而伴随流行文化的充斥,学生的思想也逐渐被这种浅薄的洗脑而变得贫瘠。
媒体将艺术洗劫一空。媒体所用的图案,广告,复制品,广告歌,短小的旋律还有记者的行话。所有的一切都使真实音乐,绘画和文字的形式与创作变得愈发苍白无力。我们也被媒体的狂轰乱炸弄晕了,感官不再灵敏,也会对非快餐式的,难以理解的,无法消费的事物感到恐惧。艺术的实体化需要我们大力抵挡流行文化。艺术家在创作中耗费了如此多的时间,金钱,学习,人道和想象。难道我们用百分之一的努力来回报艺术就不合理了吗?我其实担忧我呼吁回报会被认作是种精英主义,而使得他人对艺术起诉,精英则站在原告上努力奋力在战场上保卫自己。其实这十分接近于提出“他们为什么不能都说英语?”这样典型的,致使英美人民成为精英主义众矢之的的问题。
但是你也许会说,我又能知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呢?我可以为装饰火炉的那幅廉价海景油画感到触动,但我是不是也非得要走去泰特美术馆朝拜那片铺满染色稻米装饰的整个楼层?
多年前,我曾短暂地与一位证券经纪人生活在一起。他有着一个很棒的酒窖。我问他该如何学习品尝红酒。
“只有靠多喝。”他说。
确实如此。提升味觉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提升味觉。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想要去了解绘画时,我会走出去尽可能多地欣赏绘画,即便一直用旧有的标准来评判,我也仍要不停进行下去。你可以去喜欢一样你一无所知的东西,甚至说,永不消逝的质朴和纯真才是上天赐予的宝贵财富。而现在,我们表现得并不像艺术悲观者认为的那样封闭保守。我们可以对艺术一见钟情,只要它是好的,不错的。那些因为无知而排他的做法的确过于恶毒。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先了解事物的价值再决定要不要去喜欢它。我更赞赏坚持多年锻炼出来的自我意识和哲学观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喜欢这个吗?”的问题是对人生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如此这般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尽可能扩大自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吗?”涵盖了一件独立的事物,以及我们自己的主观认知。
我确信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严肃对待艺术,不仅仅视其为装饰或娱乐,而是一种有生命的精神,那么我们很快会学会区分什么才是艺术。美国诗人弥瑞尔-卢奇瑟曾说过:
只有艺术与非艺术之分;它们是两个宇宙,(按代数的说法)是不相容的……在我看来,把一件名作称为“好的艺术”而把不出名的作为“坏的艺术”等同于在红色与绿色之间把前者认作“好的红色”而把后者硬说是“坏的红色”一样。
倘若大家同意这点,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同样抛开一味盲从学院式的“好品味”或是走出不断否认我们自己的幼稚水彩,学生海报或全家福的怪圈呢。只要我们搞清楚这些画是什么,更重要的,得明白这些画不是什么,其余的就随他们去吧!倘若我们的感官变得更为敏锐,那么内心对美学真实的思考会触发争论及更深层次的琢磨,这样就避免政治,妒忌或时尚……甚至是我们个人喜好造成的干扰,我们也就不见得会对所有的东西都达成共识,而当看到同一幅画(或是读同一本书)时会萌生相同的触动。艺术即是一项呼吸运动。
艺术也同样令人震惊。即便是最保守最不感兴趣的人也大概会告诉你,他或她喜欢康斯坦勃尔。但是我们的坚定分子是否会喜欢1824年那个在巴黎沙龙里开展览引起诸多争议的康斯坦勃尔呢?我们忘记了艺术中每一次引发的震惊轰动,无论是书籍,绘画还是音乐,最终呈现下一代总是那么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样子,那些曾经的大胆反叛有时甚至成为了现今的评价的标尺。这些经典作品其实没有苍老,仍能为艺术提供新鲜血液,只是由于那些不满足纯模仿还能创造众人翘首以待的佳作的艺术家少了,因而总体上也淡化了对经典做出的深入探索。
我买不起康斯坦勃尔,或是毕加索,亦或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然而对绘画没有真正自己想法的喜欢岂不是和没有任何藏书的书籍爱好者一样荒唐。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公共美术馆里成群结队的游客不愿意走出来支持下新作品。拜托,我们不是在讨论“爱情故事”或是“窥视秀”,好吗?
我在我的藏画里蹑手蹑脚,接受它们的注视,如同我时时刻刻观察它们。我们三方之间有绵延不断的情感交流;不必亲自见面的艺术家;作品它本身;还有我,深爱它且离开它后无法独活的人。三角的交流不停改变,那是流动的,细微的,深远的。任何一个在意绘画的人都很快会发现这一无法考证的事实。我墙上的绘画,艺术品及艺术的过程,是条连续的,动态的,有生命的线;是我身体映射出的色彩浪潮,充满了颜色,它淹没了连同崭新当下的,将来的,甚至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些都无法排除在绘画的光芒之外。我回想我做过的事,绘画抓住了我,增添了想法,改变了思考和过去的意义。全然的绘画即评价了全然的我。而绘画越大,过程就越完整。
过程,即能量的运动,即定局的拒绝;不同于否定完整,它设定了艺术,个别及其所有的艺术,远离了限定时间那个总喊着“求你慢点,时间!”的世界。
我们知道宇宙是无限不停扩张的,十分古怪的,它也同时是完整的,它从不缺少我们除了知识外其他需要的东西。人类悲剧的模式是缺少。失去和终结,是一个原始的,无法被技术和医学科学代替的灾难的预言。艺术之于世界即是灾难的预言。艺术品,这个名词变成了一股动力而非一个收藏家的物品。艺术品。
无论是拉斯科的洞穴壁画,西斯廷大教堂的天穹,毕加索对真理思考的产物,还是凡妮莎·贝尔对真理更加安静的理解,都是在抵抗着生活中的谎言,对立着那些无意义且刻薄的意识。光阴荏苒,这些由颜色组构成的信息从不会缺乏,正相反它们是广泛的。它们也不是寂静的,反而有着众多的声音。艺术,个别及其所有艺术,是无法被冷漠和灾难割断的交流索。它是抗拒死亡的永恒不灭。
无论是拉斯科的洞穴壁画,西斯廷大教堂的天穹,毕加索对真理思考的产物,还是凡妮莎·贝尔对真理更加安静的理解,都是在抵抗着生活中的谎言,对立着那些无意义且刻薄的意识
所有的绘画都是洞窟壁画;你我的形象被描摹在低矮暗淡的墙上,为了彰显自我的伟大。图绘过的教堂是耶和华的纹身,教堂绘画其实与宗教无关,可未尝不与爱无关。爱,涵盖了信仰和乐观精神,幽默慷慨,以及人性的崇高,这些生命的必需品却因为能藉由艺术从无形转为了动人而精炼的有形表述。
我来到这世界上,一丝不挂。然而,我却能以勾勒描摹蔽体,言语文章果腹,五音六律规矩。艺术是我的“竿与杖”,是我的休憩与受庇护之处。它不仅仅属于我,因为它不会抛下任何人。即使在那些因为苛政和贫穷迫使艺术被利用的地方,仍会有一群人在努力创造着艺术,用歌声,用尘与土。即便这些作品会被销毁,创造的力量却从不能被打压。如果在西方舒适的环境中,我们对那样的精神持有怀疑和轻视,那么我们的艺术也会江河日下。艺术的进化不是那些20世纪末的城市居民能在外就可以轻易一点点制造的。严格说,艺术根本算不上遵循进化的节奏。没有附加其生物性的必要。因为伴随它漫长的时光是人类进行狩猎,采集,交配,探索,建造,求生,繁荣的过程。奇怪的是,当大限来临,我们自身也不复存在时,我们却说我们没有时间留给艺术。
如果艺术,所有的艺术,都再也与我们生命无关,那么问“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怎么样?”这种问题将会十分冒险的。而用惯常的问题:艺术会怎么样?恐怕就是一个能够回避这个问题的捷径。
我没有逃避。我瘫坐在阿姆斯特丹的一间画廊里流泪痛苦。而后,当我卖掉一本书我又会买一本马西莫·拉奥。而我的这一切改变正始于墙上最初装点的那抹新光。
❶马西莫·拉奥(1950-1996),意大利画家。主要作品有:《大火炉》、《一天在她的眼睛和她的手指抓住了星星》、《月神》、《无论在天上或地上》、《祖先的土地的梦想》、《蜥蜴王》。
编辑/张定浩
*选自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文论集《艺术品》(Art Objects:Essays on Ecstasy and Effrontery)。本文为该集中的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