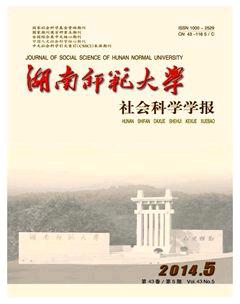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述论
陈宇翔+薛光远
摘 要:以社会思潮与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互动关系为线索,检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观念的思想过程很有必要。伴随着1920年前后“改造社会”话语的兴起,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不但视其为“个人解放”的归宿,更开始关注以“互助”、“协作”为表征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因为提供了一种“社会整体改造”的可行方案而被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重视和信奉,最终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思想因素。
关键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
作者简介:陈宇翔,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2)
薛光远,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2)
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因何放弃西方民主的愿景,转而改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观念,一直为学界反复言说,然而结论繁多,却始终不脱服膺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的“一条金线”。李泽厚所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中的阶级斗争学说而被接受、理解和奉行的”{1}成为学界定论,以至于承认或否认、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或积极反对)阶级斗争,几乎成为学界分析、判定思想人物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界限和标准尺度。这些言论当然成立,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甚至忽视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众多社会思想中选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和思想过程。任何社会理论为知识精英选择、服膺、信仰,既不可能在一瞬间“顿悟”,更鲜能一举中的。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之转换来叙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与“众说纷纭”思想资源中选择并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对学界既有之结论做必要的补充与丰富。
一、从“个人”、“国家”到“社会”的意识转换
众所周知,个人觉醒是晚清以来被反复言说的价值标识。自严复译著的《群己权界论》出版时,近代中国思想界便开始了“小己”、“国群”与“小我”、“大我”的论述/论争模式。{2}一般而言,晚清延展至民初对个人、个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将个人从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完全消融于民族国家的有机体里。梁启超是提倡这一观念的代表性人物,他极力鼓吹“新民”,要求个人从各种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强盛所要求的新“国民”。{3}在梁启超看来,“民族国家”实为个人的必然归处,因为非如此,不足以挽救民族危亡。“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4}
然而欧战的爆发和民国政治的混乱不堪,动摇了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国家”前景的信心。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惨痛景象使他们普遍认为导致这场人类浩劫的直接原因就是“民族国家”观念。“国家”迅速成为批判、鄙夷的对象。它不但是“一种骗人的偶像”{5},更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6}。陈独秀激烈地表达了对“国家”概念的厌弃:“全人类……本来都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的国,李爱李的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的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的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的事。”{7}有鉴于此,知识精英逐渐将寻求救亡之途的目光从“国家”概念上移开,并重新聚集于“个人”之上。“新人”成为“人类中的一个人”,而不再是“国家”中的一个“民”。{8}积蓄许久的“个人觉醒”在短暂的时间内急剧爆发,一时之间“个体独立”、“个人解放”的口号铺天盖地,蔚为大观。然而正如论者所言,此时群体意识与个人主义吊诡的并存于思想人物的脑海之中,甚至大有压倒后者之势。{9}陈独秀即认为“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永远生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的大问题”,他又说:“Oliver Schreiner夫人的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蝗虫,它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前后,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亦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的价值。”{10}浓厚的群体意识跃然而出。这种思想倾向与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相互影响,必然使因个人解放而来的“娜拉走后如何”的问题得到凸显。单独的个体显得孤独无依,而国家又不可恃。在此情景之中,群体概念的另一个载体——“社会”成为人们新的兴奋点。
根据学者考证、研究,戊戌前后society的中文译法主要有“社会”和“群”两种,但当时知识精英多用“群”而不是“社会”来指涉society。直到1905年后,“社会”一词才逐渐流行,并成为社会讨论的主题之一。{11}梁启超亦承认“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12}。然而处于崩溃之中的传统社会自不能提供中国知识精英必要的期待,不但各种政治黑暗要“传统社会”承担责任,甚或在部分激进青年眼中,传统中国尚不足以“社会”相指称,提倡要“无中生有造社会”。{13}于是,“改造社会”成为个人的必然使命,无法逃离;同时,它也作为嘹亮的时代口号,影响甚至左右了一大批激进青年的思想选择。1919年12月《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宣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14}1920年《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似乎也寓有放弃“个人解放”而专伺“社会改造”之意。在杂志改名的同时并有文章指出:“夫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今日中国高谈社会改造之人,约而分之,可得三种:第一,为感于自身所处环境之不良,因誓志发愿,欲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或建立新村者;第二,则为一知半解之人,偶读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之译本,或竟仅知其名,因以时髦自居,而大唱其改造社会者;第三,则为一般政治的野心家,思凭籍社会改造之美名,以为彼辈利用之武器。”{15}然而无论各种“社会改造者”的面目如何,“改造社会”毕竟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不但酝酿了日趋激进的思想氛围,更带来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