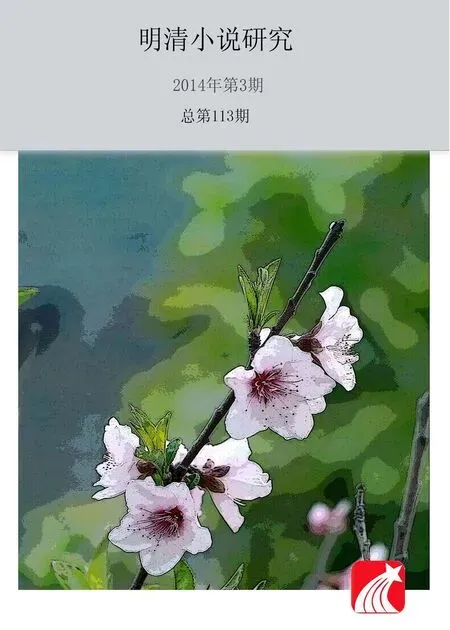明清游冥故事与小说叙事手段
··
明清游冥故事与小说叙事手段
·郑红翠·
游冥故事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叙事类型,直接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冥界观念,绝大多数游冥故事体现的是佛教地狱观念。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全面繁荣为游冥故事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游历地狱模式构成游冥故事的主要框架,游冥故事更多地成为小说叙事手段。大量的游冥故事进入小说成为小说游冥情节,在小说情节贯连发展、结构小说框架、实现小说家针砭现实的创作理念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游冥故事 地狱 冥府 小说 叙事
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个故事类型,游冥故事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俯拾即是。游冥故事的出现,源于古代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思考。游冥故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明清时期游冥故事的繁荣
伴随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全面繁荣,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游冥故事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无论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无论是短笺笔记,还是中长篇小说,“地狱”随处可见。在文人的灵感和创作里,“地狱”显示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明清时期,龙其是清代,是游冥故事经过唐代发展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游冥故事的创作达到了全盛时期。把明、清游冥故事放在同一时段加以论述,是因为明、清游冥故事在总体上有大致相同的特征。不仅是因为时段的漫长,明清游冥故事无论在数量的庞大、分布的普遍,创作主体的人数之众与层次之高,还是从篇幅、艺术技巧、美学风格、思想内涵等方面都是空前的。明清游冥故事分布极为广泛,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随处可见。这种分布不像南北朝、唐、宋时期多集中于志怪小说集,而是散见于普遍的小说创作中。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把游冥故事分为独立成篇的游冥故事和中长篇小说的游冥情节两部分,来考察明清游冥故事的繁荣。
1.独立成篇的游冥故事
从南北朝始,每一个时代都有一部分游冥故事是为宣教劝教弘扬佛法而作,这部分游冥故事基本都承前代余绪。唐代很多游冥故事就是成功的游冥小说。南北朝以来文人笔记中有很多非常简短的游冥故事,还不能称之为小说,而中长篇白话小说中的游冥情节也不能称为小说,只能是作为小说情节的故事。本文为叙述的方便,一律称为游冥故事。明清时期也是如此,一部分仍然按照南北朝唐时的故事轨迹发展,本身没有大的改变。但明清时期这类游冥故事已经很少,真正代表明清游冥故事风格的并不是这一类故事。
作为独立成篇的游冥故事,主要集中于文言志怪小说集、文人笔记及白话短篇小说集。作为明代文言小说集的代表,“剪灯系列”中的游冥故事虽然是传统的游历地狱模式,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剪灯新话》游冥故事以《令狐生冥梦录》最有代表性。《令狐生冥梦录》写刚直之士令狐生见邻居乌老为富不仁,病死后,因家人广做佛事,三日后复苏。令狐生忿而赋诗揭露地府的不公,被召入冥府。冥王感其刚直,特许放还。《剪灯余话》以《何思明游酆都》为代表,叙何思明不喜佛老,并作文批之,被鬼捉到酆都,遍历“勘治不义之狱”、“勘治不睦之狱”及“阎浮总狱”,见种种世间“不恭友兄弟”、“轻灭人伦”、“不能和顺闺门,执守妇道”、“谤毁君子”、“招权纳贿,欺世盗名”者等,备受种种酷刑①。“剪灯”系列故事承继了传统的惩恶扬善主题,却赋予游冥故事新的思想内涵,揭露“公私随处可通门”的社会现实。在行文的表达上寄予了生与死、爱与憎的深切情感。故事所描绘的冥府是作者对现实的无情剖析与深刻反思,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作者对人世百态的生动写真。

“剪灯”系列游冥故事分布
明初另一部很有影响的传奇志怪小说集赵弼《效颦集》有两篇很有影响的游冥故事:《酆都报应录》和《续东窗事犯传》。《酆都报应录》叙渝州士人李文胜梦游酆,见北阴酆都大帝审判汉代七国之乱、汉不法外戚及王莽篡汉等忠奸斗争中的各色人等,使忠节者托生贵室,奸佞者为奴为畜,以明示“既有吉凶消长之理,岂无善恶报应之机”。这个故事对明清一部分以冥判为结构框架的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因》等有启发意义。冯梦龙《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的冥判框架与此相似,应是沿用此文的冥判模式。《续东窗事犯传》叙元时秀才胡毋迪为人刚正无私,一日偶读《秦桧东窗传》和《文山丞相遗稿》,心头不平,大醉后被阎王召入地府,遍游地狱,目睹秦桧、王氏等奸佞之辈受尽酷毒,沦为牛羊猪犬,而忠臣之士居琼楼玉宇,享尽天乐,或转生为王侯将相,为明君所用。方知天地无私,鬼神明察。该篇为《古今小说》卷三十二《游酆都胡毋迪吟诗》的本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有关秦桧受报的情节完全采录《续东窗事犯传》②,《说岳全传》第七十三回亦本此而写。
此外,明代如周静轩《湖海奇闻》、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代文言志怪小说集记有游冥故事。明人编刊的文言小说总集《国色天香》、《说郛》、《续说郛》、《古今说海》、《稗史汇编》、《稗海》等,多有游冥故事。
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有不少出色的游冥故事,如《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郓州司马冥全内侄》,《警世通言》卷四《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卷二十《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喻世明言》卷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七《游酆都胡毋迪吟诗》、《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梁武帝累修归极乐》等。
游冥故事发展至清代,出现了又一个高峰,大量的游冥故事出现在众多文人笔记小说中,地狱在小说中大放异彩,这种现象和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轨迹是相一致的。《聊斋志异》及“仿聊斋”小说、《虞初新志》及“虞初体小说”等文言小说的兴盛使游冥故事又一次呈现了新的发展契机。《聊斋志异》、《子不语》、《谐铎》、《阅微草堂笔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醉茶志怪》等文言小说集有大量的游冥故事。《聊斋志异》涉及游冥情节的约30篇,其中优秀的较有影响的有《席方平》、《三生》、《李伯言》、《阎王》、《考弊司》等。
2.中长篇白话小说中的游冥情节
明清时期是中国白话小说的成熟时期,游冥故事进入中长篇白话小说中,很多小说家游刃有余地运用游历地狱模式来构建小说结构,推动情节发展。游冥故事脱离了宗教的束缚,由宣教而为劝戒,再而为小说创作手段,功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这是游冥故事的新变,也是小说创作技巧的成熟。
明清时期大量的游冥故事作为情节单元分布在各类白话小说中。明代世情小说《醋葫芦》叙临安府白圭之妻都氏不育且生性喜妒,虐待妾、婢。第十四、十六、十七回,都氏被无常勾取,打入十八层地狱,罚受种种极刑,后抽去脊梁上的妒筋,转回阳世,从此妒心全无。
世情小说《山水情》第六回“摄尼魂显示阿鼻狱”写尼姑了凡因淫荡被摄入地府受到责罚并游历地狱后复生。《姑妄言》以游冥模式作为构架全书的引子,第一回闲汉到听(寓道听途说之意)醉卧城隍庙,目睹衮冕王者对汉朝至嘉靖年间阎王所决疑案,按情节轻重,再判至人间轮回受报,对主要人物一一作出交待。李林甫转世为阮大铖,秦桧生为马士英,永乐皇帝生为李自成等等。小说以南京瞽女钱贵和书生钟情之婚姻,以及宦萼、贾文物、童自大这四个家庭为主线,以魏忠贤专权、李自成攻入北京、直至清军荡平江南这段史实为背景,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明末小说《轮回醒世》十八卷以“今生受,今生造”的佛教轮回宗旨、以游冥模式作为小说框架记叙了183则故事,每一则以阎罗王审案为结,点出两世因果缘报,让阎罗王为人世的公案主持公道,却并非“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宣扬的是传统儒家道德,表达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与对社会公正清明的企盼,形象地刻摹了晚明斑驳陆离、五色纷呈的社会众生群像。公案小说如《海公案》、《龙图公案》等更有不少冤魂告状、沟通阴阳、查访冥界之类故事。此外如《老殘游记续集》、《金瓶梅》续书、《红楼梦》续书等都有大量的游冥情节,作为小说创作手段,在推动情节发展、完成小说主题、实现小说的大团圆结局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明清小说中,出现游冥情节最多的是神魔小说。神魔小说中,各类神鬼仙魔活动于三界之中,冥界是其主要活动场所。“四游记”中除《东游记》外都有游冥情节。《西游记》第三回“孙悟空闹地府”和第九回“唐太宗魂游地府”是人们熟知的故事。明余象斗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南游记》)叙火神华光之母范氏系吉芝陀圣母附体,以吃人为事,被打入酆都。华光探寻母亲,闹东岳、闯阴司,降诸妖。华光酆都救母,显然受目连救母故事影响。《西游补》里写唐僧师徒取经西行经过火焰山之后,孙悟空化斋进入鲭鱼气袋中被迷,在青青世界万镜楼中见古今未来之世,并当了半日阎罗天子。《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中,写郑和在碧峰长老和张天师协助下擒妖伏怪,也有描写地狱的情节。明清神魔小说游冥情节分布详见下表:

作品回数回目《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第十一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西游补》第八回一入未来除六贼半日阎罗决正邪《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八十八回崔判官引导王明,王克新遍游地府《后西游记》第三回力降龙虎,道伏鬼神《北游记》第十一回关羽夜管酆都冥府《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第十三回妙善魂游地府

《华光天王传》第三回华光闹阴司《咒枣记》第十一回萨真人往丰都国,真人遍游地府中《韩湘子全传》第十六回入阴司查勘生死,召仙女庆祝生辰《东度记》第十九回清宁观道副投师,轮转司元通阅卷《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第六回秦相梦中见鬼神,济公夜来施佛法《海游记》第三十三回似人似鬼孽满受诸刑,半是半非书终成一梦
此外,还出现了大量全书以鬼为主要描写对象,以冥府为主要活动场景,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弊的中长篇小说,如《何典》、《醒游地狱记》、《钟馗全传》(包括《斩鬼传》和《平鬼传》)、《地下旅行》、《新鬼世界》、《宪之魂》,晚清李妍人的小说就以《活地狱》命名。这些小说成为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
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个叙事类型,不少优秀的游冥故事文彩斐然,艺术成就突出,人物刻画生动,描写精彩,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古代小说史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如果没有这些奇幻的充满想象力的“上天入地”,没有了阎王判官小鬼,中国的小说世界将会逊色很多,少了几分光彩和神奇。
游冥故事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在明清达到全面的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佛教的世俗化儒化及三教合一思潮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反映到小说领域里,就是小说中的三教合一现象。成熟的游冥故事发端于佛教地狱观的传播,从南北朝始,就受到佛教地狱观的规定和束缚。游冥故事的产生发展兴盛与佛教的中国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游冥故事经过宋代宗教色彩的淡化期以后,与佛教观念日渐疏离,开始脱离宗教观念的束缚。而至明清,游冥故事开始了徒具宗教外壳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小说自身的因素。作为游冥故事的载体,中国古代小说在经历了先秦、两汉、魏晋的草创、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小说的发展,明清时期,已发展成为一种与正统诗文相提并论的独立的文学体裁,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全盛时期。在长篇章回小说和白话小说空前繁荣的背景下,文言小说也到了最后的辉煌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游冥故事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晚清,也仍然成为文人揭露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工具。
二、明清游冥故事成为小说叙事手段
明清游冥故事与前期游冥故事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征是游冥故事创作主旨上的蜕变。大多数游冥故事不是以宣教劝善为主要宗旨,而是作为一种叙事手段,进入到小说中,以实现小说家的创作理念。
游冥故事中,沟通阴阳,地狱人间,融为一体,这为小说设计情节、展开矛盾、弥补漏洞,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明清时期,很多小说家把游冥故事作为一种创作手段,把地狱阎王游刃自如地运用于小说中,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构架小说结构、完成小说主题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作为情节链条的连缀推动情节发展
在不少明清小说中,游冥故事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要素,作为情节链条,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方面承上启下、勾环联结,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环节。这种游冥情节的设计使小说可以跨越不同时空领域,将彼此独立的事件,连缀成一系列因果相连的情节整体和形象实体,并统一于整体故事叙事之中。
《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写孙悟空闹地府,勾去生死簿上的名字:“另有个簿子,悟空亲自检阅,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乃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悟空道:‘我也不记寿数几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罢,取笔过来!’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掭浓墨。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扔下簿子道:‘了帐,了帐!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③这一回在情节发展上有两个作用:第一,在刻画孙行者形象上,突出了孙行者“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洒脱不羁蔑视权威的性格。第二,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做铺垫。没有这一回的“销名”,孙悟空的神奇本领可能要受到限制,更多的情节可能要无法展开,孙行者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等其他的情节便缺少了因果逻辑上的支持。
《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是联结取经前后的最为关键的一回。太宗看到地府中“哄哄人嚷”,“尽是枉死的冤业”,“都是孤寒饿鬼”,所以在唐太宗临还魂之时,崔判官便告诫唐太宗:“陛下到阳间,千万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当唐太宗回阳之后,招集天下僧尼,设无遮大会超度亡魂,并由此引出了唐僧取经故事。太宗的还魂,为唐僧作为取经团队领袖的出场酝酿了情节上的准备,唐僧在小说的出场水到渠成。太宗还魂这一环节,也是作为“齐天大圣”的孙行者到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孙悟空的重要转折,既是整个故事的主要情节之一,又是取经故事的引子,为下文创设了情节动因。作为关键的情节链条,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此外如《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中,如果没有妙善公主冥中游历情节,妙善公主死后的故事就无法继续;没有妙善公主在冥府中的诵佛修行,妙善也就不能说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修行。游冥故事为小说情节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成为情节链条断裂时的补救法宝
在不少明清小说创作中,在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在有些关键时候,在情节链条发生断裂、矛盾不可调和之际,游冥故事成为推进情节进展、解决矛盾的补救法宝。这在明末清初一部分以表现妒妇题材的小说中比较明显。
以明末世情小说《醋葫芦》为例,女主人公都氏游历地狱是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小说十四、十六、十七回都有游冥情节。因为都氏的悍妒不育,夫妻反目。一系列的家庭变故使女主人公病死身亡。都氏死后游历地狱受罚复生后变得贤惠而通情达理,接子与妾回家团圆,认祖归宗,夫妻和好,妻妾和顺,父慈子孝,家业振兴。这一切都归功于游冥情节的设计,而情节发展的转折点则是都氏死而复生的冥府游历过程。
小说中都氏的冥府游历情节,也是主人公性格发生改变的转折点。都氏患病以前,性格乖戾偏执,凶悍善妒,给丈夫制订种种不近人情的清规戒律,妒态种种,令人可恨可笑。凶悍奇妒的都氏,经历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打击,几近病死,昏迷中魂游地府,在十殿阎王关于她一生妒行的审判与惩罚被打入地狱后,性格开始发生变化,举目无亲,心生懊悔道:“原来那些王侯鬼判,口口声声,只恨我欺夫罪大,到今日教我怎生悔得!”都氏被抽去妒筋,带着《怕婆经》从阴间被放回,自此妒性全无。复生后,主动接妾与生还家,家庭团圆。
这一类小说中的地狱游历情节,不仅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也是人物性格改变的契机。在一些公案小说中,当案情无法进展,故事情节难以开展下去之时,地狱游历情节很自然被小说家派上了用场,成为解决小说矛盾、推动案情进展、实现案情破译的契机和转折点。如《海公案》、《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等公案小说中,就有不少冤魂告状、查访冥界、沟通阴阳类的情节,入地狱查访案情是解决矛盾了解案情的重要情节。早期的包公案故事就有包公为查案情魂入地府见阎王的故事。明人小说《包公演义》第二十九回《判除刘花园三怪》,写包公为断疑案,灵魂脱离肉体进入地狱,向阎罗察访案情,终使疑案得断,凶手得惩。安遇时编《包龙图判别百家公案》卷三,第二十六回、第二十九回等也有类似情节。
此外,在一部分明清小说中,在这些小说大团圆结局的实现手段上,游冥常常是作者的一大法宝,地狱、阎王是完成作者理想设计的工具和执行者,帮助实现了小说的团圆结局。
三、游冥故事成为明清文人针砭现实的载体
从南北朝始,游冥故事在宣教主旨下表达作者的劝善意图,这也是表达创作理念的一种方式,借游历地狱故事框架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思想在明清时期则更为普遍。明清时期的很多小说家利用游冥模式揭露社会黑暗官场腐败,针砭现实,表达社会理想和忠奸观念,是明清游冥故事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1.地狱是人间官场的对照——地狱是清平世界
在一部分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为创作宗旨的游冥故事中,冥府公正严明,阎罗王铁面无私,所有人间的不公,所有的善恶都会在冥府得到最为公平的清算。是非分明的冥府审判寄托了人们对执法者的尊敬和对公平正义的信心,这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社会公正清明的企盼,也是一种最为美好的人生理想。
这一类故事中,地狱是人间世间的对照,人们所向往的清平世界只能在阴曹地府中存在,这也是对人间黑暗的揭露。
明清时期一部分游冥故事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这些故事中,多数情况下是主人公自身正直无私,对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非常气愤不满,为证明善恶有报,死后世界的公平,使其相信果报不爽,主人公梦中入冥,见到一系列的善恶报应。这类故事主观上有宣扬因果报应劝善惩恶之意,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人间社会的黑暗和不平。
《续东窗事犯传》是明代游冥故事的典型之作,出自明初赵弼《效颦集》。故事叙叙锦城胡迪“性志傥倜”“好善恶恶”,魂入地下游历地狱,见秦桧夫妇及历代祸国殃民的奸佞权臣在“普掠之狱”受刑;为害百姓的贪官酷吏在“奸回之狱”受罚;忠臣义士、爱国为民者在“忠贤天爵之府”享受优待。故事表现了对现实社会律法不公、吏治腐败的不平之心,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观念。地狱井然有序的统治、赏罚分明的吏治、公正合理的法制,反衬了现实社会忠奸不辨、贤愚不明、官府徇私、法律失衡的失常现象。《效颦集》另一篇游冥故事《酆都报应录》与此相似,以“冥判”方式把汉代七国之乱及王莽篡汉的忠奸斗争作以解释,忠节者托生贵室,奸佞者为奴为畜,表达自己的忠奸观念。
瞿佑《剪灯新话》所记《令狐生冥梦录》、李昌祺《剪灯余话》所记《何思明游酆都录》与这两则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何思明游酆都录》写酆都地狱中“惩戒赃盗”门中的受惩戒者,皆“人间清要之官,而招权纳赂,欺世盗名,或于任所阳为廉洁,而阴受苞苴,或于乡里恃其官势,而吩咐公事,凡瞒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李昌祺身处官场,且又清廉自守,对社会政治的黑暗看得更为深入透彻,他的小说“意皆有所指,故一时搢绅,多有心非者”④。明末《喻世明言》卷三十一《闹阴司司马貌断狱》、卷三十二《游酆都胡毋迪吟诗》及“二拍”卷二十《贾廉访赝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故事模式亦与此相同,故事所传达的思想观念也相似,都以地狱的忠奸报应、阴府的公正来映衬人世的不公。
《聊斋志异》卷三《李伯言》记李伯言病死,在阴司为阎罗王。李在审理同邑王某被婢父诉盗占生女一案时,因王是李伯言姻家,“李见王,隐存左袒意,忽见殿上火生,焰烧梁栋。李大骇,侧足立。吏急进曰:‘阴曹不与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则火自息。’李敛神寂虑,火顿灭。”蒲松龄在“异史氏”中表达了对人世间营私舞弊、以权谋私等现象的愤慨:“阴司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谁谓夜台无天日哉?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耳!”
这一类游冥故事并没有摆脱惩恶扬善的固有主题,但写作宗旨却与前期的游冥故事迥然不同。作者在故事中寄予了生与死、荣与辱、爱与憎的深切情感,良苦用心凝聚于字里行间。“公之天性,好善恶恶。每见古今善者而天不佑之以福,恶者而天不报之以祸,故假佛老之说作为传记,发之诗章,以泄不平,亦褒善贬恶《春秋》之意也。”(赵弼五代孙赵子伯《效颦集后序》)“(赵弼)性好善嫉恶,尝于授经之暇,摘取忠良,邪佞、廉暴、淫慝、与乎儒释仙幻之谈,撰为传记。或立言以著其节行,或写事以斥乎奸回,或托辞以明乎报应,或据理以辩乎异同。其类不一,而足褒善贬恶,彰显阐幽,皆得乎好恶之正。”(潘文奎宣德六年《效颦集序》)。赵弼有如此情怀,瞿佑、李昌祺、冯梦龙亦同怀此心。
2.地狱是人间官场的映射——地狱是黑暗世界
小说家一方面利用冥府作为人间世界的对照,以映衬人间世间的昏庸无道黑暗腐败。更多的时候,幽冥世界是人间世界的真实写照,小说通过揭露冥府的黑暗,传达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使地狱成为人间官场的映射。
利用地狱影射人间世界的写法在唐代游冥故事中已较普遍,《冥报记》、《广异记》中的不少游冥故事记冥间贿赂风行,冥吏索贿厚颜无耻。明清小说中,这种写法被明清小说家运用得纯熟自如,游冥情节被小说家信手拈来,见缝插针地安排于小说的各个环节之中,所寓含对人世黑暗现实的揭露谴责、评击讽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一些白话小说如《子不语》、《续子不语》、《谐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代文言小说集的很多游冥故事,记冥间官场贪贿成风,影射现实,折射人间社会不良风气。这种现象在晚清小说中尤为突出,《何典》、《醒游地狱记》、《斩鬼传》、《地下旅行》、《新鬼世界》、《宪之魂》等中长篇小说中的地狱描写,成为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
明末小说《轮回醒世》十八卷以游冥故事作为结构框架,记叙了183个故事,利用阎王审案的“冥判”模式,形象地刻摹了晚明斑驳陆离、五色纷呈的社会众生群像⑤。《轮回醒世》对人世的揭露全面而又具体,将王公贵族、达官显宦、忠臣孝子、贪官墨吏、骚人墨客、佞臣贼子、商贾巨盗、贩夫走卒、奴婢闺秀、门子衙役、官吏地主、秀才举子、三姑六婆、地痞无赖等社会各色笼于一书,并深入到人性的各个侧面,廉慈贪酷、慷慨吝啬、贞洁卑污、侠豪吝啬、贵贱贫富、忠奸贤愚都在故事叙述的进展中表现出来。在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中,具体形象地刻摹了一个地狱般的现实。
《聊斋志异》卷六《考弊司》叙阴府考弊司“司主名虚肚鬼王,初见之,例应割髀肉”,“不必有罪,此是旧例,若丰于贿者,可赎也”。一秀才因贫未能贿赂,被反手捆绑,“一狞人持刀来,裸其股,割片肉,可骈三指许。秀才大嗥欲嘎。”对此,作者发出了“惨惨如此,成何世界”控诉。《聊斋志异》卷十《席方平》对司法黑暗的揭露更为深刻,以犀利的文字,通过对“冥府”黑暗的描写,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愤慨和反抗。席方平父与富室羊某有隙,羊某先死,贿嘱冥使,使席父被冥吏残酷拷打而死。席方平愤而入冥,欲替父申冤。由于羊某的“内外贿通”,席方平“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大喊“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也!”席方平因不肯行贿冥王,几次入冥告状,均因狱吏、城隍、冥王的徇私舞弊被维持原判。第四次告状,因遇到二郎神而洗雪父亲冤情,父子双双还阳。作者借二郎神的判词“金光盖地,因使阎魔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痛快淋漓地揭示了人间官场腐败黑暗贪赃枉法、地狱般的现状。此外,冥界高级官僚恶贯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地狱成为人间官场黑暗腐败的反射。
在清代的文言小说中,沈起凤《谐铎》中的游历地狱故事对贪官酷吏的抨击尤为激烈深刻。卷六《森罗殿点鬼》冥王稽鬼箓,唱名点簿。点饿鬼簿之时,一吏禀告,因地狱前鬼门关守者,失于防检,诸饿鬼乘机逃去偷生阳世,“大半作县令”。冥王叹曰:“若辈埋头地狱,枵腹垂千百年。今一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灵无噍类矣!”《锴铎》中的类似作品还有卷六《香粉地狱》、卷八《棺中鬼手》等。
晚清小说《地下旅行》利用游历地狱十殿影射当时的社会现实。地狱十王殿第一殿“魂魄制造所”中,官员魂魄乃“采取世上恶浊,再到血污池中提炼十次始成”,商人魂魄为金黄色,心为黑色且生于腋下,士兵心生后背而胆倒挂。造心所中,利心、名心、黑心俱全而独无良心。五官制造所中,造舌原料为柳叶,可以随风而变。所造眼中皆有磁石,见金银而灼灼不舍。这种描述深刻透骨,字里行间亦见出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
明清时期这类以地狱暴露人间黑暗现实的作品,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封建时代,有正义感的作家用以抨击时政、表达自己对社会观感的一种隐喻手段。一些文人欲述政之污浊、民之勤苦,然而“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事”⑥。故而借地狱以影射社会现实的黑暗,借“鬼神造化之理,以觉斯世之昏迷”⑦,而游冥故事恰恰是这种创作需求最好的载体。
3.地狱成为明清文人传达思想观念的工具
利用游历地狱模式表达思想观念,是小说家们较为常用的创作手段。上文提到的借地狱以写现实揭露社会黑暗,既是创作手段,也是作者观念的表达,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在明清小说中,地狱与阎罗王常常是作者表达某种思想传达某种理念的工具。
赵杏根在《我国旧小说中的地狱和阎王》⑧一文中谈到杨衔之《洛阳伽蓝记》“惠凝入冥”故事,是我国作者成功利用阎罗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权威表现其思想观念的最早例证。
明初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修文舍人传》对封建的选官制度提出质疑,主人公夏颜对阴间与阳间的用人制度作了比较:“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间可以贿赂可通,可以门第可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也。……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间……骐骥服盐车而驽骀厌刍豆,凤凰栖枳棘而鸱鸣户庭,贤者槁项黄馘而死于下,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世,故治世日常少,乱日常多,正坐此也。冥司则不然,黜陟必明,赏罚必公。”⑨以阴间公平、公正的用人制度对人世间贤者无能当其位的用人制度提出质疑。清代《萤窗异草》中《考勘司》写刑部官员多公梦阴间“考勘司”查证其近日所办案件,以此警戒现实生活中一些审案随心所欲、徇私枉法的官吏,同时也表明作者对人间政府吏治的思考,希望现实中也能设立监督吏治的机构。
清代小说家用游冥模式以地狱阎罗王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以《聊斋志异》、《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最具代表性。
《子不语》卷九“地藏王接客”中地藏王训斥副榜裘生:“自称能文,不过作烂八股时文,看高头讲章,全不知古今来多少事业学问,而自以为能文,何无耻之甚也!”表达了袁枚对时文的看法。《子不语》卷一“仲孝廉”,地狱“乌纱冠南向坐者”认为,无力葬父母,淫婢狎妓,都是小罪,“有口过,好讥弹文章”,其罪更小。《续子不语》卷十有《淫谄二罪冥责甚轻》中袁枚借判官之口,为一有淫行而托生富室的女子辩护,表达自己的观点:“男女帷薄不修,都是昏夜间不明不白之事……阎罗王乃尊严正直之神,岂肯伏人床下而窥察人之阴私乎?况古来周公制礼,以后才有‘妇人从一而终’之说。试问未有周公以前,黄农虞夏一千余年史册中,妇人失节者为谁耶?至于贫贱之人,谋生不得,或奔走权门,或趋跄富室,被人耻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谓‘顺天者昌’,有何罪过而不许其托生善地哉?况古人如陈太丘吊张让而解党祸,康海见刘瑾以救李崆峒,贬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录之入菩萨一门,且有善报矣。至于因淫而酿成人命,因谄而陷害平人,是则罪之大者,阴间悬一照恶镜,孽障分明,不特冤家告发也。”袁枚为人轻佻刻薄,女弟子颇多,袁因于男女方面的言行及常好讥弹别人的诗歌文章,常受人讥嘲诟病。袁枚此论,似有为自己辩护之意。
《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卷一,记一官入冥,神情昂然,称自己所至但饮一杯水,不愧鬼神。阎罗王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释承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云:“某虽无功,亦无罪。”阎罗王云:“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阎王关于为官的一番议论,当是纪昀针对当时官场风气而发,批判了朝廷官员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中庸思想,表达了对为官为政的思考。
注:
①⑨ [明]瞿佑《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94页。
② 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③ [明]吴承恩《西游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页。
④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
⑤ 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轮回醒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6页。
⑥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⑦ 陶辅《花影集》,程毅中校点,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⑧ 赵杏根《我国旧小说中的地狱和阎王》,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徐永斌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项目(批准号:13B015)阶段性成果。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