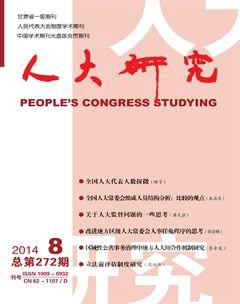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分析:比较的观点
朱海英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从精英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其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往往会充当政治、商业和文化领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精英数量和品质对民主的转型非常重要。进一步而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认为“学而优则仕”,各类精英认同从政是最体面的职业。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是,最优秀的精英不是去从商,而是从政。在现实中,执政党的统治中有“组织领导”,政党一直注重用人事控制权来分配政治精英的地位,为党的政策执行调配不同类型的精英。精英政治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诸多“人治”性质的制度设计还强化了精英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中国人已经习惯从精英的去向来猜测国家政策的变化。西方学者也是高度擅长用这一视角来观察中国 (邹谠,1994;汤森、沃马克,2004)。因此,从人员结构这一内部视角,是可以观察中国各个政权机关的制度化水平和未来发展导向的。
之所以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观察,是因为和全国人大相比,其人数不多且有多人专职,有固定的组织和职能,会期相对较长,它才更像西方国家的议会,其组成人员更像西方国家的议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在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承担着重要的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全国人大每年的会期通常在10~13天,一届的会期加起来也就50多天。而在它闭会后,我们的代议机关就消失了。所以,要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来代行全国人大的诸多职权。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集中在立法、监督“一府两院”、人事任免等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170名左右,九届是155人,十届、十一届、 十二届均是175人,每届任期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时间5天,一个任期内会期有150天左右。相比国外议会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总时长不及他国一年的开会时间,但是已经比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有效能多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者。中国的立法者是什么样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信念和行为?他们能否承担全国人大如此重要的职能?这些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下面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龄背景、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党派背景、地域背景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年龄背景分析
截至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本届常委会组成人员175[1]人,其中委员长会议14人,委员161人。他们的最小年龄是45岁,最大68岁,成员平均年龄是60.5岁。从表1来看,利用分组法可观察到,成员年龄大多集中在55~59岁,60~64岁次之,65~69岁又次之。这三个年龄段比例比较均衡,各占近30%,占总数的90%。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相比,现在的平均年龄仅下降了0.8岁,年轻化的趋势不是很明显。35~39岁、40~44岁、70~74岁、75~76岁这四组年龄段无人,意味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产生更年轻的委员,同时也没有产生更年老的委员。委员们的年龄更加集中,绝大部分委员的年龄在55~69岁之间,55~59岁的人数较十届多了近18%,同时60岁以上委员占比从十届的72%下降到59%,这显示了一点相对年轻化的趋势。在委员长会议这一层面,两届都是以65~69岁为主体,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从平均年龄、60岁以上人员占比来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总体的年龄构成还是偏向老龄化,但是出现了相对年轻化的趋势。张涛指出,外国议员的年龄在45岁左右,相比之下我国若以55~59岁的人为主体,那么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龄结构将会有较大的改观(张涛,2008) [2]。从数据分析可知,我国55~59岁这组年龄段的人10年上升了18%,改观不大。这可能主要是受制于我国的干部替补和全国人大选举的机制,后文再讨论。
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教育背景分析
这里把教育背景分成学历、专业两个方面来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在学历背景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里96%的人受过较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与十届97%的人受过大专教育相比,整个学历层级上升了一个层次。这其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接受正规大学教育者居多,只有4人在中央党校拿的函授大学文凭,1人是澳门华商贺一诚,曾在浙江大学学习,获得相当于大学的学历。少数7人未获得大学文凭者,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如劳动模范许振超的学历是初中、佛教协会会长嘉木样学历不详,还有几人是中专或大专,则与他们的出生年代有关,属于1945~1950年出生,上大学时赶上文革大学停摆。二是博士、硕士大幅增加。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由16人增加到50人,拥有硕士学位的人由9人增加到30人,相应地则是大学本科学历者减少。在博硕士中,拥有海外学历者大幅增加,海归博士16人,海归硕士3人。三是获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3]者大幅增加,65%的人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而十届只有27.9%。其中较为特殊的拥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者比较集中,多达29人。而中央党校的文凭则与国民教育系列文凭差别较大,剔出研究生这个类别后,总体中仍有46%的人接受过严格的高级学术训练。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知识化问题已经解决。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其学历与名牌大学的相关性很小,在十届还有11人来自北大、清华这两所名校,但在十二届则北大只有5人,清华3人。毕业于其他院校和研究单位的都有,来源比较多元。这与国外政治精英大都出自名校不同。
在专业背景方面,这里按照其最高学历的专业来统计。从表3来看,其专业背景中最大变化是理工类与社会科学类的比例。在十届,出身理工者是出身社会科学者的2倍;而在十二届,则是比例倒转,出身社会科学者的人数是理工科的2倍。且在社会科学出身者里,学习过经济类、管理类、政法类的比例大幅增长,人数比较多,经济管理类(31人)、法学类(18人)、政治学类(10人)。但从总体而言,其第一学历、最高学历中学习过法律、政治学类的人数还是非常少,这不利于人大立法和监督政府的工作。理工类出身的委员大大减少,则显示着中国的发展已经从技术立国到了制度立国的阶段了。随着各类组织的扩大和复杂化,中国现在发展到需要更多的企业、社会、政府管理者。就这个趋势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也符合立法者的专业之需。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军方的名额只减少了1名,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出自军事类的人员下降了一半。这也是中国立法机关要专业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方面。endprint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职业背景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业背景特指其在入职全国人大之前从事的职业。由于我国的政治机构设置的原则是“议行合一”,导致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人员会重复,加上各级党委成员在这三大机关任职,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的职业背景比较复杂,入职全国人大之前不少人可能同时担任多个国家机关、政党、事业单位的职务,确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根据张涛对十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职业背景的划分标准,我国存在专职、兼职两种常委会委员,专职常委会委员以其入职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之前一年的职业为准;兼职常委会委员的职业背景指的是在人大职务之外现在所担任的工作,对于担任各种兼职较多的委员,则以其实职、高职为准。比如,万鄂湘,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前,是民革的中央常务副主席(副部级待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以法院“副院长”为其实职,其职业背景笔者依据上述标准,确定“法院”。又如辜胜阻,之前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以全国人大的“副主任委员”为其实职,其职业背景确定为“人大”。有
10位民主党派中央专职副主席,同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在人大职务为准;有1位没有在人大任职的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则放在“政协”。通过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业背景,探测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分,可以总结我国政治精英甄补的一些规律。
根据表4可以看到,两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职业类别多达24个,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其中不变的规律是来自政府、人大、教育界、党委的比例最大,这四类的比例占到总体的62%以上。党委、政府、人大是中国的主要权力机关,所以来自这三大系统的人占比较大。教育界主要来自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或者有民主党派、无党派属性教授。这四大类中,类别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的是来自政府与来自人大的比例。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里,来自政府系统的委员最多,其次才是人大系统。在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里,来自人大系统的成员最多,比例与十届相比上升了一倍多;其次,才是来自政府的,比例与十届相比下降了一倍多。这两个变化至少说明了一点,人大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专业性,从人大系统内部来递补人选。进一步以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的成员比例来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里递补的人员主要是地方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而这些人又是刚从地方的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的位置被选举到地方人大担任领导职务,其职业经历与人大关系不大;而在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里,来自全国人大的成员大幅增加,由3人上升到40人,他们大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各专委会的成员或者人大工作机构的成员,有较长时间的立法工作职业训练。一般而言,选举自全国人大系统的成员,其适合立法、监督工作的专门素质要比地方人大的同类人员强,这进一步说明了全国人大在职业训练方面重视自身专业性的建设。
具体来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省级人大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最主要的甄补路径。来自人大系统的共有57人,占比达到32.6%。其中来自全国人大系统的有40人,主要是各专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和人大工作机构的成员;来自地方人大系统的有17人,主要是省级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其中只有1人是地方州人大常委会的主任。
来自教育界的比例变化不大,从11.4%上升到13.1%,共23人,是第二大甄补路径。甄选对象也没有改变,主要是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学院院长,有12人同时具有民主党派属性或在政协兼职,有2人具有少数民族属性,依然没有中小学的校长。他们的知识背景大都是理工科类出身,社会科学类的很少。这与我国目前校长选拔机制中重视理工类学者的制度有关。
从政府系统进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比例由十届的26.2%下降到12%,共21人,是第三大甄补路径。其中包括原国务院副总理1人(张德江),原国务院各部长(含部长级职务)8人,副部长6人,中央政府其他部门2人。地方政府是省长3人,厅长1人。
从党委系统进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比例与十届持平,都是9.7%。党委是第四大甄补路径,从党委系统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是党中央各部的副部长和地方的省委书记共3人,市委书记1人,村支部书记1人。与十届相比,来自党中央各部门的正职领导人明显减少,这些正职领导人通常被安排去全国政协。此种安排与从全国人大内部选拔成员相呼应,有执政党放权给人大的示范效果。
代表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文联等社会团体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均是其主席、副主席或者书记、副书记,大多数人员在1~2名之间。比较特殊的是十届来自妇联的人最多,多达6人,十二届降为1人。十二届社会团体中来自工会的人最多,由十届的2人上升为5人,全国总工会的主席、副主席4人全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全国总工会主席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这与当前我国的劳资矛盾现象加剧,重视发挥工会作用的政策有关。
来自政协的比例变化较大,由十届的4人上升到7人,而且新增了来自全国政协的成员2人,而十届全部是来自地方政协。其他各界特别是在教育界、社科界、科技界,很多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具有民主党派的属性。这也与当前重视发挥民主党派、政协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有关。
出自科学技术界的比例变化不大,由十届的8.5%下降为6.9%,该界成员一般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二者均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12人。其中大多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协会正副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正副主任、院士或者研究所的所长,与十届无异。但若结合来自教育界的成员来看的话,教育界23位中有2/3的人出自理工科,他们与科学技术届密切相关。这两部分合在一起的比重还是很大的。
出自社科界的比例变化也不大,由十届的2.3%下降为1.7%,该界成员一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共有3人。他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宗教研究所的所长、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这与科学技术界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endprint
出自军界的比例变化不大,由7.4%下降为6.9%,共有12人,均是具有上将或者中将军衔的职业军人。出自工商界的由2人下降为1人,十届是港澳地区各一名,十二届则只有澳门的贺一诚。
出自律师界的,十届有1人,这被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因为国外很多议员、政治家出自律师,其对法律事务的通晓有利于人大的立法工作。而在十二届,没有来自律师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
其他各界如法院、检察院、全国台联、全国侨联、宗教界、艺术界、文联、作协,具有代表各界的象征性作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中通常会有其代表。因其界别人数较少,其代表通常保持在1~2名之间,名额增减1人就可看出其所代表的阶层在不同年代中社会地位重要性的变化。有变化的是来自艺术界成员,从4人下降为0人,新增全国台联1人,宗教界减少1人,即天主教协会会长。十二届新增加了1名来自残联的成员,1名来自红十字会的成员,十届没有这两个界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律师界在十二届没有代表,这个界别与立法工作高度相关,其缺席实在可惜!
以上职业背景的分析,一方面是梳理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甄选途径,从人员构成上预测人大功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人大在以职业背景加强自身的专业性建设,适应立法机关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从全国人大的象征性功能出发,可以看到全国人大所代表的不同阶层在社会地位、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的变化。
四、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党派结构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党派结构大致可以从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三个层面来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与十届相比,十二届中共党员的人数和比例都有小幅上升,由118人上升到126人,增幅为4.6%。这126名党员中有现任政治局常委1人,政治局委员1人,中央委员7人,与十届差不多。他们大部分是普通党员,在党内的地位是中上层的,享受部厅级待遇,在各行各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八个民主党派的总人数由44人下降为41人,但占全国人大常委会总人数的比例变化不大,由25.1%下降为23.4%。这部分人员一般是各党的最高层领导,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委员和地方的主委。其中有5个民主党派的中央主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位。这些与十届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值得一提的变化是8个民主党派之间人数对比的变化。民盟、民建的人数大幅减少,民进、农工党有较大增幅,与民盟人数一样多。台盟也有2人的增幅。
无党派的人数和比例在小幅减少。人数由13人减少为8人,降幅为2.9%,减少部分主要是没有党派、宗教背景的其他无党派人士。
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地域背景分析
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一样,绝大多数成员是北京市人。因为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般都是中央党政机关、全国性社会团体、国务院各直属单位的领导人,他们常住北京。全国人大代表是以省为选区进行间接选举的,常委会的成员又是在全体代表中选举产生的。也就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的地域背景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地域背景是相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中,其居住地与选区一致的每省只有1~2人,也就是说每个省只有少量本省人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每个省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却远不止1~2人,这其中有大量的“戴帽代表”[4]。由于我国选举法对代表候选人的居住期限没有限制,“戴帽代表”们才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推荐到各选区,一般是按籍贯或者曾经工作地分配名额,以保证他们能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中央性是十分明显的。
除此之外,笔者还专门统计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籍贯,发现并没有很集中的地缘现象。其中来自山东省的成员最多,有22人,占比达到12.6%。根据表6所示,其次是来自浙江和湖北,都是12人,占比都是6.9%。第三是江苏和湖南,都是10人,占比都是5.7%。第四是河北,第五是四川和辽宁。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戴帽代表”比较多,从这里走出去的党的干部比较多。代表的来源地问题没有以往的数据可资比较,这里仅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六、结论
通过以上统计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十届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以下特征上发生了变化。
1.年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平均年龄下降了0.8岁,委员们的平均年龄相差不大,两届的年龄比较集中在55~69岁。通过年龄分组发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最年轻的、最年长的组别无人,55~59岁的人数较十届多了近18%,60岁以上委员占比从十届的72%下降到59%,这显示了一点相对年轻化的趋势。在委员长会议这一层面,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平均年龄下降了2.1岁,两届人大都是以55~69岁为主体,占总数的80%以上。从平均年龄、60岁以上人员占比来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总体的年龄构成还是偏向老龄化,但是出现了相对年轻化的趋势。
2.教育。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学历层次在上升。96%的人受过较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与十届97%的人受过大专教育相比,整个学历层级上升了一个层次。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者明显增加,海外取得博士、硕士学位者也大幅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学科背景发生巨大变化,在十届理工类与社科类的比重是2:1,在十二届这个比例反过来,具有学习社会科学背景的人员大幅增加,主要是经济管理、法学类。
3.职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职业背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届前政府官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甄补的最主要途径,来自政府系统的人员比来自人大系统的人员多11.2%。十二届则是来自人大系统的人员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甄补的最主要途径,比来自政府的人员多了20.6%。这其中尤其重视在全国人大系统内部甄补代表人选,来自地方人大的比例在下降。这说明全国人大在重视自身的专业化建设。
4.党派。这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中共党员仍然占有决定性的数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是其最高层领导人。endprint
5.性别。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仍然是男性为主体,女性占比从13.7%上升到15.4%,增幅不大。
6.民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汉族为主体,汉族有147人,占比达到84%。这个比重与十届接近。
从上述分析来看,这10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一方面在知识背景、学历层次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3以上的成员拥有研究生学历,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成员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在选举常委会成员时已经明显偏向从全国人大内部来甄选,改变了人大作为前行政高官“养老院”的形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汇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他们老成持重、学识优异、富有管理经验。这些因素有利于全国人大专业能力的提升。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受制于现有的体制,其面临的一些外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是年轻化的问题。只要全国人大代表不是直接选举、代表候选人提名制度仍由政党控制,年轻化的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一项荣誉、一项待遇仍是对党政部门、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领导人在退休之际的酬劳,全国人大也是继续发挥党的先锋作用和统一战线的重要领域。二是专职化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努力实现专职化,努力让一半以上的常委会成员成为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和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是副部级待遇,如此有吸引力的待遇为什么不能吸引人才在全国人大专职工作呢?表面看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时间太短了,一年的会期加起来不超过60天。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人大的功能还不够实化,限制了委员的作为。委员的专职化决定于人大功能的实化。三是甄选路径问题。从职业背景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甄选的路径中,我们可以看到2/3的成员来自党政军系统,其他社会精英很难进入。我们虽然看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在人大系统内部甄选了不少常委会的候选人,但是同时观察其年龄和任职经历可以发现,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大,之前也是从党委系统和政府系统退下来到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任职的,其职业训练的成熟期仍然是在党政系统。军队在我国也是一个特例,一直保持着7%左右的比例。来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各主要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各高校的领导人也都属于党管干部的范畴。从省级地方到中央国家权力机关的主要成员在一段时间内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核心机构,其人员甄选路径其实非常狭窄,来自非官方的人大代表非常少,民间或者社会精英几乎没有合法路径可以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仍富有行政化、官僚化色彩,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民意代表机关的角色不相符合。
注释:
[1]本文的统计截至2013年3月5日。175名委员中,其中1人在会期中辞世,2人在第一次会议后辞职,实为172人。文中的计算标准以选举产生的合法人数为准,委员数计为175人。
[2]各表中关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数据见张涛:《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分析:主要特点与发展面向》,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7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数据由作者自行收集与整理。
[3]张涛的统计是把研究生与博士、硕士单列,在我国拥有硕士、博士学位者,在学历上是研究生。本文为了便于比较,也采用单列,凡注明是博士、硕士者,则不计入研究生。从原始资料来看,这里的“研究生”应该指在近十几年来在各高校读的在职研究生文凭,没有硕士学位。而本文的统计中又以中央党校培养的这类研究生最多,占研究生类别比重达到85%,其生源是各省、地级官员。
[4]“戴帽代表”指在人大代表选举中,户口不在本选区,由上一层级人大分配给下一层级人大的基层代表候选人,他们算作本选区产生上一层级人大代表的名额。
参考文献:
[1]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詹姆森·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张涛:《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分析:主要特点与发展面向》,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7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刘乐明、何俊志:《谁代表与代表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分析》,载《中国治理评论》2003年第12期。
(作者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本科生吴慧婵、蔡淑珺帮作者收集了原始资料,在此表示感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