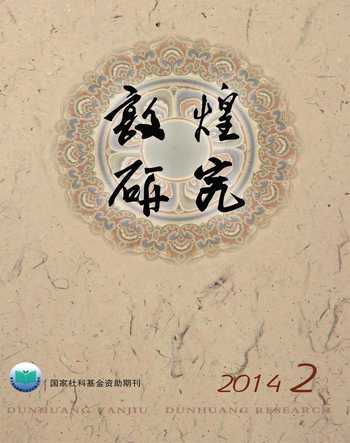敦煌书仪与日本《云州消息》敬语的比较研究
王晓平
内容摘要:《云州消息》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著名学者和文人藤原明衡以中国书仪为蓝本编写的一部书札范文。唐五代书仪中的敬语给日本“往来物”的语言以显著影响。日本书札范文中的敬语,不仅反映了那一特定时代文士人际交往的重要方面,也反映了两国文化的共同特点。
关键词:敦煌书仪;云州消息;敬语;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088-09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tiquettes and Writing Standards of D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 Honorific Speech in Unshū-Shōsoku
WANG Xiao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3)
Abstract: Unshū-Shōsoku, written by Fujiwarano Akihira, a famous Japanese scholar in the late Heian period, was a collection of epistle examples based on Chinese etiquettes and standards of writing. The standard honorific speech during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exerted a strong influence on expressions in Japanese Oraimono. These honorific expressions not only reflect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scholar communication during that time, but also indicate some common features shared by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Keywords: Etiquettes and standards of writing; Unshū-Shōsoku; Honorific speech; Comparative study
《云州消息》(以下简称《云州》),亦名《云州往来》或《明衡往来》,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著名学者和文人藤原明衡(Fujiwarano Akihira,989?—1066)编写的一部书札范文。由于明衡封出云守,故得名。这是日本第一部作为初等教育教材的“往来物”(“往来”乃“消息往来”之意)。
关于这部书,周一良先生早就指出:“《明衡往来》是以中国的书仪之类著作为蓝本的。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每卷编排各以正月至十二月为序。每月之内各有若干主题,如邀饮酒、贺升官等等。每一题材都是有往来两封信,可能因此而称为往来,全书共有信札二百余通。这种格式,显然是继承了西晋索靖《月仪》、唐代《杜家立成》以及敦煌写本书仪的传统,体现了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1]《云州》的诞生和中国唐五代的书仪在日本的流布有直接关系。除了下卷有一部分是所谓“单独状”,即不能明显看出是“问书”或“答书”的单书外,前两卷多为“问书”与“答书”两两相配,很可能编者本来就打算编写一部与中国书仪体制完全相同的书信范本,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实现初衷而已。说《云州》是“仿书仪”或者“类书仪”,均不为过。
周一良先生在同文中还对该书的影响有准确说明:“《明衡往来》一书,直到江户时期,还当作童蒙学习书法的教本使用,此书以后,出现了不少形式相似的书信范文集。都以往来为名,因此日本习惯称为‘往来物。这些书在日本文化史、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唐朝文化对日本影响的余波。”从这一点说来,《云州》是日本“仿书仪”或“类书仪”名副其实的开篇。
本书的影印与研究,现有东京高桥写真株式会社影印的内阁文库本《云州消息》、同社影印的神宫文库本《云州消息》、佐藤武义解说的《云州往来二种》[2]、《云州往来四种》①、《云州往来享禄本 本文》[3]、《云州往来享禄本研究与总索引》[4]、《藤原明横与云州往来》[5]等。不过,有关《云州》与敦煌书仪的比较研究的论著还不多见。
不论是唐五代的书仪,还是《云州》等日本“往来物”,丰富的敬语都是其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规范最主要的标尺之一。书仪中,最多的就是对对方表示敬意的词语。学界多将其分为谦词和敬词来加以探讨,张小艳曾提出谦敬语的概念,来代替一般使用的谦词、敬词的说法,将谦敬语定义为“指为了表达对别人的尊敬而使用的带有谦己或扬他的感情色彩的语词”[6]。这种表述较之“谦词”和“敬词”能更简洁地反映书仪中这类词语的特点,故本文也采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日本“往来物”中的这一类语汇。
同敦煌书仪一样,日本“往来物”也用“上、尊、贵、高、贤、华、荣、宠”等词语来指称对方事物以“扬他”,用“下、卑、鄙、弊、愚、拙、贫、微、浅、薄”等词语指称本人事物以“谦己”,在表示相互给予或行为施与时,用强烈对比的词语来严格区分相互关系。如接受他人的给予言“请、领”,给予他人称“呈、捧、奉”,而他人给予则言“贶、赐”等。这些实际上也起着表示敬意的作用。以上这些词语,在形式和效果上与中国书仪毫无二致。现代日语中仍然存在复杂的敬语体系,敬语的概念除了对他人表敬的尊敬语和对自身表谦的的谦让语之外,还包括由对对方的直接敬意而选择说法的“丁宁语”(礼貌语),日语中还有表示尊敬的补助动词“给”和表示谦让、礼貌的补助动词“侍”,这些在《云州》中都很常见。本文着重讨论前两类。
张小艳以达到有效交流,实现自己语气的目的与书仪负载的许多礼仪内容两方面,来说明书信中敬语完备的原因。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论古今,尊重对方都是沟通的前提,在特别讲究尊卑有序的时代,《朋友书仪》或者《吉凶书仪》这样在亲友之间流通的书信,更要尊字当头,等次分明。书信属于不对面的语言交流,不能用面部表情、形体动作来表达敬意,字字句句涉及到与对方关系表达的分寸,以至于敬语使用是否得当,就决定了书信的高下。从另一方面说,那一时代的敬语也就反映了交流者对相互关系的重视程度和交往规则。
唐五代书仪和日本“往来物”中的敬语,不仅反映那一特定时代文人人际交往的重要方面,也反映了两国文化的共同特点。虽然今人对古代这些表述方式已经相当陌生,但这些文献体现的某些准则仍然可以在社会生活中看到其变形的影响。今天学习日语的人,最感困难的多是对繁复敬语的掌握,原因之一正是对汉语敬语的历史知之甚少。
《云州》,原载《续群书类从》第9辑[7],为古写本的释读。重松明久著《新猿乐记 云州消息》,未照录《续群书类从》本原文,而是将其中全文进行训读,并加上注释[8]。重松明久所作的工作,还包括删除了重复的两篇,将其余各篇编号,并补充了宽永版本、内阁文库本和大田南亩校订本等所载佚文4通,共计113通。根据重松明久的分类,其中交游(57通)、赠答(7通)、请托(25通)、祭礼(9通)、仏事(15通)、借贷(12通)、升进(含推举,21通)、事情(19通)、占卜(8通)、质疑(14通)、地方官动静(15通)、作文作歌(4通),其中文人之间的交往占最大比重,与敦煌书仪中的《朋友书仪》最为相近。
在重松明久之后,进一步对《云州》进行深入的文献研究的是三宝忠夫夫妇,他们先后出版的三种著述,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原文资料。本文引用,全部根据其著《云州往来 享禄本 本文》释读的文字,括号内首先标注的是该书编号,其次是其内容属于哪类书信(问书日语称为“往状”,答书日语称为“返状”,还是不附回信的单独的书信日语称为“单独状”,即单书),原文中多有日语语法,必要时引用后以“谨按”略加说明,以便阅读对比。古抄本及校本中有明显的讹字如“枉”误作“狂”之类,径改,不予注释。
一 “礼人之词”的实义与虚义
古人的书信负载着交换信息和沟通情思两种功能,这两项功能还需要通过有限的文字来完成,因而简洁而得体的表述便是基本要求。书信中的敬语实际是一种经济的赞美形式,起着情感润滑剂的作用,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就更是如此。六朝唐代的书仪可以说是“说事仅N行,敬语一箩筐”。张小艳《敦煌书仪言语研究》指出书仪中谦敬语使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任何文体都难以企及的,这一说法,完全适用于日本的各种“往来物”,而《云州》正是其开先河者。
和敦煌书仪一样,在表示人、物与事为的词语之前,冠以表示尊卑的词素,是敬语最常见的方式。敦煌书札中竭力用高低两极的表述方式来将本人仰视对方的态度具象化。《云州》与敦煌书札相近的是,仰视的态度的以“高”来表尊的有高下、高驾、高座、高听、高命、高门、高览等。不仅与对方有关的物件须以高相称,而且对方的一切行为,也因为冠之以“高”字而显示出尊显的地位。
中国书仪中的敬语通过日本的“往来物”大量进入日语,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喜好仿照了一批新的敬语,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日语的词汇,增强了日语的表现力。《云州》中可谓满篇敬语,与敦煌书仪形同或相近的占大多数。
人的敬称:敦煌书仪中对对方的称谓,无不避免直呼其名,而以其下属称之,如陛下、阁下、足下、门下、座下之类。《云州》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而形成了对对方称谓的一系列用语,如贵下、芳下、尊下等,虽与敦煌用语不尽相同,但仰视的态度却有增无减。
【贵下】蹴鞠之兴云,若有诱引者,可相随也。汝如何者答以无此告之由,贵下定在议中欤?(卷上3通往状)
东京大学国语研究室藏宽永19年版本《明衡往来》(以下简称宽永本)注云:“贵下者,谓人也。”
贵下继没石之迹,同穿柳之艺,兼有谦下之词,还似表雄张欤?(卷上10通返状)
宽永本:“贵下者,礼人之词也”,“人虽有其能,称不堪之由,谓之谦下之词也。”
【芳下】会合何时许哉?芳下萧铿(鉴)十,中之能殊轶侪辈然而五。(卷上12通返状)
今日可参贯首之亭,密密有和歌之题,早春待莺云云。芳下可令座暖给乎?(卷下6通单独状)
谨按:贯首,官职名,处理殿上大小事务,职权显赫。密密,秘密;细密。
身体发肤,禀于芳下欤?潘岳、玉山不可及欤?(卷中25通返状)
【尊下】且又尊下无参内之间,无其兴之由,人人被申侍。(卷中70通返状)
谨按:参内,进宫,进入宫廷。
【贵殿】贵殿若无指御障,令同道给乎?(卷上45通往状)
谨按:贵殿,本指对方的居所,转义为对对方的尊称。
地的敬称:仰视态度延伸到一切与对方相关的事物。敦煌书仪中有贵道、贵藩、贵封、贵境、贵州等语词。贵,尊贵,敬词,用在表示行政区划或辖境的语词道、藩、封、境、邑之前,敬称对方的辖区或领地。这样的用法也见于《云州消息》,以贵表尊地的有贵馆、贵境、贵殿、贵房等。
【贵州】为成不日之功,可催成风之声。栋梁之材,出于贵州云云。(卷下49通单独状)
【贵境】抑藤井今武为访近亲,参下贵境,经回之间,可赐一顾。(卷上84通)
【贵馆】贵馆修良之名,已被古今。猛虎渡河,可比其德欤;狼戾之民,皆以雌伏云云。(卷下54通单独状)
【贵殿】先参贵殿,相共可咏万岁千秋之句也,其后参处处耳。(卷中1通往状)
谨按:贵殿,此指对方居所。参为本人前往的谦让语。
物事的敬称:《云州》中出现之物事无不可冠以谦敬之词素。这些词素多已虚化,变成虚拟性的套语。如“高门”一词,本来是与《汉书》中“于公高门”典故相联系的,在《云州》中作为敬语可以不问其门高低一律泛指他人之门。卷上25通:“旨酒一樽,可相具侍,嘉肴一种,令随身给耳,可追河朔之饮欤?明旦可参高门,依巡道也。”宽永本“高门”有注:“谓人门也。《汉书》于定国,字曼倩,父于公高大门而繁昌也。”进而《云州》中又多以高门指代对方的住宅。
【高门】明旦可参高门,依巡道也。令相待给耳。(卷上25通往状)
【高驾】须抛剧务,随高驾也。(卷上26通往状)
宽永本注:“随高驾者,随人行也。”“高驾”本是他人之车的敬语,又可以敬指他人出行。
言的敬称:对方来信,《云州》中有恩简、恩章、贵札、严札、严命、严训、严旨,请对方查看,谓“乞垂照鉴”、“乞垂鉴察”。“严”在汉语中有尊敬、尊重意,“严旨”即为圣旨,“严命”即对君父、长上之命的敬称,在《云州》中则意义更为扩大为对对方来信或指令的敬语。上卷2通题名“请严札事”、11通题名“请严命事”、12通首句的“伏奉严旨”、20通题名“请严训旨”,下卷170通题名“请严命之事”,大致都是收到来函的意思,其中“严命”、“严旨”、“严训”更突出的是对对方来函中所表述意见、建议和看法的敬重。
【严命】抑藤井今武寻桑梓之地所来也,难背严命,聊访旅宿。(上卷85通返状)
上卷2通“请严札事”是一封“返状”,即答书,来信(即往状)一封祝贺新年的信,近于今日的贺卡,而回信的中心内容是表示谢意。“请严札”是对收到来信的表敬说法。重松明久的校注注释“严札”一词为“严肃的、不能反对的信件”(いかめしく、反対できない手紙)[8]74,似乎忽略了“严札”的敬语性质。宽永本此处有注:“严札者,谓人消息也。”[2]72对“严札”的敬语性质的理解,正胜于重松上述所说。
意的敬称:对于对方的想法(意见、召唤、建议、指教等)有贵命、高命、尊旨、高旨等敬称。
【贵命】乏少之物,可类辽东之豕,但可随贵命也。(卷上5通返状)
【高命】但于诗歌之游,虽无其望,依难背高命,以不申故障侍。(卷中33通返状)
相反,自己的意见以素怀等来表示谦恭。
【素怀】忝迴花轩,素怀可足。(卷上29通往状)
宽永本注:“素怀,本意之由。”
事为的敬称:敦煌书札中不仅有着丰富的表敬名词,而且表敬动词也不胜枚举。《云州》中的这类敬词也十分丰富。如高览、高听等。
【高览】藏人弁有秀句,可谓席上之珍也。件和语在一品宫女房许云云,可经高览欤?(卷中18通往状)
谨按:藏人弁,官职名。件,这个、所说的、上述,同我国唐代用法。“件和歌”就是上述和歌。
【高听】昨日头中将所被示也。某事同及高听欤?(卷上9通往状)
谨按:头中将,官职名。
《云州》中的谦让语也十分丰富,自己的去信,称为“疎简”,自己去参与,言“欲付骥尾”,如“诗酒之会,游览之兴,聊付骥尾”(卷上1通往状)。指称对方的屋舍,指称自家的屋舍,则言“蓬屋”、“龙洞”、“筚糊户”,自己的儿子称为“愚息”(下卷第163通)。宽永本对敬语用法多加以注释。
【枉驾】无殊御障,必可枉驾给也。(上卷27通)宽永本有注:“枉驾者,人可来由也。”
【佳招】上卷30通题名“佳招事”,宽永本注:“人之招我也。”
“拜”是《云州》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表示敬意的谦让语。凡涉及本人与对方或与对方相关事物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都须在动词前冠以“拜”字。《云州》中有拜谒、拜贺、拜觐、拜除、拜领等。
【拜觐】拜觐之次,可承芳训。(卷下5通单独状)
【拜领】拜领三匹。右以此茧丝之赠,可为蝉翼之衣也。(卷上16通返状)
所给之牛,悦以拜领。虽千里之骏足,可无其益。(卷中52通返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书信涉及到与对方有关的行动冠以“拜”字的词语,远不及现代日语书信。现代日语书信中比较常见的也还有拜观、拜颜、拜具、拜启、拜察、拜辞、拜谢、拜受、拜诵、拜扫、拜呈、拜读、拜眉、拜复等。
二 美辞表敬、暖辞表敬与复语表敬
敦煌书仪中美化对方以表敬的,有华、芳等字。《云州》中不仅存在很多同样的词汇,而且还有变化和扩展。花同华,《云州》中都用花,少用华。出于日本人对花的钟爱,在言及他人事物的时候,多冠以花字,有花驾、花客、花轩、花厩、花毂、花辕等敬语。
【花轩】出立之所,可枉花轩也。(卷上13通往状)
忝迴花轩,素怀可足。(卷上29通往状)
宽永本注:“花轩者,人车也。”
白地罢出之间,忝枉花轩,不谒青眼,遗恨多端。(卷中36通往状)
明朝于右近马场,可试骏足,请辖花轩,早旦可御。(卷下34通单独状)
寻春花,玩秋柴(叶)之日,忝枉花轩,过荜户,老之幸也。(卷下38通单独状)
【花驾】路过蓬门,忝抑花驾,为从后乘也。(卷上9通往状)
【花毂】明朝暇日也,令促花毂,如何?聊欲追从。(卷上37通)
宽永本注:“花毂谓人之车也。”
【花辕】古集一两卷,周四郎所志也,未及披露。避暑之次,可枉花辕也。(卷下46通单独状)
可然之所,令促华辕给,如何?(卷上25通往状)
若有御暇,可枉花辕也。莫及外闻。(卷中6通)
宽永本有注:“花辕,车也。”
【花客】所召《古今和歌集》,或花客借取,未被返送。(卷中42通)
【花厩】花厩之中,定有细马欤?(卷上160通)
《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指出意为香美芳洁之芳也常用在名词性语素前敬称与对方相关的事物。用芳符、芳函、芳翰、芳诲、芳及、芳缄、芳示、芳书、芳问、芳音、芳猷、芳札等以敬称对方来信。《云州》以芳来美化对方事物的则有芳猷、芳言、芳恩、芳下、芳缄、芳训、芳契、芳札、芳赠、芳谈、芳命、芳尘、芳誉等。
其中既有芳札、芳缄用作表示对对方来信的敬称,也有用芳的语素加上表行为意义的词来表示对对方施及自我行为的敬称,还有加上对方身体部位以指称对方本人的。如:
【芳札】郁念之处,幸投芳札。数日积思,一时解散。(卷中28通往状)
【芳缄】下向之后,山重江复,朦雾难开,适逢芳感缄,喜中之喜也。(卷中二十九通返状)
右下向之后,山重江复,蒙雾难开,适逢芳缄。(卷中33通)
宽永本:“芳缄,封也,书状名也。”
【芳训】拜觐之次,可承芳训。(卷下5通单独状)
【芳猷】彦真芳猷,甚虽古体。(卷上17通单独状)
【芳命】然而难背芳命,改定他人。(卷上44通返状)
自爱之处,令蒙芳命。弥增面目者也。(卷中17通返状)
【芳赐】甲宅之果,丙穴之鳞,期芳赐耳。(卷下43通单独状)
【芳契】交态已久,莫忘芳契。(卷下43通单独状)
【芳恩】有年来之芳恩,适仰何可存疏略哉!(卷中86通返状)
【芳谈】芳谈之间,日景渐暮,所陈旧事,足断肠矣。(卷中20通往状)
【芳誉】依治国之芳誉,频飞隼舆者,福禄永保,升无疑欤!(卷下50通单独状)
【芳颜】其次参亭子,可谒芳颜也。(卷下11通单独状)
日本本不产玉,日本人对玉的喜爱远不及中国人,但在《云州》中也有一些以玉来美化对方事物的,如玉颜、玉山、玉章、玉带、玉条、玉体等。今天日本人的书信最后书收信者之名,其后有时书“玉案下”三字,乃是这种敬语习惯的延伸。此可谓玉文化影响日本人审美观之一例。
【玉颜】参内之次,可谒玉颜。(卷下2通)
【玉体】自爱玉体,不可混风尘之容。愚老之言,如良药之苦口。(卷下21通)
【玉章】悚郁之处,故投玉章,且为悦,且为恐耳。(卷上2通)
宽永本此处有注:“玉章,消息名也。”
以光来美化对方的容貌,有光仪等。光仪在汉语中指光彩的仪容,称人容貌的敬词。《云州》有时意同光临,意指他人的来访。卷上19通答书:
依无指事久不出仕,只偃息蓬屋耳,而昨日藤亚相源拾遗忽以光仪。
是说因为没有什么任务一直没有上朝,呆在家中,昨天藤原拾遗忽然来到家中。重松明久校注本注释光仪一词为“他人来访的敬称”(他人の来訪することの敬称)[8]89,所言是。又中卷78通问书邀请对方到嵯峨别墅来:“偷闲光仪,莫妨鸾台之剧务欤?”是说对方抽空前来,该不会妨碍公务吧。光仪亦同光临。卷下37通单书文士雅集演奏乐曲,询问对方能否前来:“八月十五夜,云霞若晴,忝可有光仪?”也有光临之意。
《云州》中主要有温、恩、嘉、佳等暖辞表敬的用法,这与敦煌书仪完全相同。以温来表示对方亲切感的有温颜、温言等。
【温颜】改年之后,须先拜温颜也。(卷上2通返状)
宽永本注:“温颜,人容。”
【温言】只今于禁掖边,可蒙温言也。(卷上22通返状)
宽永本注:“温言,人之雅言也。”
某奉仕故殿数十年,朝蒙教训,夕承温言,加之官爵只在吹嘘,世路之支莫不顾眷。每忆旧恩,落泪千行。(卷上32通返状)
以恩来表示对上司行为感恩的敬词有恩意、恩简、恩诲、恩唤、恩庆、恩示、恩章、恩赏、恩招、恩召、恩问、恩容等。
【恩简】不审之处,今被投恩简,如见青天于月桂。(卷上11通返状)
请恩简。(卷中29通返状)
宽永本“恩简”注:“书状也。”
【恩章】请恩章事。(卷上4通返状)
奉恩章旨。(卷上40通)
宽永本注:“恩章者,消息也。”
【恩示】世间之事,如蒙瓫对壁。今有恩示,似披雾望天,欣悦欣悦。(卷上4通返状)
宽永本注:“恩示者,为我谓告物事也。”
世间事,郁念多端。今有恩示,欣感欣感。(卷上20通,返状)
【恩诲】祭间事郁结殊甚,故给恩诲,如褰霭望月,欣悦欣悦。(卷上22通返状)
宽永本注:“恩诲者,得今消息也。”
【恩问】今有恩问,欣感尤深。明日参谢之次,欲承严旨。(卷下18通返状)
其间之事,尤可有恩问。(卷下49通单独状)
可然之间,犹可有恩问也。(卷中125通往状)
【恩招】明朝事虽无养由基之艺,若有恩招,可豫参侍。(卷上12通,返状)
【恩唤】此间忽蒙恩唤,抃跃之甚,以何比之哉!(卷上30通返状)
宽永本注:“恩唤者,人之呼我也。”
【恩容】期日可近,后素(旁注:绘也)之态,殆可阙如。绘师某候殿下者也。免给一日之暇乎?事尤要须也。枉垂恩容。(卷上17通返状)
【恩庆】诗客四五人,伶人两三辈,不期而来会,是皆当世之好士也。只依迟尊下光临,豫空座右耳。抑恩庆之甚也。忝回花轩,素怀可足。(卷上29通往状)
谨按:依;因为,由于,同唐代用法。迟,等待。
【恩意】承闻之次,令奏达给;成败之间,可有恩意也。殊有容引者,幸之无极也。(卷上39通往状)
以嘉来表示行为敬意的有嘉贶、嘉招等。
【嘉贶】书窗虽知聚萤之业,文薗未遇获雉之欢。今之嘉贶,尤可珍重。(卷上6通)
谨按:薗,同园。六朝唐代俗字。
汉语中御多仅用于对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而在《云州》中御可用于对他人一切所作所为及所用物品的敬称,成为用得最广泛的敬辞,如御暇、御牛、御歌、御带、御志、御词、御语、御作文、御障、御师、御消息、御使、御杖、御时、御供、御申文、御祭、御舞、御物忌、御弓、御庆、御车、御出、御童、御学问、御会、御庆贺、御坐、御座、御禊、御斋会、御产、御装束、御巡、御助成、御说、御所望、御边、御返事、御用、御用意、御览等。这种御字的泛滥,可谓敬语的重口味。
【御障】若无殊御障者,可枉花辕,只是连句许也。南轩之泉,北窗之风,才为来宾之储。(卷上27通往状)
无殊御障者,必可令枉驾给也。(卷上27通往状)
被仰云来月可参春日。若无殊御障,被同道乎者,仰旨如斯,悉之谨言。(卷中63通往状)
谨按:御障,障碍、故障。无御障,即无碍,不反对,没有问题。
【御览】奥州白丁名取胜村,长八尺有余,力扛鼎云云,可御览也。(卷上27通往状)
谨按:奥州,古陆前、陆中、陆奥三地的总称。白丁,兵丁。
虽然兰蕙之契芳,何有隔心哉?李善之注,可为规模,能可御览也。(卷中47通返状)
【御志】右捧物悦以给了。御志之至,不可申尽侍。(卷下94通返状)
以御为敬语的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日语。不仅令人喜爱和愉快的东西前面冠以御字,如御便当(盒饭),而且连洗手间也被叫做御手洗。这样的用法就完全是日本式的了,御字也就彻底虚化了。
敦煌书仪中以复语来表达对对方的情意,除了表示礼仪的郑重的“顿首顿首”之类的以外,也有表达本人的喜悦、幸运、盼望、无奈、惶恐等情感的,还有表现对对方的关切、叮嘱、希望的。前者如“幸甚幸甚”、“所望所望”、“奈何奈何”,后者如“珍重珍重”、“努力努力”等。在吉凶书仪中还有表哀恸的“痛深痛深”等。《云州》中与敦煌书仪中相同的或相近的复语敬语颇多,如:
【幸甚幸甚】改年之后,富贵万福,幸甚幸甚!(卷上1通往状)
自他幸甚幸甚!(卷上58通返状)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莫慕閇户先生。(卷上11通往状)
【欣感欣感】今有恩示,欣感欣感。(卷上20通返状)
【欣跃欣跃】故给恩诲,如褰霭望月,欣跃欣跃。(卷上22通返状)
【欣悦欣悦】不审之处。今被投恩简,如见青天于月桂,欣悦欣悦。(卷中11通返状)
【恐悦恐悦】今故蒙严命,恐悦恐悦。(卷上28通返状)
【有兴有兴】今胜村事,依命奉之。甚有兴有兴。(卷上28通返状)
【为恐为恐】身非相如之尊,何关上客之礼?为恐为恐。(卷上30通返状)
【战栗战栗】乱暇不候,仍不能扈从,战栗战栗。此寸(等)旨,故可参启。(卷上26通返状)
【穴贤穴贤】莫及外闻,穴贤穴贤。(卷中6通往状)
谨按:穴賢(あなかしこ),感动词,诚惶诚恐之意。
【可然可然】若是鸾凤之群,偏嫌鸟雀之类欤?其理可然可然。(卷上4通返状)
【可佳可佳】美酒一樽,令相具给者,最可佳可佳。(卷上31通)
【悚息悚息】今有此命,悚息悚息。(卷上32通返状)
【曷若曷若】远夷以贫薄为龙洞,而或人云:“虚室如洞”,不见本文欤?曷若曷若。(卷下89通往状)
【莫漏莫漏】人心不同,譬如其面。不得意之人,定嘲此事欤?梦梦莫漏莫漏。(卷下61通往状)
收尾敬语有“再拜稽颡”、“顿首谨言”等。
【再拜稽颡】再拜稽颡,谨言。(卷下28通)
【顿首谨言】诸事繁多,不能委闻。厶顿首谨言。(卷下53通)
唐代书札中,万福用来祝福对方,愿其身体起居健康多福,这种说法运用广泛,影响巨大,远及域外人士。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多次以万福来问候对方,如卷2:“仲春渐暄,伏惟押衙尊体动止万福。”[9]万福作为问候语,也见于《云州》。卷上1通有“改年之后,富贵万福。幸甚幸甚。”卷中1通往状:“年花始换之后,起居万福欤?”卷下1通:“年花初换之后,起居万福欤?”这些都是过年时发出的信函,被视为日本最早的贺年卡,万福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问候语。
三 书信时代的中日文化交融
“往来物”是日本从镰仓时代到明治初期作为初等教育的教科书、辅助读本而编写的书籍总称,平安时代就是书信的范本,镰仓时代以后变成了作文备用的短语、词汇、文案、文例集,并将社会常识、实用知识编入其中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这样的变化,但在深刻影响初等教育和庶民教化方面发挥的作用却始终是重大的。《云州》以及后来的《十二月往来》、《杂笔往来》、《尺素往来》、《释式往来》、《山密往来》、《东山往来》、《庭训往来》、《贵岭问答》、《骏府往来》、《商卖往来》等多延续了《云州往来》的基本形式,在敬语使用方面也可谓一脉相承。特别是《异制庭训往来》,篇幅大为增加,涉及的内容更为丰富,成为研究当时文化语言的重要资料。
那么,当时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痛快地接受书仪的整体形式和基本内容,尤其是对其中的敬语如此模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就想到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以汉唐文化为规范来建立自身文化的文化风气。从《云州》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和贵族文士间相互交往的实际活动来看,包括相邀参加蹴鞠、三月三曲水之宴、七夕之会、中秋赏月、祭泰山府君等中国文化色彩浓郁的文化生活、相互借用《文选》、《古诗十九首》、《新乐府》等典籍和探讨中国文史掌故、切磋诗文等话题,以及拜官、赠与、游览、造访等日常活动,六朝初唐书仪中涉及的话题几乎应有尽有,此外,还有敦煌书仪中没有的和歌会、弓会等特有文化活动的内容。中国的书仪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才能流布并被仿作,促使《云州》这样的日本化书仪得到广泛学习和运用的机会。
卷中30通往状和31通是有关三月三曲水之宴的通信。当时的皇族和贵族在这一天仿造六朝和唐代曲水流觞、赋诗同乐的故事,这是全面移入汉唐风俗之一例。前一封是邀请信,请人同往,后一封是回复,表示欣然前去:
今朝为行解除罢向东河。白川之花簇雪,锦陌之柳垂烟。三月上巳之宴,始于周公;曲水之游,后代之人,尤可钦仰也。凤鹏篱鷃,大小虽异,逍遥惟同,何如不泛羽觞?犹宜事禊除也。如此之时,不申事由。遗恨无极。厶谨言。
沽洗第一日 右少辨平
左马头殿
曲水宴,唐国则周公为滥觞,本朝亦显宗帝作权舆。其后连连不绝,传为胜躅。下官虽不才,慕其先风。侍燕席之末,可献一绝也。荒芜之词,谓时人如何?厶谨言。
廼时 左马头源
可以说,正是宫廷贵族中的中国文化热,构建出与六朝初唐书仪流行多少相似的人文环境,使得书仪中出现的事物和情绪不再陌生,才会有与敦煌书仪中类似的大量敬语在异域出现。
进一步说,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特征与中国六朝以来的等级制度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性。已故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曾经谈到这种集团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团内部的结构,常常由严格的上下关系构成[10]。同时某些方面存在上下关系的垂直因素,某些方面存在水平层面的因素,因时间、地点不同而某种因素会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书仪正全面地体现出这种垂直和水平因素并存而各自以不同方式处理的格局。其中表明通信者以及信中所涉及者的复杂关系的敬语,经适当简化之后很容易在日常交往中变通运用。
另一方面,从“往来物”使用者,即平安时代以来的作家本身来看,他们像其他时代的日本作家一样,被“巧妙地编入他们所属集团里,这个集团对外部具有封闭性的倾向”[10]16。文学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文化,或纳入统治体制的整体之内。平安朝的文学,在贵族社会里适得其所。贵族文士之间的书信是建立内部密切关系的重要手段,表明对对方敬重和本人放低姿态的敬语,不仅可以使信中涉及的事情更容易得到对方接受和理解,也是认同对方地位和表现本人教养的最简便形式。中国书仪中的某些客套化的敬语表述反而适合这些贵族文士希求快学好用的口味。
卷中42通问书,是对先前对方来信要求借书的回复,说对方要借的《古今和歌集》被人借去,尚未还来,各家的和歌集可以借出,希望对方看完后快些还回来。自己也要向对方求借白居易的乐府诗,请交给自己派去的李某,等自己将《秦中吟》、《琵琶行》抄写之后就奉还,另外还想借《扶桑集》,也请交给派去的人:
所召《古今和歌集》,或花客借取,未被返送。诸家集,随候奉借。御览之后,慥可返给也。先日所申《乐府》,付回李可给者,尤所望也。《秦中吟》、《琵琶行》书写之后,可返献也。《扶桑集》同可一见侍,可令预使者给也。不宣谨言。
月日 直讲清原
春宫学士殿
谨按:“御览之后,慥可返给也”,您读过以后,就请一定快些还给我吧。慥,同,有赶紧、急忙和确实、一定两义。《扶桑集》为平安时代诗人纪齐名的诗集,全12卷,今仅存两卷。
第43通是上一封的回信,是说已受到各家的和歌集,表示读完后就会奉还,遵嘱将《乐府》和《扶桑集》借给对方,希望对方尽快还回来。信中谈到《扶桑集》里有很多书写的错误,《秦中吟》、《琵琶记》是自己幼年时做的訓点(句读和标出日语读法),不好意思示人。
诸家集
右给毕。一见之后,早可返献也。赤人、黑主之家集,犹可求给也。《乐府》、《扶桑集》,随命奉借。《扶桑集》纰缪已多,是书写之人误也,无画马慎欤?《秦中吟》、《琵琶引》令书写之后,早可返给。竹马之比所点,狼藉也。有耻于外人之所见也。谨言。
即时 春宫学士橘
谨按:“赤人、黑主之家集”,奈良时代宫廷歌人山部赤人和平安时代著名歌人大友黑主各自的和歌集。两人的和歌分别收在《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中。“竹马之比所点”,即幼年之时所作的解读标记。
《云州》中有一些文士间相互借阅书籍的通信,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国典籍以抄本流通的情况。
诚然,自然环境的共同点也是两者文化容易交汇的一个条件。周一良先生指出:“书仪中联系季节的问候套语,对日本尺牍文字也有影响。中日两国的气候,四季变化大体比较显著,这个共同特点,看来使日本较易接受并保持这一中国传统。”[1]254平安时代以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条件和方式虽有很大变化,但书信文化却源远流长。清理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就离不开对《云州》以后的一系列“往来物”的研究,特别是对《异制庭训往来》的研究。拂去落在上面的等级尊卑的过厚灰尘,敬语也可以变成凝结在信笺上的微笑,今人学习一点敬语,想来也是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1]周一良.周一良集:第4卷[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52-253.
[2]佐藤武义,解说. 雲州往来二種[M].东京:勉诚社,1981.
[3]三保忠夫,三保サト子. 雲州往来享禄本本文[M].大阪:和泉书院,1997.
[4]三保忠夫,三保サト子. 雲州往来研究と総索引[M].大阪:和泉书院,1997.
[5]三保忠夫,藤原明衡と雲州往来[M].东京:笠间书院,2006.
[6]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59.
[7]塙保己一.群書類従:第9辑[M].东京:平文社,1992:390-437.
[8]重松明久.新猿楽記·雲州消息[M].东京:现代思潮社,1982:73-258.
[9]深谷宪一译.入唐求法巡礼行記[M].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268.
[10]叶渭渠,等译.日本文化论[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241.
——“内”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