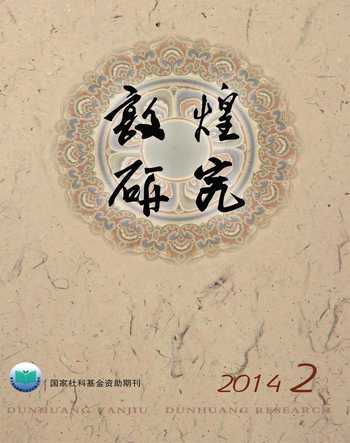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宝冠造型分析
内容摘要:本稿以实地调查与学界披露的相关资料为基础,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宝冠造型,存在卷草纹与牡丹纹两类宝冠,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获得长足发展。卷草纹宝冠上承唐、五代传统,在吸收宋代世俗卷草纹因素后继续发展。牡丹纹宝冠为菩萨像造型的创举,是宋人酷爱牡丹及牡丹栽培中心南移四川的产物。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类宝冠的造型灵活多变,尤其绍兴年间(1131-1162)彰显新时代创造力。南宋中晚期,这两类宝冠的造型繁缛细密达到极致。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宝冠造型演化,深刻地反映了佛教艺术民俗化、地域化的过程。
关键词:四川宋代菩萨像;卷草纹宝冠;牡丹纹宝冠
中图分类号:K87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2-0040-13
An Analysis of the Coronet Modeling of the Song Dynasty Stone Bodhisattvas in Sichuan
QI Qingyuan
(Academy of Art & Desig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published material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oronets of Song dynasty stone bodhisattva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oronets with patterns of coiled floral and peony were highly developed from late Northern Song to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s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absorbing the elements of secular coiled floral design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coronets with coiled floral designs were further developed; coronets with peony designs were a creation for Bodhisattva images because the peonies were very popular among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and the center of peony cultivation moved to Sichuan. From the late Northern Song to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two kinds of coronets were flexible in design, especially in the Shaoxing era (1131-1162)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showed the creativity of that time. In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patterns of these two types reached their perfect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onets of Song dynasty stone bodhisattvas in Sichuan reflects the secular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processes of Buddhist art.
Keywords: Song dynasty bodhisattvas in Sichuan; Coronet with coiled floral designs; Coronet with peony design
四川(含重庆)系宋代两大佛教石刻造像发达区域之一,其菩萨像的发展规模远超佛像,以胁侍形式表现者数量众多,作为主尊表现者也不少,且形体庞大者亦多,菩萨一跃成为佛教造像的重心。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比较密集地分布在大足、安岳两县(图1),邻近的合川、江津两县也有零星分布。北宋早中期实例稀少,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为实质性发展阶段,自11世纪80年代至13世纪40年代前后,造像活动长达160年。
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的调查研究是伴随整体佛教造像进行的。以往,学界在对各地区石窟及摩崖造像进行总录编纂、概论叙述及分期断代考察过程中,也曾涉及相关的菩萨像信息[1-4]。但是,就菩萨像造型而言,迄今尚无专论,学界还无从了解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的发展脉络和规律。笔者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1},并参考以往学界成果,应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样式论相结合的方法,对菩萨像进行系统化分类及样式考察,以期得出四川宋代菩萨像造型的规律性认知,并尽可能揭示其中蕴藏的深层文化内涵。
笔者选择有明确纪年且保存较好的实例作为切入点,建立大致的年代标尺,进而将无纪年实例比照纪年实例插入相应的位置,从而建立菩萨像发展序列。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造型涵盖宝冠、服装、装身具和躯体形态四要素,其中宝冠一项内涵十分丰富,为考察菩萨像序列和编年的首要因素,本稿抽出作为单独研究对象。具有一定数量的宝冠佛像之宝冠与菩萨像宝冠造型同步发展,故一并分析。
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一概头戴宝冠,宝冠主体则为植物纹样。依据植物纹样类别可以分为卷草纹宝冠与牡丹纹宝冠两类,每类纹样又可细分为不同的型与式。基于这种多层次的类型分析,从而建立菩萨像序列,进而揭示其造型演化规律。
一 卷草纹宝冠
四川宋代菩萨像及宝冠佛像,其卷草纹宝冠自始至终盛行不衰,北宋卷草纹宝冠较多因袭唐、五代传统,南宋卷草纹宝冠颇多受到世俗纹样影响,至南宋中晚期形成异常繁缛华丽的造型。根据卷草纹形状的差异可以细分为两型:其一,茎叶互用型卷草纹宝冠,一个个S形叶片翻转连接,茎叶互用,连绵相续,用于菩萨像宝冠;其二,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宝冠,以抽象的枝条构成波状起伏或内旋环绕的骨架,其上添加繁茂卷叶,用于菩萨像及宝冠佛像。至南宋中晚期,后者逐渐取代前者,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宝冠造型。
1. 茎叶互用型卷草纹宝冠
这种宝冠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南宋晚期罕见。北宋晚期及南宋之初实例上承晚唐、五代菩萨像宝冠传统,南宋早中期实例推测受到当地南宋墓葬雕刻等世俗因素影响,卷草纹发生显著变化。北宋及南宋之初卷草纹宝冠,多数S形叶片以中间化佛为中心,呈漩涡状左右对称配置,叶片圆润且往往刻画叶脉纹,布局疏朗。诸如,大足北山佛湾第180窟左壁第4尊北宋政和六年至宣和四年(1116-1122)观音像 (图2) {2}、第149窟南宋建炎二年(1128)观音像(图3),以及江津高坪石佛寺北宋第1龛水月观音像与第3龛日月光菩萨像宝冠[5]。各实例卷草纹细节刻画略有差异,表现意匠则颇为一致,沿用了晚唐、五代大足、安岳地区菩萨像卷草纹宝冠的造型传统(图4)。
南宋早中期实例,如大足北山佛湾第136窟南宋绍兴十二年至十六年(1142-1146)玉印观音像 (图5){1}、合川涞滩二佛寺南宋菩萨像 (图6) {2}。其卷草纹宝冠趋向复杂,一方面冠体增加了U形璎珞、如意云纹,团花等造型因素。另一方面卷草纹叶片小而多,布局繁密,与泸县宋墓雕刻卷草纹如出一辙(图7)[6]。
2. 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宝冠
(1) 菩萨像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宝冠
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约自11世纪80年代至12世纪70年代,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兼有疏朗与繁密两种形式;第二阶段南宋中晚期,约自12世纪80年代至13世纪40年代,茎蔓添叶型卷草纹概为繁密形式。
第一阶段茎蔓添叶型卷草纹,以s形、m形或8字形茎蔓为骨架,向上下或左右延伸,依托茎蔓有序地排列若干圆滑的c形叶片,形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布局,配置在单层或双层冠体。诸如安岳圆觉洞第15龛北宋元符二年至大观元年(1099-1107)观音像 (图8) {3}、大足北山佛湾第180窟右壁第4尊(1116-1122年)观音像(图9),以及大足北山佛湾第136窟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文殊像(图10),以宝冠中央为轴线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左右对称布局,由中央向左右或两上方延伸呈漩涡状密集排列,高低错落起伏,具有强烈节奏感和流动性。相似造型宝冠已流行于四川唐代菩萨像之中(图11),造型简洁,宋代则在前代基础上发生新变化。如北山佛湾第136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观音像宝冠卷草纹骨架作m形(图12),合川涞滩二佛寺主尊两侧南宋胁侍菩萨像宝冠卷草纹骨架作8字形结构(图13),前所未见。
第二阶段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在第一阶段三种骨架基础上混合或叠加使用。突出表现在茎蔓内旋成一个个圆形或圆环形,其上密布卷云状C形叶片,宝冠下缘装饰穗状璎珞、簇花、摩尼珠等,异常繁缛。诸如,大足的大佛湾、佛祖岩、广大山、松林坡,以及安岳的华严洞、毗卢洞、茗山寺、高升大佛寺等石窟及摩崖造像中菩萨像宝冠,惜缺乏纪年资料。学界认为宝顶山造像由南宋赵智凤经营于淳熙六年(1179)以后的一段时间[7-9],然而,学界对上述安岳地区宋代造像的年代尚未取得统一认识。上述大足、安岳两地菩萨像,无论宝冠,抑或服装、璎珞皆呈现高度一致性,推测两者年代应比较接近。两地菩萨像宝冠的茎蔓添叶型卷草纹,茎蔓上密集排列云状叶片造型,在邻近大足、安岳的华蓥安丙家族南宋中晚期墓葬雕刻中高频率出现,可作为相对年代参考(图14)[10]。此外,安岳千佛寨第24窟南宋绍熙三年(1192)大势至、观音像(图15),残存宝冠茎蔓添叶型卷草纹的细部特征与上述实例契合。由此可知,上述安岳地区菩萨像应为南宋中晚期作品。
第二阶段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宝冠其它因素呈现多样化面貌。以往常见宝冠中间设置化佛或宝瓶形式依然流行,其中化佛的应用呈泛化趋势,由观音像扩大到十二圆觉众菩萨像(图16)、地藏菩萨像[11],以及涅槃图像中诸菩萨像等(图17),而宝冠中间设置宝瓶依然为大势至像的标志{1}。此外,菩萨像宝冠新出现饰宝塔、五佛与七佛三式,下文分而述之。
其一,饰宝塔。迄今仅见安岳茗山寺第2龛右侧菩萨像一例,宝冠中间设置七层密檐式宝塔,底层安结跏趺坐佛像一尊(图18)。宝冠中间设置宝塔作法在以往菩萨像中罕见,可能受到来自印度帕拉朝弥勒菩萨像造型影响,七层密檐式宝塔则为典型的中国式样。
其二,饰五佛。实例一,安岳茗山寺第3龛文殊像,宝冠饰五尊结跏趺坐佛(图19)。自左向右,第一尊佛右手举起,似施无畏印,第二尊佛施禅定印,第三尊佛施拱手印,第四尊佛印相不明,第五尊佛左手施触地印,右手举至胸前。位于中间第三尊佛的拱手印与大足、安岳地区毗卢遮那佛手印一致,推测为同种尊格。第一尊佛、第二尊佛及第五尊佛分别对应金刚界五佛的不空成就如来、无量寿佛、阿閦佛,故此五佛应视为金刚界五佛。实例二,安岳高升大佛寺第1龛右侧普贤像(图20) {1},位于宝冠中间的第三尊佛略大,施弥陀定印,可判断为阿弥陀佛。余者双手笼于袖中放置腹前,无法判断其尊格属性。
菩萨像宝冠饰五佛造型在宋辽金时期流行开来,具有时代共通性[12—14]。唐宋时期翻译密教经典多提及五佛冠{2},表五智之义,为毗卢遮那佛、诸佛顶尊及诸菩萨等所戴之冠。上述文殊像宝冠配置密教金刚界五方佛,符合经典原意。普贤像宝冠配置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五佛,特别强调了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可视为《华严经》末后普贤菩萨十大行愿导归极乐净土的产物{3}。
其三,饰七佛。实例有三,安岳高升大佛寺第1龛左侧文殊像(图21)、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5龛左胁侍菩萨像{1}。宝冠中七佛分上下两层配置,上层二佛,下层五佛,均结跏趺坐。位于下层中间者形体略大,头戴宝冠且露出部分发髻,施拱手印。余者均不戴宝冠,双手置于袖中交于腹前。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5龛右胁侍菩萨像(图22),宝冠上层三佛,中间者戴宝冠且施拱手印,下层四佛。其中戴宝冠、施拱手印坐佛为毗卢遮那佛,其余六佛尊格不明。
宝冠中一再出现七佛,说明并非偶然为之,前两例看似在五佛基础上添加二佛,但其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佛教经典中与七佛关系最为密切的菩萨,当推被誉为七佛之师的文殊,此说在宋代已成为佛教常识{2}。上述二例文殊像宝冠中配置七佛,推测基于文殊作七佛之师的认识而创。那么,七佛中法身毗卢遮那佛应兼有释迦牟尼佛尊格,余者为过去六佛的简单表现。普贤经常与文殊成对出现,两者除座骑区别明显外,在造型上并没有显著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普贤像同时采用文殊像新颖的宝冠造型也是可能的。
(2)宝冠佛像之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宝冠
宋代在大足、安岳地区涌现一批宝冠佛像,自北宋晚期一直持续到南宋晚期,或为三佛的中尊,或为柳本尊十炼图像主尊,或为单尊佛像,而最多见为华严三圣主尊。学界认为此类佛像为法身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宝冠的主体纹样均为茎蔓添叶型卷草纹,盛行于南宋中晚期,与菩萨像宝冠并行发展,应直接借鉴了菩萨像造型因素。以宝冠佛形式表现的毗卢遮那佛,十分契合华严经所倡导的行菩萨波罗蜜而成就法身毗卢遮那佛之教义[15],这应是毗卢遮那佛借用菩萨像造型因素的根本所在。
宝冠佛像实例众多,遍布大足、安岳石刻。在卷草纹宝冠之下可见两、三排螺形发髻,有意凸显佛陀尊格。据宝冠前面饰物可以大体分为柳本尊像与摩尼宝珠两式。
其一,饰柳本尊像。诸如,大足宝顶山小佛湾毗卢庵南宋绍定四年(1231)主尊 (图23){3}、佛祖岩毗卢遮那佛像[16],以及安岳的茗山寺第5龛、高升大佛寺第1龛、华严洞的毗卢遮那佛像(图24),宝冠正中设置柳本尊像,除少数破损者外,一概头戴四方平顶巾,身着交领居士装,结跏趺坐,左袖软搭于膝上,其造型与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21龛主尊柳本尊像相近。大足、安岳宋代石窟三处柳本尊十炼图像之第八炼,表现柳本尊割舍左臂,已而在毗卢遮那佛像宝冠中表现为左袖软搭的柳本尊像,表述柳本尊经由菩萨行证得法身毗卢遮那佛的过程。上述实例集中在南宋中晚期,与赵智凤极力传承弘扬柳本尊教法不无关系。
其二,饰摩尼宝珠。诸如,安岳毗卢洞第8龛、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4窟毗卢洞与广大山华严三圣龛之毗卢遮那佛像[11]56,[16]146。宝冠中央设置火焰状摩尼宝珠,有的发出两道豪光。宋辽金时期,火焰状摩尼宝珠常见于菩萨像宝冠上,宝冠佛像则应借用了这一造型因素。
以上可见,四川宋代菩萨像茎叶互用型与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宝冠,在唐、五代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造型灵活多变、疏密兼有,至南宋中晚期后者取代前者,且逐渐受到当时世俗社会卷草纹影响,渐趋繁缛细密。南宋中晚期毗卢遮那佛像宝冠造型,借鉴了同时期菩萨像宝冠茎蔓添叶型卷草纹因素,其中配置柳本尊像则呈现浓郁地域特征。
二 牡丹纹宝冠
牡丹纹宝冠是菩萨像造型史上的一大创举,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为佛教造像本土化、世俗化的真实写照。宋人热爱牡丹,促使牡丹纹样普遍流行,随之影响到菩萨像的装饰。牡丹纹宝冠在特定的时间盛行于四川地区,与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的南移密切关联。
牡丹原产中国,在唐代牡丹被视为繁荣昌盛、雍容华贵的象征,赢得了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喜爱。至宋代,牡丹的发展进入全盛期。据花卉史研究成果,宋代牡丹谱录约21项,品种多达191个,远超前代[17][18]。欣赏牡丹风俗从宫廷到民间无处不有,佛教寺院亦成为观赏牡丹的绝佳场所,“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19]。四川彭州“囊时永宁院有僧,种花最盛,俗谓之牡丹院,春时赏花者多集于此[20]。中国第一部牡丹谱《越中牡丹花品》即为僧人仲休(或仲林)所作①,可见佛教人士对牡丹的由衷热爱。在爱牡丹习俗风靡宋代社会的情况下,牡丹花卉亦成为该时期最重要的装饰纹样,在陶瓷、丝织品、建筑雕刻、器物装饰、壁画上皆见其身影,同时牡丹纹用于装饰佛教尊像。
虽然宋代社会普遍热爱牡丹,可是用牡丹纹装饰菩萨像的实例,却集中在四川地区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牡丹栽培中心的转移成为主要动因。在唐代,牡丹种植集中在北方地区的长安与洛阳。牡丹在五代十国时期作为观赏名花流入蜀地,但直到五代十国之末名贵牡丹花种才流入民间[21]。牡丹栽培和欣赏一经传入四川民间,在两宋时期迅速发展起来。诗人陆游在南宋淳熙五年(1178)写成《天彭牡丹谱》,详细记述了彭州牡丹的盛况。其《花品序》有云:“牡丹在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中略)崇宁(1102-1106)之间亦多佳品。”[20]259可见,北宋晚期四川彭州牡丹已闻名于世,与此同时,菩萨像牡丹纹宝冠流行开来。南宋时期,四川成为全国牡丹栽培中心,菩萨像牡丹纹宝冠亦进入鼎盛时期。
在菩萨像牡丹纹宝冠中,牡丹纹基本由花、叶、茎构成,茎表现为各种抽象曲线,花、叶为造型的重点。据牡丹纹花、叶的形态,可以将牡丹纹宝冠分为写实、装饰、介于二者之间三型。
1. 写实型牡丹纹宝冠
牡丹纹花、叶基本模拟实物形状。这种宝冠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集中见于大足妙高山第3窟文殊像(图25)及第4窟左壁第3尊观音像(图26-1)。前者宝冠正中刻画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叶呈上面观,花朵边缘曲皱,四周伸展叶脉分明的叶片,宝冠两侧各装饰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苞。后者硕大牡丹花配置在宝冠上方,作侧面观表现,形象地刻画花瓣中的篦纹与花蕊(图26-2)。宋代写实牡丹纹极为发达,在四川宋代墓葬雕刻中经常表现花瓣肥大且有篦纹的牡丹花,与菩萨像宝冠的牡丹纹相近(图27)[6]图19,26,63,[10]图15,125。
菩萨像宝冠上牡丹纹样栩栩如生,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的簪花习俗。簪花也称戴花,是将生花或像生花戴在发髻或冠帽上。据学界研究,簪花习俗汉代已流行,至宋代达到鼎盛,不论男女老少,不分尊卑贵贱均戴花。簪花不仅是宋朝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亦是节日喜庆的象征,更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民俗景观[22-25]。文献关于簪花的记载比比皆是,由于宋代牡丹为诸花的代表,成为簪花首选{1}。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宋真宗赐戴牡丹花于重臣的场景[26]。北宋苏轼《吉祥寺赏牡丹》描绘了众人簪牡丹的情景,“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27]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描述了“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的宫廷簪花壮观场面[28]。实物资料更形象地展示戴牡丹的场面,北宋刘履中《田畯醉归图》描绘了老翁高冠上簪牡丹骑牛醉归的情景②,仿佛苏轼诗中记述那般。南宋摹本周文矩《宫中图》贵妇发髻上戴着一朵盛开的硕大牡丹(图28)[29]。南宋《杂剧打花鼓图》一朵艳丽的牡丹插在女子冠帽的右侧 (图29){3}。通过上述例证推测,宋代盛行簪牡丹风俗,或许是促成菩萨像写实型牡丹纹宝冠流行的诱因。
2. 装饰型牡丹纹宝冠
牡丹纹花、叶经过艺术家重新创作,形成富有装饰意味表现。这种宝冠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实例分布在大足地区,诸如北山佛湾第136窟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数珠手观音像(图30-1、30-2),以及妙高山第3窟普贤像(图31)、第4窟左壁第4尊观音像(图32)。前两例宝冠中三、四朵牡丹花随枝条起伏,后者宝冠正中刻画一朵饱满的牡丹花。三者牡丹花瓣为三、四层,中心为花蕊,外层花瓣肥大为造型的重心,一概表现为卷云状,其余花瓣为简洁的圆形或尖桃形,装饰意味浓厚。其中前两例亦着力刻画叶片,形成叶茂花繁、生机盎然的表现。
该形态的牡丹纹系唐代同种纹样的延续,富贵华丽的气质曾一度赢得北宋上层社会喜爱,成为北宋皇陵主要装饰纹样。巩义宋太宗之李皇后陵及宋神宗之陈皇后陵东列望柱刻画的牡丹纹(图33)[30],卷云状花瓣与叶片,呈现与菩萨像宝冠装饰型牡丹纹相近面貌。特别提及的是,宋代官员的官帽也采用装饰型牡丹纹。巩义宋真宗之子周王墓出土石刻像(图34){1},头戴高冠,冠体正中刻画一株盛开牡丹,花朵饱满,花瓣曲卷翻转,充满生机,上述妙高山第4窟观音像宝冠与之大致相当。在装饰牡丹纹流行及世俗官帽装饰的影响下,菩萨像装饰牡丹纹型宝冠的流行自然顺理成章。
3. 介于写实与装饰之间的牡丹纹宝冠
牡丹纹花、叶在模拟自然形态基础上经过艺术处理,更具秩序感。这种宝冠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为了便于分析,根据花朵的形态细分为密集式牡丹纹宝冠与疏朗式牡丹纹宝冠。
其一,密集式牡丹纹宝冠。牡丹花瓣密集,层层叠叠,这种牡丹纹宝冠所存实例较多,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为主要发展期,个别实例延续到南宋中晚期。诸如,大足北山佛湾第180窟北宋政和六年至宣和四年(1116-1122)5尊观音像(图35、36)、第136窟南宋绍兴十二年至十六年(1142-1146) 日月观音像(图37-1、37-2),大足妙高山第4窟大势至像(图38),大足佛祖岩南宋文殊像等[16]148。其宝冠刻画牡丹花二至五朵不等,随枝条起伏作正立、侧立、倒立姿态左右对称排列于冠体。多数花冠内层花瓣呈三瓣状,其余花瓣或密集尖细,或舒展肥大。该形态的牡丹纹在宋代格外受重视,或许直接影响到菩萨像牡丹纹宝冠。宋太宗之李皇后陵东列望柱北宋牡丹纹(图39)[30]94,铜川黄堡镇窑址出土印花“大观”、“政和”款牡丹纹碗[31],以及泸县宋墓雕刻牡丹纹等(图40)[6]31,171,其花瓣重叠密集与菩萨像宝冠的牡丹纹意匠相近。
其二,疏朗式牡丹纹宝冠。牡丹花瓣肥大稀疏,该牡丹纹宝冠始自北宋晚期,流行于南宋。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形式多样,如大足北山佛湾第180窟左壁第2尊观音像,宝冠刻画六朵上面观单层牡丹花,花瓣边缘呈三瓣状(图41)。大足石门山第6窟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诸菩萨像①,多数宝冠刻画二至四朵缠枝牡丹,花冠呈上面观,花瓣圆润饱满,瓣内装饰篦纹,花瓣中间常表现两片花蒂(图42)。以上两种造型的牡丹纹常见于宋代瓷器表面装饰,或施加菩萨像造型一定影响{2}。大足妙高山第5窟的南宋水月观音像(图43){3},宝冠左右各刻画三朵侧面观牡丹花,随波状枝条俯仰形态各异,与华蓥安丙家族墓雕刻牡丹纹有诸多共同性[10]图36,37。
南宋中晚期,菩萨像宝冠牡丹纹趋向统一,如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1龛菩萨像(图44)、第29窟菩萨像等[16]50。多数宝冠为左右各一朵(少数为二朵)牡丹对称配置于冠体,花冠一概为侧面观,花瓣呈勾云状翻转与叶片相得益彰。类似造型的牡丹纹一并流行于四川宋墓,具有浓郁地方特征,菩萨像牡丹纹宝冠的盛行与此不无关系(图
45)[10]图13,83。
密集式与疏朗式牡丹纹,可与宋代牡丹谱录中记载的千叶(或多叶)与单叶牡丹对应,其中前者占牡丹品种的四分之三,尤为宋人所喜爱[32]。在北方地区千叶(或多叶)牡丹逐渐取代单叶牡丹,在四川地区千叶(或多叶)牡丹自北方引进后盛行。《洛阳牡丹记》载:“……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19]529《天彭牡丹谱》曰:“彭人谓花之多叶者京花。单叶者川花。近岁尤贱川花,卖不复旧。”[20]260又,“宣和中,石子滩杨氏皆尝买洛中新花以归,自是洛花散于人间”[20]259。可知,四川的千叶(或多叶)牡丹并非当地品种,或许正是宣和年间从洛阳引进的新品种。完成于宣和四年(1122)的大足北山佛湾180窟13尊观音菩萨像,6例牡丹纹宝冠中5例为密集式千叶(或多叶)牡丹,1例为疏朗式单叶牡丹,足可见人们对新品种牡丹的热爱程度。以至于在最初引进的几十年间,菩萨像密集式牡丹纹宝冠盛极一时。从牡丹谱可知,单叶牡丹先于千叶(或多叶)牡丹,又是四川当地品种,在四川应该有相当长的发展期。虽然单叶牡丹后来不受重视,但是在宋代牡丹纹样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四川宋墓中不乏实例且富有变化,该地区疏朗式牡丹纹宝冠如实记录了单叶牡丹纹发展历程。
以上可见,四川宋代牡丹纹宝冠是在牡丹栽培到达全盛时期的产物。北宋晚期牡丹纹宝冠开始流行,至南宋风靡一时,与牡丹在四川发展的背景紧密相联。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菩萨像牡丹纹宝冠丰富多彩,写实型、装饰型、介于两者之间的牡丹纹宝冠均得到较大发展,反映了艺术家旺盛的创作力。南宋中晚期,菩萨像牡丹纹宝冠趋向一致,造型单调,多为介于写实与装饰之间的疏朗式造型,与当地世俗社会牡丹纹样发展相辅相成。
三 菩萨像宝冠形体
四川宋代菩萨像宝冠形体复杂多变,总体上经历了由多样到统一的过程。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宝冠或高或低,或单层或双层,冠体边缘或有明确边界线,或依赖花卉纹样而边缘参差不齐。南宋中晚期,宝冠多为形体高大的单层结构,花卉纹样边界即冠体边缘。鉴于宝冠形体十分复杂的情况,本稿仅讨论几种特殊形体的宝冠。
其一, “吕”字形冠。大足妙高山第3、4窟菩萨像,宝冠分为上窄下宽的两层结构,上层为较规则的平板状,下层略呈不规则的三、五面体(图26-1、46)。相似实例较早见于安岳圆觉洞第59龛后蜀菩萨像[33],只是宝冠上层近半圆状。推测该形式宝冠出现与五代硬胎幞头的流行有关{1}。四川宋代菩萨像“吕”字形宝冠边缘虽不甚平整,但从中似乎可以看到宋代皇帝所戴硬质幞头的影子(图47)。
其二,筒形冠。集中见于合川涞滩二佛寺南宋菩萨像(图13),宝冠外形呈长筒状。筒形冠为辽代菩萨像的典型冠式,尔后影响到金代与西夏菩萨像。二佛寺菩萨像筒形冠形体高大,比较接近辽代菩萨像,不排除受其影响的可能。
其三,博鬓冠。安岳石羊场华严洞南宋华严三圣像(图24、48),宝冠两侧上翘的翅状物,为宋代皇妃命妇博鬓冠影响下的产物。《宋史·舆服志》载:“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皇太子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中兴(南宋初年)仍旧制。”“命妇服,政和议礼局上花钗冠,皆施两博鬓,宝钿饰。”[35]宋代妇女戴博鬓冠以表尊贵,如台北故宫藏宋仁宗后像与宋真宗后像(图49)[34]71,195,以及河南登封城南庄宋代壁画墓贵妇人画像[36],均头戴博鬓冠。此外,四川阆中市双龙镇宋墓出土的一对金博鬓簪更可提供实物参考[37],卷草式边框里装饰各式镂空花卉,晶莹剔透。华严洞三圣像宝冠借鉴世俗最尊贵的博鬓冠造型,足见人们在塑造佛、菩萨像时饱含崇敬的心情。
综上所述,四川宋代石刻菩萨像以精美的宝冠为造型重心,卷草纹宝冠与牡丹纹宝冠均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展现大发展面貌。卷草纹宝冠上承唐、五代传统,并紧随宋代世俗卷草纹演变的步伐而变化,至南宋中晚期形成异常繁缛的造型。牡丹纹宝冠在牡丹栽培重心南移四川,以及宋人热爱牡丹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为宋代菩萨像造型的创举,生动地反映了佛教造像的民俗化过程。
四川宋代菩萨像宝冠可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约自11世纪80年代至12世纪70年代,卷草纹宝冠与牡丹纹宝冠造型多样,无论是宝冠纹样还是形体均灵活多变,尤其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获得极大发展,造型各异的宝冠彰显了新时代人文创造力。第二阶段即南宋中晚期,约自12世纪80年代至13世纪40年代,卷草纹宝冠与牡丹纹宝冠呈同步发展趋势,纹样虽然繁缛,但是略显单调。总而言之,四川宋代菩萨像宝冠是佛教造像民俗化、地域化进程中代表性实物,造型华丽而精致。
参考文献:
[1]李永翘,胡文和.大足石刻内容总录[C]//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2]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黎方银,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J].文物,1988(8).
[4]曾德仁.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与分期[J].四川文物2001(2).
[5]刘长久.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8卷·四川 重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231,238,239.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泸县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6,28,33
[7]东登.再谈宝顶山摩岩造像的年代问题[J].文物,1983(5).
[8]胡昭曦.大足宝顶山石刻浅论[J].乐山市志资料,1983(3).
[9]陈明光.试论宝顶山造像的上限年代[J].四川文物,1986(S1).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华蓥安丙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图版11,24,25,27.
[11]陈明光.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宝顶石窟卷(上)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120.
[12]李玉珉.易长观世音像考[C]//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1期.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6.
[13]齐庆媛.中国北方地区辽代与北宋菩萨像造型分析[C]// 艺术史研究:第1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
[14]齐庆媛.金代与西夏菩萨像造型分析[C]//故宫学刊:总第11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15]李静杰,黎方银.大足安岳宋代石窟柳本尊十炼图像解析[C]//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6]邓之金.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宝顶山石窟卷(下) [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146.
[17]陈平平.我国宋代的牡丹谱录及其科学成就[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3).
[18]陈平平.宋代牡丹品种和数目研究之三[J].中国农史,2003(1).
[19]欧阳修.洛阳牡丹记[C]//欧阳修全集(上) .北京:中国书店,1986:529.
[20]陆游.天彭牡丹谱[C]//陆放翁全集(上) .北京:中国书店,1986:259.
[21]马文彬.试论牡丹在蜀地作为名花之年代[J].四川文物,2000(3).
[22]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160.
[23]李鹏翔.古代男子簪花杂谈[J].文史天地,2003(10).
[24]郑继猛.论宋代朝廷戴花、簪花礼仪对世风的影响[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5]冯尕才,荣欣.宋代男子簪花习俗及其社会内涵探析[J].民俗研究,2011(3).
[26]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2.
[27]苏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65.
[28]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7.
[29]盛天晔.宋代人物[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80.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93,242.
[31]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4.
[32]陈平平.我国宋代牡丹品种和数目的再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4).
[33]刘长久.安岳石窟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70.
[34]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 [M].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68,70.
[3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3535、3536.
[3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登封城南庄宋代壁画墓[J].文物,2005(8):66.
[37]杨伯达.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2·金银器(2)[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