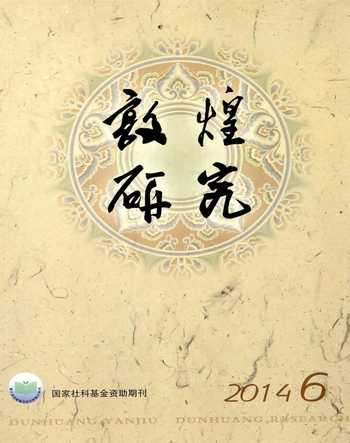大桃儿沟第9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考释
陈玉珍 陈爱峰



内容摘要:大桃儿沟石窟位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西段的大桃儿沟内,现存10个洞窟,是一处藏传佛教石窟。其中,第9窟两侧壁为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图像。与西藏江孜白居寺以及莫高窟第465窟四壁下部的大成就者图像对比可知,大桃儿沟第9窟的图像与莫高窟第465窟更加接近,均出现了执镜师的图像(不见于江孜白居寺)。这隐约表明它们的绘画底本为同一个版本,可见莫高窟第465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是大桃儿沟第9窟的源头,这是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向西传播的一个鲜明例证。
关键词:大桃儿沟第9窟;莫高窟第465窟;八十四大成就者;藏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6-0036-12
一 大桃儿沟石窟概况
大桃儿沟石窟位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西段的大桃儿沟内,沟为南北走向,山势较缓,地表为夹砂石土层,东距吐鲁番市亚尔乡葡萄沟约3千米,与小桃儿沟相邻。
大桃儿沟现存10窟,分为山崖内凿洞与崖前土坯垒砌两种。洞窟自南向北编号,其中:第1至5窟为一组,在最下层;第6、7窟为一组,基本在同一平面上;第8、9窟相邻,第9窟位置高于第8窟;第10窟位于第9窟东北约50米的半山腰上,高度最高。此外,尚残存三处佛寺及两处佛塔遗迹,残损得非常厉害。
残存壁画的洞窟有4个。第5窟后室穹窿顶部绘大莲花,红线描绘,花瓣间有回鹘文题记。第6窟是方形穹窿顶窟,建在崖壁前,土坯垒砌。穹窿顶部绘一朵大莲花,莲花内有五个圆环,一个圆环在穹顶中心,其余绕其四周分布。每个圆环内绘一身坐佛,仅残留头光与身光,穹顶圆环周围的四个圆环间隔部分,绘有五身站立的菩萨,脚踩莲花台,残留头光与身光。据我们初步分析,穹顶圆环内坐佛为大日如来,其余四个圆环内坐佛为四方佛,四个菩萨为四波罗蜜菩萨。莲花之外的穹窿部分,隐约可见几十身佛像(或菩萨像),惜仅有模糊的头光或身光。第9窟为长方形纵券顶窟,左右侧壁绘制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
第10窟为长方形纵券顶窟,建在半山腰的一个平台上,整个窟室虽然不大,但存留的壁画非常珍贵。左侧壁中心位置绘制一佛,为无量寿佛,具身光与头光。两侧各绘四身弟子与胁侍菩萨,具头光。弟子两侧各绘一高僧(极有可能是上师),胁侍菩萨两侧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无量寿佛上方绘制一佛二菩萨,佛呈坐姿,具身光与头光;两侧菩萨具头光与舟形身光,站立于佛两侧。左侧菩萨面向佛,身体微向前倾,左腿前伸,膝盖弯曲。右侧菩萨绘制工整,面向前方。无量寿佛下方有莲花池,莲池上有一佛,四周彩带飘扬。左侧壁周边绘制十六观想图,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可以辨认的有宝树观与宝池观。
右侧壁中部绘砖(?)结构塔,每层均有卷檐。塔下有大波浪纹作为支撑。第1层绘一佛二菩萨,第2层绘二佛并坐,第3层绘一佛,塔顶模糊不清。与每层对应,左右两侧均有9至10身不等的伎乐菩萨,有头光,立于回廊内。
券顶部绘两排坐佛,相向而对,每排8身,总16身,每个坐佛均具覆钵形头光与身光,其外再罩覆钵形背光。券顶下部绘帷幔,造型别致。正壁有一巨型身光几乎占满全壁,从残存痕迹看,原来应有一立佛塑像。
大桃儿沟石窟没有留下任何纪年的题记,只留下一些模糊不清的回鹘文题记以及弥足珍贵的藏传佛教壁画。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吐鲁番石窟进行了碳十四测定,其中大桃儿沟石窟第6窟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年■,同时我们在石窟内没有发现二次绘画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石窟的开凿与壁画的绘制均在宋元时期{1}。
二 第9窟形制、现状及内容
大桃儿沟石窟壁画保存较少,但内容尚称丰富,尤其是所反映的藏传佛教风格的壁画尤为引人瞩目,第9窟即是很好的例证。
形制:平面略呈长方形(后室正壁稍带弧形),纵券顶(图1)。
现状:崖内开凿。窟门坍塌,形状不明,前壁也仅留左右两边上部一小角。洞窟经过两次改建。第一次改建时,在窟室后部封堵土坯墙,后室弃之不用。第二次改建是上世纪当地居民暂住时所为,前壁左边坍塌部分重新用土坯垒砌,角部开一烟囱。正壁左右两边开小门,通向后室,并在前室左右两侧壁上方开6个小龛,左壁1个,右壁5个。窟深7.00米(前后室总长),宽3.00米,券顶至地表堆积2.15米。正壁左窟门宽0.53米,高0.80米,右窟门宽0.66米,高1.05米。
内容:窟室正壁右下角残存三层塔,其上有覆钵,塔的上方有缠枝花卉;右上部分残存两个头光,疑为菩萨,左面一个头光后菩提树叶非常繁茂,周围饰以缠枝花卉;右面上方部分残存半个头光及五叶冠冠叶。门壁左上角有一动物(龙?)形象,旁有缠枝花卉;动物腿的下部残留菩萨五叶冠冠叶;门壁右上方有一菩萨头光,其后有菩提树叶。左右两角也残存稍许,保存状况较差,顶部中心绘大莲花,周圈绕以同样大小的莲花,惜已被烟熏,仅剩大致轮廓。左右侧壁有大幅壁画,下面详细叙述。
三 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考释
大桃儿沟第9窟左右侧壁以连环画形式绘制图像,每个侧壁均残存上下两排,内容为八十四大成就者像,根据格伦威德尔《1902—1903年冬季在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的记述,我们得知,每个侧壁原来应为4排,上面两排因脱落已荡然无存,每排11幅,总88幅,其中4幅非大成就者图像。每幅像尺寸为0.33×0.36米。每幅画间隔以红、白底色,佛像间隔以白、红底色。上下两排图像之间以莲花图案作为装饰,莲花造型较为独特。下部有红色边框,宽5厘米。图像保存不佳,大部分已经脱落,亦有盗割痕迹(表1)。
左上5:尊者坐于兽皮垫上,腿上放一圆形鼓(?),图像损毁严重,仅存兽皮垫与圆形鼓,且脱落不全,原有榜题无存,尊者身份无从考释。
左上6:尊者立于兽皮垫上,抱一琴(或琵琶),右手抚之,还可见两个大耳环,胳膊上有臂钏,脚踝处有脚环,腰间有飘带。图2为17世纪末拉萨鲁康壁画中所描绘的韦那巴大师[2],头戴骨制首饰,身挂骨制项链,冥想带自肩上环绕至左腿之上,他双臂抬起,轻轻举起维那琴,身边的明妃与韦那巴双腿交缠,互相对视。考诸现代唐卡或绘画,韦那巴的典型特征是必带乐器,或琴或琵琶或古筝,亦或印度的维那琴。图3为左上6大成就者图像,虽保存不甚完整,原有榜题无存,但其所抱之琴尚可辨别。据此笔者推测,此即为《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11位韦那巴大师、《如意宝树史》之第16位邬那波(毗婆波){1}。
“韦那巴”意为弹六弦琴者。韦那巴非常喜爱音乐,据说他在专注打鼓声的同时,还能弹奏玄琴。瑜伽士布达巴教授了他不用放弃音乐来禅修佛法的要诀。他依据上师的教导禅修了九年,心的染污得到了清净,生起了如灯火般的明光觉受,得到了大手印的成就,也证得他心通的成就{2}。
左上7:尊者侧坐于兽皮垫上,具背光,宽肩细腰,上身赤裸,胳膊上有臂钏,着红色短裙,短裙上饰以连珠纹饰,腰后系红色飘带,双腿盘曲,右腿置于左腿上,兽皮垫前方卷起,其前置一长条形红色板状物(?)。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头部损毁,原有榜题无存。格伦威德尔描述此尊者右手拿一把锤子(现已脱落),并推知其为甘巴力巴[3],为《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45位,为《如意宝树史》之第45位甘婆梨波(铁匠师)。
“甘巴力巴”即铁匠之意。瑜伽士给他加持灌顶,并给他三脉的修持教授:“观想你的身体外在是风箱、炭火以及炼铁等三者。左脉和右脉是风箱,中脉当火炉,心识是铁匠,以智慧之火来燃烧,妄念作木炭,来锤炼三毒之铁块,提炼出法身无二大乐的果实。”并开示了口诀。铁匠就依照上师的教授,日夜禅修六年,也得到了大手印的究竟证悟。
左上8:尊者坐于兽皮垫上,左腿贴于垫上,脚掌向上,右腿跷起,具头光与背光,胳膊上有臂钏。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头部损毁,胸部以下至腰间有大片脱落,原有榜题无存。格伦威德尔描述此尊者右手拿着一个碗,旁边还立着一个陶罐[1]169(现已不存),尊者身份待考。
左上9:尊者坐于兽皮垫上,瘦骨嶙峋,双臂弯曲,两手置于大腿上。右下角一小童立于兽皮垫上,骨瘦如柴,作舞蹈状(或戏弄状)。尊者头部上方隐约可见一消瘦人形。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唯尊者及小童形象保存较为完好,余皆损毁严重,原有榜题无存,尊者身份待考。
左上10: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图像保存甚差。格伦威德尔描述此尊者左手拿一本书[1]169举在胸前(现已无存),由此笔者推测,此即《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24位巴查巴大师、《如意宝树史》之第26位跋陀罗波。
巴查巴大师原是个富有的婆罗门,一天,一位博学多闻的瑜伽士来向他乞食,婆罗门以他身体不净为由而拒之。瑜伽士巧妙地向婆罗门讲述了心的染污,这种心的染污只有上师的教授才能清净。婆罗门遂心中生起了信心,恳求瑜伽士赐予这样的教授。瑜伽士要他用酒、肉来布施,才肯教授。婆罗门带着酒和肉前往尸陀林中供养瑜伽士,瑜伽士为其加持灌顶,为了消除婆罗门对阶级种姓的执着,让他擦净地面以开显他行为的见地。婆罗门了解到上师教授的意义,对种姓阶级的妄想执着完全舍弃了,按照上师的教导认真修持了六年,也得到了大手印的成就,利益无量众生。
左上11: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戴五叶冠(?),还可见两个大耳环,胳膊上有臂钏,左臂抱一女性,束发。图像保存不甚完整,腰部以下图像脱落,原有榜题无存,尊者身份待考。
左下14:尊者站立姿势,具头光,宽肩细腰,身体扭曲呈S形,上身赤裸,下身穿短裙,左手执杨枝(?),膝盖并拢,下腿部成八字分开。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头部及脚部损毁,原有榜题无存,尊者身份待考。
左下15:尊者坐于兽皮垫上,头上隐约可见冠饰,宽肩细腰,上身赤裸。左手扬起,右手置于胸前,两手似执一物,似为某种乐器。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头、胸及腿部损毁,左上有回鹘文题记,有盗割痕迹,内容待考。
左下16: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头上似有冠饰,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裙,腰间系飘带,两手置于胸前稍向下,右手莲花指,似捻一细小物什,左手执一布条。图4为莫高窟第465窟西壁中部所绘甘大力大师{1},一尊者坐于小圆毯上,左手执布条,右手似捻一物。考诸画像,甘大力典型特征为一手拿布条,一手执针线。图5为大桃儿沟左下16大成就者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头部及腿部损毁。从左手所执布条,右手似捻一细小物什,笔者推测,此尊者为《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69位甘大力大师,为《如意宝树史》之第65位甘多梨巴(烂衣师)。
“甘大力”的意思是裁缝师,他只能以零星的缝补乞讨为生。一次,他在缝补衣服时,不小心针扎到自己的手臂,疼痛难忍在地上跳来跳去。此时空行母贝达力化作女孩,给予他喜金刚的灌顶,并且开示了四无量心、上师瑜伽以及生起次第瑜伽等等。但他在禅修时,却常不自觉地生出妄想,于是便求助于贝达力上师,上师给予他生活入道的证悟口诀。他依照上师的教授努力禅修,证悟了诸法本来即空性,对未能明白此理的众生生起大慈悲心,由于慈悲和空性的双运,得到了大手印的证悟。在八十四大成就者中,甘大力、宗比巴、毗瓦巴等都是喜金刚密法修行者。
左下17: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头上隐约可见冠饰,上身赤裸,腰间有红色飘带,胳膊上有臂钏,右臂搭于右腿上,自然下垂,左手前伸。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头部及腿部损毁。尊者身份待考。
左下18: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宽肩细腰,上身赤裸,胳膊上有臂钏。图像保存较差,头、胸及腿部损毁,尊者身份待考。
左下19: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图像保存较差,仅存头光、背光、腿部与兽皮垫。尊者身份待考。
左下20:尊者站立姿势,身体前倾,扭曲呈S形,有头光,黑发卷于脑后,戴大耳环,胳膊上有臂钏,着短裙,腰间系飘带。图像保存较差,脸部、前胸及腿部无存。尊者身份待考。
左下21: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束发偏右,宽肩细腰,上身赤裸,胳膊上有臂钏。图像保存较差,脸、胸及腿部无存,右上角有回鹘文题记。尊者身份待考。
左下22:尊者立于兽皮垫上,有背光,着红色袒右袈裟,右手执锡杖(或天杖),左手托颅钵。图6为莫高窟第465窟南壁东起第三铺所绘班德巴大师{1},坐于鼓形高座上,两脚自然垂下,踏于莲花上。左手托钵,右手执锡杖,着袒右袈裟,面前有侍者,双手托人头钵供奉。图7为大桃儿沟第9窟左下11大成就者图像,保存不甚完整,头部无存。通过对比,两者不同之处仅在于成就师的坐与立,共同特征是手拿锡杖与钵。由此笔者推测图7可能为《八十四大成就者》中第32位班德巴大师,亦为《如意宝树史》之第32位跋尼达波(持财神师跋达梨婆)。
班德巴意思是“财神中尊贵者”。一天,他看到一位阿罗汉于天空穿越而过,身着僧伽衣,拿着乞钵和锡杖,身上闪耀发光。班德巴心生仰慕,于是向纳波巴上师求法,上师给他密迹金刚的灌顶,并且授予他瑜伽守护法门的四无量心,即慈心见地、喜乐禅修、大悲行、平等性的果报等观修方法。他依照上师所教来精进禅修,终将完全清净了错误的邪见偏执,得到了大手印的证悟。他的身周常摆放长寿瓶、海螺、水果、甘露壶等供养品。
表2右上2:尊者立于兽皮垫上,有背光,仅存衣饰飘带。图像保存甚差,尊者身份无从考释。
右上3:尊者坐于兽皮垫上,胳膊上有臂钏,脖子上戴有项链,菩萨头部及左右两边绕七条鱼。图8为15世纪初江孜白居寺壁画所绘米那巴大师[2]139,瘦骨嶙峋,腰上缠一条瑜伽带,眼睛盯着手中的嘎巴拉,一空行母站在他的身边。米那巴周身环绕三条大鱼,象征其身处鱼腹中的经历。图9为莫高窟第465窟西壁南起第一铺所绘米那巴大师{2},坐于大鱼之上,左手掌心向上平摊足上,右手置于胸前,有头光,绿色靠背,裸身仅着短裙。考诸画像,我们发现米那巴大师的典型特征为坐于或站于一条鱼上,或者周身围绕几条鱼。图10为大桃儿沟第9窟右上6大成就者图像,图像保存较差,头部及腿部损毁,围绕尊者的鱼尚清晰可见。据此笔者推测,此即为《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8位米那巴大师、《如意宝树史》之第13位那婆,亦名金刚足或阿旃陀罗。
米那巴以三个名字闻名于世,即米那巴、多杰夏以及阿金巴多。传说他原是一渔夫,曾被大鱼吞入腹内。此时正遇女神乌玛向梵天王求取法教。在传法时,乌玛竟睡着了,梵天王问乌玛这个密法明白否,米那巴回答明白。等乌玛醒后,梵天王已传法圆满,乌玛再向梵天王请法,梵天王便觉奇怪,就以神通力观察,于是看见鱼腹中的米那巴,梵天王认定米那巴是他真正有缘的弟子。米那巴在鱼腹中接受了梵天王的灌顶教授,在鱼腹中继续修行禅定了12年,得到了世俗悉地成就。世俗成就是修炼初级阶段的成就,有助于修行和觉悟。米那巴后来在地道上渐次进升,即身前往法界空行净土。
右上4: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头戴三叶冠,冠内有宝珠,宽肩细腰,上身赤裸,胳膊上有臂钏。图像保存较差,头部及胸部损毁,内容待考。
右上5:尊者侧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头光内有火焰装饰,脖子上有项链,胳膊上有臂钏,腰系红裙,腰后有飘带。右手拿锤,左手执凿,凿子已嵌入石块中。图11为莫高窟第465窟北壁西侧所绘札巴力巴大师{1},坐于小圆毯上,右腿平置,左腿屈起,面前上方有人头钵。面前置一石器,尊者左手持钎,右手举锤,正在凿石。有头光,裸身短裙,身饰璎珞环钏。图12为大桃儿沟第9窟右上5大成就者图像,两者比较,如出一辙,据此笔者推测,此即为尊者札巴力巴,是《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64位、《如意宝树史》之第63位遮波梨巴。
札巴力巴是大成就者嘎啦嘎啦的上师,并与加力巴互为师徒,他给札巴力巴大手印教授,并教导他持明身之仙丹的成就。传说札巴力巴曾接受一位丈夫外出的妇人的供养,他的丈夫却大发雷霆,妇人便带着儿子气愤地来找札巴力巴大师。大师以咒水洒在母子二人身上,他们都变成了石像。男主人闻讯赶来,也变成了石像。就连陆续赶来三百多亲友,也同样变成了石像。此事传遍四方,引来国王马伊等人参拜,并为石像建了一座名为杜马巴的寺庙。据说,心生邪念的修行者若在寺庙内禅修,会遭受到石像的叱喝修理。因寺院成就了很多有修持的行者,后被誉为佛教圣地。据说妇人的儿子被称为当玛巴,证得了世间八种空行悉地成就,在等待弥勒菩萨下生成佛时,他将一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右上6:尊者交脚而坐,周身绕以大蟒蛇,头上残存蛇头。图13为莫高窟第465窟西壁南起第一铺所绘龙树菩萨{1},坐于两条交尾龙上,脚心朝上,双手结定印。面前有三种供器,上为山形供器,中为三足形供器,下为人头钵,尊者头上有蛇头(似为五头),无头光,着袒右袈裟。图14为15世纪初江孜白居寺所绘龙树菩萨[2]37,身着僧衣,面带微笑,双手结说法印,头顶有肉髻,周身绕蛇,头后伸出七条蛇头,身侧一明妃,为他递上一钵盂。图15为大桃儿沟第9窟右上6大成就者图像,保存较差,头部、胸部以下至左腿部损毁,围绕尊者的蟒蛇尚清晰可见。考诸画像,龙树菩萨典型特征为周身绕蛇或坐于蛇(龙)上,头上有蛇头,这与龙尊王佛的形象是一样的。据此笔者推测,图15为《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16位龙树菩萨,亦为《如意宝树史》之第2位那罗诃弟子那迦祖那(龙树)。
龙树菩萨又叫龙猛、龙胜,是大乘佛教的两位开山祖师之一,中观派的奠基者。与圣天、无着、世亲、陈那、法称、功德光、释迦光一起被称为“六严二圣”。龙树一生撰写了大量阐释三藏四续密意的论典,其中最主要的有《中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据说龙树从术士处学到隐身之术,常偷跑到王宫玩耍,竟使宫女怀孕。因此,他的朋友被乱刀砍死,他幸免遇难。龙树认识到贪欲是痛苦祸患的根源,便在那烂陀寺师从大手印法门始祖萨惹哈出家,圆满通达了大乘三藏的所有经论。他还修持大鹏鸟法、作明佛母法、九夜刹法和马哈嘎啦,成就了妙丹、眼药、土行、宝剑、空行、隐形、不死和除病八种共同悉地,还有制伏、死而复生等悉地。
传说龙树晚年成就了长寿金丹术,得金刚不坏之身。国王色拉邦札得到了龙树的殊胜口诀,也修成了金丹术。王子为了及早得到王位,便请求龙树以头颅布施。龙树爽快答应了。但龙树的头无论如何都切不下来,后被吉祥草才把头切下来布施于大梵天。从此树林干枯,人们的福德都出现障碍,后由八大女夜叉守护着菩萨的身体。传说龙树的舍利遗骸由龙王菩萨守护着,光芒射出如同月光般。而龙树菩萨的身体在弥勒菩萨来临时,将会再度起来利益众生。
右上7: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头上有冠饰,胳膊上有臂钏。图像保存甚差,仅存身体左半部分,无从考释。
右上8: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图像保存较差,脸、胸部以下至腰间皆损毁,无从考释。
右上9:尊者呈站立姿势,两臂上举,胳膊上有臂钏,上身赤裸,下身穿红裙,裙摆飞扬。尊者身前的小侍从像,左手托颅钵,腰系虎皮短裙,两脚踝处各有一条小蛇盘绕,其姿势颇类大黑天。图像保存较差,尊者及侍者头部无存,内容待考。
右上10: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胳膊上有臂钏。图像保存较差,头、胸及左腿部均残失,内容待考。
右上11:尊者面向左呈站立姿势,有头光,可见两大耳环,腰间飘带自然下垂。尊者右腿前迈,左腿后撤,微向前弯曲,左脚踩在木头上,下横插一木作为支点。尊者两手握斧头,用力向木头砍去。图16为莫高窟第465窟北壁西起第一铺所绘阿津达大师{1},作行走状,似背一捆木材,右腿向前,左腿在后,左手置胸前施无畏印,右手握长柄斧头,扛于肩上。面前有侍者,双手捧人头钵,正向后回头顾望尊者。图17为15世纪初江孜白居寺所绘阿津达大师[2]173,手持一根木杖,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他身着紧身短裤,肩披长条布巾,头戴骨饰,挎着一条冥想带,眼睛直视着地面上象征财富的海螺。他身边站着一个红色身的空行母,正恭敬地向他敬礼。
图18为大桃儿沟第9窟右上11大成就者,图像保存尚可,唯头、两臂及手部图像脱落。考诸画像,阿津达大师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其一为写实,手拿斧头,肩背木材,或正在做劈柴动作;其二为写意,阿津达执着于对财富的追求,面前象征财富的海螺是辨认其身份的重要标识。据此我们推知,图18为《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38位阿津达大师,亦为《如意宝树史》之第38位阿旃陀(无忆师)。
“阿津达”就是没有念头的意思。因为家里非常贫穷,他以卖木材为生,沉浸在发财的梦里。一天,拉瓦巴大师经过大师处,大师给了他上乐金刚的灌顶,并且给了他基本的圆满次第的教授。阿津达依照上师的教授来禅修,将妄念观修置于明星中,明星则融于虚空之中。阿津达继续禅修,了悟了上师教授的意义,得到了大手印的成就。在其后三百年中,他向众生教导心的本性,利益众生。
右下18: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耳戴耳环,颈有项饰,胳膊上有臂钏,宽肩腰细,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裙右手上举,其上悬浮一双面鼓,左手托颅钵于胸前。考诸画像,嗄那巴大师的典型特征是空中有七只宝伞与七只手鼓。这里的图像由于画面空间狭小,仅用一只手鼓代替,具有象征意义。据此笔者推测,此即为嘎那巴大师,是《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之第17位。
嘎那巴大师从上师札连达拉巴得到了灌顶以及喜金刚的教授,经过了12年的禅修,自以为已经得到了成就,就集合了众弟子宣布,为了利益众生,决定出发前往罗刹国兰卡布里山。当他带领众人来到了海边,走入大海中,毫不下沉。心生傲慢自大,就失去了神通力,沉入海中。他从天空中看到了自己的上师札连达拉。嘎那巴向上师忏悔了他的傲慢自大,上师就指引他修持,又再次获得了以前的神通力。
右下19:一尊者,衣饰繁复华丽,具头光。图像保存甚差,模糊不可辨,尊者身份无从考释。
右下20:尊者坐于兽皮垫上,具头光与背光。图像保存甚差,模糊不可辨,尊者身份无从考释。
右下21:一尊者,有头光与背光,戴耳环。图像保存甚差,模糊不可辨,尊者身份无从考释。
右下22:尊者坐于兽皮垫上,有头光与背光,着袒右袈裟。图像保存尚可,脸及手部损毁,左上角残存回鹘文题记。尊者身份待考。
四 小 结
大成就者,专指对以修习密法获得成就并对密法传播做出贡献的那些印度上师的称呼。由于他们身份特殊,又有惊世骇俗之举,他们的故事中充满了神通与智慧。八十四大成就者代表着八十四种不同的人格,他们都是大乘经论开始弘扬时,修习密乘获得悉地成就的修行者。全都是发生在8—11世纪印度境内的故事。其中鲜为人知的,如创立中观论的龙树菩萨、提婆菩萨、寂天菩萨,密教著名祖师提洛巴、色拉哈巴、纳洛巴,将佛教传入西藏并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莲花生大师,等等。佛陀入涅槃后,他们以各种善巧方便来教授大乘法要,调伏众生,使得大乘中显宗和密宗的佛法得以弘扬流传。藏传佛教各派视他们为印度的传承上师,其教法一直传承至今。相对于汉传佛教而言,藏传佛教更注重密宗的修习传承。
密宗“悉地”一词,即指修习密法的成就,可以解释为真正的成就、证得、加持和证悟等。密法有一般悉地和无上悉地两种成就,一般悉地即共同成就、世间成就;无上悉地又称不共成就、超世间成就、殊胜成就。
世间成就就是修炼初级阶段的成就,即各种神通及具有息、增、怀、诛等法之能力;殊胜成就是解脱成佛的终极成就,亦即生出觉悟,得全知智能与身、口、意成就,证得佛果,能利益自己和一切众生。八十四大成就者正是获得殊胜成就者。
大乘又称菩萨乘,把凡是立下宏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称之为菩萨,主张自觉觉他、自利利他,“下度众生、上求佛果”甚至要求“自未度先度他”。在修行目标、证悟的果位上,大乘的显宗和密宗有着相同的见解,只是在成就果位的方便道或方法上,存有差异。显宗又称因乘,修行更侧重于因,以因趋向果,认为正见、正定和正行是成佛的根本;密宗又称果乘或金刚乘,密宗更倾向于果位的修习,但密法是不能轻易向别人透露的,只有少数具有上根的弟子才能学到。
在藏传佛教中,密法的传承是由根本传承上师口耳相传于弟子,因此,皈依上师及上师供奉在密宗中是十分重要的。喜金刚本续中这样说道:“俱生超越智慧的出生,只能藉由对上师的信心和所积聚的功德中产生。”[2]22尊师是密教成就的根本,即是道上一切功德的出生处,是源于以正确的方式来承侍上师。也就是说,弟子以虔诚清净心供养上师,并努力完成上师的指示,由此生出一切智慧功德,将能迅速成就世俗与究就悉地。
当上师和弟子的三昧耶誓愿关系存在时,有时即使上师不说任何一个字,甚至弟子也未能察觉,但是只要一个注视,或是一个简单的手势或姿势加持,即可使弟子得到证悟。对于此,提洛巴上师和弟子纳洛巴的故事,最能够说明此情况。纳洛巴完成了上师所交办之事,一天,上师以鞋子将其击昏。他醒来时,已了悟一切诸法现象的本性。
纳洛巴大师以所传的“那若六法”著名于后世,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噶举派始祖玛尔巴大师三次入印求法,在印度21年,期间16年余7月求教于纳洛巴。阿底峡尊者也师从纳洛巴学法。“那若六法”为噶举派主要修法,其他各派也都加以吸收。如宗喀巴大师将脐火修法作为圆满次第的主要修法;夺舍法为以后的转世说做出了依据;光明、幻身等修法也为格鲁派所吸收[4]。
藏传佛教将大成就者作为密教上师崇拜有加。据《八十四大成就者传》的记载,大成就者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并且大部分都是出身低微、生活贫困的下层阶级,如渔夫、屠夫、小偷、乞丐等等,他们的行为多于当时的社会普遍道德相抵触,而且他们通常进行独特的瑜伽体验时选择在一些怪异的场所(如坟场等)。他们不仅是身怀绝技的高级瑜伽师,也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佛教徒,是探索一切有情脱离生、老、病、死的在世之苦和无限轮回的永恒之苦的先驱和思想家。他们利用现世短暂的生命,追求永恒存在的精神,达到永恒快乐的彼岸,精神永存的家园。他们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他们经由努力禅修上师的口诀教授,现已得到解脱成就,能够弘法利益众生,而我们依然还在世俗的痛苦中挣扎。
八十四大成就者的生平故事宣示了“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佛理。让人们了解到获得证悟所仰赖的是行者精进的程度,与性别、年龄、职业、阶级种性及社会地位毫无关系,而且在修行过程中并不须放弃其日常活动,相反,他们可藉由其日常生活来修持。在开始时,他们都遇到了神圣的上师,并从上师处得到令心识成熟的灌顶以及所教授的甚深解释,使他们能以日常生活作为禅而修道。成就师的伟大,使我们能了解到不论处境多么艰难困苦,只要能由上师处得到正确的教授,经由自身的努力修持,都能得到成就而解脱。
从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大桃儿沟第9窟的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有被切割的痕迹。对此格伦威德尔也供认不讳[3]381。俄国探险队也曾来此,并盗走大批壁画、塑像及文书,他们的考察成果多未公诸于世。我们只能根据格伦威德尔的报告,复原现在已缺失的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如格氏编号第4号人物为一个坐在虎皮兽垫上的尊者,手执一面镜子。此图像在《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中尚未找到对应者,可喜的是我们在莫高窟第465窟中见到了同样的图像,位于东壁门南,伯希和记为“□□□□巴此云执镜师”,并说:“执镜师坐于小花圆毯上,前有三足供器。左腿前伸,盘右腿,左手执镜自照,右手置于胸侧。无头光,戴尖顶僧帽,耳珰裸身,仅着短裙,项、臂、腿均有璎珞腕钏等装饰。”[5]第52号(格氏编号)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到遮掩在云中的太阳,显然表现的是毕鲁巴大师的故事。第66号(格氏编号)人物的肤色为棕褐色,有一只狗伴随着他,此即为古古力巴大师。第79号人物描绘的是手拿洗衣板的多毕巴大师[3]380-381。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确定大桃儿沟第9窟两侧壁为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图像,与西藏江孜白居寺以及莫高窟第465窟四壁下部的大成就者图像对比可知,大桃儿沟第9窟的图像与莫高窟第465窟更加接近。首先用色上均偏淡,为冷色调,不像江孜白居寺浓烈的红色那么强烈。其次,大成就者多上身赤裸,宽肩细腰,腰系短裙,人物造型多为本土风格,而江孜白居寺的大成就者更接近印度风格,如佩瑜伽带或冥想带、印度的维那琴等。再次,构图简单,画面具有写实特点,不及江孜白居寺那么华丽。此外,莫高窟第465窟与大桃儿沟第9窟中均出现了执镜师的图像(而此图像不见于江孜白居寺,也无法与《八十四大成就者传》相对应)。这隐约表明它们的绘画底本为同一个版本。由此笔者推测莫高窟第465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是大桃儿沟第9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的源头,此为宋元时期藏传佛教向西传播的一个鲜明例证。
参考文献:
[1]Albert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覿ologische Arbe
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M].Munchen,1905:168.
[2]白玛僧格.唐卡中的八十四大成就者[M].北京:紫金城出版社,2008:143.
[3]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M].赵崇民,巫新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80-381,389.
[4]石世梁.金刚乘佛教流传中的几点质疑[J].西藏研究,1990(3):74.
[5]赵晓星.莫高窟第465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考释[C]//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问题要集.北京,2009: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