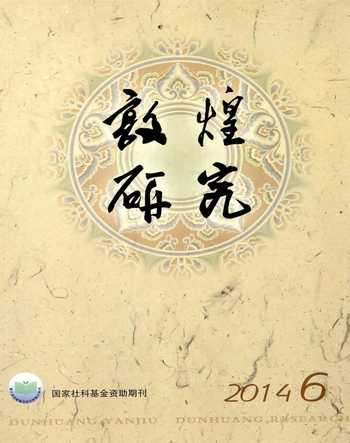麦积山石窟第5窟西方净土变
李梅



内容摘要:麦积山石窟第5窟正壁右龛上部所绘一铺西方净土变,包括净土变及下方供养人两个部分。净土变画面以主尊为中心左右对称分布,宝池与宝地大面积绘出,楼阁与虚空等要素具备,为比较完整的西方净土变。宝池和延伸至宝地上的水渠同处一个画面是其独到之处。净土变下方绘女供养人,左右相对而列。供养人三人一组,为主从形式。女主人衣着交领开敞,大袖;发髻上拢,顶平。本文具体考察净土变中的纹样、建筑等细节,结合供养人的服饰特征,基本判断其绘制年代在隋代。
关键词:麦积山;隋代;西方净土变
中图分类号:K87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6-0025-11
序
麦积山石窟第5窟位于窟区最上部,东邻第4窟散花楼,原为三间四柱崖阁,前崖坍塌,现存正壁三龛(图1)。第5窟前廊正壁壁画大部分已毁,或由后代重绘,仅有正壁右龛上部所绘一铺西方净土变可辨认其大略(图2)。这一铺净土变出现时间较早,具备宝池、水渠以及宝地、宝楼等,净土变的基本特征可见其中,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实为净土变研究不可或缺的。在文化中心西安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可通过对麦积山壁画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了解西安的一些状况。
关于第5窟西方净土变的研究主要见于:《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认定年代为隋、唐(宋、明重修);《甘肃石窟艺术·壁画编》,其中提及顶部平棋壁画为隋代(6世纪末),供养人为初唐(7世纪末);《麦积山石窟所见古建筑》与《麦积山第5窟壁画遗迹的初步观察》中主要提及其建筑特征,尤其后者从壁画的整体构成以及建筑等考察壁画的年代,基本倾向于隋代制作。除以上研究以外,最新研究有:江苏美术出版社的《麦积山》,指出顶部壁画为隋代或唐代,西方净土变及供养人为唐代;《甘肃石窟志》认为西方净土变及供养人为唐代;《中国仏教造像の変容南北朝後期及び隋時代》认为西方净土变为隋代,窟内造像为隋代稍晚时期,而天王像为唐代塑造[1-7]。据此可见,针对这铺壁画的绘制年代大致有隋代和唐代两种意见。
第5窟的这铺净土变绘于右龛上,由于位置较高,实地观察时仅能站在狭窄的栈道上由下向上仰视,其画面不仅呈压缩状态,而且右龛龛楣恰好与部分画面重叠,所以很难掌握画面的整体布局。另外,由于长期暴露在外,画面损毁严重,基本漫漶不清,主尊左右大面积剥落。本文基于现有资料,力图辨清细节,深入着手,整理并恢复这铺净土变的大致原状,然后分析净土变下方供养人的服饰状况,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试论其制作时代。
本文西方净土变包括净土变与下方供养人,其主体在正壁,一部分延伸至右侧壁(图3)。净土变周围,尚有平棋部仅存的一幅飞马图,平棋左侧侧梁的坐佛图,正壁下方的上下两幅说法图,右侧壁净土变下方的比丘像、头光以及小幅说法图(图4)。本文将后述净土变与这几处现存壁画的关系。经实地观察,本文讨论范围的壁画仅为一层,未发现重绘迹象。
一 前廊正壁右龛上方西方净土变
本文首先整理正壁净土变的内容。这铺净土变大致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由界线清晰划分。其上半部为净土变,以主尊为中轴左右对称,水渠及宝池呈梯形,具有透视效果。主尊上方接近平棋处绘有飞天,但现状仅能辨认出部分天衣。主尊左右宝地延伸,可辨认出菩萨、水渠、宝楼、化生童子、狮子等。右侧壁净土变延伸部分可见菩萨、水渠和建筑。净土变下半部为供养人,左侧三列,右侧一列。
本文将这铺净土变划分为A—F六个部分,以便说明。A为宝池,包括主尊及主尊前方部分;B与C为宝地,处于主尊左右,由于被宝池所延伸出的水渠隔开,左右对称,分为三组,即B-1和C-1,B-2和C-2,B-3和C-3;D为净土变右侧壁延伸部分;EF为供养人(图5)。
(一)宝池
主尊于此居中,须弥座束腰,上部及底座为多瓣莲花,甚显豪华。主尊左手置腹前,右臂曲肘上举。此处主要有两个特色。其一为主尊无头光、身光,其后置一长方形板状物,犹如靠背。再向后由三面屏风围成一个空间,屏风表面竖向排列环状连珠纹样,为双环之间夹绘连珠的形式,双环内则是连珠纹样(图6)。类似的双环纹样还出现在下部供养人大袖袖缘上。屏风边缘侧柱上有序排列着数列横向连珠,清晰可辨。关于连珠纹样,在莫高窟隋代洞窟中十分突出,“敦煌隋代连珠纹样有直条与环形两种,主要绘于塑像衣裙和龛口边饰上” [8],隋代第295、401、419、403等窟的龛沿、壁面、藻井边界等处,比比可见。
首先说直条连珠纹。平棋方形边沿均绘有连珠。主尊身后方形板状物的左右边缘各绘两条纵向直条连珠纹,其间夹绘唐草(卷草)纹样,这一形式又见于本窟中央龛的入口内侧壁面边缘,也并列绘有两道直条连珠纹样,中间夹绘同一形式的唐草(卷草)。不仅如此,这一唐草形式又与净土变右侧侧壁所绘头光的唐草完全一致,头光处也绘有条状连珠纹(图7)。这一唐草为半忍冬式4—5叶状形式,两片相对为一组,其中央绘有椭圆或十字等花形。在麦积山石窟,这一唐草纹样由北周开始流行,持续到隋代。同一形式的直条连珠夹绘唐草的纹样出现在同一洞窟,其绘制可以想见基本在同一时期。
其次说环状连珠纹。下部供养人大袖袖缘上同样为双环,虽然双环之间没有夹绘连珠,形式上应归类为主尊处的环状纹。同样的环状连珠纹还见于其他多处:如炳灵寺石窟隋代第8窟赴会弟子袈裟边饰,环内绘盛开的花样;西安北周安伽墓,石塌边缘刻有环状连珠纹,环内为兽面[9];西安碑林隋开皇二年(582)李和石棺下缘以及棺盖上均刻有浅浮雕环状连珠兽面纹。可见,这一纹样流行范围不仅仅限于佛教美术作品,墓葬中也在采用,并且它的流行地区比较广泛,如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侍女衣裙边缘以及马鞍织物边缘均绘有相同的环状连珠纹,环内绘戴头冠的菩萨[10],尤其马鞍织物边缘两道直条连珠纹内夹绘环状连珠纹,装饰性极强。该墓出土金戒指的戒盘边缘也为环状连珠纹,环内阴刻一持杖人物[11],这与当时北齐崇尚胡风的社会风气相关。
主尊身后所绘三面屏风,意在主尊身后形成一个空间或背景。类似的表现见于莫高窟第419窟南壁下部主尊以及第302窟东壁门上主尊身后屏风,均呈曲尺状。净土变中主尊身后出现建筑的表现与这一形式应有某种联系。第302窟有开皇四年(584)铭文,为莫高窟隋代第一期窟基准窟[7]326。
其二为主尊内衣绘有竖向条纹,胸部结带,具有同样条纹的内衣见于右龛右侧上方说法图的交脚主尊。
主尊前方(图8)置香炉,现仅可见其底座和顶部。香炉斜前方左右各一化生童子,左侧一身较清晰,单膝跪于莲座上,合掌面向主尊。左右菩萨莲台后亦为化生童子,右侧两身,前方一身坐于莲台上并合掌面向主尊,后方一身于水中手臂伸展;左侧一身俯身游动,面向主尊。主尊左右莲座上的菩萨仅见其足部以及部分天衣,天衣翻卷飘动,垂于水面。莲座前后错落有致,剥落严重,左右各有四五身菩萨,现仅能辨出其腿部或后背;接近主尊处有菩萨头部痕迹,主尊左侧莲座上菩萨仅存上身及腿部,天衣从莲座垂下,轻拂水面。香炉斜向接近宝地处坐两头狮子,尾巴浮于水中,水漪涟涟,仿佛见其左右摆动。左侧狮子轻举右足,右侧狮子则左足高举。宝池在此呈倒“凸”字形,其凸出处有一方形陆面,仔细辨认之后发现,其左边上方紧靠化生童子莲座处有两个圆状突起,其下更有人物面部轮廓。这两个圆状突起的形式可将视线上移至平棋,平棋上所绘飞天宝冠的侧面即为同样的两个圆形突起。由敦煌莫高窟的净土变推测,这一方形陆面很有可能为舞乐平台,上坐伎乐天不止一身,两个圆形突起为伎乐天的头冠。
上述可知,A画面为宝池,呈倒“凸”字形,主尊、香炉、左右菩萨、化生童子、狮子和伎乐天所在平台均处于宝池当中。由宝池延伸出水渠横向左右延伸至宝地,直至侧壁。水渠上各个部分均有桥梁将宝地相互连接起来。
(二)宝地
宝地为B(图9)、C(图10)部分,分布于宝池左右。宝地由水渠分隔成三处,B-1与C-1、B-2与C-2、B-3与C-3,它们相互对应。其中B-3、C-3由赫红连珠缘的透明砖铺成,砖有绿、黑两色,与B-1、C-1以及B-2、C-2仅一色的宝地不同。“四边阶道,金银琉璃颇梨合成。”[12]宝地的形式恰好反映了这一经文。
这一部分临近主尊的B-1、C-1基本剥落,难以推断其原状。仅于主尊右侧C-1上存数身菩萨痕迹,接近主尊一身保存相对较完整,坐姿,宝冠呈“山”字形,左右宝缯下垂。“有二菩萨最尊第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12]273对面B-1上的一身已完全剥落,可以想见主尊左右两菩萨相对而坐,很有可能为观世音和大势至。这一身坐姿菩萨周围还能辨认出三身菩萨,但仅能看到头部,其面部椭圆,与宝冠相映,项饰及蓝绿色天衣等服饰与坐姿菩萨相同。对面B-1处隐约可分辨出两三身菩萨的头部或头冠。
B-2、C-2在纵向水渠外侧,其上建筑宝楼鳞次栉比。主尊左侧B-2保存较好,由上至下可见三座宝楼(图9),最上一座为双层,上层建筑基本剥落,约见四柱,W字形屋檐装饰;下层十二柱三间,屋内似有长案,三身菩萨见于其中,头冠清晰。屋外三身,隐约可见,戴三面宝冠,天衣下垂。中间一座宝楼有勾栏,一菩萨从中探身,尚有三身现于窗边,均戴三面宝冠;最下一座宝楼前一棵芒果系大树,树叶繁茂,主干直立于地,树后数身菩萨从宝楼中陆续走出,朝向水渠上的桥。菩萨有的手捧供物,天衣于身后长垂曳地。
C-2之上宝楼漫漶不清(图10),最上方一座与B-2呼应,十二柱三间,三身菩萨隐约其间。此宝楼前立一菩萨,正面姿,身体略微扭动呈S形,与净土变下方说法图中的菩萨姿态极为相似。邻近菩萨的水渠中立一水门(图11),“靓柱间为双扇栅栏门,水门屋顶为四柱顶,正脊与四戗脊,绘以绿色,与其余建筑同,屋顶面为蓝色平涂。这种反映应是隋代壁画中表现琉璃剪边的情况。檐下柱头斗拱侧面看为一斗三升,补间为有舒脚的人字拱(叉手)”[4]299。临近还有两座宝楼,但基本模糊难辨,中间一座上下两层,上层一菩萨由勾栏探身伸臂,下层中陆续走出六身菩萨朝向桥梁,与对面B2意趣相同。两宝楼之间有一芒果系大树,叶片与B上相同,而花蕊各有异趣,B上呈星状,C上呈椭圆状。C-2宝楼也由上至下分布三座,具备勾栏、双层等特征,与B-2宝楼在细节上意趣相符,相互呼应,呈对称布局。
关于宝楼的描述,《阿弥陀经》:“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梨车■赤珠马瑙而严饰之”;《无量寿经》:“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复以真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露覆盖其上。”[12]271
水门所在水渠流经宝地后,右转平流,《无量寿经》说“微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逝不迟不疾”[12]271。这一道横向水渠与侧壁相接处由于侧壁部分剥落严重而难以判断是否在侧壁延伸,而向下接近供养人的横向水渠通向侧壁并延伸开去。
“建筑楼阁多用北朝以来流行的一斗三升斗拱和有舒脚的人字补间,未见初唐已出现的成熟的出挑拱,更未见刻画出转角铺作。这与天水博物馆的周隋石棺床上刻画的殿阁形象及其斗拱细节的情况十分相似”[4]300,据此可见建筑显示隋代特征而尚未进入初唐。
下方宝地即B-3、C-3。此处宝地由两色方形透明砖铺成,“以是七宝相间为地”。宝地侧面的方形图案清晰,宝地的厚度及其浮于水面的状况明显可见。菩萨身姿窈窕袅娜,天衣于身后长垂。这一部分保存较好,菩萨上身半裸,项饰当胸,腕饰双环。菩萨下裙分两种形式,一为单色,二为红绿蓝黑四色相间的横条宽纹,颜色多用复合色,延续北周以来的特色。菩萨略弓背凸腹,侧面观呈S状。现状可辨认出B-3约九身,C-3约十一身,侧壁D约四身,均徐徐朝向主尊。众菩萨或互相侧耳交谈,或立于桥上,姿态各异。宝地的各个部分均有桥梁连接,C与下方供养人之间略偏右处亦有桥连接。按照图形对称设计,B的部分对应处也有桥,但由于右龛龛沿恰好处于相应处,C3没有绘出。由此,B上有桥三座,C上有五座,纵横连接A、B、C三处。
(三)右侧壁
C下方横向水渠转向侧壁后斜向延伸,与右侧壁方形琉璃砖铺成的宝地结成一片,即本文中D(图3)。这一部分方形琉璃砖铺成的宝地上立四身菩萨,朝向侧壁中心。而接近顶部的壁画基本剥落,可隐约辨认出整齐的横线,为一道道界线,应是建筑痕迹。最上方可见横向水渠,其上可分辨出宝地的侧面,可见宝地一直延伸到上方,接近平棋。由正壁延伸而来的水渠和D下方横向水渠组成一个三角画面,莲座上坐菩萨,身形较大,天衣由肩斜下,其左侧有四身菩萨坐于莲座上,姿态随意。此四身菩萨保存完整,侧壁画面最外侧一身菩萨,左足轻搭于莲座边缘,膝部弯曲,天衣绕足腕;紧邻一身曲臂合掌。菩萨戴三面宝冠,中央突起,上饰宝珠,宝缯细长,于两鬓飘逸下垂,显得面部略长。此处菩萨形象可弥补宝池中已不可再现的菩萨。立于宝地上的各个菩萨宝冠的形式稍显简略,其描绘尺寸小于莲座上的菩萨,但两者的宝冠、披帛等装束相似。近旁水渠上一桥梁连接两处宝地。
画面下方横向水渠没有与正壁相连,对应位置为正壁供养人。
(四)净土变部分的小结
通观正壁及右侧壁这一铺净土变,以主尊为中心左右对称分布,正壁与侧壁相接,侧壁部分如果没有坍塌,画面将更广更丰富,“恢廓旷荡不可极限。”[12]270侧壁部分也延续两种宝地,整体画面大略复原如下(图12)。正壁各部分的描绘以及正壁和侧壁的关系可以看出这铺净土变有着严密的整体设计。正壁宝池与宝地均大面积绘出,宝楼与虚空等要素具备,为比较完整的西方净土变。宝池居中体现其重要性,主尊及其周围菩萨、供养童子、狮子、香炉和伎乐平台均处于宝池当中[4]296[13]。“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12]346莫高窟第57窟北壁说法图、第220窟西方净土变在突出宝池这一点上具有同样特色,但缺乏本文净土变透视效果所体现出的画面进深。除此之外,本文净土变宝池和延伸至宝地上的水渠同处一个画面是其独到之处。此后的净土变大约分为两个趋势,一为取宝池而无水渠,莫高窟第220窟为其代表;一为取水渠而无宝池,莫高窟第220窟以后如第321窟北壁东侧阿弥陀净土变等较为典型。宝池和水渠的取舍问题关系到净土变构图的发展与变迁,这一点以本文净土变作为基本参考,有其重要意义。
二 下方供养人
(一)供养人
净土变下方相隔界线所绘供养人位于宝池下方的右龛龛楣两侧,相对而列,左侧三列(图13),右侧一列(图14),各由僧人前导。供养人每组三人,左侧最上一列八组,第二列八组,第三列六组;右侧仅有一列共十一组。左右供养人人数及数列不同,左侧三列依佛龛弧形排列。而右侧仅一排,将十一组安排成一列,略显拥挤,其下方绘有上下两幅说法图以及几身供养人。
观察第5窟外观现状(图1),与踏牛天王对应处即左侧三列供养人下方有三个桩孔,其高度与供养人的位置没有冲突,即原有造像与踏牛天王对应;而净土变右下二说法图处有两个桩孔,其对应位置即正壁左龛处也有两个。但左龛桩孔凿于龛沿和龛柱上,在此安置造像似乎有些勉强。现在还可观察到壁画的痕迹,尤其左龛左侧上方留有华盖的顶部弧状及宝珠。另有飞天天衣的部分痕迹,其色彩为北周乃至隋代常用的蓝、绿两色,明显区别于周围后绘痕迹。可见这个部分和右龛二说法图相对应,原为说法图的可能性极大。由此回到二说法图处,这里安置造像的桩眼没于壁画中,极有可能是放弃原计划而改为描绘壁画,即为现存的两幅说法图。上方供养人并为一列能窥见其扩大空间的意图。另外,左右侧壁存有两个头光,左壁上的为后代重修,与右壁头光位置相对应,说明重修是在原有位置上进行的,可见第5窟整体强调左右对称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供养人先导的僧人头部突出于净土变界栏线之上,供养人绘制应在净土变完成或基本完成之后。左侧僧人身后紧跟一沙弥,形象略小,手持一物;右侧僧人持长柄香炉。
供养人均为女子,三人一组,为主从关系(图15)[14]。每组前方均有长条榜题,但已不可辨识。供养人三人一组中:先头一人略高大,为主人;后跟两人略小,为侍女。主人肩后倾,突腹,交领大袖,右衽。其交领左右开口较大,至肩,领缘几乎平直,非常夸张;其大袖前笼,由胸至膝下,呈椭圆状,中间交缝处见袖缘双环纹样,无连珠,环内绘向心射线。此双环纹样应属隋代流行的环状连珠纹的一种,于宝池内主尊背后屏风纹样中已述。女主人长裙高提至胸,后裙由身后侍女双手上提。供养人右侧最前组主人手持长柄香炉,左侧第一排不清,第二排最先头主人手持莲花,第三排持莲蕾,后跟的每组主人手持莲蕾。此铺净土变的供养人足不外露,不见鞋靴,足部仅以横线一撇进行表现,与炳灵寺第8窟的供养人类同。
两侍女中前方侍女略高,臂下夹一垫状物,后方仕女较小。两侍女肩披帔巾,或由肩下垂绕臂,或覆肩后披,或覆肩斜披,形式各异,长垂过膝;发髻上束,个别能辨出头巾。发髻于头顶呈偏平状。长柄扇绘于侍女之间或侍女头后,其上部为圆形。
(二)供养人服饰特征
上述供养人,尤其女主人的服饰与发髻形式比较特殊,形成这一交领大袖的服装形式首先在麦积山石窟有一个发展过程。随着汉化政策的深入,女子“多数身穿交领大袖衫,下着长裙”[15],这一特征在菩萨着装上也有反映。西魏时这一交领形式明显可见,服饰上有此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有第127窟净土变中所见圣众形象,交领,双手笼袖,长袖下垂,形式上与本文供养人极为接近。另有第4窟平棋处坐于车舆中的女子形象,与第26窟窟顶左斜披上的供养人相近,交领大袖,且交领较开敞。由此至北周时,麦积山石窟这一交领大袖的服装形式基本形成。
在麦积山石窟,同形式的交领大袖式供养人除上述以外尚见于其他洞窟(图16),如第160、140、23、26窟等。第140窟紧邻第141窟并与之打通,壁画有重绘迹象。第160、23窟为隋代重修[1]290[16],供养人与本文完全相同,女主人在前,后跟侍女双手提裙。隋代所绘女供养人形象具备的相同之处可归纳为这一特点鲜明的交领以及大袖的形式上。
其次,同类服饰特征的供养人不仅出现于麦积山石窟,位于麦积山石窟以西、与麦积山同属陇南石窟群的水帘洞石窟绘有形式相同的供养人。水帘洞壁画No9的供养人形象为交领、大袖,袖缘分明。No11下排供养人不仅在服饰上与本文相同,且发髻上拢,顶部呈起伏状,饰物简略(图16) [16]109,其中一身外加小袖式披风,“有的贵族妇女另加小袖式披风,竟成一时风气”,为隋代风尚[17]。
主从关系形式的供养人始于龙门石窟古阳洞503年,而交领这一形式则始于南北朝,一直流行到隋代[14]71。另外,这一形式不仅仅存在于北周地区,如巩县石窟第2、4窟,河北邯郸水浴寺西窟众多供养人当中,居中的女供养人与本文所述麦积山供养人形式基本一致,同样为主从关系,侍女随后并手托主人后裙。主人交领,大袖前笼,中缝、袖缘清晰可见。
西部地区在莫高窟隋代洞窟如第295窟、第407窟,壁面下部可见到形式相近的供养人形象,亦具备上述几个特征,如第295窟中,由僧人前导,身材高大的主人与侍女随之,主人与侍女前后排列形成主从关系。主人交领大袖,双手前笼,手持莲花(第407窟无莲花,榜题已模糊),大袖笼为椭圆状;第407窟的一列女供养人尚外披小袖披风,与前述水帘洞石窟的情况相同。
(三)供养人发髻特征
供养人所体现的隋代特征不止于服饰,尚见于其发髻形式。本文供养人女主人发髻上拢,顶平。平顶侧面略有洼陷,隐约可见结带装饰。这一装饰于左侧第二列存留较为明显,如第一组女主人发髻上结带,随后的第二、五、六组亦能辨认出带状装饰。侍女二人发髻较小,与主人形式基本相同,“大量陶俑反映,可知同式发髻,在隋代实具一般性,贵贱差别不甚多”[17]201。后方提裙侍女结头巾,平顶。供养人头部略前撑,收下颌,安静行进。
隋代发式“比较简单,上平而较阔,如戴帽子,或作三饼平云重叠”[17]202。从莫高窟第390、295、389窟等的女供养人形象来看,发髻基本相似,且少饰物。炳灵寺石窟隋代第8窟赴会菩萨下方所绘供养人中,下列女供养人发髻上结,平顶,反映出同样特征。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女陶俑“发式和敦煌壁画所见相同。大袖衣,长裙,垂带,发作三叠平云,上部略宽,仍近隋式一般样子”[17]206。本文供养人的发髻形式,主人与侍女无大差别,恰符合上述观点,体现出典型的隋代特征。无论壁画还是墓葬出土陶俑,隋代供养人装饰较少,与其社会风俗简约息息相关[17]203。
三 西方净土变周围壁画
本文西方净土变的周围壁画尚存(图4),上方平棋绘一方飞马图,上绘飞天、飞象;平棋左侧梁绘坐佛,现仅见三佛。净土变下方、右龛右侧壁面上下各绘一幅说法图,上图主尊为交脚,下图主尊结跏趺坐。两图同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华盖形式近似,下图华盖处脱落较严重,但由华盖下垂数条条帛以及铃状物一点,两者一致。供养人形象出现于说法图下方,上图供养人形象较高大,一前一后,为主从形式。前方一人长裙,后方一人略小,肩披长帛。右侧仅存一人,披长帛。此处现存供养人为窄袖。下图说法图供养人与净土变供养人完全相同,主从形式,女主人交领大袖,发髻顶平。侧壁净土变下方分两处,各由明显的界栏线分开,上为三身僧人形象,已模糊难辨;下为一头光,仅存半边,其上下角绘一飞天与一说法图。
这些壁画与西方净土变的绘制时期相差不远,以下就其具体细节,如主尊、菩萨、飞天、供养人和纹样等进行略述。
各图主尊共五处:净土变,平棋侧,下方右龛右侧上下说法图,右侧壁头光左下。五处主尊主要有几点相近之处,其一主尊的身体表现及衣着方式,其二台座,其三华盖。五处主尊上身敦厚,除平棋侧三坐佛模糊难辨之外,其余右臂贴身上举至胸,由肩至肘轮廓浑圆;除两处交脚之外,其他三处结跏趺坐,尤其净土变主尊两膝微上抬的形式显示出隋代的典型特征。袈裟右肩斜搭,下摆仅覆于台座上。袈裟宽幅沿边,非常醒目。内衣袒右,斜过胸部,尤其净土变与其下方说法图主尊的内衣一致,上有竖条纹样,腹上结带。袈裟由右臂下搭向左臂或左肩时,袈裟边缘横于腹部,搭上左臂后下垂,在左腕处形成一个如三角的凸起形状。几处主尊均为此同样形式,可见其绘制时间间隔不大。
五处主尊当中有两处为交脚形式,一为平棋侧梁三尊的中间一尊,二为净土变右下方二说法图的上方一尊,两者台座同为方形,双足踏莲花。其他主尊均为须弥座,包括侧壁净土延伸处菩萨形的莲座。除平棋侧梁三坐佛外,其他几处主尊均有华盖,净土变主尊的华盖保留相对完整,虽有脱落但非常清晰,可见其大致原状。华盖双层伞式,腰部交界有一圈连珠纹,并排另有宝珠立体装饰其上。一朵朵花座宝珠环顶一周,最中心一朵恰嵌于平棋边缘连珠纹的大珠内。华盖边缘下垂一圈铃状装饰,左右残存飞天天衣,华盖右侧可辨出两身,可见至少左右各绘两身。与此华盖最为近似的是侧壁头光左下说法图。华盖双层伞式,盖顶饰宝珠,边缘呈波状,下垂一圈铃状装饰。
菩萨以净土变为主,有宝地上坐姿与立姿的菩萨,侧壁净土变延伸处坐于莲台上的菩萨,另有净土变下方二说法图中的胁侍菩萨。通观其服饰,均头戴三面宝冠。宝冠山形,中央及左右耳部各有圆形饰物,头后部中央也饰一圆形饰物。宝地上的立姿菩萨有的回头向身后同伴交谈,可见宝冠呈箍状至头后部。其周围颜料脱落后,圆状饰物突显,侧面观恰如头顶和侧面两圆形饰物连接起来的形式。如前所述,这一点与平棋飞天相同,也为判断宝池中伎乐平台上的伎乐天提供了参考。另有菩萨,头部左右下垂细长宝缯,面部椭圆,尚可以联系炳灵寺石窟隋代第8窟南北两壁上部的菩萨,宝冠在饰物细节上较为简略,但形式与本文菩萨形象一脉相承。
保存状态最佳的菩萨为侧壁净土变延伸处最外的三身,身体部分已变黑,三面头冠及搭肩天衣映衬,显得轮廓清晰。菩萨佩项饰及腕饰,闲适地坐于莲台上,由此可以推断宝池中已完全脱落的胁侍菩萨形象。立姿菩萨当属右侧上方水渠近旁的一身比较典型,正面姿,左臂屈肘外举,身体呈S形。这一立姿同于净土变下部上下二说法图中的胁侍菩萨,腰部略有扭动。
飞天首推平棋,画面中心一飞马与一飞象,上下可辨认五身飞天,尤其下方三身完整,均为侧面观,天衣于身后环绕呈椭圆形,戴三面宝冠,与上述菩萨宝冠形式相同,顶部与耳侧圆形装饰由横箍连接。右侧壁飞天与净土变下方二说法图基本接近,尤其与上方说法图类似,几为正面观,飞天身体由胸部向后扬起,天衣于头上方飘扬呈椭圆形,动感极强。四瓣形花散在平棋、右侧壁和下方说法图中各处可见,花瓣作十字形,围绕中央圆饰。二说法图下方说法图的飞天呈侧面观,上身曲线鲜明,手臂上举。
供养人有两处,除净土变下方左右数列以外,尚有净土变下方二说法图的供养人,均为女子形象。其中与净土变的三人一组形式的供养人完全一致的是二说法图下图的供养人,仅于主尊右下绘有一组,前方主人保存较好,大袖,拢手持花,后方侍女几近模糊。而上图供养人左右而立,现左侧二人,主人在前着红衣;右边一人,绿衣,肩披长帛。此处供养人均为窄袖。
右侧壁坍塌部分尚存半面头光(图7),头光外围火焰纹,火焰由红绿两色交替描绘,并由一类似“3”字的纹样显示火焰的升腾。火焰纹内侧两条暗色圆形之间,夹绘唐草(卷草)纹样。关于唐草纹样见本文第一节“宝池”部分,主尊背后方形板状物及龛口边缘纹样处已述。
四 绘制年代
本文分析重点在于净土变,虽然龛内造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有必要稍事涉及一下造像的特点,尤其中央龛内主尊与胁侍弟子像、菩萨像与同石窟隋代造像具有密切的联系,最为典型的是第24窟。两者主尊在身体造型上相似,上身敦厚,宽肩,袈裟披着方式及手印基本一致,悬裳下垂。此外,右胁侍弟子与菩萨均极其近似,双腿与上身厚度相比较,略显细且短。弟子右手持袈裟一角以及菩萨前发的特征等细节两者均相同,可见中央龛内造像的隋代特征明显。第5窟中央龛内右壁外侧菩萨身体微微朝向龛口,与莫高窟第427窟菩萨相似[7]363-364。
在分析净土变及下方供养人的特征时,本文联系了这铺净土变周围现存的壁画。净土变画面重点在于宝池和宝地,将主尊及胁侍菩萨、化生、狮子和伎乐平台等均安排于倒凸字形宝池当中,由宝池延伸出带状水渠纵横环绕宝地。宝池与带状水渠共存于同一画面的构图形式,是这铺净土变的独到之处。宝池中主尊身后屏风上的双环连珠为隋代常见纹样;宝地上建筑的表现和手法,细节如水门顶的平涂等显示出隋代特征,菩萨形象的侧面观略突腹,正面观稍有扭动,呈现出动感。下方供养人交领大袖及发髻形式均体现出典型的隋代特征,为年代判定提供了确实依据。
净土变周围现存壁画在主尊衣着、菩萨形象等细节以外,纹样等方面均相互联系,可见现存壁画的绘制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唐草(卷草)纹样、连珠纹等与龛内存留的原作壁画基本一致,同时尚有关于龛外踏牛天王的研究,“着平巾帻袍服,髭须上作菱角翘,下作尖锥式,为隋代特有式样……如麦积山牛儿堂彩塑天王”[17]213。由此,无论构图还是细部,这一铺西方净土变的绘制年代基本可定于隋代。
五 构 图
西方净土变于麦积山尚有第127窟右壁上方一铺,带状宝池置于画面下方,水中绘莲花、莲叶。画面以主尊为视觉集中点,两旁以左右对称形式安排弟子圣众及树木直线排列,与其后的阙门一起体现透视效果。这些特点均与成都万佛寺二菩萨立像光背背面上部净土变,在构图形式和表现方式上意图接近,尤其突出的是以俯瞰的方式表现画面的进深。本文净土变在构图上基本汲取了这两铺净土变的特点,进而在强调宝池方面,本文净土变又与莫高窟初期净土变紧密联系,宝池居中,比较忠实于经文。本文净土变在结合麦积山传统并参照成都万佛寺净土变的基础之上,发展了带状水渠,有序安排宝地、宝楼等,使净土变构图进一步完善。如此来看,本文净土变可谓承前启后,串联东西,这也和麦积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万佛寺净土变于画面下部中央刻出桥梁,以示通往净土之道,而本文净土变于画面下部略偏右处绘出桥梁,显示出随意性,但联系观者进入净土的意图明显,随意性显示更易于进入净土。
本文净土变画面中心广大宝池的描绘与莫高窟第57、220窟的表现有相近之处,但两者在构图意图上又有明显的不同。莫高窟第220窟以平面画面展现各个细节,而本文净土变宝池居中,宝地广阔,同时注重表现画面进深,呈现出一个非平面的而为立体的画面。其后的净土变逐渐减少宝池在画面所占的面积,扩大华座,画面左右延伸的水渠进一步发展完善,强调的重点有所转移。本文净土变的宝池和水渠共存,除此以外,对于宝地、宝楼、桥梁和虚空等净土变图像的各个构成要素都有细致描绘,并无遗漏。虽然这些描绘尚不完善,但它出现于隋代,对于后期净土变的发展起到开启先河的作用,同时在西安地区现存净土变较少的情况下,为了解西安同一时期净土变的状况提供了参考。
附记:文中图1、图2采自《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图12、图16为笔者制作。图16中,第140窟与160窟线描图采自孙晓峰氏论文,水帘洞No11采自《水帘洞石窟群》。文中图片由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提供,部分图片由魏文斌氏提供。
参考文献:
[1]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壁画编[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引言.
[3]傅熹年.麦积山石窟所见古建筑[M]//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01-218.
[4]李志荣.麦积山第5窟壁画遗迹的初步观察[M]//麦积山石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89-301.
[5]花平宁,魏文斌.麦积山[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185-187.
[6]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石窟志[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319.
[7]八木春生.中国仏教造像の変容南北朝後期及び隋時代[M].东京:法藏馆,2013:363.
[8]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9-110.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0]荣新江.略谈徐显秀墓壁画的菩萨连珠纹[J].文物,2003(10):66-68.
[11]张庆捷,常一民.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J].文物,2003(10):53-57.
[12]高楠顺次郎,等.大藏经:第12卷[M].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7:347.
[13]八木春生.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相图[J].敦煌研究,2012(5):13.
[14]石松日奈子.古代中国·中央アジアの仏教供養者像に関する調査研究[D]//2008年度-2010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2011:35.
[15]孙晓峰.麦积山石窟北朝供养人调查[M]//麦积山石窟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87.
[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水帘洞石窟保护研究所.水帘洞石窟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40.
[17]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