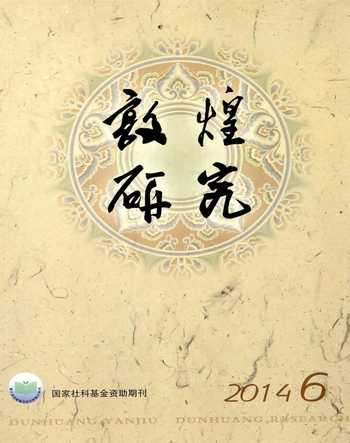佛传中的洗浴太子:从经文到图像的转变
王慧慧



内容摘要:浴佛节为纪念释迦诞生而设,是佛教的一个重要节日。摩耶夫人怀胎十月,于四月初八(一说二月初八)在一处花园里生下了释迦,多数佛经记载当时还有两条龙从空中口吐温水、凉水,为他洗浴,是为“二龙灌顶”。二龙灌顶图流行于藏传佛教和西域地区。只有一部佛经记载是九龙灌顶,但中国佛教却流传九龙灌顶之说,早在北魏时期九龙灌顶在当时已经得到普遍认同,佛教造像中频见九龙灌顶图像,佛教文献中也有记载。本文对二龙灌顶、九龙灌顶的佛经记载和图像流传进行了分析,提出从经文的二龙灌顶到图像的九龙灌顶的转变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绝好例证。
关键词:佛传;二龙灌顶;九龙灌顶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6-0001-07
佛传是指释迦从诞生前后至涅槃的一生事迹(本行),有时也追溯前生(本生,主要是儒童本生)。关于佛传的经典很多,主要有(东汉)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2卷、(东汉)支谦《太子瑞应本起经》2卷、(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8卷、(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5卷、(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4卷、(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60卷等,这些佛经着重是对释迦诞生前后的背景、释迦活动的描述。至于释迦涅槃前后的事迹,则详见于独立的《涅槃经》。另外,中国僧人(梁)僧祐集各经所说而编有《释迦谱》5卷。
佛教造像中,单一画面的佛传较多,如乘象入胎、夜半逾城、降魔、初转法轮、涅槃等,一般称之为佛传图。连续性长画的佛传,可称之为佛本行经变。太子诞生时有龙神吐水为太子洗浴,是为龙神灌浴太子,各种佛经对龙神灌顶的记载略有差异,试作一辨析。
一 洗浴太子的佛经依据
(东汉)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卷上记载:“到四月八日,夫人出游,过流民树下,众花开敷。明星出时,夫人攀树枝,便从右胁生,堕地行七步,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应时天地大动,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大明。释梵四王与其官属,诸龙、鬼神、阅叉、揵陀罗、阿须伦,皆来侍卫。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郁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梵摩持天衣裹之,天雨花香,弹琴鼓乐,熏香烧香,捣香泽香,虚空侧塞。夫人抱太子,乘交龙车,幢幡伎乐,导从还宫。”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1记载:“尔时夫人既入园已,诸根寂静,十月满足。于二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花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花,大如车轮,菩萨即便堕莲花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说是言已,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身黄金色,有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亦于空中作天伎乐,歌呗赞颂,烧众名香,散诸妙花,又雨天衣及以璎珞,缤纷乱坠,不可称数。”按:此经说释迦是二月八日诞生,而《修行本起经》等经说是四月八日诞生。
(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33记载:“是时于佛母前,有清净好池,以浴菩萨,梵王执盖,帝释洗身,二龙吐水。”
有的佛经只提到空中有冷水、暖水流下洗浴太子,没有明确提到是龙王所为。(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卷1记载:“应时虚空中,净水双流下,一温一清凉,灌顶令身乐。”(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8记载:“菩萨生已,诸眷属等求觅于水,东西南北皆悉驰走,终不能得。即于彼园菩萨母前,忽然自涌出二池水,一冷一暖,菩萨母取此二池水,随意而用。又虚空中,二水注下,一冷一暖,取此水洗浴菩萨身。”这两部佛经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二龙灌顶,但所表达的意思相当于二龙灌顶。
(东汉)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没有记载诸龙灌顶,也没有提到冷水、暖水洗浴,而是四天王为太子洗浴:“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汤,浴太子身。”
九龙灌顶,佛经记载不多,笔者仅查到一部佛经有九龙灌顶之说。(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卷2记载:“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圣尊。”九龙灌顶似仅见于此经记载。
上述与释迦诞生相关的佛经多数记载是二龙洗浴太子(《修行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大智度论》、《佛本行集经》等),另外还有天空下温水与凉水洗浴太子(《佛所行赞》)、四天王洗浴太子(《太子瑞应本起经》)、九龙洗浴太子(《普曜经》)等多种说法。玄奘《大唐西域记》卷6“劫比罗伐窣堵国”条记载:“箭泉东北行八九十里,至腊伐尼林,有释种浴池,澄清皎镜,杂花弥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无忧花树,今已枯悴,菩萨诞灵之处。菩萨以吠舍佉月后半八日,当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则曰以吠舍佉月后半十五日,当此三月十五日。次东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二龙浴太子处也。菩萨生已,不扶而行,于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随足所蹈,出大莲花。二龙踊出,住虚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暖,以浴太子。浴太子窣堵波东,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龙从地踊出之处。菩萨生已,支属宗亲莫不奔驰,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暖,遂以洗浴。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释捧接菩萨处。菩萨初出胎也,天帝释以妙天衣,跪接菩萨。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萨处也。菩萨从右胁生已,四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萨,置金几上。”
尽管多数佛经记载是二龙灌顶,但中国佛教却普遍流行九龙灌顶之说,汉传佛教造像中基本上都是九龙灌顶图,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二 九龙灌顶图像
九龙灌顶在4世纪上半叶就开始流行,(晋)陆翙《邺中记》有两处记载石虎(295—349)举办九龙灌顶佛事:“石虎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门徘徊,反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粲丽。四月八日,九龙衔水浴太子之像。”“石虎性好佞佛,众巧奢靡,不可纪也。尝作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木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亦解飞所造也。”
佛教造像碑中,表现太子诞生时的龙神灌顶图可见多例,最早有纪年的一例可能是日本私人收藏的《北魏太安三年(457)宋德兴造像碑》,正面是禅定佛,背面上刻树下诞生、下刻九龙灌顶(图1)[1]。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和平二年(461)造像碑》的正面是禅定佛,背面是佛传和须大拏太子本生,碑背面正中为九龙灌顶,榜题是“九龙浴太子时”。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皇兴五年(471)造像碑》的正面是交脚佛,背面是佛传,最上面是八龙灌顶。该博物馆还有一件没有纪年的北魏造像碑,刻有七龙灌顶{1}。由于佛经中没有七龙灌顶、八龙灌顶之说,我们视之为九龙灌顶的变通形式。日本大和文华馆藏《延兴二年(472)张伯和造像碑》的正面是禅定佛,背面上起:上残,存七佛一列;树下诞生,太子左右各刻三龙;供养人一列;背面碑座为发愿文[1]10。
此后的汉传佛教造像中龙神灌顶多数是九龙灌顶,不一一列出。
在石窟造像中,我们也能看到若干龙神灌顶的图像,如:
莫高窟第290窟建造于北周,窟顶佛传有87个情节,其中有九龙灌顶(图2);莫高窟第61窟建造于五代晚期,佛传屏风画中画有九龙灌顶[2]。莫高窟第454窟建造于宋初,西壁下方屏风画佛传中有龙神灌顶,图像比较模糊,似乎画出六龙。榆林窟第36窟建造于五代,南壁佛传屏风画中有九龙灌顶[2]169。英国博物馆藏敦煌绘画品S.P.99佛传故事画中也是九龙灌顶,S.P.89佛传故事画中是七龙灌顶。按:六龙、七龙可视为九龙灌顶的省略。
云冈石窟第6窟开凿于5世纪后期,该窟佛传之九龙灌顶图中,太子左右各一人,可能是帝释天、大梵天(图3)。《过去现在因果经》记载:“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头顶8身龙王,与经文略有区别,但仍应视为九龙灌顶。赵昆雨先生认为太子身边的人物为龙王,上面的8龙是龙王身份体现[3]。
青海瞿昙寺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环寺回廊画有47幅佛传,其中第13幅为九龙灌顶图。九龙在云中吐水。榜题:“护明菩萨降生,九龙吐水,灌沐金躯。九龙吐水沐金躯,大地山河尽发辉。穷劫至今无垢净,满堂花雨落霏霏。”[4]据研究,“回廊壁画的创作年代当在永乐十六年(1418)或宣德二年(1427)前后。”部分清代重绘{1}。
另外,弥勒经典中也提到与释迦类似的弥勒佛传故事,记载较详细的是义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其他弥勒经典对于弥勒诞生都是一笔带过,都没有提到龙神灌顶,如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记载:“弥勒托身,以为父母。”只有义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记载有龙神灌顶:“龙降清凉水,澡沐大悲身。天散殊妙花,虚空遍飘洒。”但没有提到龙神的数量。敦煌石窟中,约有30铺弥勒经变有龙神灌顶图像。由于弥勒佛经没有记载弥勒下生时几条龙降水,所以弥勒经变中龙神的数量不一,但多数是九龙灌顶(第85、133、186、222、231、240窟等),有的则画出一龙(第117窟等)、五龙(第112窟等)、六龙(第72窟等),有的则只画云彩、没有画龙(第360窟等)。第85窟窟顶西披弥勒经变的九龙灌顶图的榜题是:“龙降清凉水,澡沐大悲身。天散殊妙花,虚空遍飘洒。是名浴太子。”其中最后一句不是经文,而是画工所加。莫高窟第112窟建造于中唐(蕃占期间),西壁龛内三壁各画屏风二扇,其中南壁东起第2扇、西壁南起第1扇画采花供佛得生天故事,见(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6。其余四扇画弥勒故事,南壁东起第1扇画灌顶,一童子手指天地,上方画五龙灌顶。该窟东壁门上、门南侧画弥勒经变(门上降魔成道、门南中央画弥勒菩萨立像,宝塔冠,左手持花,右手不清楚,两侧以条幅画形式画弥勒事迹,南侧存4个画面,上起:见迦叶、迦叶献袈裟、迦叶显神通、弥勒说法)[5]。弥勒经变中的灌顶图多数为九龙灌顶,当为吸纳了释迦诞生的情景。由于是弥勒经变的一个场景,所以图像比佛传简略得多,多数只有太子一人,周围没有其他人物,如中唐第186窟的窟顶西披、南披、北披画弥勒三会,东披画拆幢,拆幢与三会周围画各情节,南披东侧有九龙灌顶,红色祥云间露出9个龙头,下方站立一童子(图4)。
三 二龙灌顶图像
九龙灌顶流行于汉传佛教,而受印度、尼泊尔、藏传佛教影响的佛教壁画中则流行二龙灌顶,敦煌石窟有两例宋、西夏时期的一龙灌顶图像,可视为二龙灌顶的简略形式。
莫高窟宋代第76窟东壁门两侧画八塔变,其中南侧上层南起第一铺为第一塔,画出释迦诞生,一龙乘彩云而下至太子头顶(图5);榆林窟西夏第3窟东壁佛传中,画一龙灌顶(图6)[2]168,193,213。莫高窟第76窟的八塔变,有学者认为佛经依据是宋代法贤译的《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但该经内容极其简略,没有佛传的具体情节,这铺八塔变的内容当另有所本。榆林窟第3窟为西夏时期建造的藏传佛教洞窟,壁画题材不应按汉文佛经来解读,笔者不懂藏文和西夏文,该窟一龙灌顶的经典依据也无法确定。敦煌石窟从北朝到宋代的灌顶图像中没有发现二龙灌顶图像,莫高窟第76窟、榆林窟第3窟的一龙灌顶可视为二龙灌顶的变通形式,较少受到汉地九龙灌顶图像的影响。
克孜尔石窟第99、110窟佛传中有灌顶图,为二龙灌顶,丁明夷先生等《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一文介绍说:“二龙浴太子。这一题材,仅见于第99窟左甬道外壁和110窟主室左壁。画面作一站立的裸体小儿,双龙从虚空中注水而下,洗浴太子身,右侧跪立各一人。此为二龙洗浴太子身的故事。”{1}
拉达克阿齐寺松载殿(三层殿)大殿中尊是泥塑弥勒立像,高4.6米(左胁侍为文殊、右胁侍为观音),根据题记,松载殿弥勒像制作时间约是12世纪晚期或13世纪早期。弥勒裙摆上绘佛传,经克里斯蒂安·卢恰尼茨(Christian Luczanits)编号整理,共有46个场景。场景10为“龙王施洗”,龙王在太子两侧,卢恰尼茨记录为:“龙王难陀和优波难陀用冷水和温水为新生的释迦沐浴。两位龙王都具四臂,靠下的一只手上拿着的东西好像是螺。”[6]
西藏阿里扎达县阿钦沟石窟的年代约是13—14世纪。第2窟佛传壁画位于后室两侧壁(东西壁)的下方,画幅长卷式自左至右排列,画幅高仅29厘米。佛诞场景为第5幅,图中两龙王是在佛上方左右两云朵上,张建林先生记录为:“赤身裸体的释迦牟尼已经站立在莲花上,四周各有莲花,象征释迦牟尼向四方各行七步,步步生莲。旁边站立一天人向其招手,上方的云朵上两龙王手持水瓶向下浇水。”[7]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景耀寺石窟始建于清代,有3个洞窟保存有壁画,其中第1窟佛传故事中有三龙在云中吐水,下方佛母侧举右手,表示右腋诞生,有二人用双手拉着布兜着太子,太子仅露出头部,三龙的上方有一行藏文题记“Sku khrus gsol ba”(浴佛)。接婴儿的二人也有藏文榜题,画面左侧:“tshangs-pa ”(大梵天); 右侧:“brgya-byin ”(帝释天)(图7)。景耀寺第1窟三龙灌顶图可视为二龙灌顶的变通形式。
成都万佛寺出土的佛教造像中,有一件造像碑,碑背线刻佛传,其中之一为一龙灌顶{1}。因为佛经中没有一龙灌顶之说,所以可将此一龙灌顶视为二龙灌顶的简略形式,但这一灌顶形式并不流行,属于例外。
四 九龙灌顶图所反映的佛教中国化问题
九龙灌顶仅见于《普曜经》的记载,而记载二龙灌顶的佛经很多,但5世纪中后期的造像碑、石窟、文献记载都采用九龙灌顶之说。二龙灌顶与九龙灌顶的转换,值得关注。
印度、中亚的佛传图像中有龙神灌顶,李静杰先生在《北朝佛传雕刻所见佛教美术的东方化过程——以诞生前后的场面为中心》一文中,考察了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犍陀罗地区的太子灌顶雕刻、瑞士日内瓦民俗学博物馆所藏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太子灌顶雕刻等。李静杰先生指出:“印度的灌水场面中没有发现龙的造型,而龙出现在犍陀罗、新疆、中原北方地域,说明了此三地佛传经典记述与印度存在着差别。中原北方比较固定地表现为九龙灌水,与新疆众多龙灌水的表现有所不同,这种情况也应视为经典记述的差异所致。”[8]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不仅是“经典记述的差异所致”,应该与佛教中国化有很大的关联。
莫高窟第290窟佛传主要依据竺大力等译《修行本起经》绘制的,樊锦诗先生在《敦煌石窟全集》第4卷《佛传故事画卷》研究部分中指出:“第290窟佛传故事画主要依据东汉译《修行本起经》绘制。东汉末至南北朝汉译佛传经典较多,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绘画的内容,既不采用西晋竺法护在西北地区译的《普曜经》,也不用距北周时间最近,由名僧僧祐撰《释迦谱》的经本,而选用佛陀传记经本中最早的译本《修行本起经》作为依据,其用意是为了表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悠久。”但《修行本起经》记载“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郁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经文明确提到是二龙灌顶,因此,樊锦诗先生在《敦煌石窟全集》第4卷《佛传故事画卷》第39图第290窟九龙灌顶图版说明中指出,这是依据《普曜经》绘制的[2]53,63。
莫高窟第61窟建成于947年,南壁、西壁、北壁下方有33扇佛传屏风画,计有128个情节,九龙灌顶位于第10扇屏风画中(西壁南起第1扇)。万庚育先生依据残存榜题分析,发现这些榜题多数取自(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指出:“大部分榜题内容与此经文相符,因此可断定第61窟《佛传》是根据《佛本行集经》绘的。”[9][2]139《佛本行集经》长达60卷,但相关经文并没有提到九龙灌顶,该经卷8记载:“菩萨生已,诸眷属等求觅于水,东西南北皆悉驰走,终不能得。即于彼园菩萨母前,忽然自涌出二池水,一冷一暖,菩萨母取此二池水,随意而用。又虚空中,二水注下,一冷一暖,取此水洗浴菩萨身。”虚空中流下冷水、暖水,应该属于二龙灌顶。显然,第61窟九龙灌顶图不符合《佛本行集经》的二龙灌顶记载。
莫高窟第454窟建造于10世纪70年代,西壁下部、北壁下部有佛传屏风画,其中的龙神灌顶图比较模糊,大约画出六龙,佛传的榜题保存若干,郭俊叶先生对第454窟佛传进行了考察,指出:“佛传前面部分榜题来自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等绘制,中间部分取自隋代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经》,尾部分(据)S.2084《佛母经》与唐代若那跋陀罗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后分》等绘制。”[10]
从《邺中记》的记载看,九龙灌顶早在4世纪就开始流行,画工在绘制第290、61、454等窟的九龙灌顶图像时,未必参考了《普曜经》,而是选择当时普遍流行的九龙灌顶图像,与经典的关系不大。
从二龙灌顶变为九龙灌顶,在中国佛教文献上,也可找到一些资料。(梁)僧祐抄集诸经,编成《释迦谱》5卷,卷1提到:“《大善权经》云:菩萨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为正士应七觉意觉不觉也。举手而言,吾于世间,设不现斯,各当自尊,外道梵志,必坠恶趣。为善权方便,天帝释梵雨杂名香,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萨。”但竺法护译《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上原文是:“何故菩萨清净无垢而复洗浴,释梵四天所见供侍?凡人初生皆当洗浴,菩萨清净,随俗而浴,况世人乎?故现此义,是为菩萨善权方便。”比较得知,《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并没有说是九龙灌顶,显然僧祐混淆了《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与《普曜经》的内容,僧祐的错误,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现在无法确定。
东汉末年成书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开篇即云老子诞生时,有九龙灌顶:“既诞之旦,有三日出东方。既育之后,有九龙吐神水。”[11]是否竺法护翻译《普曜经》时将原经文的二龙灌顶以格义的形式译成九龙灌顶了呢?古人认为数字九代表最尊贵之意,如九州、九鼎、九五之尊等说法,佛教造像不用佛经记载很多的二龙灌顶之说,而是取记载甚少的九龙灌顶之说,并广泛采用,应该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经典记述的差异所致”吧!
学者已有的研究表明,莫高窟第290窟佛传多数画面依据《修行本起经》绘制、第61窟佛传多数画面依据《佛本行集经》绘制,但两种佛经记载洗浴太子都是“二龙灌顶”,两窟的洗浴太子图却都是“九龙灌顶”,可能不是依据《普曜经》内容绘制,而是采用了当时普遍流行的九龙灌顶造像形式。至于西域、藏传佛教造像则依然依据佛经记载,用经典中的“二龙灌顶”来表示“洗浴太子”,汉文化对佛教的改造,于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6.
[2]樊锦诗.佛传故事画卷[M]//敦煌石窟全集:第4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63,139.
[3]赵昆雨.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46.
[4]金维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藏传寺院壁画(1):第115图[M].天津:天津美术出版社,1989.
[5]樊锦诗,梅林.莫高窟第112窟图像杂考[J].敦煌研究,1996(4).
[6]克里斯蒂安·卢恰尼茨.松载殿的佛传图.廖旸,译.[M]//张长虹.越过喜马拉雅:第1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90.
[7]张建林.阿钦沟石窟的佛传壁画——兼谈古格王国早中期佛传壁画的不同版本[M]//刊拉巴平措,等.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8.
[8]李静杰.北朝佛传雕刻所见佛教美术的东方化过程——以诞生前后的场面为中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
[9]万庚育.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画《佛传》之研究[M]//敦煌文物研究所.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88-89.
[10]郭俊叶.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0:203.
[11]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