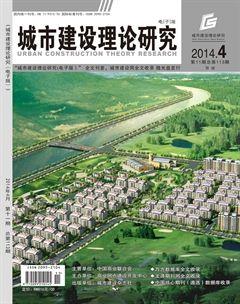城市新区控规弹性控制体系初探
毛磊
摘要:当前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已然显现,特别表现在面对城市新区地块开发过程中用地调整问题包容性的欠缺,从而对控规的适应性产生冲击。面对这些问题,通过技术与管理手段结合的方式,形成完整的弹性控制体系,在保证控规刚性的同时赋予地块开发一定的弹性,保证新区建设按照控规的指导思路顺利进行。
关键词:控制性详细规划; 弹性控制; 城市新区; 控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 A
城市新区是我国城市郊区化的产物,早期主要由于城市蔓延及老城区衰败而产生了功能相对单一的城市片区,如工业区、物流园区、居住区等。近年来城市高速发展,功能结构更加完备,老城更新与旧城改造的深入进行使得城市承载能力趋于峰值,而城市化带来大量人口的涌入与饱和的城市空间产生了矛盾。为避免城市圈层式外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开始了卫星城的建设,被称之为城市新区或新城。此类新区为综合性城市,其功能混合,结构复杂,集居住、工作、休憩、交通四大基本功能与一体,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独立性特征,在地域空间上具有相对明确的发展界限的集中城市化区域。
城市新区的特征决定了其开发控制的弹性要求,由于其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前期招商引资中开发商的土地调整要求等因素,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地块的指标、性质都存在着较大的变数。管理部门往往为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而默许上述调整要求,使得传统控规的控制方法丧失控制能力,控制性详细规划(下文简称“控规”)也因丧失其法定性从而失去控制效能。文章通过对当前控规存在的问题及法定控制体系中的不足分析,寻求控规控制体系对地块调整的包容,形成自身内部的动态调整机制,配合合理的规划管理方式,构建出针对城市新区的弹性控制体系。
1,控规的缘起与作用
控制性详细规划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的中国城市规划体系中并不存在控规,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总体规划太泛,不能指导具体地块建设;修建性详细规划又过于细致,不利于整体的把控。当时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土地也从计划经济时的无偿划拨转向市场经济的有偿出让,土地的使用强度与利益的挂钩使得了开发商以高强度开发来追求高额利润,从而导致了城市建设朝无序状态发展。在此之下,控制性详细规划应运而生。1982年上海虹桥土地出让规划的编制完成可以说是形成了我国第一个控规,其后桂林中心区详细规划、广州70平方公里的街区规划都在不断完善控规体系,终于在1991年,建设部将控规的内容列入到《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当中,这标志着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系的形成,同时也是规划应对中国市场经济初期的城市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反应。
控规作为法定规划被确立使得我国城市规划体系更加完善,其产生对城市开发控制具有以下几点作用:首先,承接了上层次的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将上位规划的构想与空间布局通过指标的形式深入落实下来,并指导下一层级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其次,控规明确提出了地块的具体控制要求,对规划管理中土地出让、项目审批提供了依据,加强了城市开发中规划、管理、建设三个方面的联系;第三,以数据的形式对城市三维空间进行引导,同时从城市美学、建筑空间等艺术方面对未来开发的建筑体量、色彩、形式、组群等方面进行要求,指导城市设计的进行。
2,当前法定控制体系
控规的控制体系为规划研究的结果,包括规定性(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引导性)指标。其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土地使用、设施配套、建筑建造、行为活动[1][[1] 城市规划资料集4—控制性详细规划 [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P17—P18]四个方面:
土地使用包括土地使用性质及环境容量控制。土地使用性质主要对用地进行定性、定量、定位,也就是确定土地的使用性质、用地面积及用地边界;环境容量主要强调城市的环境品质及土地的承载力,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控制要素。土地使用主要以规定性指标为主,突出其控制的核心性。
建筑建造主要包括建筑建造控制及城市设计导引。建筑建造从建筑高度、建筑后退及建筑间距方面进行控制,强调建筑群之间的关系,及城市的消防、抗震、卫生、安全等多方面技术原因;城市设计导引以城市美学为基础,空间艺术设计为手段,对建筑体量、建筑色彩、建筑形式等建筑单体空间环境及建筑空间组合、建筑小品、其他环境要求等建筑组群空间环境方面进行了引导性控制。
设施配套包括市政设施配套和公共设施配套。设施配套保障了城市的生产生活。市政设施包括城市给水、排水、供电、交通等设施;公共设施包括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休闲、办公等设施。
行为活动包括交通活动控制及环境保护规定。行为活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了人的活动的舒适性与安全性。交通活动控制包括交通组织、出入口方位及数量、装卸场地等;环境保护规定包括噪声、废气、废水、垃圾等方面进行控制。
3,当前控规实施过程中呈现的问题
3.1编制技术方面的不足
3.1.1传统控制方法弹性不足
传统的控制方法指对总体城市与具体地块两个层级进行控制的方法。总体城市延续分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发展目标,预测城市发展规模、建设总量、建设量分布状况等;具体地块承接总体城市层面确定的建设总量,综合建设量分布状况将具体的建设指标平衡到具体地块之中。此种方法在逻辑上并不存在问题,但城市建设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若干具体地块的建设共同完成城市发展的目标。而现实的建设过程中,地块调整层出不穷,面对如此情形,一旦地块的调整突破了规划的控制性要求,这种控制方法便失去其控制效能,大量的地块调整将导致控规失效。
在城市建设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地块指标调整必然导致其他地块指标随之变化。若在不强制保障城市建设总量,过多地块调整可能导致控规失效的结果;而为了保证城市建设总量要求,可能引发城市建设的混乱。在市场面前,控规便显得极为脆弱,其结果是既未保障公共利益,又制约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完全偏离了开发控制的初衷。[2]
3.1.2控制指标科学性、灵活性不足
控制指标是控规的核心内容,当前控规指标确定多以类比法、布局模拟法、规范规定法等方法进行确定,这种直接“拍脑袋”或套用国家及地方规范确定的指标难以与具体地区的现实情况相符合,而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日照间距要求、地块位置条件等各有不同,因而形成控规指标与实际要求不符,难以指导控规实施。
控规指标对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的限定主要通过限定其最高值的方法进行,而限高值的确定在城市新区这种空间限制条件较少的区域难以确定,而具体地块开发在此区间的取值将受到上限值的限制,指标的可选择幅度难以满足市场要求。
3.1.3土地兼容控制不完善
当前土地分类是按照2011年最新出台的标准制定的,较之1990年标准的分类有所进步,但变化不大。城市用地分类的类型并不能满足规划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城市用地开发中的用地混合问题,住宅与商业开发混合一起,新兴物流呈现商业、办公、仓库于一体等多种用地混合形式,这些要求都难以在控规的用地分类中得到满足,简单的强制性要求会造成项目难以实施或过长的申请时间,从而导致了时间与金钱的浪费。
而当前的土地兼容性也难以弥补不同类型用地之间调整的不足,土地兼容性的应用多用于分类中的小类用地之间的兼容,对用地的多样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其应用范围依旧过窄,主要是涉及到中类兼容的多是用于商业性用地对公益性用地,实际操作能力有限,对于用地性质变更问题并无指导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