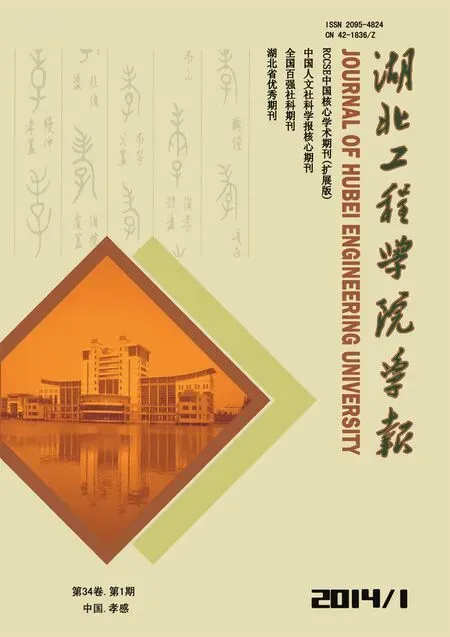从《蛙》中的农民形象看莫言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张 丽
(1.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77;2.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歌德曾说:“现实主义作家认为小说是一种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记叙性文学体裁,应把人物看作是小说的灵魂。”[1]中国当代小说成功塑造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但在各类人物中,农民形象塑造得最为出色。从古至今,农民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冲击和困惑最具代表性和隐喻性。作为一个被现代化改造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体验者,又是中国农村巨大深刻历史性变革的见证者,是现代化的主体。他们构成了独特的形象体系,这一体系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因此,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与生活中真实的农民形象相比,有了更加丰富的扩展空间,在现实语境与精神构建两个层面上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审美价值。
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中,农民成了落后、愚昧、守旧、迷信等传统社会性质的标志。农村留给读者的大多是破落和衰败的景象,破落和衰败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国家民族遭受侵略时的隐喻,对这种颓废景象和农民生活状况的描述,一方面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民族身份的自我确认;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和现代化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发展到现代,农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的改善,更体现在当代农民于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中价值观念的转变。因此,一批性格多元、美学品质丰富、文化内涵复杂的新农民形象便进入到作家的视野中。莫言就是其中一位。莫言对农民的认识是独特而深刻的,他在农村度过自己的童年,对农村生活有深刻的记忆。因此,在其农村题材的小说中,他没有回避或遮盖农村的一些现实和苦难,而是在真实描绘这些生活的基础上,展现不同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关心农民的命运,也从中洞察了中国农民的病态与弱点,针对这些病态和弱点,他提出: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新时代的农民必须要改变自身的不足,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
提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时,莫言曾说:“如果说我的作品在国外有一点点影响,那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思想的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的个性,这些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我不了解很多种人,但我了解农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2]前言2可以看出,作家浓厚的乡土情结和对农民形象的热爱程度。莫言在描写乡土风情特色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射到农民面对社会快速发展时的心理变化过程。对这种心理变化过程的探索,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农村现代化建设所持的肯定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家对传统的“城市/农村”二元论思维的反思。《蛙》中塑造的农民形象便表现了莫言对“城市/农村”二元论思维的超越现代文明冲击下农民精神世界的担忧。
《蛙》以在农村做乡村医生的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广大农民平凡而真实的生活。小说以农民的生活为题材,以姑姑的生活为主线,并穿插了农村具有代表性的各类人物的故事,主要有陈鼻的故事、小跑的故事、袁腮的故事。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当下农村的生活百态和以蝌蚪为叙述者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蛙》中除了叙述形式比较特殊之外,小说中农民形象塑造摆脱了之前比较单一的趋势,出现了理想的追求者、为改变命运的奋斗者、游荡的破坏者等多种农民形象。
一、裂变与重构——农民形象的多元化
莫言的小说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生活和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他有了“农”的思想、“农”的精神、“农”的审美趣味,因此,莫言始终坚持着“农”的身份,以“农”的视角来关照乡村生活,讴歌传统的乡村文明的同时也在反思和排斥着现代城市文明。他以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民间文化为基础,采用民间写作立场,贴近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从而能准确地发觉农民的灵魂深处,剖析他们深层的精神世界。《蛙》是围绕乡村生活中的结婚、生子主题展开,比较突出的也是具有“农”意识的劳动者。他们既是乡村中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者,也是努力改变命运的奋斗者。他们的变化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新时期当代农民复杂和真实的一面,并揭示了农民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
1.理想的追求者。莫言把传统意义上很顺从的“良民”,放到商品经济的改革大潮中。他们欣然接受了改革所带来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教育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改变过程中,他们坚持对事业、爱情的执著追求,不管成功与失败,为自己的信念而活,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蛙》中的姑姑便是对事业执著追求的典型。在故事没有开始叙述之前,叙述者先向读者交代了年轻时刚做乡村医生的姑姑:“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对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形象,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您说这些形象时而合为一体,时而又各自分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组雕像”[2]3接着叙述正式开始,首先出现在读者面前刚参加工作的姑姑热情、干练、有正义感,当她第一次为艾莲接生时,看到村里的“老娘婆正骑在艾莲身上,卖力地挤压着艾莲高高隆起的腹部”[2]16时,姑姑“扔下药箱,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抓住那老婆子的左臂,右手抓住老婆子的右肩,用力往右后方一别,就把老婆子甩在了炕下。”[2]17其次展现了姑姑对事业执著追求的信念。姑姑年轻时,不仅是村里的美女,也有去正规医科大学学习的经验,对当时医疗技术比较落后的农村来说,这类医生很少,姑姑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医院工作,但她坚守在养育她的农村,为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为一名为计划生育奉献的医疗工作者,姑姑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她为了完成计划生育的使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的额头被张拳打破,也曾被人用剪刀戳,但她始终认为:“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命,也是值得的。”[2]107在小说中,叙述者对姑姑的叙述始终是崇拜和敬仰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姑姑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者的代表,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不可磨灭。
如果说姑姑是对理想坚定执著的追求者,王肝则是一个勇于抛弃世俗偏见大胆而浪漫的爱情追求者。他从小便单恋小狮子,并不断默默给她写情书:“如果你不答应我,最亲爱的,我不会退却,不会放弃,我会默默地追随着你,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会跪在地上亲吻你的脚印。我会站在你窗前,注视着室内的灯光,从它亮起,到它熄灭。我要把自己变成一根蜡烛,为你燃烧,直至燃尽。”[2]101这份情书简单而质朴,然而就是这简短的几句话,表现了王肝对爱情的执著与专一,也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的爱情观。如果说王肝对爱情的追求比较直白的话,秦河对爱情的追求就显得默默无闻,秦河一直单恋着姑姑,从未表白,直到姑姑与郝大手结婚后,他将失恋的痛苦转化为艺术,成了高密东北乡的工艺大师,他捏的泥娃栩栩如生,吹弹可破。
总之,这类形象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对理想和事业坚定、执著,对生活乐观、热情,他们是莫言小说中新时期农民的代表,在对理想的追求中,他们也会遇到挫折,也会面临种种诱惑,但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继续努力下去。
2.为改变命运的奋斗者。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改革大潮涌向农村,农民从各种渠道看到了城乡、贫富之间的差别,他们开始感到不公、羡慕、惊奇,梦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类型的农民超越了老实厚道、安分守己的小农思想,成为积极进取,有商业头脑和创新精神的奋斗者。他们反映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农民对自身精神和物质要求的提高,贫困不再是一种物质上的刺激,而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蛙》中所塑造的这类农民形象,有的直接响应改革的号召,通过经商,成为“有钱人”,如陈鼻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了村里比较出名的万元户,他通过去深圳倒卖电子表,去济南批发香烟,让老婆王胆在集市上出售而致富。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作品中比较常见。有的坚信“知识改变命运”,通过考上大学的方式,离开农村,走向城市,在城市中安家落户,他们中一部分人通过奋斗获得了丰厚的物质财富,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后,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农村,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从出生以来独具特色的一个习惯或一个眼神却始终无法改变他的农民身份。如肖下唇考上大学后走出农村,若干年后,叙述者小跑从他身上的名牌服装、步履轻快的走路姿势和充满自信的脸部表情中,判断出他成为“一个有身份的人”。对这类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新型农民,作者肯定了他们奋斗中的韧劲,说明了农民也可以掌握、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令作者担忧的是, 在新型农民中,一部分人会因价值观念的转变而放松对自身的约束,从而走向堕落。肖下唇的成功和堕落便是很好的例子。
3.游荡的破坏者。他们在现代农村小说中既是迷失自我,面对挫折以消极的态度听之任之的悲观者,又是缺乏竞争能力和道德观念的旁观者。他们生活在社会夹缝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只能以“混”的方式来苟且偷生。他们的存在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加深了读者对社会的思考。比较典型的是袁腮。年轻时的袁腮,在别人看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个能预知未来的大能人,从别人对他的评价中可以得知,袁腮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没有正确运用自己聪明的头脑,而是做一些违背伦理和社会道德的事,在他的脑海中,人的价值、人的追求都以钱为目标,他迷失了作为农民真正朴实的一面。还有受到打击后一蹶不振的陈鼻,在老婆死后,以前被别人羡慕的万元户,整日喝酒,喝醉了又哭又唱,满街乱窜,把之前的存款全部挥霍完后,在李手的饭店里当伪桑丘。当小跑叙述在堂吉诃德饭馆见到年轻时的好友时,语气非常冷静:“那天晚上,我一眼就认出了陈鼻。虽然将近二十年我没见过他,但即便是一百年没见过,即便在异国他乡,我也能认出他来。当然,我想,在我们认出了他的同时,他也认出了我们。童年时的朋友,其实根本不需要眼睛,仅凭着耳朵,从一声叹息、一声喷嚏,都可以判断无疑。”[2]238多年的好友,在这种情景下见面,更多的是无奈。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没有了安静、质朴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喧嚣的商业化色彩,城市与农村完全成了先进和落后的象征,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侵蚀着农村,城市给当下农村的生活、文化和秩序带来了冲击。然而在这样的冲击中,作家面临的一方面是养育自己的故乡,另一方面是现代文明,在创作中出现了进退两难的情感困惑。
二、莫言的情感困惑对农民形象塑造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小说模式比较讲究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在这个过程中,注重故事的讲述和悬念的设置。近代中国的小说模式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变,作家在注重故事情节塑造的同时,也融入了抒情环节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从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都有他自己的价值尺度,在文化多元的21世纪,莫言既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又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多种文学现象所具备的叙事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在他的创作中,他将自己的想象力融入到寻常百姓生活中,展现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风貌。他热爱自己的故乡,对高密东北乡倾注了所有的激情和梦想,将自己的灵魂安放在这一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但与此同时,莫言也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价值缺失、方向迷失的现象表示了担忧。《蛙》中的各类农民形象,既体现了他们渴望现代化的情绪,又体现了作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徘徊与困惑。
在中国,乡村是一个独特而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发源地,也是众多知识分子心中一块洁净的精神领域,它一方面具有古代文学传统中的田园诗意,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化的产物。莫言的乡土情结,源于他对乡村深深的依恋和对故乡的审美幻想。20世纪初,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代表了中国社会转型带给人们内心的矛盾和情感冲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冲突上,也表现在人们的精神追求、物质享受、价值判断等方面的不同,而能表现这些关系的最好载体就是文学作品。在高密生活了近二十年的莫言,从小就对高密的乡村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童年是在饥饿、贫穷中度过,他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因此,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直到今天,他骨子里还是与农民和乡村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同时,他文学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自于山东高密东北乡的高密文化,而高密文化结合了齐鲁文化中鲁文化的理性与厚重,齐文化的感性与飞扬,这些使莫言文学作品中的高密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礼仪性和智慧性的特色。他因此在小说中纵情讴歌齐鲁大地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并有意无意突出故乡农民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惑,从而观察这些苦难对人性变化的影响。
莫言小说中所表现的农民与乡村的关系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他由于从小便躬耕于山东高密东北乡这块多情的土地上,对那里的一切,都有一股割舍不断的乡情,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小说讲述这块土地的悲苦、传奇和梦想。童年的经历,对莫言来说既是一种磨练,也是一笔用不完的精神财富。虽然后来他从军,但小说中很少涉及军旅题材。作为一个农民作家,他有着农村生活的根,有着农民的血液和气质。他在书写这一群体的生活时,也表达了他们长期以来受压抑的心声,但他对个人和乡土苦难的关照同样也带着知识分子的理性,莫言是以痛苦为起点来揭开他的人生序幕的,他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他对中国农村历史和现实有独特的认知方式。他坚定地认为,在新中国,农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因此,他在讴歌高密文化独具特色的乡土风情时,不自觉地要构建一个诗意的精神家园。但这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阻挠和变异,一方面是对故乡的眷恋,不希望故乡传统文明中的美好被现代文明破坏,另一方面,又希望农民通过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样就使作家对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文明产生了焦虑情绪,同时开始担忧现代社会进程中农民身上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
三、结 语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比较有争议的乡土叙事作家,虽然他既属于寻根派小说家,又带有先锋派小说家的某些特点,但他对乡土小说中所体现的现代文明具有独到的见解,即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并超越。他的民间创作立场表达了他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扬。陈思和曾经对作家创作的“民间立场”有过精当的论述,他认为:“民间立场是指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不是专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于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3]中国的乡土文学从鲁迅开始,发展到现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打破了以往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中对和谐美的追求,他不再将故乡和故土作为梦中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他放弃以往对乡土文明中美好一面的讴歌和颂扬,而是将农村的原生态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也运用审丑、变形等手法描绘乡村生活。莫言更加关注的是人类生命的物质状态,他把生活还原为最基本的两个字:吃和性,他像人类学家一样,以“他者”的目光对故乡进行了“田野研究”进而站在被研究对象的文化观点上来了解特定文化内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现象,他因此也发现了农民文化的本真意义以及与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和强悍的生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使他笔下的乡村具有浑然状态下的丰富内涵。
“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应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多种主题并存。在共名状态下,知识分子对社会履行的责任显得比较重大,而无名状态下相对要轻些。”[4]社会改革使农村的生活条件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城乡之间距离的缩小。《蛙》中,无论是理想的追求者,还是为改变命运的奋斗者、游荡的破坏者,他们的性格中既有坚韧的一面,也有奴性的一面,当韧性战胜了奴性时,他们会保持真正的自我,为了理想而不懈努力;当奴性战胜了韧性时,他们会迷失自我,逐步堕落而成为现代社会的破坏者。莫言站在理性的高度,努力表现现代文明冲击中的农村变革和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历程,他关注农民的内心世界,把农民的生活纳入作者所追求的精神世界中,并把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作为现代文明下新型农民的评判标准。这些农民形象蕴含了现代人对社会、对人性的反思和担忧,这也说明了莫言在建构农村小说的叙事模式时,没有摆脱城市/农村的二元论思维模式。
总之,莫言的乡土小说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摒弃了传统文学的创作原则,试图建立自己的规则和范例,他的小说是一种无视任何既定规范的、极度自由的“破坏性”文学。毛姆曾说:“要想诚恳地批判文学作品的优劣实在太难了。批判一部作品,几乎不可能不受评论家或大众的影响。对于公认的伟大作品来说,它之所以伟大,一部分是舆论意见赋予的,这使其评价工作更加困难。”[5]在莫言的自我认知和感受中,他叙述普通人的真实故事,对自己所生活的高密东北乡的地域文化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从高密东北乡文化这一视角切入,通过对其中农民形象的解析,探究他们在作品中所蕴涵的文化因子,并分析这种“文化因子”对作家文化心理的深层影响,进而了解他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迷惘的矛盾心态后,不得不说:“莫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忧患意识的农民作家。”
[1]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9.
[2] 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3] 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中山大学学报,1999(5):25.
[4] 陈思和.陈思和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5.
[5] 萨默塞特·毛姆.作家笔记[M].陈德志,陈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