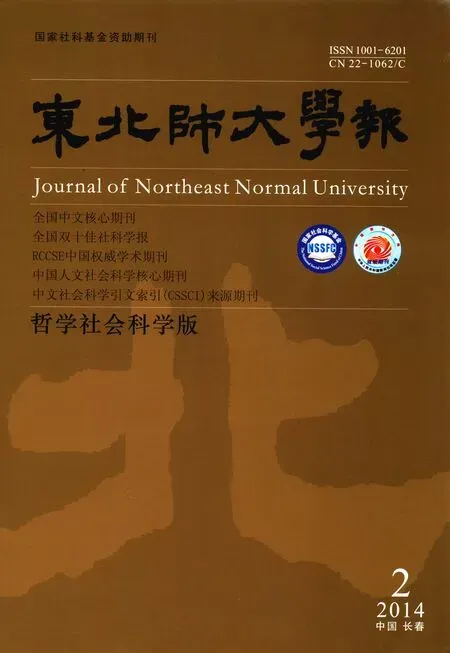经典文献对本土话语的拯救
——1980年代“手稿热”探源
包 妍,程 革
经典文献对本土话语的拯救
——1980年代“手稿热”探源
包 妍1,程 革2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奠定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话语选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理论资源自有其合理与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的“手稿热”体现出新时期中国美学话语寻找自我表述方式的尝试。
“手稿热”;美学话语;“实践”
“手稿热”指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在我国学界的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热潮。“手稿热”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蔡仪发表在1979年《美学论丛》上的《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一文。1980年,《美学》第2期专门刊发了朱光潜重译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同期发表的还有朱光潜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郑涌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张志扬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三篇文章。该组文章可看作是对《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一文的回应,“手稿热”的序幕由此拉开。
在“手稿热”期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手稿》讨论会。一次是1982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四届学术年会”,另一次是1982年9月14日至19日在天津举行的,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天津美学学会和南开大学联合举办的“巴黎手稿美学问题讨论会”。1983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各地纷纷推出纪念特刊。此后“手稿热”才开始降温。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奠定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话语选取《手稿》作为理论资源自有其合理与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的“手稿热”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美学话语寻找自我表述方式的尝试。
一、“经典”的选取:合理与合法性
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话语选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理论资源有其合理与合法性,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手稿》与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线索的符合关系。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接提出了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艺批评要以政治标准为第一的原则。可以说,《讲话》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界确立正统地位提供了“法典”。与“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相呼应,也与从前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与批评理论相呼应,系统性的美学理论产生了。蔡仪的《新美学》和《文学概论》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理论成果。1980年6月4日,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在昆明举行,周扬在会前专门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美学,努力建立与现代科学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1]。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始终是中国美学界的努力目标,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美学学科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了天然的优先性。正因如此,中国美学学者必须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引经据典,寻求自身的合法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部分,第三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货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部分,涉及审美现象学、美的起源和本质等问题。并且,《手稿》中也提到“劳动创造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等直接涉及“美”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眼里,这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诞生地。
其次,是《手稿》话语内部的张力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契合关系。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虽然《手稿》主要是一部关于经济学/哲学的著作而非美学专著,但它的研究中心是人,是人的本质、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其中论述了人从最初的非“异化”状态到“异化”再到“异化”的扬弃这一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并对未来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描绘。而人、人与美、人与艺术是美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在“人”这个连接点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可以说,“手稿热”中论争的美学问题背后是“人”的觉醒,是“人”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因此,对《手稿》的阐释从一开始就被当时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然而,这种“背离”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却又是其合法性的通行证。在结束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国家将社会实践逐步转移到以“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为重心的前提下,美学话语把《手稿》作为逻辑的起点的选择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满足了当时人们要摆脱物对人的奴役状态的愿望。
最后,是援引《手稿》中理论资源的历史脉络。1937年,周扬在《我们需要新的美学》中就引用马克思的《手稿》中的相关论述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只有音乐才唤起人的音乐的感情,在非音乐的耳朵的人最优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一句话,人的要求享乐的感情才会一部分新生,一部分发达起来”[2]。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朱光潜、吕荧都曾引用马克思的《手稿》来说明自己的观点。1956年,李泽厚在《论美感、美和艺术》(《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中借助《手稿》中“自然人化”的理论提出“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命题;他在《论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朱光潜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新建设》1960年第4期)一文中也借用了马克思“实践”的观点重新阐释其美学思想。李泽厚和朱光潜等引用《手稿》中的片段来说明自己的美学观点,以及同时期的学者转引前苏联“审美学派”的中文译介,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关注马克思《手稿》中美学思想最早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部分学者又有了与《手稿》进一步接触的机会。他们是在“‘文革’后期与插队时通过时称‘灰皮书’的60年代版的内部读物了解到这部著作的”[3]。这些内部读物包括1964年商务印书馆内部版的一套《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及利·拉贝兹编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等。
二、“实践”:话语生成的关键词
在“手稿热”中,中国美学学者纷纷到马克思的《手稿》中寻找思想资源,围绕《手稿》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人化自然”、“美的规律”、“异化与美”等几个命题上。
关于“人化自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其一是“人化自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蔡仪等人认为,《手稿》中“人化自然”的观点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蔡仪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探》中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人本倾向”的说法,“作为表述马克思的思想的言论来引用,显然又是错误的”,更不能用来说明美学问题[4]。与蔡仪等人相反的观点认为,《手稿》中“人化自然”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单纯从字面角度理解“人化自然”与美学的关系。朱狄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一文中对蔡仪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反驳。程代熙在《试论马克思、恩格斯“人化的自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美学学习札记》中也肯定了“人化自然”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给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奠定了基本原理”[5]。其二是对“人化自然”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在“人化自然”这个命题的争论中,把“实践”视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的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人化自然”可以作为美的本体,但因为他们对“自然人化”的理解有异,具体阐释也就不同,比如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刘纲纪、朱狄、楼昔勇等各有独到的见解。马克思“自然人化”的观点的引入,打破了主客两分的认识论美学,使主客体在劳动实践中辩证地统一,使美的本质得到一种新的阐释,并且“自然人化”的观点使美学领域的研究从以“物”为中心转到了以“人”为中心。
关于“美的规律”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美的规律”;其二是对与“美的规律”相关的“内在的尺度”与“物种的尺度”的理解。在如何认识马克思的“美的规律”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美的规律”是客观的。蔡仪认为“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6],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的结论。与蔡仪等人观点相反的一方认为,“美的规律”与主体、人的“实践”相联系。朱光潜、李泽厚、马奇、蒋孔阳、陈望衡、朱狄、周来祥等人均持此种观点。在与“美的规律”相关的“内在尺度”与“物种尺度”的看法上,一方观点认为“内在尺度”与“物种尺度”指的都是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尺度。如朱光潜认为“内在尺度”与“物种的尺度”指的都是对象本身的标准。蔡仪认为两个尺度都是属于物的特征,陆梅林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文艺研究》1982年第5期)中也认为“内在固有的尺度”“显然指客体”。程代熙在《关于美的规律——马克思美学思想学习札记》中,认为尺度和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制造不出任何一种对象的“尺度”,“马克思说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生产’这句话的真谛,就是要人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7]。与以上观点相反的一方认为,“内在尺度”指的是主体的尺度,“物种尺度”指的是客体的尺度。此种观点,在李泽厚的《美学三议题》、刘纲纪的《马克思怎样论美》和《关于马克思论美》、朱狄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究竟在哪里?》、陈望衡的《马克思“美的规律”说初探》和《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邓晓芒的《劳动异化与其根源》等文章中均有体现。
在异化与美的问题上,“美正是一切异化的对立物”这个命题得到普遍认同。但就“异化劳动”能否创造美仍存在着严重分歧。蔡仪认为异化劳动不能创造美,他认为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不能肯定、观照自己的创造力,所以把马克思所讲的“自然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美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只有在私有制得到扬弃的时候,人的劳动才能真正的对象化。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异化劳动可以创造美,因为异化劳动也是人的劳动,是人的一种对象化的活动。
在这场围绕《手稿》的论战中,美学界的众多学者接受了以马克思的实践观来建构美学本体的观点。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由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6月第一次出版,曾被再版过29次之多。书中认为:“美是人们创造生活、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8]29。1961至 1964年参加过讨论稿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的有:丁子林、于民、马奇、王靖宪、田丁、甘霖、刘宁、刘纲纪、司有伦、叶秀山、朱狄、杨辛、李永庆、李泽厚、李醒尘、佟景韩、吴毓清、周来祥、洪毅然、袁振民、曹景元。1978至1979年对讨论稿先后做过一些修改和提过意见的有:甘霖、叶秀山、朱狄、杨辛、李泽厚、李醒尘,1979年参加集中修改的有刘宁、刘纲纪、曹景元[8]33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参编人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讨论中大都对“实践”观点持支持态度,并在其美学论著中有精彩的阐发。而这本教材作为以后“美学概论”写作者的“基础范本”,其中的“实践”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产生了深远影响。
《手稿》为探索美的起源和本质提供了本体论哲学基础,即人通过“实践”的方式与自然双向辩证化发展。如果说“实践美学”在20世纪50、60年代引述《手稿》主要是基于“认识论”角度,“实践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述《手稿》则主要是基于“主体性”角度。这种“实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正如李泽厚所言:“‘人类的’‘人类学’‘人类学本体论’……强调的正是作为社会实践的历史总体的人类发展的具体行程”[9],它源自康德以来的人的哲学。李泽厚认为贯穿康德——席勒——马克思这条美学线索的是对感性的重视,是不脱离现实生活和历史具体的个体。康德的感性是抽象的心理,席勒虽然提出了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问题,把审美教育看作由自然的人上升到自由的人的途径,但他仍缺乏真正历史的观点。而马克思从劳动、实践、社会生产出发来谈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0]。“在这种认识之下,传统哲学体系中的两个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位置被颠倒过来了:是人的历史活动决定了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和人与自然关系及自然规律的理解”[11]。由此,美学的哲学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足以引起美学理论相应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这种鲜明的自觉意识使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能够对时代的变迁予以敏锐的回应,使以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为代表的美学理论探索具有很强的现实和历史批判性,成为美学领域的主流话语。而且毛泽东也是讲“实践”的。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中认为实践包括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部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12]。实践论美学借助“实践”的观点,合理合法地解构了一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反映论美学。
结 语
总之,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思潮,“手稿热”的发生是“文革”后美学话语寻求突破的策略性表达,也是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转向在美学上的折射。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新时期伊始的那场关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各种关涉到人的价值的人文话语的建构,终于在《手稿》中找到了依据,并且在对《手稿》的阐释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同时,在对《手稿》的激烈争论中,“实践美学”确立了在中国美学界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了中国美学的主流,其美学话语中的关键词“实践”、“主体性”、“自由”等积极地配合了“思想解放运动”,从而在美学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桥梁。中国美学终于冲破了反映论、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但中国美学在过于急切地“破旧立新”的过程中,更加凸显了诸如“实践”、“主体”等“权力话语”,而“美”的问题在终极上被归结为偏重于价值论的“自由”的问题,更表明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参照始终存在。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那样,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总是特定时代和文化语境下特定群体的理论设定,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政治意识形态[13]。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国美学理论与话语的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处于契合的状态,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能作为解放文论的内部武器及策略发挥应有的作用,它是中国美学话语寻求自我表述的一次尝试。
[1]周扬.关于美学研究工作的谈话[J].美学,1981(3):3-4.
[2]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17.
[3]尤西林.“美学热”与后文革意识形态重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页[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3.
[4]蔡仪.蔡仪美学论文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305.
[5]程代熙.试论马克思、恩格斯“人化的自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美学学习札记[A].程代熙.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391.
[6]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971.
[7]程代熙.关于美的规律——马克思美学思想学习札记[A].程代熙.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思想讨论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450.
[8]王朝闻.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94.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
[11]聂振斌,章建刚,王柯平,等.思辨的想象——20世纪中国美学主题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120.
[1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9.
[13]马晓虹,张树武.论四大名著影视改编与传播的当代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作者单位:1.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2.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树武]
B83-09
A
1001-6201(2014)02-0221-04
2013-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