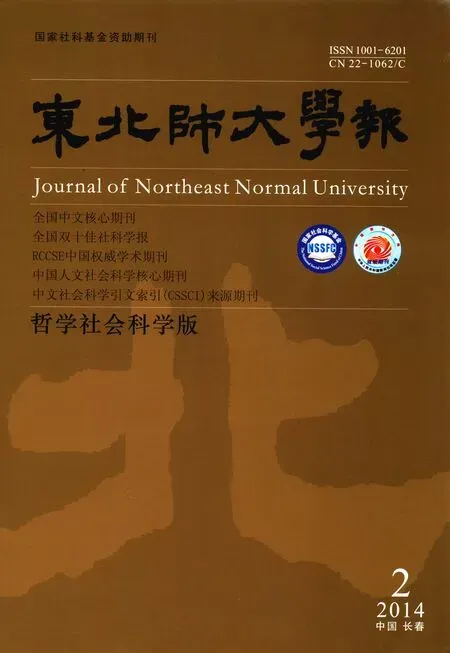互文视野下的《咆哮了的土地》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第一部正面描写土地革命的小说。”[1]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表现的是1946年中共“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以前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土地改革的情况。这两部作品虽然创作背景和年代不一样,但也有诸多相似的元素。其中最大的相似就在于两部作品都是以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为表现对象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小说,农民、土地、革命、阶级斗争是这两部作品共同的“关键词”,这让两者之间有了最重要的相似基因。另外,两位作家都是革命文学序列中的作家,这种身份和角色上的类似也是我们把两部作品进行互文性解读的有力支撑。本文拟从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和主题建构模式三个方面来考察两部作品之间的互文现象。
一、引路型和成长型的人物塑造模式
蒋光慈作为早期引领革命文学创作风潮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中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弊端是毋庸讳言的。蒋光慈曾自称是“专门从事革命文学工作的人”[2],他将大量的革命文学理念深植于文本之中,在他的小说中都有一个“引路型”和“成长型”人物存在。
在蒋光慈的最后一部作品《咆哮了的土地》中,引路型人物是革命党人张进德,成长型代表人物则是李杰。在《咆哮了的土地》第一章和第二章,直接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张进德的身世。张进德是一个没有家室的人,没有房屋,没有田产,唯一的老母亲死后更是无一个亲人,没有亲情的牵挂。把张进德塑造成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以及在亲情血缘关系中了无牵挂的人,蒋光慈的意图非常明显,即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成为最坚定的革命家和引路人。
张进德的身世和引路人形象,这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张裕民极为相似。张裕民生活在无亲情、无温暖、无欢乐的环境中,他父母早逝,“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亲爱一类的事”,是一个经济上一无所有、亲情血缘无牵无挂的无产者。这样的人物身世背景,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能看出张裕民实际上是张进德的翻版,有着浓厚的张进德色彩。在农村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只有张裕民能透过重重迷雾,认为暖水屯真正的地主和斗争对象是“八大尖”中的钱文贵。
既然有引路型人物,那么势必有被引路型人物即成长型人物的存在。这里所说的成长,主要指的是精神和思想境界的成长。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成长型的代表人物是李杰。李杰本来是地主大少爷,因恋爱受阻毅然决然同家庭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李杰在蒋光慈的笔下明显带着青年人的盲动,充满着幼稚的想象和犹疑不决的立场,这也暗示出大部分成长型人物在背叛家庭与阶级后呈现出精神的断裂性,这种断裂为引路型人物的介入提供了充分的话语空间。在参加农民运动时,由于自己的出身受到农民的怀疑,李杰主动向引路型人物农民出身的矿工张进德学习,他认为张进德是“向导”,甚至在张进德的引领下,李杰学会了面对异常粗劣的饭菜,“粘着许多洗濯不清污垢”的碗筷而毫不犹豫的进食。展现“新人”的成长也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目的之一。丁玲曾毫不讳言地说,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表现土地改革在农村是如何进行的,以及“村里的人们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3]。在这部小说中,成长型人物的代表是程仁。程仁作为农会主席,曾经是钱文贵的长工,也是暖水屯早期的党员。但是,他在暖水屯土改运动中表现得不坚决、不彻底,这与他和钱文贵的侄女黑妮有着感情上的牵连有关系。在张裕民和章品等引领下,程仁终于发现了为了爱情而袒护一个地主恶霸是“丑恶”的。
这两部小说中的成长型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相同,两个作家都着重描写了这种成长过程中的焦虑、苦痛。李杰在想到革命行动会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带来伤害时的痛苦焦虑,程仁在想到黑妮和钱文贵的关系时的焦灼,都极其相似。甚至他们的成长模式也相同,即在引路型人物的指引、带领,在暴力革命的血与火的历练中,改变了原有的单纯、犹疑、不坚定,变成一个符合革命要求和斗争需要的真正的革命家。李杰是在烧李家老楼这个“成长仪式”之后,才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程仁也是在不徇私情以暴力的方式批斗钱文贵之后才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两人都以大义灭亲的方式成长为作者所期望的革命家。
二、二元对立的情节设计模式
罗兰·巴尔特曾通过考察文学文本中的“二元对立”现象,提出了文学批评要对这种“二元对立”现象予以重视,他认为“通过找出文本中其他的对立双方以及分析这些对立双方是怎样相关的”,就能够“解构文本并解释其意义”[4]。这两部作品也有较多的二元对立情节设计:
(一)革命与恋爱的冲突
“因为蒋光慈写过不少的小说,有众多的读者,而且被认为是普罗文学的‘师’。”[5]蒋光慈既是普罗文学的“师”,也是普罗文学中“革命加恋爱”这种情节模式的始作俑者。他的小说《少年漂泊者》、《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咆哮了的土地》,都有革命加恋爱的元素。这种古典小说“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模式的现代变种,极大满足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革命的想象。革命和爱情的同构,使得刀光剑影的革命益发浪漫,使得花前月下的爱情更加神圣,这种宏大叙事和私人话语的杂糅,也让政治与性在相互转换间产生了巨大的文本张力。
在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以“革命”的语词感召了毛姑,收获了毛姑的爱情——他向毛姑讲解“北伐军”、“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唤起民众”、“妇女部”、“女宣传队”,这些具有魔力的革命话语瞬间使毛姑“处女的生活史中”,“第一次感到对男性的渴望”,“感觉到李杰这个人隐隐地与她的命运发生了关系”——公共的革命话语巧妙地嵌入到私人的恋爱心理之中了。张进德和何月素的爱情属于“革命决定了爱情”类型。何月素原先喜欢的是李杰,由于农民出身的张进德比地主出身的李杰更革命,加上曾经英雄救美,何月素最后选择了农民革命领袖张进德。
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也有革命与恋爱的二元冲突的情节设计。黑妮是地主钱文贵的侄女,被伯父一家人当作使唤丫头,爱上了伯父家的长工程仁,然而伯父却要将黑妮另嫁。正当恋爱的悲剧要发生的时候,“革命”解救了“恋爱”——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解放了村子,程仁成了农会主任。到后来,“恋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程仁由于黑妮的关系,一直不能正确地面对地主钱文贵,在批斗钱文贵的立场上,表现出不革命的一面。第四十六章,当钱文贵的老婆以黑妮为筹码试图收买程仁时,程仁反而迸发出了革命的激情,以革命的方式迅速解决了此前恋爱带来的羁绊。
(二)父与子的对抗
在普罗文学的创作公式中,父与子的对立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咆哮了的土地》里的父子对抗,实际上就是新型农民和旧式农民的对立。王荣发作为旧式农民的典型,一辈子勤劳、本分、隐忍、认命,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封闭的乡村。当他听到李杰说脱离家庭,参加革命军,老人的第一想法是“大大的不孝”、“简直是疯话”,始终理解不了地主大少爷的革命行为。儿子王贵才则代表着革命感召下的新型农民,有着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善于接受新的思想,不像父辈那样面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只有隐忍和屈服,充满了斗争精神。王贵才在张进德的带领下,积极参加农会和打击地主的斗争,最后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父子二元冲突和《咆哮了的土地》表现极为相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侯忠全就是《咆哮了的土地》中的王荣发,侯清槐就是王贵才。侯忠全是位一年四季只能在“劳动中麻木自己”,“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虏了去”的旧式农民。在大家让他出来斗争侯殿魁时,这位老实本分的农民认为自己受的苦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拿回来了,下世还得变牛变马”,并把分到手的一亩半地给退了回去。而且他还是革命的阻力,把儿子侯清槐关在屋子里不让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程仁的眼中,侯忠全是一个“死也不肯翻身的人”。而他的儿子侯清槐则是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先是积极参加农会,后来又参加了运输队和评地委员会,积极响应党的土改号召。
父子冲突的情节模式,儿子的反叛意味着对既有权威的反抗,对僵化阻碍革命前进的制度、思想以及伦理的反抗,儿子的胜利既隐喻了革命的正义性,也暗示革命实际上是要消除文化恋父心理,以抽象的革命取代文化上的父亲,从而在文化心理层面把革命切入进来。这种父子冲突模式被纳入到革命话语体系,实际上是在古老的审父主题中加入了革命化诉求,这也是后来诸多红色经典的情节设计套路。
(三)革命伦理与民间伦理的龃龉
革命伦理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统摄一切,强调革命的正义性,要求为了革命的目的牺牲和奉献一切。它是以“集体主义”、“阶级至上”为其最基本的信仰和规范,先天地具有阶级性、目的性和排他性。而民间伦理,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引导规范着大众的普遍行为模式的伦理规范、伦理信念、善恶观念和道德标准,它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家庭伦理和民间道义是它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围绕家庭血缘这个核心展开的伦理规范,它强调亲情和血缘的重要性,强调家庭的施恩与图报,以家庭家族的利益为旨归;后者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种种风气、行为方式和价值观等,强调惩恶扬善、善恶有报,以民间特有的正邪、善恶观念作为伦理准则。与正统伦理不同,民间伦理在乡村的现实生活中对民众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咆哮了的土地》实际上就是革命伦理和民间伦理发生冲突并最终取代民间伦理的过程。王荣发恪守民间伦理,把自己的受穷受苦都归结为“生前造了孽”,而李敬斋的福气是“李家老楼的风水好”“东家的命好”,夺取东家的田是“违背天理”的事。李杰的革命行为在王荣发看来,更是违背了民间伦理尤其是家庭伦理。李杰所操持的革命伦理话语在以民间伦理为规范的王荣发这里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民间伦理既是阻碍旧式农民向革命靠拢的因素,也是促使他们走向革命的动力。王荣发从最初对革命不理解不赞同的落后典型,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革命的感召或者说是革命伦理优越的结果,他的落后和先进都是民间伦理在起作用:正因为儿子王贵才被地主武装杀害才促使他走进革命队伍。这其中的动因完全是因为家庭血缘伦理的作用。
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对革命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冲突的处置却相对聪明。她看到了民间伦理对于革命伦理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是阻碍革命伦理话语取得胜利的因素,又是革命伦理话语取得胜利的基础和有力支撑。因此,她在作品中处理革命伦理和民间伦理时,首先是突出了民间伦理的意义——稳定的民间伦理秩序是革命伦理合法性的前提。她将笔下的地主恶霸,首先置于民间伦理的审判台——被民间伦理认定的最坏的人必然是革命对象。暖水屯最终要斗的地主恶霸钱文贵,也是在民间伦理层面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因此被看作是暖水屯最大的“恶人”,最后“武斗”和批判的只有钱文贵。其他几个地主,因未直接违反民间伦理,因而在暖水屯的土改运动中没有受到“武斗”。
丁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首先看到了支配乡村社会正常运行的民间伦理的巨大作用,并且意识到了民间伦理之于革命伦理,并不是决然对立的两种标准。她的小说没有《咆哮了的土地》中为了实现革命而不顾伦理人常的情节,反而有对诸如李子俊等人充满人情味的“有限同情”。同时,丁玲也看到了革命伦理和民间伦理作为两套不同的标准规范和话语体系之间难以弥合的差异,看到了民间伦理会以各种隐匿和变通的方式阻碍、规避革命伦理,因此,她在小说中也一再表现了民间伦理对革命伦理的阻滞和拆解[6]。
三、翻身翻心的主题建构模式
在1946年至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农村曾广泛地开展了“翻心”运动。即解放区在通过革命斗争取得政权后,对政治上翻身做主的农民开展的一次革命教化活动。当时的报纸曾广泛报道农村“翻身翻心”的经验。丁玲在以河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为背景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无疑会受到这种“翻身翻心”思想的影响。小说中这种“翻身翻心”主题模式的建构,虽然是时代的要求和政治的需要,然而,从文学层面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不是最早以“翻身翻心”为主题的小说,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早已有了这样的主题建构模式。
《咆哮了的土地》中,蒋光慈一方面通过渲染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来反映农民取得了政治上翻身;另一方面,他又通过革命教化和诉苦仪式、反省仪式来让农民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实现心理上的“翻心”。翻身往往是和气势恢宏的暴力革命场景相连。暴力的翻身场景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比比皆是,比如批判张举人和胡小扒皮时,就是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第五十章批斗钱文贵时,也有类似的场景描写。《咆哮了的土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以这种暴力化、公开化和仪式化的阶级革命斗争场景为其高潮部分。
翻身不可避免的与阶级暴力相勾连,翻心则和诉苦仪式密不可分。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较早地描写了翻心的“仪式化”程序。在第五十三章中,癞痢头、何三宝等人分别通过回忆、反省和诉苦来显示自己的“翻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翻心仪式和《咆哮了的土地》高度相似,表现得更为激烈。在第四十九章描写刘满和王新田的“翻心”仪式,几乎是《咆哮了的土地》的翻版。
英国著名诗人、理论家艾略特曾戏谑地说:“小诗人借,大诗人偷。”艾略特的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文学传统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每个作家都要面对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传统或惯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以吸收和改造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谱系,而不能完全脱离和不受制于这个谱系。“每一个文本把它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7]“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累积的参与等”[8]。克里斯蒂娃的这种观点给我们一种启示:要真正理解和考察一个文本,一定要考察这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以及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书写,这有助于我们对文学传统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文学谱系及其嬗变过程的理解。
[1]马德俊.蒋光慈写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十五个第一[J].党史纵览,2001(4).
[2]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A].蒋光慈文集:第4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166.
[3]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495.
[4]朱刚.20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3.
[5]茅盾.茅盾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78.
[6]赵凌河,卢兴.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历程的发展方向[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23.
[7]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J].外国文学,1996(1).
[8]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