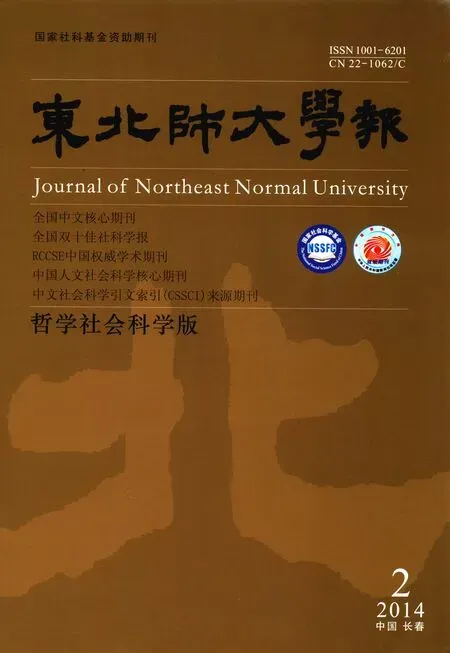儒道融合与明代文论的文化走向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明代思想文化十分复杂,这一时期统治者一直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因而程朱理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明代又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主的“心学”学派,心学的出现给予“理学”以极大的打击,造成了理学的瓦解。明代的理学与心学虽然都属于儒家学术体系,但其思想中亦有道家因子,有时甚至占很大比重。因此,明代思想文化的总体趋势是儒中有道。在这种思想文化整合下,这一时期文论的文化走向,也明显趋向于儒中有道。
一、儒中有道的思想文化形态
明初统治者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明确地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意识形态大力推行。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曰:“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高攀龙传》)明成祖朱棣命胡广行等人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成书后下令颁布天下。从此,这三部《大全》成了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尽管明代统治者大张旗鼓地推重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道统思想,实际上在明代,“程朱理学”是走下坡路的,许多文人学士并不看重程朱理学,在他们思想中,道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的兴起,程朱理学逐渐淡出思想文化领域。
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时人称之为“活孟子”。但是,就在这样人物的身上,道家思想的影响比比皆是。《明史·儒林传·陈献章传》写道:“从吴与弼讲学。居半载归,读书穷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其中的“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所说的是陈献章学术成就获得的实际过程,也是他的学术风格。《明史·儒林传·陈献章传》云:“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这就是说,他做学问的方法主要是守静,通过守静“养出端倪”。我们虽然不能说陈献章运用“静坐”方法“养出端倪”,就是道家思想,但是,从上面的引述看,陈献章通过“静坐”来“养出端倪”的过程,与道家的“虚静”思想是十分相近的。应该说,陈献章“以静为主”的做学问的方法与过程,是具体实践了老子的“虚静”理论。陈献章虽是儒学代表人物,但他的祖父却好老氏,这种家学传统对他不能没有影响。
陈献章做学问除了“以静坐为主”,还“以自然为宗”。他说:
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弦。(《陈献章集》附录一《答张内翰廷祥书括而成诗呈胡希仁提学》)
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得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泽民·七》)
从上面所引述的内容看,陈献章竭力反对人为的安排,特别强调在做学问过程中顺乎自然的重要性,“立本贵自然”,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获得成就,获得快乐。这种思想与道家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是一致的。
王守仁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创立“心学”主要是针对程朱理学。他通过自己的静思凝想,形成了“心学”的理论体系,这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运用抽象思辨的方法形成的理论成果。王守仁的思想是属于儒家的学术体系的,然而,在其“心学”的理论命题中依然能见到道家思想的表述。
王守仁“心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就是“心即理”。与程朱理学所主张的“性即理”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王守仁提出理就在心内,“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王守仁认为“心”才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心产生的,“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答季明德书》)这就是说,心就是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只要抓住了心,宇宙内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既然如此,我们认识宇宙世界就要用心去认识,心可以独立思考,自行决定,因此要以心为是非评判出发点。他说:“夫学贵得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于孔子乎?”(《传习录》中)这就是说,对世界万物的判断,皆从我心出发,即使是孔子说的话也不能超越我心。这虽然不是道家追求自由思想的直接体现,但将桎梏人心的儒家封建伦理规范都抛在一边,给心以广阔的空间,任其自由发展,这实际上已然把道家思想的精髓体现在其中了。另外,同陈献章一样,王守仁在心学思想的探索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静坐凝思的过程。他在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时,生活在困苦的生活环境中,每天默然静坐,以求达到“静一”的境界,并且经常心中默念:“圣人处此,更复何道?”终于在某一天夜里,恍然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矣”。(《王阳明全集·顺生录之八》)如同陈献章一样,王守仁的这一过程,也是实践道家“虚静”思想的过程。
王守仁心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良知”论。在王守仁看来,所谓“良知”,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他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始终,天理即是良知。”(《传习录》下)由此看来,“良知”是“心学”的核心和关键。那么,具体来说,“良知”是什么呢?王守仁指出: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传习录》下)
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传习录》中)
可见良知是具有自知是非的道德知觉能力,它“自然会知”(《传习录》上),是一种先天形成的知觉能力,不是后天人力安排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这与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是有联系的。
二、明代文论的文化走向
如前所述,“心学”是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主要哲学思潮,这一哲学思潮本质上看是具有儒中有道的内涵的。而明代的文论,主要受到“心学”的影响,呈现心性修炼、性灵阐释和情境追求的文化走向。
作为明代新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李贽,在王守仁“心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童心”理论。他说: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1]117。
在李贽看来,“童心”就是“绝假存真”的真心,是一种原初状态的“本心”,这种“童心”是没有经过世尘污染的,因而是最真实的、最可贵的艺术创作出发点。李贽认为,“童心”是不能被蔽障的,如果被蔽障,那就会失去自然本真。他说:“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而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及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1]117由此可见,李贽所说的“童心”,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这与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崇尚纯真,绝圣弃智的思想是一致的。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因此他提出“见素报朴”、“复归于朴”的主张。“见素报朴”,河上公释云:“见素者,当报素守真,不尚文饰也。报朴者,当报其质朴,故可法则。”[2]76
在“童心”说的基础上,李贽又提出了文学创作不应该“代圣人立言”,而应该是胸臆情感的自由抒发的主张。他在《杂说》中说:
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惊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吐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李氏焚书》卷三)
这段对文学创作过程的形象描述,说明李贽对于冲破一切障碍,自由抒发作者内心情感的作法是十分推崇的。在他看来,能够呈现“童心”的创作,一定是作家胸中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和自由表达,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这种推崇“自然流露”和“自由表达”的思想,同庄子对自然与自由的追求是一致的。
同时,李贽还提出在艺术上要达到“化工”之美。他在《杂说》中说: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功,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李氏焚书》卷三)
李贽认为,所谓“化工”,是指不加人工雕琢的天地造化之功,亦即自然造化之功,而“画工”则是对天地造化之功的表现,因而具有“人工”的含义。在李贽看来,天地造化之功是最伟大的,是第一义的,而“能夺天地之化工”的“画工”,则是第二义的。李贽对自然造化之功的推崇,与老庄的天道自然观是一致的,他认为,“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这就是说,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是非有意为自然,而是在无意之间自然天成,不要加入任何的人工痕迹,这才是真正的自然。
公安三袁的“性灵”理论,亦是对明代文艺思想影响较大的理论之一。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其中袁宏道的理论思想最为全面、系统,诚如钱谦益所说:“中郎(袁宏道)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袁宏道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性灵”理论。他在《序小修诗》中写道:
……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袁中郎全集》卷一)
对于其弟小修的诗作,袁宏道所喜之处在于其“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正是“性灵”理论的核心。袁宏道十分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想,他甚至说:“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与张幼于》)他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见从己出”创作原则,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要使文学创作不受任何限制,让心灵得到自由抒发。由此可知,“性灵”理论的内涵与道家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是一致的。在阐述“自然之趣”的问题时,袁宏道这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辩说书画、涉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略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
这里的“趣”,指的是一种审美感受、审美情趣,是与文学创作的成绩紧密相联的。“趣”的真正获得,在于复归自然,而童子得趣,正在于自然与自由之中。这里袁宏道实际上所阐发的正是道家的自然观,但同时也将孟子的赤子思想引入其中。
作为文学家和文论家的王夫之,其文学理论思想则以儒家为主,也兼有道家,对后世影响很大。王夫之在谈到文学的社会作用时,特别强调孔子的“兴观群怨”理论,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他说: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诗译》)
王夫之关于诗的“兴观群怨”思想来自于孔子,但王夫之又有自己的独到理解,他认为兴观群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的,“兴而可观,其兴也深”、“观而可兴,其观也审”、“群者而怨,怨愈不忘”、“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在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中,其作用更大。这可看出其文论中的儒家思想影响。
王夫之在谈到“情景交融”的问题时,则体现了道家思想。他说: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船山遗书·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情景互相触发,“妙合无限”自然是好诗[3]。那么,如何做到情景交融呢?王夫之认为是“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这就是说,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不是作家追寻得到的,而是在“神理凑合时”,也就是灵感到来时,自然获得的。此时,作家的心灵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才能抓住这种“才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的灵感,展现情景交融的境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自然拾得”。
总之,明代儒中有道的儒道融合形态,对于明代文论的文化走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的。当然,对明代儒中有道的思想文化形态,我们是从思想整合格局方面考量的,并非只着眼于具体表述。而对于文论的文化走向的影响,则是比较直接的,并且,这种影响也涉及了清代。
[1]李贽.童心说[A].中国历代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张立文.和合学及其现实意义[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6.